- +1
中西科學(xué)傳統(tǒng)為何如此迥異?淺論西方科學(xué)發(fā)展過(guò)程的四個(gè)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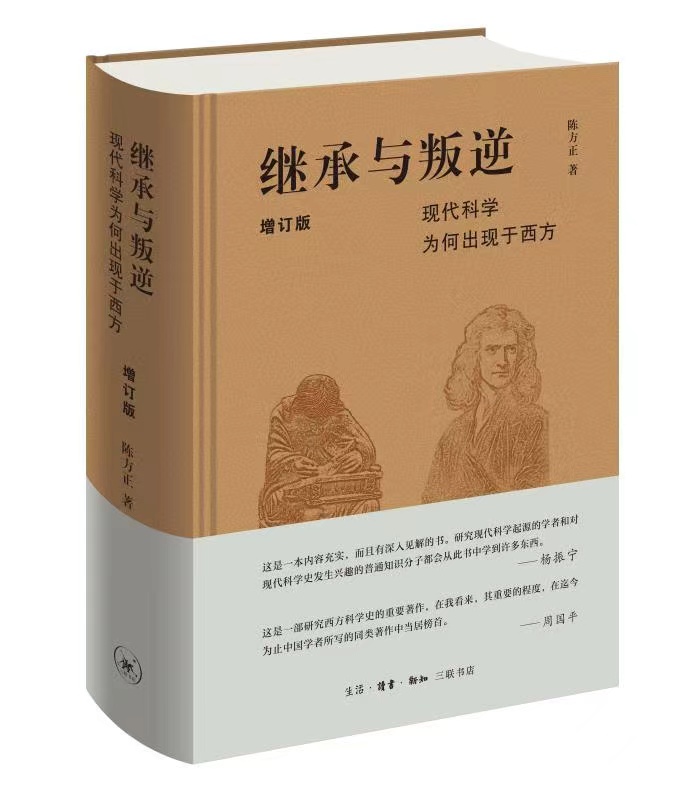
《繼承與叛逆:現(xiàn)代科學(xué)為何出現(xiàn)于西方(增訂版)》,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22年11月版,陳方正著。
一、李約瑟問(wèn)題的消解
西方科學(xué)在它發(fā)生根本性革命的前夕,以難得的機(jī)緣進(jìn)入中國(guó)并且贏得士大夫和皇帝青睞,由是廣為傳播達(dá)一個(gè)多世紀(jì)之久,卻仍然未能夠在神州大地生根、發(fā)芽、滋長(zhǎng),更不用說(shuō)觸發(fā)中國(guó)科學(xué)的真正革命。
這不能不令我們意識(shí)到,本書(shū)“導(dǎo)論”中討論過(guò)的李約瑟“中國(guó)科技長(zhǎng)期優(yōu)勝說(shuō)”和“科學(xué)發(fā)展平等觀”,都可能有嚴(yán)重缺陷。因?yàn)樘热舾鱾€(gè)文明對(duì)于現(xiàn)代科學(xué)的貢獻(xiàn)都大致同等,或者中國(guó)科學(xué)在公元前1世紀(jì)至公元15世紀(jì)的確比西方遠(yuǎn)為優(yōu)勝,而現(xiàn)代科學(xué)革命出現(xiàn)于西方只不過(guò)是在文藝復(fù)興刺激下的短暫現(xiàn)象,那么就絕對(duì)無(wú)法解釋,為何耶穌會(huì)教士所傳入的西方科學(xué)沒(méi)有觸發(fā)中國(guó)科學(xué)更劇烈、更根本的巨變,也就是使得它在17世紀(jì)或者至遲18世紀(jì)就全面趕上西方科學(xué)前緣,并且確實(shí)地完全融入世界科學(xué)主流。
這是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而且李約瑟對(duì)其中利害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66年一篇演講詞中詳細(xì)討論此問(wèn)題,并且如上面所提到,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與歐洲的數(shù)理天文學(xué)早在明末即1644年就完全“融合”。不僅如此,他在該文中還詳細(xì)討論了西方與中國(guó)各支不同科學(xué)之間所謂“超越點(diǎn)”(transcurrent point)與“融合點(diǎn)”(fusion point)的準(zhǔn)確時(shí)間,并且用圖解加以說(shuō)明。但從上節(jié)討論我們清楚看到,就數(shù)理科學(xué)和天文學(xué)而言,他這說(shuō)法距離事實(shí)是如何之遙遠(yuǎn)。至于有關(guān)其他科學(xué)分支的問(wèn)題則柯亨也已經(jīng)有詳細(xì)批判,在此就沒(méi)有必要重復(fù)了。
倘若如此,那我們自然就必須重新檢討“中國(guó)科技長(zhǎng)期優(yōu)勝說(shuō)”到底是怎樣建立起來(lái)的了。如本書(shū)“導(dǎo)論”所指出,“優(yōu)勝說(shuō)”在《大滴定》第六章開(kāi)頭有很嚴(yán)謹(jǐn)?shù)囊饬x:“從公元前1世紀(jì)以至公元15世紀(jì)之間,中國(guó)文明在將人類自然知識(shí)應(yīng)用于人類實(shí)際需要的效率,要比西方高得多。”
它具體所指,最主要的就是,傳入西方社會(huì)之后對(duì)之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指南針、火藥、印刷術(shù)等三種培根特別提到過(guò)的發(fā)明,以及機(jī)械計(jì)時(shí)器即蘇頌的水鐘,這些是李約瑟在比較中西方文明對(duì)“普世科學(xué)”(oecumenical science)貢獻(xiàn)所繪示意圖中所特別標(biāo)明者。除此之外,它自然還包括《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史》中所詳細(xì)研究、論證過(guò)的大量其他發(fā)明,包括連弩、船尾舵,馬鐙、手推獨(dú)輪車等。
然而,由此進(jìn)一步論證傳統(tǒng)中國(guó)在應(yīng)用技術(shù)上有許多方面領(lǐng)先于歐洲(而假如沒(méi)有忘記像羅馬斗獸場(chǎng)、高架引水道和歐洲中古哥特式大教堂那些顯著例子的話,我們恐怕也會(huì)意識(shí)到,這不可能是在所有方面領(lǐng)先)固然很有力,但倘若像上述文章那樣,由此而逐漸改變命題重心,以至最后滑動(dòng)到另外一個(gè)位置,即宣稱中國(guó)科學(xué)與技術(shù)都比歐洲全面優(yōu)勝(predominant),那就變?yōu)榻厝徊煌膊豢赡艹闪⒌男旅}了。
在李約瑟的論證方式中,這是個(gè)核心問(wèn)題,值得詳細(xì)討論。而以磁現(xiàn)象作為例子可能是最適當(dāng)?shù)模驗(yàn)槔罴s瑟對(duì)它極端重視:“可是,要聲稱中國(guó)對(duì)這歐洲文藝復(fù)興晚期的現(xiàn)代科學(xué)大突破沒(méi)有貢獻(xiàn)是不可能的,因?yàn)闅W幾里得幾何學(xué)以及托勒密天文學(xué)雖然無(wú)可否認(rèn)是發(fā)源于希臘,但它還有第三個(gè)重要部分,即有關(guān)磁現(xiàn)象的知識(shí),其基礎(chǔ)完全是在中國(guó)建立的。”
磁石和磁針的性質(zhì)首先由中國(guó)人發(fā)現(xiàn),時(shí)間不晚于11世紀(jì)末,它為歐洲認(rèn)識(shí)則不早于12世紀(jì)末,也就是在中國(guó)之后整整一個(gè)世紀(jì),這些李約瑟有詳細(xì)考證,那沒(méi)有什么爭(zhēng)議。但是,他對(duì)于這個(gè)事實(shí)的引申和解釋卻令人十分吃驚。
他宣稱,磁力提供了“超距作用”的例證,而吉爾伯特認(rèn)為地球可能是一塊大磁石的觀念,影響開(kāi)普勒和牛頓,為萬(wàn)有引力觀念提供了靈感,因此,“在牛頓的綜合中,我們幾乎可以說(shuō)重力是公理性的,它擴(kuò)展到所有空間,正如磁力可以沒(méi)有明顯的中介而跨過(guò)空間發(fā)生作用。因此中國(guó)古代的超距離作用觀念通過(guò)吉爾伯特和開(kāi)普勒成為牛頓(思想)準(zhǔn)備工作的極其重要部分”。
這個(gè)說(shuō)法表面上順理成章,實(shí)則充滿問(wèn)題。
首先,如上文所說(shuō),雖然開(kāi)普勒和伽利略的確為磁力的神奇作用吸引,并且猜想這與天體所受引力相關(guān),但牛頓則很清醒地拒絕對(duì)萬(wàn)有引力的根源做任何假設(shè)或者猜測(cè),因此,磁現(xiàn)象對(duì)于17世紀(jì)科學(xué)革命雖然不無(wú)關(guān)系,卻絕對(duì)說(shuō)不上產(chǎn)生了決定性影響。
其次,中國(guó)古代雖然知道磁石、磁針有恒定地指南或者指北的性質(zhì),卻不可能有“超距作用”觀念,因?yàn)槟鞘呛汀爸苯优鲎沧饔谩保╝ction by impact)相對(duì),并且是由后者衍生出來(lái)。“直接碰撞作用”觀念的基礎(chǔ)是古希臘的原子論,即宇宙萬(wàn)物是由極其微細(xì)、不可見(jiàn)也不可直接感覺(jué)的原子構(gòu)成的,它們的相互碰撞是一切力和運(yùn)動(dòng)的來(lái)源。
在17世紀(jì),笛卡兒提出機(jī)械世界觀,那便是以充斥太空的原子流亦即所謂以太所產(chǎn)生的旋渦之沖擊來(lái)解釋天體之間的吸引力。而磁力則顯示,兩塊磁石之間可以超越空間而發(fā)生吸引或者排斥力量,這不是用產(chǎn)生碰撞作用的中間媒介能夠解釋的,因此稱為“超距作用”。
可是,古代中國(guó)壓根就沒(méi)有原子論和“直接碰撞作用”的觀念,那又怎可能平白無(wú)端冒出相反的“超距作用”觀念呢?
李約瑟在討論物理學(xué)的《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史》第四卷第一分冊(cè),將中國(guó)古代大量有關(guān)日月盈虧、陰陽(yáng)消長(zhǎng)、精氣感應(yīng)、聲氣相通相應(yīng)等觀念,附和于“超距作用”,但這些循環(huán)消長(zhǎng)觀念基本上是時(shí)間現(xiàn)象,并沒(méi)有空間觀念在其中,而他提到的感應(yīng)、相通觀念,或需依賴充斥空間的介質(zhì)傳遞,或者屬于人事、精神而非自然事物范疇,和“超距作用”根本不相干。因此他也不得不承認(rèn):“氣在這連續(xù)介質(zhì)中的波動(dòng)與嚴(yán)格意義的超距離運(yùn)動(dòng)這兩者之間的對(duì)立是中國(guó)古代思想所從未認(rèn)真面對(duì)的”,但卻又仍然堅(jiān)持“但對(duì)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整個(gè)宇宙是如此息息相關(guān),因此他們倘若有理由認(rèn)為這物質(zhì)介質(zhì)在某些特定地方不存在,那么大概也不會(huì)堅(jiān)持其普遍性”。
可是,中國(guó)古代思想從未經(jīng)歷古希臘巴門(mén)尼德的“存有不生不滅不動(dòng)”悖論和原子論派以“大虛空”來(lái)破除此悖論的曲折歷程(§2.5—6)或者類似爭(zhēng)論,因此這奇特假設(shè)對(duì)中國(guó)古人毫無(wú)意義,它只不過(guò)是將“超距作用”投射到中國(guó)古代思想中的手段而已。
此外,李約瑟用了大量篇幅來(lái)論證中國(guó)人自古以來(lái)對(duì)于磁石的了解和應(yīng)用,但其實(shí),古籍如《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等的有關(guān)記載,都僅限于“慈石召鐵”“慈石能引鐵”“磁石上飛”“以磁石之能連鐵也”“司南之杓”“磁石引針”那樣極其簡(jiǎn)短的一言半語(yǔ),即使偶有論述,也都只是物以相類感應(yīng)的粗糙觀念。即使到了宋代,提到磁石、磁針的文字,大多仍然屬于異志、雜志或者技術(shù)類型的簡(jiǎn)短記載,其性質(zhì)可以視為認(rèn)真與系統(tǒng)學(xué)理探究的絕無(wú)僅有。
例如,李約瑟所引沈括《夢(mèng)溪筆談》有關(guān)磁石的一條全文僅百余字,列于卷二十四“雜志一”章,基本上只談到制造、懸掛、支撐磁針的方法,觸及原理的只有最后“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這么寥寥數(shù)語(yǔ);至于曾公亮《武備總要》的一條記載長(zhǎng)度相若,也純粹是敘述行軍辨向所用“指南魚(yú)”的制造方法而已。這些與13世紀(jì)佩里格林納斯長(zhǎng)達(dá)十?dāng)?shù)頁(yè)的《磁學(xué)書(shū)簡(jiǎn)》(§10.6),或者17世紀(jì)吉爾伯特《磁論》那樣洋洋灑灑十?dāng)?shù)萬(wàn)言的專著(§13.3),顯然是屬于完全不同類型的文獻(xiàn)。
統(tǒng)而言之,中國(guó)雖然首先發(fā)現(xiàn)磁石及其應(yīng)用,但古籍僅有磁石、磁針發(fā)現(xiàn)、應(yīng)用和制造方法的極端簡(jiǎn)略記載;西方有關(guān)文獻(xiàn)時(shí)間較晚,卻是詳細(xì)、有系統(tǒng)的長(zhǎng)篇現(xiàn)象研究和學(xué)理探討,兩者性質(zhì)迥異,完全沒(méi)有可比性。因此,上文所引“有關(guān)磁現(xiàn)象的知識(shí),其基礎(chǔ)完全是在中國(guó)建立”,或者“中國(guó)古代的超距離作用觀念通過(guò)吉爾伯特和開(kāi)普勒成為牛頓(思想)準(zhǔn)備工作的極其重要部分”那樣的論斷,不但西方學(xué)者無(wú)法接受,恐怕中國(guó)學(xué)者也難以居之不疑吧。
當(dāng)然,如上文所已經(jīng)討論過(guò)的,磁針、火藥、印刷術(shù)和許多其他中國(guó)發(fā)明傳入歐洲之后,的確對(duì)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產(chǎn)生巨大和深遠(yuǎn)影響,它們對(duì)現(xiàn)代科學(xué)之出現(xiàn)有間接促成作用是無(wú)疑的。然而,這些發(fā)明都屬于應(yīng)用技術(shù)范疇,它們雖然也往往牽涉某些抽象觀念或者宗教、哲學(xué)傳統(tǒng),但這和科學(xué)亦即自然現(xiàn)象背后規(guī)律之系統(tǒng)與深入探究,仍然有基本分別。除非我們?cè)谠瓌t上拒絕承認(rèn)科學(xué)與技術(shù)之間有基本分別,否則恐怕難以從古代中國(guó)在多項(xiàng)技術(shù)領(lǐng)域的領(lǐng)先來(lái)論證中國(guó)科學(xué)的“優(yōu)勝”。
另一方面,倘若要將《墨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周髀算經(jīng)》《九章算術(shù)》《夢(mèng)溪筆談》乃至《數(shù)書(shū)九章》《測(cè)圓海鏡》這些古代經(jīng)典與科學(xué)著作,來(lái)與同時(shí)期西方科學(xué)典籍如托勒密《大匯編》、泊布斯《數(shù)學(xué)匯編》、費(fèi)邦那奇《算術(shù)書(shū)》、柯洼列茲米《代數(shù)學(xué)》、海桑《光學(xué)匯編》等比較,從而論證自公元前1世紀(jì)以迄15世紀(jì)中國(guó)科學(xué)一直比西方優(yōu)勝,恐怕也戛戛其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吧。
這樣,“中國(guó)科學(xué)長(zhǎng)期優(yōu)勝說(shuō)”就必須放棄了。放棄此說(shuō)的最重要后果是:現(xiàn)代科學(xué)出現(xiàn)于西方這個(gè)基本事實(shí)不復(fù)是悖論,它不再意味在十六七世紀(jì)間中西科學(xué)的相對(duì)水平發(fā)生了大逆轉(zhuǎn)。但這么一來(lái),“李約瑟論題”就難免失去根據(jù),“李約瑟問(wèn)題”也連帶喪失力量乃至意義,因?yàn)槲覀兙驮僖膊豢赡芟裨凇皩?dǎo)論”中那樣,將它以“既然古代中國(guó)的科技長(zhǎng)期領(lǐng)先于西方,
那么為何現(xiàn)代科學(xué)的錦標(biāo)卻居然為西方奪取?”的質(zhì)詢形式來(lái)表達(dá)。
同時(shí),席文的批判,即“它(李約瑟問(wèn)題)是類似于為什么你的名字沒(méi)有在今天報(bào)紙第三版出現(xiàn)那樣的問(wèn)題。它屬于歷史學(xué)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會(huì)去研究的無(wú)限多問(wèn)題之一”,也就變得尖銳和不可忽視。事實(shí)上,這就意味著“李約瑟問(wèn)題”之消解。
二、西方與中國(guó)科學(xué)的比較
倘若我們至今的努力沒(méi)有白費(fèi),那么讀者當(dāng)會(huì)同意,“現(xiàn)代科學(xué)為何出現(xiàn)于西方”這問(wèn)題的解答已經(jīng)有清楚輪廓,而具有那么特殊背景與結(jié)構(gòu)的“李約瑟論題”和“李約瑟問(wèn)題”,也再?zèng)]有必要繼續(xù)困擾我們了。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個(gè)問(wèn)題是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所無(wú)法,也不應(yīng)該忘懷的,那就是我們?cè)诒緯?shū)一開(kāi)頭所提到,由胡明復(fù)、任鴻雋、馮友蘭、竺可楨等學(xué)者在20世紀(jì)上半葉所提出來(lái)的:為什么中國(guó)古代沒(méi)有產(chǎn)生自然科學(xué)?
李約瑟與合作者在過(guò)去半個(gè)世紀(jì)的開(kāi)創(chuàng)性工作,使我們深深意識(shí)到,中國(guó)古代有大量技術(shù)發(fā)明與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學(xué)以及對(duì)自然現(xiàn)象的探究與認(rèn)識(shí)。然而,中國(guó)沒(méi)有發(fā)展出西方那樣的科學(xué)傳統(tǒng),中國(guó)古代科學(xué)至終沒(méi)有獲得現(xiàn)代突破,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所以,胡明復(fù)等所提出的,是個(gè)真正有意義的重大問(wèn)題。它可以重新表述為:在過(guò)去兩千年間,中國(guó)與西方科學(xué)的發(fā)展為何出現(xiàn)如此巨大差別?造成此差別的基本原因何在?這個(gè)問(wèn)題的深入探討,牽涉中西文明的全面比較,那自然超出本節(jié)乃至本書(shū)范圍,因此它必須有待于來(lái)者。但我們?cè)诒緯?shū)剩余篇幅仍然要試圖為讀者提供對(duì)上述問(wèn)題的幾點(diǎn)粗淺看法,以冀引起思考和討論。
我們?cè)?jīng)再三強(qiáng)調(diào),現(xiàn)代科學(xué)革命是由古希臘數(shù)理科學(xué)傳統(tǒng)的復(fù)興所觸發(fā),而且,倘若沒(méi)有這傳統(tǒng)作為繼續(xù)發(fā)展的軸線,那么文藝復(fù)興時(shí)代所有其他一切因素,包括實(shí)驗(yàn)精神、對(duì)自然現(xiàn)象本身的尊重、學(xué)者與技師之間的合作,乃至印刷術(shù)、遠(yuǎn)航探險(xiǎn)、魔法熱潮等刺激,都將無(wú)所附麗,也不可能產(chǎn)生任何后果。
這是個(gè)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事實(shí)。從此事實(shí)往前追溯,可以很清楚見(jiàn)到,公元前3世紀(jì)的亞歷山大數(shù)理科學(xué)已經(jīng)決定性地將西方與中國(guó)科學(xué)分別開(kāi)來(lái);從此再往前追溯,則可以見(jiàn)到,西方與中國(guó)科學(xué)的分野,其實(shí)早在畢達(dá)哥拉斯—柏拉圖的數(shù)學(xué)與哲學(xué)傳統(tǒng)形成之際,就已經(jīng)決定。那也就是說(shuō),公元前5世紀(jì)至前4世紀(jì)的新普羅米修斯革命是西方與中國(guó)科學(xué)的真正分水嶺。
自此以后,西方科學(xué)發(fā)展出以探索宇宙奧秘為目標(biāo)、以追求嚴(yán)格證明的數(shù)學(xué)為基礎(chǔ)的大傳統(tǒng),也就是“四藝”的傳統(tǒng),而中國(guó)科學(xué)則始終沒(méi)有發(fā)展出這樣的傳統(tǒng),故而兩者漸行漸遠(yuǎn),差別越來(lái)越大,以至南轅北轍,成為不可比較。
那么,中國(guó)科學(xué)傳統(tǒng)到底是怎樣的呢?我們無(wú)法在此簡(jiǎn)單回答,但可以這樣說(shuō):中國(guó)古代并非沒(méi)有數(shù)學(xué),而是沒(méi)有發(fā)展出以了解數(shù)目性質(zhì)或者空間關(guān)系本身為目的、以嚴(yán)格證明為特征的純數(shù)學(xué);也并非沒(méi)有對(duì)于自然規(guī)律的探究,而是沒(méi)有以這種探究本身(即宇宙底蘊(yùn)之發(fā)現(xiàn))為目的,更沒(méi)有將數(shù)學(xué)與這種探究結(jié)合起來(lái),發(fā)展出數(shù)理科學(xué)傳統(tǒng)。
誠(chéng)然,這說(shuō)法不完全準(zhǔn)確。中國(guó)第一部天文學(xué)典籍即《周髀算經(jīng)》,就是結(jié)合數(shù)學(xué)與天文模型的純粹科學(xué)著作。然而,它所開(kāi)拓的范式雖然頗為接近于現(xiàn)代科學(xué)精神,卻很不幸未能在中國(guó)的文化土壤中繼續(xù)生長(zhǎng)、發(fā)展,其后竟然成為絕響。
甚至,中國(guó)也并非沒(méi)有將數(shù)學(xué)應(yīng)用到自然現(xiàn)象上去:歷代為建構(gòu)歷法而做的天文測(cè)算就曾經(jīng)達(dá)到很高的精密度。然而,這些計(jì)算都是利用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和內(nèi)插法(interpolation)來(lái)構(gòu)造數(shù)值模型(numerical model),目的在于提高測(cè)算的精確程度,而并非在于描繪天體運(yùn)行的空間圖像,也就是通過(guò)空間關(guān)系來(lái)理解宇宙。雖然這些數(shù)值模型的建構(gòu)可能應(yīng)用了非常高妙的數(shù)學(xué),例如導(dǎo)致“中國(guó)剩余定理”之發(fā)現(xiàn)的不定分析,甚至也可能牽涉某種幾何模型的應(yīng)用,但這些手段始終都是為皇朝對(duì)歷算的現(xiàn)實(shí)需要服務(wù),而沒(méi)有轉(zhuǎn)變?yōu)榘l(fā)展數(shù)學(xué)或者天文學(xué)的動(dòng)力。所以,以探究自然為至終目標(biāo)的數(shù)理科學(xué)在中國(guó)曾經(jīng)萌芽或偶一出現(xiàn),但未能發(fā)展,更沒(méi)有成為傳統(tǒng)。
歸根究底,中國(guó)古代科學(xué)中的數(shù)學(xué)和宇宙探索是分家的:一方面,牽涉數(shù)量關(guān)系的數(shù)學(xué)與歷算都以實(shí)用為至終目標(biāo),甚至術(shù)數(shù)、占卜等應(yīng)用組合數(shù)學(xué)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以解釋宇宙現(xiàn)象與奧秘為目標(biāo)的陰陽(yáng)五行、生克變化等學(xué)說(shuō),則缺乏數(shù)學(xué)思維的運(yùn)用。
西方科學(xué)傳統(tǒng)則不然:從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開(kāi)始,數(shù)學(xué)觀念就和宇宙生化、建構(gòu)過(guò)程緊密結(jié)合,柏拉圖的《蒂邁歐篇》就是其最貼切、最全面的體現(xiàn)。其后尤多索斯、阿里斯它喀斯、托勒密等所建構(gòu)的天文學(xué)模型,以及阿基米德的靜力學(xué),也莫不是從同樣精神發(fā)展出來(lái);甚至在中世紀(jì)萌芽,至伽利略方才成形的動(dòng)力學(xué),亦無(wú)非是將數(shù)理精神貫徹到亞里士多德物理學(xué)上去的結(jié)果而已。因此,以新普羅米修斯革命也就是畢達(dá)哥拉斯—柏拉圖傳統(tǒng)的形成作為中西科學(xué)之間的分水嶺,應(yīng)該是很適當(dāng)?shù)摹?/p>
三、西方科學(xué)發(fā)展的特征
那么,中西兩大文明為何會(huì)形成如此迥異的科學(xué)傳統(tǒng)呢?此困難問(wèn)題我們自不可能解答,但在其巨大誘惑力驅(qū)使下,亦不免要從本書(shū)整體出發(fā),來(lái)做一些觀察和揣測(cè),那可以表達(dá)為西方科學(xué)發(fā)展過(guò)程的四個(gè)特征。
1.古代革命之前的悠久傳統(tǒng)
也許,西方科學(xué)史最令人矚目、最令人感到震驚的,就是其數(shù)學(xué)傳統(tǒng)之悠久。《九章算術(shù)》是相當(dāng)圓熟的實(shí)用型算書(shū),它成形于西漢,但從內(nèi)容和用語(yǔ)判斷,一般認(rèn)為起源于周秦之間,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三四世紀(jì)之交,與《幾何原本》大體同時(shí)。
然而,在此之前大約一千五百年,亦即中國(guó)最古老文字甲骨文出現(xiàn)之前五百年,巴比倫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數(shù)學(xué)陶泥板,稍后埃及也出現(xiàn)林德數(shù)學(xué)手卷了。而且,這些遠(yuǎn)古數(shù)學(xué)文獻(xiàn)所顯示的數(shù)學(xué)運(yùn)算能力,與《九章算術(shù)》相比大體上是各擅勝場(chǎng),說(shuō)不上有顯著差別,但在某些方面,例如以幾何方式解二次方程式及其他問(wèn)題,則巴比倫先進(jìn)甚多。因此,西方數(shù)學(xué)的起點(diǎn)并非在古希臘,而是在埃及的中王朝和巴比倫的舊王朝即漢謨拉比時(shí)期,也就是比中國(guó)要早足足一千五百年。
這個(gè)觀點(diǎn)是基于《幾何原本》與巴比倫數(shù)學(xué)傳統(tǒng)之間有明顯繼承痕跡,古希臘記載中不止一次提到泰勒斯、畢達(dá)哥拉斯從這兩個(gè)遠(yuǎn)古文明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和其他知識(shí),以及最近有關(guān)伊斯蘭代數(shù)學(xué)源頭的研究。所以,埃及、巴比倫遠(yuǎn)古數(shù)學(xué)與希臘數(shù)學(xué)是一脈相承的,后者不應(yīng)該視為從公元前5世紀(jì)憑空開(kāi)始,而應(yīng)該視前者為希臘所繼承,然后再經(jīng)過(guò)新普羅米修斯革命而出現(xiàn)的結(jié)果——否則,沒(méi)有其前的遠(yuǎn)古傳統(tǒng),何來(lái)翻天覆地的革命呢?從此觀點(diǎn)看,中西方數(shù)學(xué)傳統(tǒng)之迥然不同,便極有可能是與這一千五百年的起點(diǎn)差距密切相關(guān)。
2.在廣袤空間中的復(fù)雜軌跡
不過(guò),時(shí)間差距雖然可能是因素之一,完全以此來(lái)解釋西方與中國(guó)科學(xué)的基本差異還不足夠。最明顯的反例就是:蘇美爾—巴比倫數(shù)學(xué)可以說(shuō)是與其文明同步發(fā)展的,然而在漢謨拉比時(shí)期的短暫開(kāi)花之后它就停滯不前,再也沒(méi)有令人矚目的變化了。那么,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導(dǎo)致希臘數(shù)學(xué)、科學(xué)那種非常特殊形態(tài)之出現(xiàn)的呢?
在試圖回答此問(wèn)題之前,我們先要討論西方科學(xué)傳統(tǒng)另外一個(gè)令人矚目的特點(diǎn),那可以稱為“中心轉(zhuǎn)移”現(xiàn)象,它表現(xiàn)為西方科學(xué)發(fā)展往往集中于一個(gè)中心區(qū)域,而這中心是不斷移動(dòng)、游走,并非長(zhǎng)期固定的。
在遠(yuǎn)古時(shí)期,這中心從巴比倫或者埃及轉(zhuǎn)移到希臘的過(guò)程已經(jīng)湮沒(méi)不可考,但在希臘時(shí)期,我們知道它曾經(jīng)先后在愛(ài)奧尼亞、南意大利、雅典、亞歷山大等四個(gè)中心區(qū)之間轉(zhuǎn)移;然后它移植于伊斯蘭世界,在此時(shí)期它也先后經(jīng)歷了巴格達(dá)、伊朗和中亞多個(gè)城市,以及開(kāi)羅、科爾多瓦、托萊多、馬拉噶、撒馬爾罕等許多中心區(qū);在轉(zhuǎn)回西歐之后,它又先后經(jīng)歷了巴黎、牛津以至博洛尼亞、帕多瓦、佛羅倫薩等北意大利城市,最后才在十六七世紀(jì)間回轉(zhuǎn)到法國(guó)、荷蘭和英國(guó)。
因此,西方科學(xué)傳統(tǒng)雖然悠久,但科學(xué)發(fā)展中心卻不斷在亞、歐、非等三大洲之間回環(huán)游走,它停留在任何城市或者地區(qū)的時(shí)間都頗為短暫,一般只有一兩百年甚至更短。與此密切相關(guān)的則是西方科學(xué)的文化和語(yǔ)言背景也因此不斷轉(zhuǎn)變:它最早的文獻(xiàn)使用巴比倫楔形文字或者埃及行書(shū)體文字,其后則依次使用希臘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乃至多種歐洲近代語(yǔ)文,包括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英文等。
科學(xué)發(fā)展的這種“中心轉(zhuǎn)移”和“多文化、多言語(yǔ)”現(xiàn)象所意味、所反映的是什么呢?那很可能是,具有非常特殊形態(tài)和內(nèi)在邏輯的西方科學(xué),必須有非常特殊社會(huì)、環(huán)境、文化氛圍和人才的結(jié)合才能夠發(fā)展,但這樣的結(jié)合顯然是極其稀有和不穩(wěn)定的,因此科學(xué)發(fā)展中心需要經(jīng)常轉(zhuǎn)移,以在適合其繼續(xù)生長(zhǎng)、發(fā)展的地區(qū)立足。
由于廣義的西方世界是具有復(fù)雜地理環(huán)境和包含多種民族、文化與文明的廣大地區(qū),它從來(lái)未曾真正統(tǒng)一于任何單獨(dú)政權(quán),因此在其中適合科學(xué)立足、發(fā)展的地區(qū)總是存在的。倘若這猜想并非無(wú)理,那么也許它還可以說(shuō)明科學(xué)在諸如埃及、巴比倫、中國(guó)等大河農(nóng)業(yè)文明之內(nèi)發(fā)展的問(wèn)題。這些文明的共同點(diǎn)是:幅員寬廣、時(shí)間連續(xù)性強(qiáng),在強(qiáng)大王朝控制下地區(qū)性差異相對(duì)細(xì)小。因此,在其中具有特殊形態(tài)與目標(biāo)的科學(xué),即類似于西方的科學(xué),就無(wú)法通過(guò)中心轉(zhuǎn)移來(lái)尋求最佳立足點(diǎn),并且因?yàn)榘l(fā)展受窒礙而逐漸為社會(huì)淘汰。在此社會(huì)過(guò)濾機(jī)制的作用下,能夠長(zhǎng)期生存、發(fā)展的,主要限于適合王朝或者社會(huì)實(shí)用目標(biāo)的科技,或者能夠?yàn)樯鐣?huì)大眾所認(rèn)識(shí)、認(rèn)同的那些觀念。
在我們看來(lái),為什么像《周髀算經(jīng)》那樣的數(shù)理天文學(xué)著作,和像《墨子》那樣包含精巧、復(fù)雜科學(xué)觀念的經(jīng)典,最后都未能充分發(fā)展而成為絕響,為什么在魏晉南北朝和南宋這兩個(gè)極其混亂時(shí)期,中國(guó)數(shù)學(xué)反而呈現(xiàn)蓬勃發(fā)展的現(xiàn)象,都可以從此得到解釋。那就是說(shuō),中西科學(xué)發(fā)展模式的巨大分別,最終可能是由地理環(huán)境所決定的文明結(jié)構(gòu)差異所產(chǎn)生。
3.科學(xué)與宗教的共同根源
我們還應(yīng)該提到,雖然在現(xiàn)代觀念中科學(xué)與宗教嚴(yán)重對(duì)立,但那只不過(guò)是十六七世紀(jì)以來(lái)的發(fā)展而已。在此之前,無(wú)論在西方抑或中國(guó),科學(xué)與宗教都有密切關(guān)系,甚至可以說(shuō)是共生的。畢達(dá)哥拉斯—柏拉圖傳統(tǒng)對(duì)西方科學(xué)的孕育之功,以及這思潮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代對(duì)于現(xiàn)代科學(xué)革命所產(chǎn)生的推動(dòng)作用,還有基督教與科學(xué)的密切關(guān)系(諸如顯示于阿爾伯圖和牛頓者)我們已經(jīng)言之再三,不必在此重復(fù)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這個(gè)將“追求永生”與“探索宇宙奧秘”緊密結(jié)合的大傳統(tǒng),也同樣出現(xiàn)于中國(guó)。中國(guó)傳統(tǒng)科學(xué)中最強(qiáng)大和獨(dú)特的兩支是中醫(yī)藥和煉丹術(shù)。如眾所周知,這兩者的發(fā)展和道教都有不可分割,乃至本質(zhì)上的密切關(guān)系:醫(yī)藥是為養(yǎng)生全命,煉丹所求,便是白日飛升。所以毫不奇怪,葛洪、陸修靜、陶弘景、孫思邈等著名道教人物,同時(shí)也是杰出的煉丹師、醫(yī)藥家。
不但如此,道士也同樣有研習(xí)數(shù)學(xué)、天文學(xué)的傳統(tǒng):例如創(chuàng)立新天師道的北魏寇謙之與佛教人物頗多來(lái)往,因此也與印度數(shù)學(xué)、天文學(xué)之傳入中國(guó)有關(guān),并且很可能還對(duì)著名數(shù)學(xué)家祖沖之父子有影響;金元之際的劉秉忠基本上是全真道長(zhǎng),他曾經(jīng)長(zhǎng)期在河北邢臺(tái)紫金山講論術(shù)數(shù)、天文,培養(yǎng)出像郭守敬、王恂那樣的歷法專家。
不過(guò),道教的科學(xué)傳統(tǒng)還是以醫(yī)藥、化學(xué)為主,它涉及數(shù)理天文只是后起和附帶現(xiàn)象,說(shuō)
不上是其核心關(guān)注點(diǎn),這是它與宣揚(yáng)“萬(wàn)物皆數(shù)”的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之基本分歧所在。這巨大分歧到底如何形成頗不容易解答,但在中西科學(xué)分野成因的探索中,這當(dāng)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線索。
4.科學(xué)革命之出現(xiàn)
最后,西方科學(xué)傳統(tǒng)最特殊而迥然有異于中國(guó)、印度或者伊斯蘭科學(xué)之處,在于它先后發(fā)生了兩次“突變”(transmutation),即新普羅米修斯革命和牛頓革命。這兩次革命,無(wú)論在探究方法、問(wèn)題意識(shí)或者思維模式上,都相當(dāng)徹底地推翻了其前的傳統(tǒng),也因此開(kāi)創(chuàng)了嶄新傳統(tǒng)。沒(méi)有這兩次翻天覆地的突變,希臘科學(xué)或者現(xiàn)代科學(xué)都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那么,為何科學(xué)革命只是在西方,而沒(méi)有在其他文明中出現(xiàn)呢?
這是相當(dāng)根本的大問(wèn)題,我們認(rèn)為其解決或有可能從兩個(gè)方向?qū)で蟆?/p>
第一個(gè)可能方向是上述“中心轉(zhuǎn)移”現(xiàn)象。正因西方科學(xué)發(fā)展既有強(qiáng)韌久遠(yuǎn)的傳統(tǒng),又無(wú)固定地域或者文化背景為其桎梏,因此在舊傳統(tǒng)中注入新意從而整體改造之,使之脫胎換骨成為可能。如本書(shū)第三章所詳細(xì)論證,畢達(dá)哥拉斯便是擷取諸遠(yuǎn)古文明精華,加以融會(huì)貫通,然后移植于希臘文化土壤者,他的宏圖為費(fèi)羅萊斯和阿基塔斯所繼承,而新普羅米修斯革命則是通過(guò)他們將教派精神移植、貫注于柏拉圖學(xué)園而完成。同樣,從16世紀(jì)中期開(kāi)始?xì)W洲各地的科學(xué)發(fā)展風(fēng)起云涌,諸如意大利、德國(guó)、法國(guó)、荷蘭都人才輩出,然而至終能夠精研覃思,綜會(huì)各家學(xué)說(shuō)而神奇變化之,得以完成現(xiàn)代科學(xué)突破的,反倒是獨(dú)守寂靜劍橋校園達(dá)三十五載之久的牛頓。
第二個(gè)可能方向則是宗教。畢達(dá)哥拉斯視宇宙奧妙之探索為超脫輪回,獲得永生之道,其教派視數(shù)學(xué)發(fā)現(xiàn)為絕頂秘密,相傳泄露此秘密者甚至可以被處死。那么,對(duì)于學(xué)園內(nèi)外的教派傳人而言,數(shù)學(xué)與天文奧秘、規(guī)則是如何值得凝神竭智、畢生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也就不言而喻了。
同樣,如最近數(shù)十年的深入研究所揭露,牛頓不僅究心于數(shù)學(xué)、力學(xué)與光學(xué)探索,其宗教信
仰之認(rèn)真、堅(jiān)定也遠(yuǎn)遠(yuǎn)超乎想象:他不但花費(fèi)大量精力于煉金術(shù)以求窺見(jiàn)上帝的生化創(chuàng)造之功,更力圖從自然法則中尋找世界末日的根據(jù),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革職危險(xiǎn)而堅(jiān)守阿里烏派信仰(§14.3)。畢達(dá)哥拉斯和牛頓這兩位先后觸發(fā)科學(xué)革命的人物,都具有無(wú)比強(qiáng)烈之宗教意識(shí)與向往,那自然不免令我們奇怪,這到底是巧合,抑或有更深意義在其中呢?
例如,科學(xué)大突破需要焚膏繼晷、廢寢忘餐的苦思冥索,這精神上之高度與長(zhǎng)時(shí)間集中對(duì)于
常人而言是極其不自然,甚而根本無(wú)法做到的事,但在宗教熱誠(chéng)驅(qū)動(dòng)下,或者在宗教意識(shí)的移情作用下,則很有可能變?yōu)樽匀弧r且,具有強(qiáng)烈宗教信仰的人往往也具有堅(jiān)執(zhí)不撓、百折不回的稟賦,只要其信仰與科學(xué)探索所需要的開(kāi)放心態(tài)沒(méi)有抵觸,那么這兩方面也就可能相通而相成了。因此,宗教與科學(xué)的密切關(guān)系也極有可能是科學(xué)革命只出現(xiàn)于西方的原因。
當(dāng)然,以上兩個(gè)方向都只能夠視為何以科學(xué)革命只發(fā)生于西方文明的一種揣測(cè),至于其實(shí)際發(fā)生所需要的充分條件則如以上第五節(jié)的討論所顯示,是非常復(fù)雜而絕不可能簡(jiǎn)單歸納于少數(shù)原因的。
中國(guó)人最初接觸西方科學(xué)是從17世紀(jì)開(kāi)始,也就是與現(xiàn)代科學(xué)的出現(xiàn)同時(shí),至今已經(jīng)超過(guò)四個(gè)世紀(jì)了。在此數(shù)百年間,國(guó)人對(duì)于西方科學(xué)的看法經(jīng)歷了三次根本轉(zhuǎn)變:在17世紀(jì)認(rèn)為它可學(xué)但又需發(fā)揚(yáng)傳統(tǒng)科學(xué)而超勝之;在20世紀(jì)上半葉則通過(guò)在西方留學(xué)的知識(shí)分子而生出“中國(guó)古代無(wú)科學(xué)”的感覺(jué);自50年代以來(lái),卻由于李約瑟龐大研究的影響而令不少人認(rèn)為,長(zhǎng)期以來(lái)中國(guó)古代科學(xué)比西方優(yōu)勝,其落后只不過(guò)是文藝復(fù)興以來(lái)的事情而已。
很顯然,這多次轉(zhuǎn)變都是由于對(duì)西方科學(xué)和它的發(fā)展史認(rèn)識(shí)不足所致。這并不值得驚訝,因?yàn)?strong>西方科學(xué)并非只是其眾多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里面的分支,而是其整個(gè)文明精神的體現(xiàn)。要真正認(rèn)識(shí)西方科學(xué)及其背后精神,就需要同時(shí)全面了解西方哲學(xué)、宗教,乃至其文明整體。這十分高遠(yuǎn)的目標(biāo)并非本書(shū)所能企及,我們?cè)诖怂鶉L試的,只不過(guò)是朝此方向跨出小小一步而已,倘若它能夠喚起國(guó)人對(duì)此問(wèn)題的注意和興趣,那么本書(shū)的目標(biāo)也就達(dá)到了。
(本文節(jié)選自《繼承與叛逆:現(xiàn)代科學(xué)為何出現(xiàn)于西方(增訂版)》,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22年11月版,作者陳方正,系物理學(xué)博士,香港中文大學(xué)物理學(xué)系名譽(yù)教授,中國(guó)文化研究所前所長(zhǎng)、現(xiàn)任名譽(yù)高級(jí)研究員,中國(guó)科學(xué)院自然科學(xué)史研究所竺可楨科學(xué)史講席教授,學(xué)術(shù)工作包括現(xiàn)代化比較、科技與現(xiàn)代化關(guān)系以及科學(xué)哲學(xué),曾經(jīng)創(chuàng)辦及主持《二十一世紀(jì)》雙月刊,主編“現(xiàn)代化沖擊下的世界”叢書(shū),近年則致力于科學(xué)史研究,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紀(jì)的門(mén)檻上》《在自由與平等之外》《迎接美妙新世紀(jì):期待與疑惑》等。澎湃科技獲授權(quán)刊發(fā)。)





- 澎湃新聞微博
- 澎湃新聞公眾號(hào)

- 澎湃新聞抖音號(hào)
- IP SHANGHAI
- SIXTH TONE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滬公網(wǎng)安備31010602000299號(hào)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