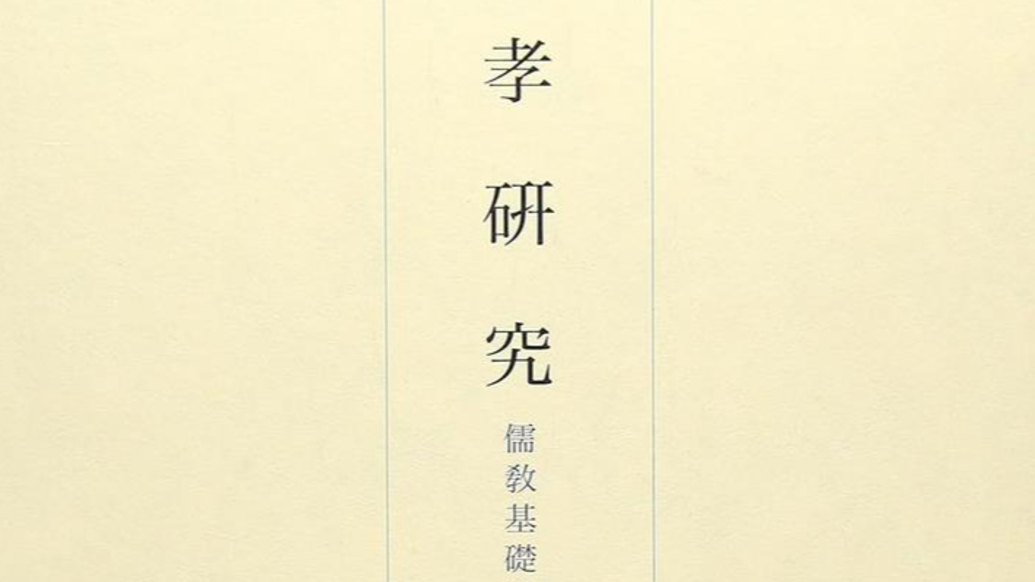- +133
國內思想周報|藥價的理論之辯;“扶貧送老婆”鬧劇
藥價高誰的鍋?理論之爭背后,是備受關注的社會保障問題
由文牧野導演,寧浩、徐崢監制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一經上映便引發熱議,本周話題熱度持續攀升。影片講述了一個生活在上海的藥商在偶然的機遇下接觸到了慢粒白血病病人,發現針對這種病的由瑞士某制藥公司研發的特效藥“格列寧”在國內價格極其高昂,是患這個病的普通人完全無力承擔的。然而在印度卻有一種仿制藥,藥效幾乎一樣,但是價格是原版藥的近百分之一,然而“印度格列寧”在中國被列入違禁名單,被官方當作假藥對待。由徐崢飾演的藥商開始冒著違法的風險在中國售賣這種藥,也經歷了由一個只想賺錢的“藥販子”到深深體認這個群體的苦難從而成為“救贖者”的轉變。

在爭論的一方,是微信公眾號“土逗公社”刊出署名“子團”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認為,我們社會中存在一種商品經濟的邏輯,認為藥物應該跟蘋果手機一樣,如果不能夠保障研發者收回成本且有足夠利潤,就會導致研發者沒有積極性,造成科技進步的停滯。從而,作者認為,必須思考以營利為驅動力的公益事業,而藥物研發顯然具有公益價值。
文章進而質疑“藥物專利權”的存在。作者認為,藥物專利權的營利,到最后大多數都不會落到研發人員手上,而是會進入大公司的腰包;其次,對比上世紀中葉我國的許多藥物研發——如青蒿素的研發,會發現團隊工作相比個人競爭式的專利權保護,不見得效率要低,反而因為團隊協作而可以產生同樣豐厚的成果。
另一邊,質疑這種簡單歸因的文章也接踵而至,“浪潮工作室”刊出一篇文章,題為“《我不是藥神》錯在了哪”,文中質疑將天價藥問題由“無良藥企”和專利權“背鍋”是否合適。其主要觀點是,研發新藥不是做慈善,其成本極高,又經常失敗,因而由專利權和高價格保證一定的盈利是刺激企業研發新藥的重要手段。
文章進一步解釋了中國的“天價藥”問題:首先,進口藥物面臨征稅問題,其次,它會被視為醫療機構的盈利來源,不納入醫院考核體系中,還因為規避了藥物零加成政策的約束,從而維持在高價。另一方面,藥物流通中間環節有不少灰色地帶,也形成了藥物價格難以控制的原因。
而進口藥又在我國因為“原研藥”的專利定價權享受了“超國民待遇”,導致就算過了專利期,進口藥依舊有特權保證價格。加上種種“吸血的中間人、監管漏洞和違法行徑”,作者指出,專利權在我們的高藥價問題中已經“是清白無暇的一個環節了”。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朱恒鵬對藥價的看法也吸引了很多人關注。他認為,藥價的真正問題是公立醫院的壟斷,導致對定價權的壟斷,形成了“以藥養醫”的畸形模式。這種局面經過多次改革仍然難以改變。對藥品生產方來說,公立醫院的采購是大客戶,這導致了公立醫院可以采取回扣、強行要求保證金等手段從藥商手上獲得大量資金以滿足自身的業績需求,結果是很多藥企的經費用來支付回扣,創新動力不足。
這些結論,逐漸讓醫藥問題的討論從政策層面,上升到社會理論層面:究竟是放開市場好,還是加強監管、實行制度改革好?一時之間意見紛涌。針對“《我不是藥神》錯在了哪”,有人撰文“《我不是藥神錯在了哪》錯在了哪”,認為最終導致價格虛高的原因是專利保護期造成的壟斷,導致了高進入門檻……圍繞到底怎么改變,如何看待市場的問題,各家意見齊出,眾說紛紜。
公眾號“北大飛”則選擇批判了一些討論中的“自由意志主義意識形態”,他認為,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關于藥價的討論要在怎樣的倫理測度上進行。比如,如果有人相信凡藥商研發的藥,定多高價格都是他們的自由,無論人們多么強調救死扶傷都無權干涉,那這種討論就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在北大飛看來,以“社會效用最大化”為尺度的功利主義路徑,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討論向度。比如,我們是否可以討論這樣的問題:在開發新藥成本高昂,而投入同樣資金讓普通人能夠用上廉價藥更可行的時候,先將資源投入后者,從而能保證大部分人不會一生病就破產,日常可以更加舒適。
北大飛認為,很多對于藥物開發的完全市場化的呼吁,背后都忽略了一點:芝加哥學派這樣極度強調市場功能的經濟學思潮背后,反而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態度,即認為市場能夠幫助分配,帶來最佳的效用。在自由意志主義興起之初,仍要借用功利主義的討論方式——可以讓富人更富,但前提是窮人也變富了一些,盡管貧富差距拉大了,但是能夠實現社會的“帕累托改進”。
但北大飛認為,在今天堅持自由意志主義的市場理論,意味著要拒絕很多已經證實的研究。比如因為信息不對稱導致“負向選擇問題”,從而醫療保險是不可以完全市場化的。而今天的自由意志主義已經無視這些結論,變成了一種倫理上的規則,“餓死事小,財產權事大”,但到頭來,這種對市場的呼吁變成了一種自我的循環論證。
市場、監管……在過去幾天的互聯網上,圍繞著藥價的種種爭論,不僅僅關乎具體的政策,也已經上升到了經濟學、社會哲學上一些很基本的分歧。而這種激烈、充滿交鋒和來往的討論,多少也說明,在今天,社會輿論對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大病保障等等問題的關注愈發上升,在未來,這樣的爭論顯然會更有現實意義,也會更多進入我們的視野。
“扶貧送老婆”鬧劇背后,對女性和農村的雙重偏見
最近,有關精準扶貧的一些新聞,引發了許多爭論。其中出現了一些“出格”的言論。比如,有一些地方的扶貧宣傳以“送媳婦”為賣點,強調如何幫助貧困家庭的男士找到對象。又有一些聲音鼓勵女性參與扶貧,暗示這樣做可以幫助貧困地區男性在脫貧的同時擺脫光棍地位。
這些聲音出現之后,無不受到了網友的聲討。相關新聞一出,一時之間網絡上充斥著“農村太可怕了”、“女生千萬不要去支教”、“不要被忽悠去扶貧”之類的言論。
學者陳亞亞在公眾號“尖椒部落”撰文分析了這種現象,并提出了對應的建議。在陳亞亞看來,這些把扶貧和“娶老婆”乃至女性下鄉結合在一起的觀點非常過分。但很多對它們的指責和吐槽,則有另一重問題,即充斥著對農村和女性的雙重預設。
第一重預設是,很多人沒有多想便直接代入對農村的某些誤解。有些人認為“農村人就是這么想的”,從而加深了對農村人的妖魔化印象。而事實上,對農村人來說,會把支教、扶貧理解為“送媳婦”的人,在現實中是很少的。對他們來說,真正的問題是如何發展,如何得到更多公共資源的支持,獲得更多社會保障的兜底,在這種情況下,把農村想象為等著城里人來當媳婦,只會復制對農村的誤會,還會加深一種“底層男女通過傳統婚姻抱團取暖”的錯誤認識,而這種認識,忽視了農村真正的問題,是對農村的“忽悠”。
第二重,也是更關鍵的問題是,圍繞著“女性支教”等討論,有一系列對女性權益的忽視和對女性主體性的漠視。陳亞亞認為,在以前的支教、下鄉等活動中,艱苦的、貧困的地區往往被認為不適合女生,就算女性表現出強烈的參與熱情,也往往被拒之門外。而從這種保護,到鼓勵女性參與扶貧工作,其中體現的邏輯是一樣的:女性整體上是弱勢的,邊緣化的,面前的機會和選擇權是不平等的。而這些問題,都亟待改變。更體現問題的是,當城市女性面對這些問題,面對對性別的歧視,還能夠發出聲音吐槽,但農村女性的聲音在這樣的討論中,是徹底付之闕如的。
陳亞亞還指出,在城鄉差別仍然存在,貧富差距顯現的今天,凡是提及城鄉之間的很多社會問題都很尖銳、緊迫。越是在這種時候,越會有很多引爆輿論的“爆款文”以消費這些問題為樂趣,而人們也容易被自己平時積累的偏頗印象所吸引。而這些輿論浪潮過去之后,農村問題仍然沒能解決,城里人熱衷的短期支教、扶貧也常常變成一種流于表面的事情。
對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來說,真實的農村問題,并不是一個距離自己很遠的問題。陳亞亞舉例指出,在今天的農村,很多城市人可以享受到的福利和便利仍然有一定距離。比如優質學校資源、優質醫療資源、住房資源……假如政策真的讓這些資源向農村更多傾斜,以彌補城鄉之間的不平等的話,城市人能否接受這種變化?這是在喧囂的熱點爆款背后,值得許多人思考的問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