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科玄論戰(zhàn)”百年祭
【編者按】整整100年前,中國思想文化領(lǐng)域發(fā)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科玄論戰(zhàn)”,又稱“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
論戰(zhàn)歷時兩年之久,自1923年2月學者張君勱發(fā)表“人生觀”演講、地質(zhì)學家丁文江與之多次激辯起,其后一年多以梁啟超、胡適為代表的“科學”與“玄學”兩派紛紛登場參戰(zhàn),直至1924年歲末“科玄論戰(zhàn)”發(fā)展為科學派、玄學派和唯物史觀派三大派的思想論爭。
在一片政局動蕩、普通人不識“賽先生”的土地上,為何會產(chǎn)生一場有些超前的思想大碰撞?“科學”派是最后的贏家嗎?思想文化界對“科學”的態(tài)度,在這100年中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產(chǎn)生了怎樣的深刻影響?21世紀科學技術(shù)迅猛發(fā)展,對于張君勱提出的問題“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嗎”,我們是否有了新的思考?
本版特邀請科學史家劉鈍,對這一場思想大碰撞進行回顧與梳理。

張君勱

丁文江

梁啟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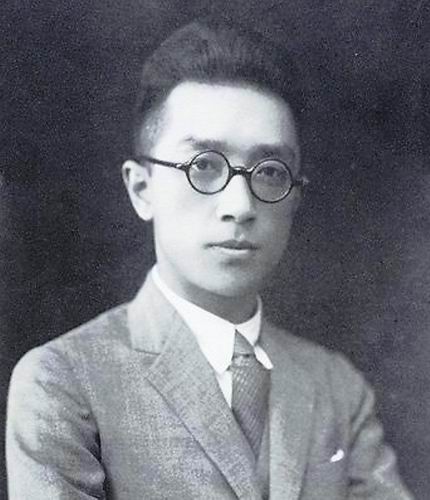
胡適

陳獨秀
1.緣起
1923年2月14日,學者張君勱應(yīng)邀到清華學校演講,聽眾主要是即將赴美學習理工的留學生。
演講的主題是“人生觀”,要點是說明科學與人生觀的五點差異,即科學是客觀的而人生觀是主觀的、科學為推理支配而人生觀由直覺主導、科學重分析而人生觀重綜合、科學服從因果律而人生觀遵從自由意志、科學致力于想象的統(tǒng)一性而人生觀源于人格之單一性。結(jié)論是“科學無論如何發(fā)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唯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講義整理后發(fā)表于當年的《清華周刊》272號。
張君勱的說辭引起地質(zhì)學家丁文江(字在君)的反感,兩人當面激辯兩個小時沒有結(jié)果。后者遂于是年4月12日寫了一篇《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的文章,文辭激烈,用語尖刻,登在《努力周報》48和49期上。丁文江批評張君勱“西方為物質(zhì)文明,中國為精神文明”的膚淺說法,指出:“至于東西洋的文化,也決不是所謂物質(zhì)文明、精神文明,這樣籠統(tǒng)的名詞所能概括的。”文章最后說:“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單一性的人生觀是建筑在很松散的泥沙之上,是經(jīng)不起風吹雨打的。我們不要上他的當!”
“科玄論戰(zhàn)”由此開啟。
隨后張、丁二人又分別發(fā)表長文《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勱》,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并批駁對方,戰(zhàn)火愈演愈烈。
2.眾將與主帥
到1924年夏天,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陸續(xù)參加論戰(zhàn)的學者有將近30人。
“科學”陣營一邊的有胡適、任鴻雋、孫伏園、章演存、朱經(jīng)農(nóng)、王星拱、唐鉞、吳稚暉、陸志韋,以及署名穆、頌皋的作者;“玄學”陣營一邊的代表有梁啟超、張東蓀、甘蟄仙、屠孝實、王平陵、林宰平、瞿菊農(nóng)等。就中國當時思想界的狀況而論,前者大多屬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后者則傾向于文化保守主義。如果說丁文江、張君勱是兩軍的先鋒,雙方的主帥無疑就是胡適和梁啟超了。
正在兩派打得不可開交之際,斜刺里殺出一彪人馬,為首大將是陳獨秀,緊隨其后的有瞿秋白、鄧中夏、蕭楚女等。他們“左劈右砍”,借助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兩面作戰(zhàn)。但是就“科學”與“玄學”的爭論來說,秉承科學進步理念的這一派,大致屬于“科學”陣營。
有些作者的身份不明朗,如謝國馨、陳大齊、張顏海。還有一些特立獨行的人物,從其言論來看很難歸于哪一派,但他們的意見在今日看來顯得十分可貴。
例如被陳獨秀譏為“騎墻派”的范壽康,在批評張君勱將人生觀與科學完全分離“未免過于超絕事實”的同時,對丁文江等人“看人類直同機械一樣”的見解“也不敢表示贊同”。
身為“科學”陣營的中堅分子,任鴻雋指出:“張君是不曾學過科學的人,不明白科學的性質(zhì),倒也罷了,丁君乃研究地質(zhì)的科學家,偏要拿科學來和張君的人生觀搗亂,真是‘牛頭不對馬嘴’了。”結(jié)論是“科學有他的限界,凡籠統(tǒng)混沌的思想,或未經(jīng)分析的事實,都非科學所能支配”“人生觀若就是一個籠統(tǒng)的觀念,自然不在科學范圍以內(nèi)”。
王平陵反對濫用“玄學”,認為這場辯論應(yīng)該叫作“科哲之戰(zhàn)”,指出“科學進步,則哲學亦必進步;哲學發(fā)達,則科學亦必有同樣的發(fā)達,兩者各盡其職能,于是人生便得完全的進步了”。
3.“玄學”之辯
玄學是魏晉時期出現(xiàn)的一股哲學思潮,“玄”字源于《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學的特點是立言玄妙,行事曠達,旨在從本體論上調(diào)和自然與名教。后世則把浮夸虛渺的清談風氣視為玄學,帶有很強的貶義。
丁文江在文章起首就稱“玄學真是個無賴鬼——在歐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來漸漸沒有地方混飯吃,忽然裝起假幌子,掛起新招牌,大搖大擺地跑到中國來招搖撞騙”。后文干脆直接點名稱張君勱為“玄學鬼”。丁氏筆下的“玄學”,顯然不是何晏、王弼等人的主張和竹林七賢的行為藝術(shù)。
什么是丁文江意指的“玄學”呢?他自己在文章第四節(jié)給了明確的交代:“玄學(Metaphysics)這個名詞,是纂輯亞里士多德遺書的安德龍聶克士(Andronicus)造出來的。”下面話鋒一轉(zhuǎn),說廣義的玄學在中世紀與神學始終沒有分家,伽利略研究天體運動的時候,反對者正是“玄學的代表”即羅馬天主教神學家;及至“向來屬于玄學的宇宙”被科學搶去,“玄學家”又以“活的東西不能以一例相繩(意無法按規(guī)律呈現(xiàn)和表述)”與科學抗衡,“無奈達爾文不知趣”作了一部《物種起源》,“生物學又變作科學了”。文雖機巧生動,所云“玄學”卻大大超出了張君勱原意的人生觀。
好在今日懂英文的國人遠多于100年前,Metaphysics字面的意思就是“物理學之后”,這里的“物理學”并非伽利略們研究的那門精密科學,而專指亞里士多德有關(guān)自然知識的一部同名著作,后來Metaphysics這個詞被法國哲學家與科學家笛卡爾用來指稱“第一哲學”,主要包括本體論和認識論兩方面,所謂人生觀就屬于本體論的一部分。
日本明治時代哲學家井上哲次郎借用《易經(jīng)》“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說法,將其譯作“形而上學”。嚴復不滿意他的翻譯,曾經(jīng)倡用“玄學”取而代之,但是沒有被人接受。所以說,“科玄之爭”的說法不夠準確,有人提議改稱“科哲之戰(zhàn)”是有道理的,不過前說早已約定俗成,本文還是循例沿用。
4.時代背景
“科玄論戰(zhàn)”發(fā)生的時候,正值中國近代社會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時期,雖然不同派系的軍閥混戰(zhàn)不斷,畢竟帝制傾覆,黨派政治初露頭角,民族資本主義開始發(fā)展,新聞、出版、教育和思想文化界也出現(xiàn)了相對的繁榮景象。以10年為限,對“科玄論戰(zhàn)”產(chǎn)生影響的重大事件共有四樁,四者之間也不無聯(lián)系。
第一是1914—1918年期間歐洲發(fā)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4年多的時間里,大約有7000萬人卷入戰(zhàn)爭,數(shù)千萬人在機器絞殺和炸彈或毒氣中傷亡,原本世界上最繁榮富庶的地區(qū)一下子尸橫遍野。面對戰(zhàn)后滿目瘡痍的慘狀,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反思科學與技術(shù)對社會的影響,追問它們給人類帶來的是福音還是災(zāi)難。
1918年底,梁啟超以非正式顧問身份赴歐洲觀察巴黎和會,隨員有張君勱、丁文江等6人,取道海路于1919年2月18日抵達巴黎。和會期間中國外交蒙羞,國內(nèi)爆發(fā)五四運動,梁啟超等人游歷歐洲多國并會見了柏格森、倭伊鏗等西方哲學家,回國后寫了《歐游心影錄》,1920年3月首先發(fā)表在上海《時事新報》上。該書指出西方文化中的進化論、功利主義和強權(quán)意志學說導致歐洲陷入權(quán)力崇拜,迷信“科學萬能”動搖了宗教與道德的基礎(chǔ),認為國人應(yīng)該從中吸取教訓,實事求是地看待東西文化的優(yōu)劣短長。
第二是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這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1916年9月遷往北京并更名為《新青年》,與蔡元培任校長的北京大學一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團結(jié)在《新青年》周圍,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向封建傳統(tǒng)思想發(fā)起全面的沖擊。1917年胡適等人又祭起“文學革命”大旗,提倡白話文,主張廢除文言文。1919年傅斯年、羅家倫等五四運動中涌現(xiàn)出來的學生領(lǐng)袖創(chuàng)辦了《新潮》,繼續(xù)推進“文學革命”。
1922年胡適退出《新青年》編輯部創(chuàng)辦了《努力周報》,旗下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自由派知識青年,寄望于“好人政府”,鼓吹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同時繼續(xù)批評北洋政府與帝國主義列強,呼吁“國民要不畏阻力、不畏武力,為中國再造而努力奮斗”。
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義者們則于1919年創(chuàng)辦了《解放與改造》(后改名《改造》),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張東蓀、張君勱等。1922年,另有一批以“新保守主義”標榜的歐美留學生創(chuàng)辦了《學衡》雜志,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為導師,堅守文化道統(tǒng)的同時,提倡以“人的法則”取代“物的法則”的新人文主義。
第三是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評論》為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如同大自然的規(guī)律一樣,都是確定的和可以認識的。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以及黑格爾)那里,“辯證法”作為“形而上學”的對立面出現(xiàn),后者是靜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思維方式的代名詞,與Metaphysics的本來意義相距甚遙,可惜這一誤會至今還未被消除。
第四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抗議巴黎和會對中國主權(quán)的損害與北洋政府的妥協(xié),北京學生走上街頭游行和請愿,工人、市民、商人紛紛加入,不久波及全國。“五四青年”們高揚愛國、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承負啟蒙與救亡的使命,成為中國民眾覺醒的重要標志。
5.思想淵源
有趣的是,論戰(zhàn)雙方的先鋒丁文江和張君勱生于同年(1887),早年皆獲清廷功名,后來又都有留學海外的經(jīng)歷。
張君勱15歲中秀才,19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科學習,回國后通過清政府的鑒定考試被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赴德,留學3年,師從柏林大學倭伊鏗學習哲學。
丁文江15歲東渡日本,兩年后轉(zhuǎn)赴英國,先后在劍橋與格拉斯哥攻讀動物學和地質(zhì)學,1911年回國后被垮臺前夕的清廷賜了個格致科進士頭銜,1916年創(chuàng)辦地質(zhì)調(diào)查所并自任所長。
1918年丁、張二人隨梁啟超訪歐時還有過同居一室的經(jīng)歷,“科玄論戰(zhàn)”期間他們也曾多次見面乃至聚餐。丁氏雖然行文尖刻,在第二篇《玄學與科學》的最后還俏皮地說:“我再三向君勱賠罪道:‘小兄弟向來是頑皮慣的,請你不要生氣!’”
有人總結(jié)兩位“海歸”的思想淵源和傾向,歸納出如下的對局(前者為丁文江的,后者為張君勱的):洛克的經(jīng)驗論對抗康德的二元論(Lockian Empiricism vs.Kantian Dualism)、馬赫-皮爾遜的認識論對抗德里施的活力論(Mach-Pearsonian Epistomology vs.Drieschean Vitalism)、赫胥黎的不可知論對抗倭伊鏗的唯心論(Huxleyean Agnosticism vs.Euckenian Spiritualism)。
縱觀整個論戰(zhàn),也許還可以補充一些對抗的圖景,例如拉普拉斯的決定論對抗柏格森的生命沖動論、孔多塞的科學進步論對抗斯賓格勒的歷史循環(huán)論;馬克思主義者參戰(zhàn)后,還有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對抗形形色色的唯心論等。
細檢參戰(zhàn)雙方“將士”,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是文史哲政經(jīng)方面的學者:“玄學”那邊不用說,就是站在“科學”陣營這邊的,除了丁文江學地質(zhì)、王星拱與任鴻雋學化學、胡適學過農(nóng)學、陸志韋和唐鉞研習的實驗心理學可以算作“科學”之外,其余諸位也都是文科人士。
不過近代歐美名校的“文科”訓練并非誦經(jīng)做八股,而是踐行博雅教育理念,重在培養(yǎng)具備綜合文化修養(yǎng)的人才。以胡適為例,他先入美國康奈爾大學習農(nóng),繼而轉(zhuǎn)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服膺并終生奉行導師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對西方科學與哲學的發(fā)展脈絡(luò)都有相當?shù)牧私猓紊蟿t推崇西方的自由主義。
6.政治譜系
辛亥革命勝利之后,1912年成立的國民黨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早期國民黨的成分十分復雜,既有追隨孫中山推翻清廷的老同盟會成員,也有李石曾、吳稚暉等無政府主義者,還有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和投機分子,更多的則是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熱血青年。1927年北伐勝利之后,國民黨成為一家獨大的執(zhí)政黨。以蔡元培、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多數(shù)場合采取與執(zhí)政黨合作的立場。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在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獨立富強國家的大方向上,與國民黨是一致的。直到北伐戰(zhàn)爭前期,國共兩黨一直是政治盟友,也可以說都是革命黨。1923至1924年的“科玄論戰(zhàn)”中,共產(chǎn)黨人與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捍衛(wèi)科學的尊嚴、批判復古倒退這一點上,是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的。
“玄學”派的情況比較復雜。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流亡日本,鼓吹君主立憲和“開明專制”。由于接觸了一些西方近代思想,他與主張尊孔復辟的康有為開始分道揚鑣,加上其人學問淹博筆力雄健,在民國初年的知識界比“康圣人”有更大的影響。他又有強烈的政治抱負,1913年發(fā)起組織的進步黨后來演變成研究系,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受辱的消息就是他通過研究系大將林長民透露出來,從而引爆五四學潮的。
1920年梁啟超訪歐回來后又組織共學社和講學社,前者是一個沒有明確政治綱領(lǐng)的民間學術(shù)社團,后者旨在邀請國外著名學者來華講學,重在開啟民智。從進步黨、研究系到共學社、講學社,張君勱和張東蓀都是梁啟超的緊密追隨者,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也都是“第三種力量”的重要代表。但是梁氏曾為“保皇黨”的原罪很難消弭,在“五四新青年”眼中他們都是保守派和反動派。
因此當年的“科玄論戰(zhàn)”多少帶有黨爭色彩。今日中國思想界的三種主要思潮——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在“科玄論戰(zhàn)”中亦可覓到蹤影。
7.誰是贏家
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及當代語境中),多數(shù)人習慣按照“進步-落后”或“革命-反動”的二分框架判別是非,結(jié)論是“科學”派大獲全勝,“玄學”派丟盔棄甲。就像胡適在《孫行者與張君勱》中所言,科學和邏輯是如來佛,“玄學”再翻多少跟頭也逃不出他的掌心。
“玄學”派把戰(zhàn)爭對歐洲文明的重挫歸咎于科學與物質(zhì)文明,顯然是李代桃僵,胡適的上述比喻卻露出“科學萬能”論的底牌,在思想的深度上并沒有本質(zhì)的超越。難怪陳獨秀要感嘆,“只可惜一般攻擊張君勱、梁啟超的人們,表面上好像是得了勝利,其實并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不過打散了幾個支隊,有的還是表面上在那里開戰(zhàn),暗中卻已經(jīng)投降了”。這真是一個諷刺味十足的判斷。
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言,“如果純從學術(shù)角度看,玄學派所提出的問題和所作的某些基本論斷,例如認為科學并不能解決人生問題,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有根本的區(qū)別,心理、生物特別是歷史、社會領(lǐng)域與無機世界的因果領(lǐng)域有性質(zhì)的不同,以及對非理性因素的重視和強調(diào)等,比起科學派雖樂觀卻簡單的決定論的論點論證要遠為深刻,它更符合于20世紀的思潮”。
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嗎?如果僅就張君勱提出的這一問題來說,“科學”派沒有勝算,也沒有一位學者給出了全面和令人信服的肯定答案。
但是“五四青年”們自恃有強大的資本,他們挾社會革命與思想解放的狂飆,以“科學”和“民主”為武器向舊制度和舊傳統(tǒng)宣戰(zhàn)。面對神州沉淪的現(xiàn)實和各種新潮思想的涌入,堅信科學將給人類帶來永恒的福祉。在他們眼中,對科學的任何微詞無異于挑釁五四運動張揚的旗幟,必須迎頭痛擊。
就“玄學”陣營而言,他們實在是生不逢時,談心論性與中國的嚴酷現(xiàn)實存在太大的反差,質(zhì)疑科學的適用尺度不啻于反對科學。結(jié)果是,這場有著諸多頂尖思想家和學者參與、本來可以成為更高水準理論交鋒的“科玄論戰(zhàn)”,未能達到塑造更具前瞻性文化形態(tài)的效果,隱身其后的涉及物質(zhì)文明與價值判斷的深刻意義,沒有也不可能引起國人的充分注意。
在一片政局動蕩、民生無保、普通百姓不識“賽先生”為何方神圣的土地上,“科玄論戰(zhàn)”是一場有些超前的思想碰撞,撞出了火花,但沒有贏家。
8.意義和影響
沒有贏家不等于沒有意義。丁文江挑起爭論功不可沒,他借用“玄學”這個詞將論辯范圍擴大好多倍,引出了這場眾多學術(shù)達人參與的大辯論。論戰(zhàn)的焦點已經(jīng)不單是科學與人生觀,還涉及科學與哲學、理性與直覺、客觀事實與價值判斷、物質(zhì)與精神、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
“對于中國來說,其傳統(tǒng)文化從本質(zhì)上講是一種人文文化,西方意義上的科學精神相對匱乏,因而中國歷史上也就較少西方那樣對科學的頂禮膜拜。然而‘兩種文化’的沖突在本世紀的中國也出現(xiàn)了另一極端:例如對于1923年那場‘科玄大戰(zhàn)’,從受到五四影響的新青年到當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輿論,無不對‘玄學鬼’們嗤之以鼻,卻很少有人認真思考過僅靠科學是否可以解決人生觀的問題。”
以上妄言出自我2000年寫的一篇小文《科學史、科技戰(zhàn)略和創(chuàng)新文化》,之后又在不同場合多次宣揚此意。盡管“兩種文化”的命題是1959年才被正式提出來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割裂卻由來已久。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詩人畫家)對帕多瓦(醫(yī)生科學家),啟蒙運動時代的盧梭對伏爾泰,18到19世紀歐洲的浪漫主義對理性主義、功利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維多利亞時代的阿諾德對赫胥黎(參見拙文《“兩種文化”的前世淵源》,載于《中國科學報》2019年4月19日),都可以說是“斯諾命題”的先聲,只是沒有人用斯諾那種圖譜式的清晰命題表達出來而已。能夠在“兩種文化”的視野下審視“科玄論戰(zhàn)”,這一事實本身就彰顯了那場思想論戰(zhàn)的意義。
1965年,美籍華裔學者郭穎頤寫了一本《中國現(xiàn)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其中著力分析的事例就是“科玄論戰(zhàn)”。他認為,無論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無政府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科學”陣營中的許多辯詞都帶有強烈的唯科學主義傾向,這種傾向后來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唯科學主義(Scientism),從字面上看似乎應(yīng)該譯成“科學主義”,中國的一些學者也認為無須加這個“唯”字,并且以“科學主義者”自詡。實際上這是望文生義,范岱年先生指出:“唯科學主義在國外是一個貶義詞,是對那種把自然科學看作文化中價值最高部分的主張的一種貶稱。而有意思的是,我國有一些科學主義者卻把這當作一個美稱來加以提倡。關(guān)于唯科學主義的定義,國內(nèi)的學者已做過許多詳細的介紹。強唯科學主義是指‘對科學知識和技術(shù)萬能的一種信念’。弱唯科學主義是指‘自然科學的方法應(yīng)該被應(yīng)用于包括哲學、人文和社會科學在內(nèi)的一切研究領(lǐng)域的一種主張’。”(范岱年《唯科學主義在中國——歷史的回顧與批判》,載于2005年10月21日、11月18日《中國科學報》〈時名“科學時報”〉)。
胡適把科學比作如來佛就是“科學萬能”論的典型。他還寫道:“有一個名詞在國內(nèi)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對它表示輕蔑或戲侮的態(tài)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丁文江直接提到“科學的萬能”。吳稚暉則有七個堅信,最后一個是“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這些都是強唯科學主義的言論。
王星拱認為,“科學是憑借因果和齊一兩個原理而構(gòu)造起來的;人生問題無論為生命之觀念、或生活之態(tài)度,都不能逃出這兩個原理的金剛?cè)Γ钥茖W可以解決人生問題”。鄧中夏聲稱,“唯物史觀派,他們亦根據(jù)科學,亦應(yīng)用科學方法,與上一派(指科學)原無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們相信物質(zhì)變動(老實說,經(jīng)濟變動)則人類思想都要跟著變動,這是他們比上一派尤為有識尤為徹底的所在”。似乎可以算是弱唯科學主義的表述。
當代生活中,不乏將空洞的“科學”賦予價值判斷的奇事,如說某人或某事“不科學”,就意味著其人其事不正確。再如把某一特定學說或政策觀點稱為“科學的”,與之抵牾的就是“不科學”不正確。這種將科學判斷等同于邏輯真理和政治正確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危害性更大的唯科學主義。這方面的教訓數(shù)不勝數(shù)。
本世紀開初,一些思想活躍年富力強的學者打出“反科學”的旗號,他們批判“科學萬能”論,反對將科學賦予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tài)化,提倡加強人文素質(zhì)教育,起到了批判唯科學主義的作用。但是“反科學”這個旗號除了能夠吸引公眾的一時注意外,很容易引起誤會并招致科學家的反感,對此我是不贊成的,更不要說那些故作驚人的激進口號與宣傳手段了。
9.羅素是個“玄學鬼”嗎?
1923年2月4日,也就是張君勱在清華演講前10天,后來成為著名遺傳學家的“猛人”霍爾丹在劍橋大學發(fā)表了一篇演講,題為《代達羅斯,或科學與未來》,以希臘神話中的巧匠代達羅斯為隱喻,宣稱科學將向傳統(tǒng)道德提出挑戰(zhàn),在科學探索的路上無須任何顧忌。
霍爾丹的演講中包括一些驚世駭俗的想法,有些今日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有些還受到社會或倫理方面的約束,有些也許正在某個實驗室里偷偷地進行。
例如迷幻藥物的臨床應(yīng)用,通過藥物增強人的膽量或耐力(以培養(yǎng)勇敢的士兵和不知疲倦的工人),通過化學方法延長婦女的青春,借助生理學而不是監(jiān)獄來處理邪惡本能,無性生殖、試管嬰兒、計劃生育與優(yōu)生控制,甚至暗示了人獸雜交和安樂死。
霍爾丹還認為生物學家“是現(xiàn)在地球上最羅曼蒂克的人”“是腐朽的帝國與文明的破壞者,是懷疑者、動搖者和弒神者”,宣稱“未來的科學工作者將越來越像孤獨的代達羅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可怕使命,并為之感到自豪”。
已經(jīng)功成名就的哲學家羅素對其言論非常不滿,翌年發(fā)表《伊卡洛斯,或科學的未來》予以回應(yīng)。文中借代達羅斯之子伊卡洛斯飛天墜落的故事,警告人類對科學的濫用將導致毀滅性災(zāi)難。
文中寫道:“伊卡洛斯在父親代達羅斯指導下學會了飛行,由于魯莽而遭到毀滅。我擔心人類在現(xiàn)代科學人的教育下學會了飛行之后,亦會遭遇相同的命運。”在結(jié)論部分他又寫道:“科學并沒有給人類帶來更多的自我控制,更多的愛心,或在決定行動之前克制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會獲得更大的力量,去放縱自己的集體激情,但通過社會的更加組織化,科學降低了個人激情的作用。人的集體激情主要是一種罪惡的激情,其中最強烈的激情是針對其他群體的仇恨和競爭。因此,現(xiàn)在所有使人得到放縱激情之力量的東西都是邪惡的。這就是科學可能導致我們文明毀滅的原因。”
希臘神話中,代達羅斯在雅典犯下殺人罪后逃到克里特島避難,為當?shù)亟y(tǒng)治者米諾斯王修造囚禁牛頭怪的迷宮,又用鳥羽和蜂蠟為自己和兒子伊卡洛斯制作了飛天的翅膀。飛行途中伊卡洛斯罔顧父親的囑托,飛得太高而被太陽熔化了翅膀,最終墜海身亡。
在霍爾丹與羅素論戰(zhàn)的語境中,代達羅斯既是科學與發(fā)明的象征,也帶著技術(shù)“原罪”的烙印;伊卡洛斯則顯示了人類與自然抗爭的勇氣和雄心,既是飛天英雄,也是因藐視自然而遭報應(yīng)的代表。
在與霍爾丹交鋒之前不久,羅素曾于1920年訪問中國,10月12日抵達,次年7月11日離開,在華居停整整9個月,步履所及包括上海、南京、漢口、長沙、北京5個城市,發(fā)表了五大系列演講和十余場單篇演說,會見了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就改造中國這一議題向不同的人提出了建議。羅素來華的邀請和接待由梁啟超領(lǐng)導的研究系主持,對外出面的是講學社為首的多家單位。
梁啟超一向被新文化運動的闖將們視為保守派甚至反動派,此時他的《歐游心影錄》剛剛出版。由他發(fā)起的邀請活動,在“五四新青年”那邊得到的反應(yīng)遠沒有預(yù)期那樣熱烈。胡適曾經(jīng)警告趙元任不要為羅素擔任翻譯,陳獨秀還在《新青年》上發(fā)表公開信質(zhì)疑羅素關(guān)于優(yōu)先發(fā)展教育與實業(yè)的觀點,周作人等則借《申報》的報道批評羅素不諳中國國情。
我這里異想天開地提出一個問題——假如羅素晚來3年并目睹了“科玄論戰(zhàn)”的全過程,他會站在哪一邊呢?在中國當時的語境中,他是否會被人斥為“玄學鬼”呢?
10.羅家倫的反思
在回顧“科玄論戰(zhàn)”的敘事中,有一個常被忽視的人物,他就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lǐng)袖羅家倫(字志希)——喊出“外爭國權(quán),內(nèi)懲國賊”口號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就出自其手,“五四運動”這一提法也首見于他以“毅”為筆名發(fā)表在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上的文章。
1920年羅家倫從北京大學畢業(yè),蔡元培商請上海紡織巨頭穆藕初提供獎學金,將他和另外4名學生領(lǐng)袖一道送往美國留學。羅家倫于當年9月赴美,先后就讀于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以及英、德、法等多所名校,主修歷史與哲學。他在西方游歷7年,回國后投身北伐,1928年出任清華大學首任校長。
“科玄論戰(zhàn)”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羅家倫正坐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里苦讀和思考,并寫成名為《科學與玄學》的一部書稿。游歐期間他也隨身攜帶著書稿,曾與趙元任、俞大維、傅斯年等人切磋討論,修訂后寄回國內(nèi)于1924年出版,署名羅志希。按照羅氏的學術(shù)譜系與國內(nèi)人脈,他應(yīng)該是“科學”派的擁躉,其實不然。
作者自序開頭就說:“這本書的內(nèi)容,與從前國內(nèi)發(fā)動的所謂‘科玄論戰(zhàn)’毫不相關(guān),雖然著者發(fā)動寫這本書的時候,多少受了那次論戰(zhàn)的沖擊。”“毫不相關(guān)”是說自己沒在國內(nèi)加入論戰(zhàn),受了“沖擊”坦白了寫作此書的動力。
由于置身事外,又擁豐富藏書之便,還能就近向杜威等大師請教,這部《科學與玄學》自有一種山外望山的清朗氣象,可以說是對“科玄論戰(zhàn)”予以全面審查和公允判斷的第一部專著。
書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楔子”交代緣由,認為“張、丁二君的辯論……是學術(shù)界元氣將蘇的一種征兆”,同時指出“張、丁二派不足以代表玄學與科學”。中間兩部分分別詳論科學與玄學,各四節(jié)。
科學部分包括:(1)科學簡史、休謨問題、因果律、經(jīng)驗共性;(2)描述與解釋、共相問題、精確性與確定性、排除價值判斷、數(shù)學化;(3)科學的限度、主客關(guān)系、對科學的誤解;(4)歷史上的科學流派(筆者按,實為科學哲學流派)、純粹與應(yīng)用。
玄學部分包括:(1)名詞之辯、基本問題、認識論與本體論;(2)玄學的批判性勝科學一籌、時空觀念的變更、歸納法、矛盾律之蔽;(3)玄學家不當超越知識范圍;(4)對玄學的種種誤解及著者的辯護。
最后一部分“尾聲”討論科學與玄學的關(guān)系,講了“玄學精神流入科學后之貢獻”和“近代科學逼近玄學問題之良征”,指出“玄學與科學的合作,無論是為知識或為人生,都是不可少的。強為分離,則不但兩者同受災(zāi)害,而且失卻兩方面真正的意義”“從人類知識發(fā)展的歷史方面看去,科學的促成玄學,玄學的幫助科學,是顯著的事實,也是知識界最得意的一件事”。
11.今日大哉問
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顛覆了傳統(tǒng)的時空觀,因果律、同一律和確定性這些科學的金科玉律都遭到質(zhì)疑,“科玄論戰(zhàn)”中的“科學”派對此知之甚少。在西方,剛剛經(jīng)歷了一戰(zhàn)浩劫的人們,怎么也不會想到20多年后就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人類還會發(fā)明并使用遠比黃火藥毒氣彈兇殘千萬倍的原子殺人武器。
100年過去了,中國與世界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經(jīng)濟繁榮、社會進步、高新技術(shù)層出不窮的同時,人類也面臨著生態(tài)惡化與資源枯竭引起的生存危機,財富分配的不公、恐怖主義的猖獗、病毒的肆虐以及全球化的退潮,構(gòu)成新的嚴峻挑戰(zhàn)。對這些挑戰(zhàn)作出合理的應(yīng)對,既需要科學也需要人文。
寫作這篇瑣談的時候,ChatGPT一類的新聞不絕于耳,幾個老舊大問題卻一再浮現(xiàn)于腦海,對它們的應(yīng)答遠遠超出本人的智力和學養(yǎng),不揣淺陋寫出來與讀者分享并就教于方家。
人類社會一直是進化的嗎?歐洲的中世紀比之古希臘古羅馬是倒退嗎?文藝復興比之中世紀是進步嗎?無論進步還是退步,什么是客觀的標準呢?進而言之,當代社會還會遭遇大的倒退嗎?
如果按照對社會變革的態(tài)度區(qū)分左右,“科玄論戰(zhàn)”中“科學”一方大抵可歸為“左派”;100年后,當代西方左派卻與民粹主義、文化相對主義和激進環(huán)保主義者結(jié)盟充當批判科學與西方文化的先鋒,這種鏡像轉(zhuǎn)化是怎么發(fā)生的?與當代科學和技術(shù)的發(fā)展有多大關(guān)系?
無論是在物理世界、生命世界還是在人類社會中,現(xiàn)代性與確定性共生共榮都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從19世紀末開始,許多領(lǐng)域相繼出現(xiàn)確定性喪失的傾向,不僅是科學與數(shù)學,還有視覺、聽覺藝術(shù)和某些文學流派,乃至人類社會的演進方向。有人認為這是“后現(xiàn)代”(或后工業(yè))社會的一個標志,人類在翻過“后現(xiàn)代”這一篇后,是否會見證一個確定性回歸的“后-后現(xiàn)代”(Meta-Postmodernity)呢?
許多物理學大師信奉的還原論是否有其適用的限度?“終極理論之夢”有望成真嗎?生成論(或自演化論)的本體論基礎(chǔ)是什么?
機器是否會自我進化?人機混合的“賽博格”(Cyborg)會成為未來世界的主宰嗎?元宇宙世界為心物二元論留下了存在的空間嗎?
人工智能與生物工程能否造出“最強大腦”“最強鐵人”一類的生命個體?未來的技術(shù)可否實現(xiàn)人類在智力與體力上的完全平等?沒有天才和英雄,沒有理想或野心,世界是否會變得平庸無奇從而達到學者福山意義上的“歷史終結(jié)”?
謹以此文紀念“科玄論戰(zhàn)”100周年。
(作者劉鈍,系清華大學科學史系特聘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所長。原標題《“科玄論戰(zhàn)”百年祭》)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