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2
- +1360
《無名》:程耳的又一次冒險
注:本文沒有核心劇情劇透
《無名》在預售階段,打出“超級商業片”的宣傳語。對于一部商業片來說,它本可以不必大張旗鼓地聲稱自己是商業片的;但如果這部電影的導演是程耳,這么宣傳也就顯得合情合理了。

《無名》海報
程耳也算中國當代導演里的一個“異數”,他的作品少卻精,《無名》之前只有三部公映的電影,2012年的《邊境風云》、2016年的《羅曼蒂克消亡史》都是迷影群體中的佳作。在此前的作品中,他明明拍的是商業片,但獨特的程耳式美學卻賦予電影強烈的文藝氣質,這種文藝氣質甚至完全碾壓了類型元素,這就造成一個頗為可惜的結果:明明電影在影迷群體中口碑很好,票房卻很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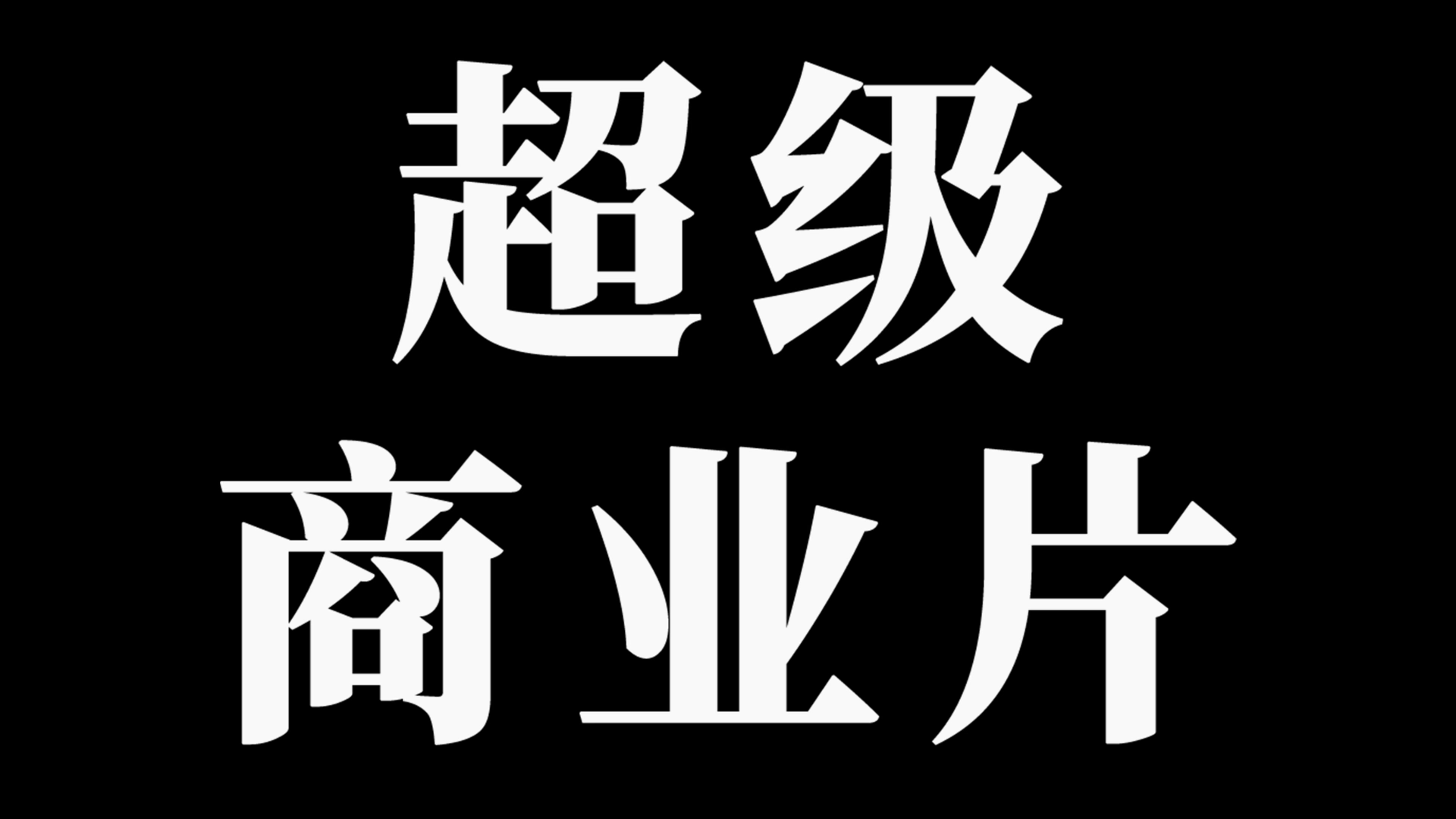
《無名》預告片打出了“超級商業片”
來到了這一回的《無名》,坦白講,相較于梁朝偉和王一博,對我個人而言,程耳美學的吸引力要更大一些。很多影迷也是由衷期待:“超級商業片”《無名》,既能夠保留和發揚程耳美學,也能夠獲得商業上的超級回報。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程耳能否在商業元素與個性表達這兩方面上實現“并駕齊驅”。
那么,《無名》做得如何呢?
“超級商業片”的努力
從演員陣容的選擇上,可以很直觀地看出《無名》在商業上的努力。不僅僅是因為梁朝偉、周迅等頂尖電影演員的加入,更在于頂流王一博的參與。
在電影的整個宣發階段,王一博粉絲的凝聚力、行動力,讓業內一些搞宣發的朋友嘖嘖稱奇。《無名》的首日票房已經超越《羅曼蒂克消亡史》,創下程耳導演生涯的最高紀錄——雖然對于“超過三個億”投資的《無名》(于冬的一個采訪中透露)來說,這個成績并不夠。
當然,也不能傲慢地認為,程耳使用頂流是在向流量妥協。《無名》中的王一博確實呈現了不同于他以往在熒屏中的形象,更顯冷峻、沉穩、肅殺。對于新人演員來說,這種“冷面”角色是有助于藏拙的。

王一博飾演“葉先生”
《無名》的商業性,還體現于它的類型特征上——這是一個諜戰故事。暫且不論諜戰是否與春節檔契合,在程耳這里,“類型”本身就是存疑的。
回想起《邊境風云》《羅曼蒂克消亡史》公映時,都曾因為所謂的“晦澀”而勸退一部分觀眾,可事實上,這兩部電影都可以歸類為商業類型片,《邊境風云》是緝毒題材的警匪片,《羅曼蒂克消亡史》是以舊上海為背景的黑幫風云。
但觀眾在接受時卻有強烈的錯位感,除了獨特的程耳美學外(下文我們會予以闡釋),還在于程耳對于類型“賣點”的疏離,或者說反類型呈現。就比如《羅曼蒂克消亡史》沒有多少黑幫槍戰戲,哪怕是槍戰戲,也不是常規的快節奏剪輯、大量的近身肉搏,而是固定鏡頭搭配升格鏡頭,槍戰戲都拍得氣韻十足。
至于《無名》,我只能說:程耳努力了,它具備了更多類型元素。
故事主要發生在1937年-1945年的上海,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周旋于重慶、汪偽、日本間諜機構之間,通過錯綜復雜的敵后情報系統,獲取情報,誅殺漢奸……
有意思的是,電影的大部分劇情都聚焦在汪偽政權的幾個特工身上,包括梁朝偉飾演的何先生,王一博飾演的葉先生。這里其實有著電影的第一重謎題:這些特工里,誰有可能是共產黨?

梁朝偉神秘莫測
“身份之謎”,這是諜戰題材核心的審美特征之一。諜戰故事中的主人公一定有雙重甚至多重身份,畢竟特工就得潛伏,潛伏就意味著偽裝。身份的多元讓人物關系復雜化,盤根錯節,而特工身份隨時有被看穿的風險,這讓特工始終處于險境當中,懸念迭生,極具戲劇張力。
“身份之謎”是《無名》最關鍵、最具巧思的一個謎題。尤其是周迅飾演的陳小姐,決定著謎題何時最終揭曉。

周迅飾演的陳小姐,戲份不多,但非常關鍵
動作戲也是諜戰片里的一大看點,尤其是在大銀幕上,動感刺激的視聽語言一向是吸引觀眾的利器。《無名》中有大量的動作戲,在呈現上程耳突破了他自己的風格舒適區。
誠如前文所言,在《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動作戲,依然拍得非常“羅曼蒂克”;《無名》中的動作戲,在確保鏡頭語言格調的基礎上,程耳的處理就相當“超級商業片”了。尤其是梁朝偉與王一博那一場幾分鐘的打戲,近身肉搏、驚險刺激、凌厲暴裂、酣暢淋漓,動作設計非常驚艷。

電影中的幾場動作戲很精彩
作為一種帶有強烈本土特色的影視類型,諜戰片是主旋律的重要分支。我黨的地下工作者信仰堅定、恪守使命、機智勇敢、忘我工作,為了民族解放事業,將生死置之度外,視死如歸,他們身上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令人感佩。《無名》本身也是博納集團繼《中國醫生》《長津湖》之后,“中國勝利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謳歌了那些“無名者”的偉大奮斗。
難得的是,《無名》的主旋律表達上并不生硬(或許,除了張婧儀飾演的角色那幾句有點像口號的臺詞)。就像電影的英文名“Hidden Blade”——袖劍所寓指的,它代表的是一種普遍的忠勇與犧牲,始終有著優雅從容的美學支撐。
依然是程耳美學的冒險
不過,程耳并未因此丟掉他獨具特色的程耳式美學,《無名》仍與觀眾所預想的傳統諜戰故事有很大的不同。從商業利益角度來看,《無名》實在是一次巨大的冒險。
程耳式美學,首先體現在敘事特征上。
一個是突破時空限制的非線性敘事。線性敘事主要按照時間發展順序推進劇情,簡單理解就是1-2-3-4-5。在程耳的電影里,時空順序是打亂的,呈現效果可能就變成了2-5-2-4-5-1-2-3。
《無名》依然如此。電影中有幾個相對關鍵的時間點,比如1938、1941、1944,但它們完全不是線性推進的,而是反復交叉。就比如故事一開始,“周迅”坐在香港的咖啡館里,觀眾得直到電影快結束時,才知道這一幕的前因后果。同樣地,“梁朝偉”一個往向觀眾的眼神,一次突然響起的電影鈴聲,或者“王一博”與“王傳君”對峙時的突然靠近,觀眾只能在劇情某個出其不意的時刻與它重逢,從而破解奧秘。

猜不到人物在想什么
非線性敘事的長短處都非常明顯。優點是,能夠給觀眾帶來一種類似于拼圖或者走迷宮的智識上的樂趣,可以激發觀眾保持投入和思考,一同卷入這段波詭云譎的歷史,并在謎題揭曉時獲得意出塵外的審美快感。缺點是,對于純粹想放松的觀眾來說,它過于晦澀難懂,稍微一走神就很難接上劇情,極大考驗耐心。
程耳敘事的另一個特點是,多視點敘事。電影的敘事視點很少是由某個主人公出發的,它是“不定式”的,敘事焦點在不同人物之間不斷的變動和轉移。就比如《羅曼蒂克消亡史》中,以小人物鋪展出歷史的眾生相,也才能更好地呈現淪陷中的上海,被戰爭毀掉的秩序、禮節、美感及詩意;正是不同身份的人構成了一個時代,也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消亡。
《無名》依然是多視點。它時而是“梁朝偉”的視角,時而是“王一博”的視角,時而是“黃磊”的視角,時而是“大鵬”的視角,時而是日寇的視角,時而是戰亂中被日寇踐踏的普通人的視角……這就像是對歷史的全景廣角呈現,容納盡可能多的信息,讓我們窺見歷史更迭背后的死水微瀾。
程耳的多視角敘事,敘述者又是明顯<角色的。也就是說,觀眾從鏡頭所見所得,比電影中的人物知道得更少,觀眾只能從人物的外部表情和動作去揣度他的內心。就像電影的前中段,“梁朝偉”始終是深不可測,觀眾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這就形成“冰山理論”的效果,有巨大的留白空間和想象空間,從而獲得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等到謎底揭曉時就會帶來一種澄澈的恍然大悟感,興味大增。

人物就像“冰山”
可無論是多視角敘事,還是“敘述者<角色”的外聚焦敘事,它們無不進一步加劇劇情理解的難度。程耳構建的這個謎題相當精致復雜,感興趣的觀眾愿意三刷;不感興趣的,就讓人想起古人對一位宋代詞人的評價,“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
除了敘事,程耳美學還體現在它的鏡頭語言上。比如以固定鏡頭拍攝一些吃飯的場景,讓觀眾產生一種“凝視”般的沉浸式的觀影體驗,在亂世中感受或難得或“麻木”的日常。
比如以俯視鏡頭拍攝殘酷,在冷靜克制的疏離中蘊含著濃烈的情緒。在《羅曼蒂克消亡史》中,那是陸先生全家被屠殺的一幕;在《無名》中,那是華夏大地在日軍的轟炸下滿目瘡痍,盡顯殘酷無力。
再比如程耳對畫面的構圖一向是精益求精,以大量考究的對稱、均衡,形成一種典雅、端莊、深沉的美學鏡頭。

電影構圖精致
好在,考究的鏡頭語言除了讓《無名》充滿腔調、韻味十足外,并沒有加劇解謎的難題,否則難上加難,電影將進一步失去通俗性。
總之,《無名》中程耳嘗試了更多的商業手段和商業表達,但它仍是典型的程耳美學作品。《無名》是否會收獲“超級商業片”的市場回報?這讓人憂慮。電影無疑是程耳美學的勝利,但在快消時代,抒情詩人不見得受捧,無論是程耳此前的電影,還是去年婁燁一部充滿個人特色的諜戰片《蘭心大劇院》的票房冷遇,都在說明這一點。
程耳曾在《對得起這碗白米飯》寫道:“欲望無休無止,但我們要注意吃相,對于這份工作,我們應有起碼的品味與現時代的審美,趨于準確的表達,不要讓觀眾在漆黑的電影院里,因我們的草率無知甚至胡鬧而感到羞愧。強大過后更應該克制貪婪,否則只會越拍越差。”
不論怎么說,程耳的《無名》是“有起碼的品味與現時代的審美”。只能祝電影好運了。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