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丁帆:江南秋雨中,我望見了許許多多歷史的輪回
秋雨·古鎮·云煙
江 南

回眸我的人生軌跡,在我的出生地上,我不知道在我的血脈中,還有沒有江南文人的文化基因,但是,我清楚,在江南秋雨中,我望見了在許許多多歷史的輪回,各種各樣蘇州人的背影并沒有消逝在云煙之中。

江南·秋雨·古鎮·云煙
文/丁帆
刊于2023年1月19日文學報
踏著淅淅瀝瀝的江南秋雨,伴著踢踢踏踏高跟鞋擊打青石板路的悅耳聲,我們打破了千年古鎮的寂靜。
行走在蘇州鄉間古鎮逼仄的阡陌街巷里,老宅舊屋,斑駁陸離的高大顯赫仿舊門樓,依然靜靜地述說著這里昔日的輝煌。
與周莊、同里、木瀆、甪直、震澤等著名古鎮游人如織不同,我們所到之處卻是半開發的古鎮村落。寂靜,對于一個旅人來說,那是一種行路的福祉,因為你可以駐足停留下來,站在風景旁仔細勾留觀察,用靈魂去體驗遐思古今人生。

從太湖第一古村落陸巷,到西山明月灣古村,再到疫情時代人跡罕至的古鎮黎里,我似乎見到了藏匿在江南煙雨明月中的深閨美人。
吳地乃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之圣地,毋庸置疑,僅明清兩季,這里盛產的文化名人就占據江山社稷的一半,光是狀元及第者就占南北直隸考生的百分之四十,兩代帝師翁同龢這樣的人物更是不乏其人,當然,當年的蘇州道也是囊括如今上海松江府的。
號稱“江南四大才子”的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更是名聞遐邇,其放浪不羈的浪漫故事被夸張放大后,流布于市,竟也成為文人士子另一種浪漫主義風骨的呈現。金圣嘆竟然在梟首之際,說出的是黃豆與梅干菜同煮能吃出肉味的“昏話”;東林黨人并非只是打嘴炮的等閑之輩;松江府夏完淳與陳子龍英勇抗清,被捕后在獄中談笑自若,寫下了著名詩篇《南冠草》,我始終覺得1943年被郭沫若改編成的歷史劇《南冠草》,似乎缺少了一點什么。夏完淳在南京就義時年僅17歲,少年時代的我常常在他被囚禁的地方玩耍,卻不知道那里有過他的足跡。江南的性格是柔美婉約的,卻有著被人忽略了的強悍豪放的另一面,20年前讀夏堅勇的歷史大散文《湮沒的輝煌》,我被江南士子那種大江東去、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氣勢嚇住了,原來那是江南煙雨背后的電閃雷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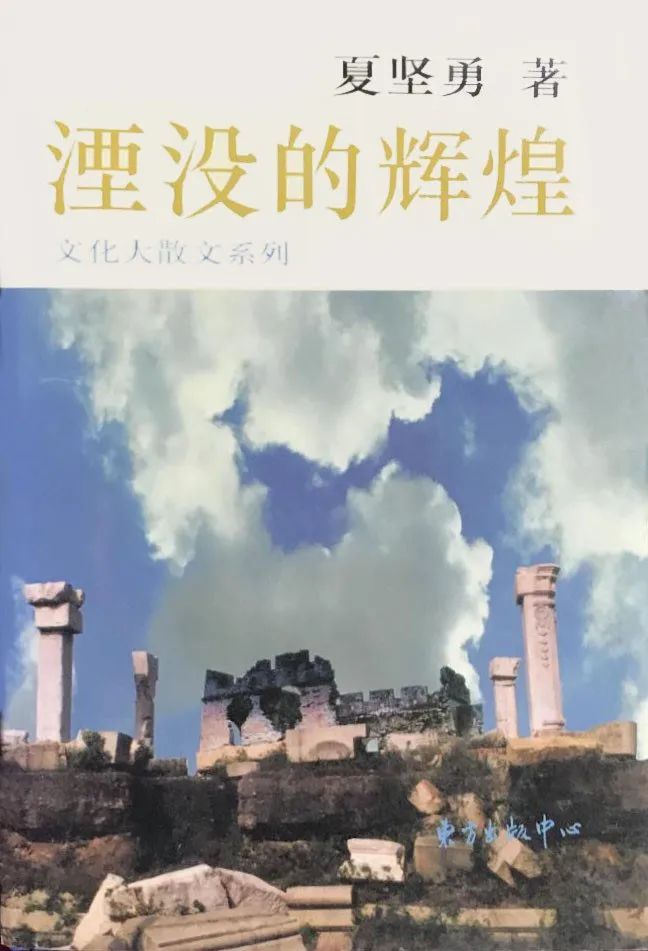
夏堅勇《湮沒的輝煌》
今天,沿著這些先賢走過的足跡,在氤氳朦朧的細雨中,我陷入了對歷史的無限遐思。千年的歷史煙云,是一個永遠訴說不完的故事,那只是一種歷史的參照物而已。而于我而言,這一塊土地是我生命的始發地,因為這里是我的衣胞之地。
1949年以后,父親從上海善后管理所來到了新中國的蘇南公署,那時上海還隸屬于蘇南公署管轄,用蘇州大學已故教授范伯群先生一句經常調侃揶揄的俏皮話來說,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只是蘇州的一個后花園而已。1952年我出生在蘇州的閶門,那里是公署的機關。后來聽父親談起往事時,不斷抱怨那時下鄉出差調研的時間多于蹲機關坐辦公室的機會,他們坐著一輛舊吉普車,幾乎跑遍了蘇南各縣各個鄉鎮。記憶猶新的是,他說許多地方并非是江南魚米鄉,像沙洲(今張家港)那樣的窮縣是無法和蘇州吳江一帶富足的鄉鎮相比的。
車輪滾滾,父親躑躅蹀躞在江南古鎮里,他的足跡有無抵達陸巷、明月灣和黎里古鎮長長的街巷里呢?重要的是,在這些歷史的街巷中行走的時候,他只是去調查那里的經濟狀況嗎?推開那些沿街商鋪門面并不沉重的歷史店門,他能夠看到他們所建構的鄉鎮商埠未來的前景嗎?一連串的歷史叩問在幾十年的變遷史中只有一種答案,到了上世紀80年代后才開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他那時卻進入了生命的最后階段,相約一起再去蘇州各地鄉鎮轉轉的愿望卻化作一團云煙,飄逝在他曾經徘徊的古巷舊院中,遁形于茫茫江南煙雨的太湖湖畔。如今,我躑躅蹀躞在這三個古鎮長長的青石板道路上,我不知道父親的足跡當年有無抵達這個深藏在偏僻之地的古鎮,倘若沒有,我代父親走過這長長的歷史長街,一睹他沒有看到的這四十年的歷史景觀,也算作一次替他還愿的旅行罷。

其實,我在任何旅游景點都十分反感那種商業化的炒作,它抹去的是文化的意義,攻擊的是人們對地域風景、風俗和風情的那份閑心游意。
說實話,陸巷與明月灣古鎮古村并沒有進行過度的文化包裝,但是,那里卻是在重走商業規劃的改造模式,我只能一聲嘆息,倒是那個已經改造成型的黎里古鎮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走在那長長的石板路上,在江南秋雨中行走竟然不用打雨傘,才驚奇地發現它與其它古鎮不同的地方,路是在商鋪的廊檐之下的。這種歷史建筑風格在國內鄉鎮街巷鮮見,也許它始于閩粵地區吧,我在東南亞地區看到過許多,尤其是長期去新加坡,看到臨街長長的商鋪廊檐,便想到路人在雨天里的方便。如今走在吳江這個古鎮里,猜想當年父親的足跡會到達這里,因為他說過,他跑遍了吳江許多有名的古鎮。
時斷時續的秋雨反而拉升了我們的游興,看著那一座座充滿著古意的石橋橫跨在黎里長街兩岸廊檐之上,油然而生莫名的遐思,那不是兩個時代的歷史比照,而是兩種世界的影像。

在幾乎全無游客的空曠街巷里,隔岸相問的原住民吳儂軟語的聊天,傳遞的卻是千年歷史風景風俗風情的遙遠回聲——那一名狀元,帶著26個進士和61個舉人站在歷史的客棧和橋頭上向今天的旅人招手,他們是在召喚你歸化嗎?瞬間,耳邊卻又響起了東林黨人的那幅著名的對聯。
坐在荊歌先生的文化客廳里喝茶真是一件愜意的事情,啜飲著碧綠的蘇州碧螺春,吃著黎里著名的小吃油墩子,天南海北地胡吹亂侃,方顯出江南文人雅士的生活風格。
想到鄰處的柳亞子故居,便有了些許的惆悵。他才是正宗的黎里人氏,又想到提倡“操南音,不忘本也”的蘇州“南社”,曾經將民族氣節置于其社團宗旨之上,實乃令人敬佩不已。未曾料到的是,柳亞子在新中國初創時期,懷才不遇的心境竟是那樣的不堪,在“萬方樂奏又于闐”時,卻不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這是江南文人悲哀的另一面嗎?而我卻更喜歡像金圣嘆、唐伯虎那樣玩世不恭的江南文人行狀。
寫小說散文的荊歌,選擇慢生活的古鎮黎里作為他面對世界的生活方式,是一個對抗現代文明侵襲的不錯選擇,但愿人居長久。

回眸我的人生軌跡,在我的出生地上,我不知道在我的血脈中,還有沒有江南文人的文化基因,但是,我清楚,在江南秋雨中,我望見了在許許多多歷史的輪回,各種各樣蘇州人的背影并沒有消逝在云煙之中。
原標題:《丁帆:江南秋雨中,我望見了許許多多歷史的輪回 | 此刻夜讀》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