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家,能夠為我們帶來什么?
有些研究顯示,連續感對于產生家的感覺必不可少。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知道自己很快要離開某個地方,就不太可能對那里有家的感覺。這就是為什么如果我們短時間內在像紐約這樣的地方換過好幾個地址,那么這個城市會讓我們更有家的感覺,而不是那些我們居住過的房屋,因為這座城市提供了建筑物本身沒有給到的足夠的連續感。
但話說回來,沒有人想要生活在垃圾堆里。尋覓房屋的人很少會接受他們看到的第一套房子:他們毫無例外地要繼續看房,想要找到“最佳”選項。那么,他們一在尋求關于家居建筑的某些特性和品質,或許那就是讓大腦做出積極響應的特點,哪怕只是在潛意識層面。我向露西詢問了人們在紐約尋找住處時最本質的要求。

“空間往往是最主要的考量。這是一個人口密度極大的城市,所以但凡什么地方能夠提供充足的空間,都會非常緊俏。事實上,人們最終離開紐約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需要更多的空間。他們想要組建家庭,或是因為別的理由而需要更大的空間,但是他們一般無法在這座城市實現這一點,所以只能搬往別處。”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而露西接下來告訴我的情況讓我意識到,在紐約,空間甚至比金錢更有價值。
“我曾經寫過一系列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我調查了那些超級富翁的家,即所謂的‘百分之一階層’,發現甚至就連他們都必須做出一些犧牲,才能生活在城市的中心地帶。在曼哈頓,他們住的是兩居室公寓。當然了,那是極其寬敞、富麗堂皇的兩居室公寓,但這些人在別的地方都可以住一大套宅邸了。然而,他們還是心甘情愿地居住在更小的空間里,只為了能夠把家安在像紐約這樣的理想之地。”
似乎所有人都需要在購買向往的生活空間時做出犧牲。但為什么空間如此重要呢?如果家只是為了滿足對安全感的本能渴望,我們應該不需要太大的空間。如果要我說的話,只要能夠容下財物和所有必需品(衛生設施和一張床等),家居空間越小越好。房子越小,取暖費用越低,維護越輕松,安保也越容易,諸如此類。

可是,居室小也意味著我們不能獲取任何新的東西,或是邀朋友來玩,或是拓展家庭。此外,還存在社會地位的問題:擁有更大的房子,是財富和成功的象征。
我們對空間的渴望遠比這些考慮更深刻:我們的大腦需要一定的空間來感到平靜和避免壓力。有一整個學科領域專門研究我們對空間的感覺,即所謂的空間關系學(proxemics),最早由人類學家愛德華·T. 豪爾于1966年創立。他指出,一個典型的人有4個空間“區域”,相互之間有著令人驚嘆的清晰邊界:親密區域、個人區域、社交區域,以及公共區域,每個區域與我們身體的距離漸次增大。
更新的數據顯示,人們對于空間的感覺既因人而異,也因文化而異。人們對什么算“近”或“遠”各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某一項研究顯示,具有程度夸張的接近感的人更容易患幽閉恐怖癥(claustrophobia)。不過,即使沒有出現臨床問題,人們也對空間非常敏感: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大腦感覺系統中有好幾個區域與三維環境的處理和編碼直接相關。如果我們身處有限的空間之中,我們的大腦會在多個層次上意識到這一點,而且它對此并不喜歡。如果有人激動地喊道“我需要更多空間!”然后憤然離去,他們說的很可能就是字面意思。
(點擊圖片查看書籍信息)
這一切想要傳達的重點在于,考慮到我們的大腦處理空間的方式,一個狹小的住處很可能令人難以忍受。有限的空間意味著受困,無法知道附近發生了什么(被墻壁阻隔),逃脫的選擇也更少。我們的家本該是在我們感到壓力和焦慮時的退避之所,可是如果它太小了,大腦里的威脅探測系統就會持續處于激活狀態,這可不是在家時該有的狀態。
此外,有些研究表明,如果我們已經積蓄了壓力和焦慮,我們的個人邊界就會“擴張”,意味著我們更加無法接受別的人或東西靠得太近。因此,暫且放下實用性和建筑學方面的考慮不說,某些居所僅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就太小了。我們并非不能生活在狹小的空間里,只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更難以感到積極和快樂。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使人們想要一個空間寬敞的家:隱私。

大多數人都不是獨居的。總體而言,這是一件好事——分享和互動對于快樂非常重要,就像前文已經提到的。但是,有誰希望時時刻刻都有人在身邊嗎?即使最外向、最熱情的人,有時也需要在自己的私密空間休息片刻,哪怕只是睡個覺。
與他人的互動,無論多么令人愉快,畢竟是在給大腦增加工作量。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幾乎在所有的情況下,當互動進行到某種程度后,都會令所有的參與者感到厭煩,主要是因為每個人都會覺得精神疲勞。正因為如此,我們最終都需要后退一步,暫時避免與人交往。這既能讓我們重新“充電”,又能避免社交煩躁,兩者對于維持重要的社會關系都很有幫助。有時候我們需要與人相處,有時候我們又需要私密空間。
對身處人滿為患的高壓環境之中的城市居民來說,是否有能力退避三舍無疑更加重要。在城里有一個家,既能夠讓我們立即投入社交,同時也可以讓我們從中抽身,意味著我們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展開行動。這將給我們帶來獨立和可控的感覺,這種感覺普遍受到人們的青睞。而這,又是一種家能促進快樂的方式。

說到空間,帶有花園或是附近有綠色空間的家居總是特別受歡迎。露西指出,紐約最令人夢寐以求的(也是最昂貴的)區域,就是那些能夠看到中央公園的街區。而那些帶有院子的居所一般都被視為比沒有的更高級,哪怕所謂的院子只是一小塊地皮。顯然,能夠踏出房門走到戶外,但又仍在自家的“界限”范圍之內,會給人帶來極佳的空間感,而我們都知道這很重要。
另外,即使是那些沒有院子的人,也傾向于在家里布置上一些盆栽綠植或床掛花架之類的東西。這種讓自己被綠植環繞的所謂強迫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這不僅僅是出于美學上的偏好:與大自然和多樣生物進行互動似乎對我們的大腦有著顯著的積極作用。史蒂芬·卡普蘭對此給出了一種解釋,他將其命名為“注意力恢復理論”。卡普蘭表示,大腦的注意力系統通常都處于“激活”狀態,不停地掃描四周,應對來來往往的人流,并且有意識地將焦點導向當前最重要的事情(例如你正在讀的這本書)。這需要消耗精力和能量,因此對我們的大腦造成負荷。

假如我們度過了漫長而忙亂的一天,注意力一整天都在接受考驗,我們就會感覺自己需要“放空”一下,做點完全不需要用腦的事情,這時我們會明白,這理論說得有道理。
自然環境能夠被動地調動我們的注意力,卡普蘭將這個過程稱為“魅力性”(fascination)。我們的注意力在自然環境中可以更好地漫游,讓大腦暫停導向性專注模式,后者對精神具有消耗性。這樣一來,大腦得以休息和調整,補充資源,鞏固神經連接,增強認知機能,最終改善我們的心情。有鑒于此,卡普蘭將充滿綠植和生物多樣性的環境命名為“恢復空間” (restorative space)。
綠色空間帶來的益處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它甚至可能影響我們的身體。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在病情程度相似的住院患者中,相比在病房中只能看到磚墻的患者,那些在病房中看得到樹木和自然環境的患者恢復的速度更快——從中不難看出演化的邏輯。
——節選自《我的快樂還有救嗎》
推薦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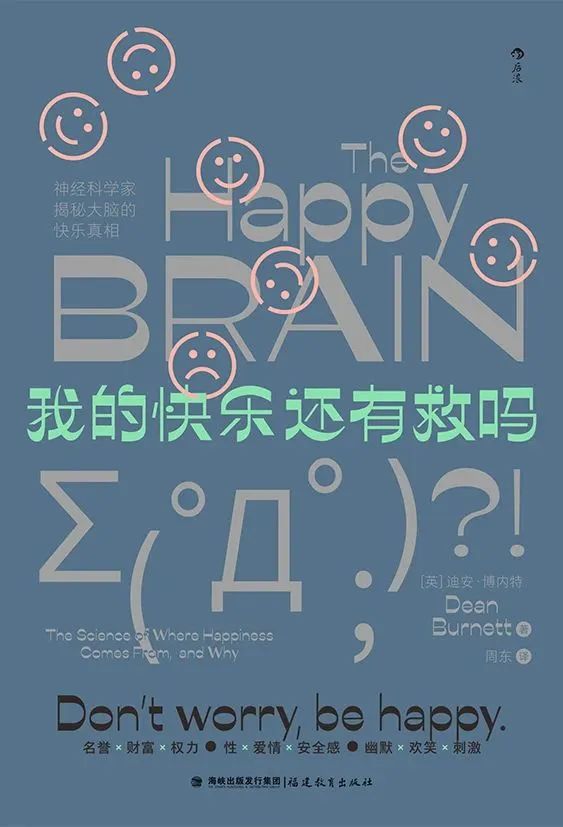
《我的快樂還有救嗎》
什么是快樂?快樂源自哪里?存不存在保持恒久快樂的秘訣?《是我把你蠢哭了嗎》作者全新誠意之作—《我的快樂還有救嗎》
內卷竟是追求快樂的副產品?
電子游戲是會減壓,還是讓我們更暴力?
為什么家會給人帶來純粹的放松和愉快感?
“王子和公主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真的只是神話嗎?
如果喜劇和歡笑能帶來即時的快樂,為什么據說喜劇演員都十分痛苦?
……
還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看神經科學家揭秘大腦的快樂真相,一起破除關于快樂的種種迷思。很多你深信不疑的“關鍵”或“秘訣”,其實只是互相矛盾的誤導!
原標題:《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家,能夠為我們帶來什么?》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