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94
親身參與疫情公益送藥的不完全社會觀察
一、這是一個性別問題嗎
幸運地轉陰后,我把手里常備藥品清點好準備送給需要的人。因為出生在醫生家庭,一直有備藥習慣,100片裝的布洛芬曾經只要幾塊錢,沒想到如今稀缺至此。所以藥物互助公益平臺剛推出,我就去注冊了。
因為平臺推出得十分倉促,很快我就發現,隱私保護方面做得不夠完善,送藥人電話地址身份證全部實名得清清楚楚,取藥人找上門來倒是可以連電話甚至姓什么都不給一個。為了避免騷擾,我小心地把定位設置在了隔壁小區,盡可能隱藏了個人信息。實操中我還發現,一些應該有的安全提示這個平臺也沒有,比如雙方請盡量選擇無接觸取藥(隱私保護不說,哪怕是出于減少傳播風險的考慮,這也是必要的),比如最好提供藥品使用說明規避用藥風險(我會發藥品說明書給對方,用藥劑量和禁忌都會給出,萬一對方拿退燒藥下酒或者是不能吃布洛芬的人群,出了什么事,我這邊已經事先告知盡了義務,責任追不到我身上)。

不論男女,只要確實是高燒急需,我都會給藥,而且不止給四粒。最終我給出了一百多粒藥,雖然樣本小了點,但令我吃驚卻實打實的觀察結果是:求藥的女性普遍更有禮貌和素質更高,溝通過程更愉快。無論是事后答謝還是追著給我塞禮物的,無一例外全都是女性。
我以為上海已經是中國男性家務參與率比較高的地方了,沒想到求藥的人里女性還是主要的家庭照料者角色,電話打過來時問及病患情況,最后還是得換成女性接聽才能把需求講清楚。
我運氣大概還不錯,沒碰到新聞里會踹門罵人去死的男性求藥者這種極端案例。但是沒禮貌的確實都是男性,比如有些男性求助者在我送出藥后就沒任何下文了,還要我主動問藥有沒有丟,才告知“收到藥了謝謝”。女性求助者則全部都沒有這種情況。我遇到最糟心的例子,是有人根本沒生病,他通過這個平臺找過來,想免費囤藥。
當然,男性求藥者里也有不錯的人。比如有一個突然留言說謝謝我,但自己退燒成功不要藥了,不想占用資源,請我留給其他需要的人。這么有道德的高素質男性同胞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已經達到遇到的女性求助者的平均素質水平了。
等等,這真的是一個性別問題嗎?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異?我試著和同樣參與過送藥的朋友討論這件事,發現并不是我一個人遇到這樣的情況。
2020年初我給武漢的醫護對接過物資,今年上半年在上海我是小區團購發起人和最大的團長,也算是有一定的公益參與經驗。這次送藥,我最初是想送給家附近需要的鄰居,他們在我當團長的時候給過我不少幫助,使用平臺送藥給的都是附近的人,我本來認為問題不大。
明明都是在同一片區域,居住人群也沒有什么很大的變化,為什么上半年上海封控期間當團長時(雖然團長無疑以女性占多數),感受到的性別差異沒有送藥平臺這次這么明顯呢?或者換句話說,封控時期小區里明明遇到了不少人品和素質都很不錯、也很熱心的男性鄰居出手相助,為什么這次全部消失了呢?
二、性別分化:一些可能的原因
無法獲取更多數據的情況下,只能基于一些樸素的觀察和粗淺的判斷進行討論。我的看法不一定對,但可以分享一下。
說到底,送藥和小區當團長,都是公益互助,但運作機制是有很大不同的。
和送藥平臺可匿名的設計不一樣,當團長期間的小區,每個人其實都等于是半實名狀態的。當時有阿姨買的惠民菜被送錯到另一戶,團長們安慰阿姨別著急時,有一句很重要的話是,“放心吧阿姨,大家都是有門牌號的人,跑不掉。”——團購群里一般入群都會改名成所在門洞單元樓號戶名,物資被拿錯也能很快找到人,因此所有人都盡量表現出了禮貌和友好,不講道理的人全小區都會知道他或她住在哪里,并避免打交道。后來六月解封后,鄰居們在路上碰到,都還會以門戶號來相稱呼:“啊你好啊702,還記得我嗎我是和你一起搬過菜的201啊!”
這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鄰里監督機制。參與團購的過程中如果有心術不正的人,一旦被鄰居發現,至少在小區剛剛因為缺少物資而自發形成團購的過程里,他或她的信用會迅速被透支,從而失去當團長的資格。因此早期的小區團購能組織起來,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大家必須相信發起人是一個沒有私心、為了公眾利益在做事的人,這樣才會迅速聚攏起來,把錢和采買權放心地交出去。
而送藥平臺是沒有這樣一層監督機制的。即使遇到了騙子,或者是不講道理的人,也很難通過平臺投訴或報警來維權——而有些時候警方的監督效力,可能還不如封控時期能干預居民團購事務的一些小區居委干部。
“監督”以外,第二個關鍵詞是“篩選”。
能夠參與到團購活動,或主動幫助女性團長跑腿賣力的男性,本身等于是被篩選出來的人群,比如是家務參與很多或者要幫忙照顧小孩的男性,有需求要和媽媽們一起團購買奶粉尿布。他們本身就是交流溝通能力比較好、有同理心的男性。我所在小區第一次團購成功的參與男性里就有一個奶爸,太太是基層干部去當大白,已經很久沒回家了,團購物資做消殺時他甚至帶上了小孩,“因為孩子自己想來,留在家里沒人看也不放心。”于是給孩子戴上了面罩和做了很細心的防護。而擔心快遞傳播病毒而反對團購的人,是不會加入到這類活動里的。
因此在當團長初期,只要能在小區里從零起步、成功發動起人來,是非常容易能遇到好人的時期,也很容易形成多贏的局面。我個人當時雖然完全不缺物資但也要去做這樣的事,就是出于當年我在武漢封控期間的觀察:小區的鄰居質量將直接決定封控生活的質量——但好鄰居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自己篩選尋找出來的。
篩選出可信的鄰居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自己能放心的互助網絡,遠遠比個體單打獨斗對抗各種不確定性,要靠譜得多。比如說,如果我因為陽了要進方艙,至少我知道哪些鄰居會可能同意幫我照顧我的貓。如果我的貓要被不合理地無害化處理,我知道小區哪些養了貓狗的鄰居會站出來幫我說話。
從后來的結果來看,我的這個實踐目的基本已經達到,成功認識了一些非常不錯的鄰居,收獲了一些友情,其中女性占八成以上(畢竟干得好的團長和活躍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這個占比并不奇怪)。不過,以非營利為目的的“團長”公益行為,本身只是物資緊缺情況下解決需求的一種權宜之計,等后期物資寬裕一點后,這個模式就很難持續下去了。我從未認為自己參與公益僅僅是為了行善,對我來說,去努力做這些事情收到的實際回報是,當發生齟齬和誤解時,會有鄰居支持和理解,當缺什么東西時,只要開口,就會得到熱情回應。我幸運地靠著很多陌生人的善意和信任撐過了兩個月。封控結束后,團購的大群就地解散,但這可能是多年來一直習慣各掃門前雪的上海人的鄰里關系最好的時期了。
相比之下,送藥的公益行為里要篩選掉不靠譜的人,就要困難和麻煩很多,不愉快的經歷也會變多。如果填寫了送藥人信息,等于被動地等待自己被別人篩選。自己在明,對方在暗,考慮到女性是這類送藥活動里占相當大數量的人群(很簡單,對于痛經的女性朋友來說布洛芬就是常備藥),這實際上勸退了非常多在意個人安全和隱私的女性。
平臺本身帶有篩選性,最好的例子大概是,二手交易平臺上女性被騷擾的概率會驚人得大。所以顧忌這件事的一部分送藥人會直接選擇不注冊平臺,轉而在發布信息里挑選求助人。實際詢問了一些參與者后,發現大家篩選的標準各種各樣:比如不看沒寫清個人病情的求助者(你都來求助了難道還差這兩句話嗎),不理會填寫了多種數量藥物需求的人(只要四粒布洛芬就能成功退燒,要這么多藥品恐怕是囤藥或倒賣藥品者吧)。這實際上等于是倒逼用戶為了安全,去選擇以一種效率非常低下的方式來助人(比如我就沒有選擇這樣做是因為實在沒時間每天瀏覽那么多信息),也很容易造成重復送藥等浪費(有些人不動聲色地收取了不止一個人送出的藥,來得如此輕易,自然不會珍惜)。
求藥踹鄰居門這種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幾乎是一邊倒的公憤——送藥的當事人妹子,算是非常罕見的、標準意義上的完美受害人了(這個詞簡直和真空里的球形雞一樣一般只存在于理論中呢):她動機無私,事發選擇報警,不但完整保留了視頻證據,維權的微博文字為自己辯護時也注重條理,明顯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但她還是要花上篇幅,解釋自己為什么要送藥給男性,并被訓“你懂不懂法律”。
為什么過程如此簡單、是非曲直如此明晰的一件事,竟然能直接擊穿和毀掉互助送藥這種還沒完全成熟的公益行為機制呢——我認為,問題就正好出現在“篩選”和“監督”這兩塊上:有暴力傾向的男性沒有被篩選掉,也沒有一個公正的監督機制來保護好心的人。
這也許能解釋送藥參與者遭遇的性別分化現象的一部分原因。如果沒有更好的隱私保護,在篩選和監督方面提供足夠的支持力度,恐怕活動參與者觀察到的結果,都會有些大同小異。
三、可以脫離性別來討論嗎
可以脫離性別、中立客觀地來討論這件事嗎?我的一些男性朋友這樣說。女性朋友也有人這樣說,覺得“這不是一個性別問題”。包括我自己,也曾經試圖這樣思考。
但是,實踐的過程中,能“中立客觀”、“脫離性別”地以個體身份參加公益的,恐怕只可能是男性。女性可以偽裝成男性,在網上使用男性頭像名稱和性別(很多避免騷擾的女性就是這樣做的),我一直很喜歡以中性的身份和名字出現在網絡上,注冊平臺信息時我會模糊性別,我寫作的風格一直傾向于中性(這次除外)。女性的生活里,假裝自己是一個男性并不少見,就像假裝陽臺上有男人的衣服,門口擺了男人的鞋子。一切都沒有什么問題,直到露出女性身份。即使什么都沒做,女性都會成為了一些人眼中的靶子、獵物和軟柿子,或者被視為有某種義務或被賦予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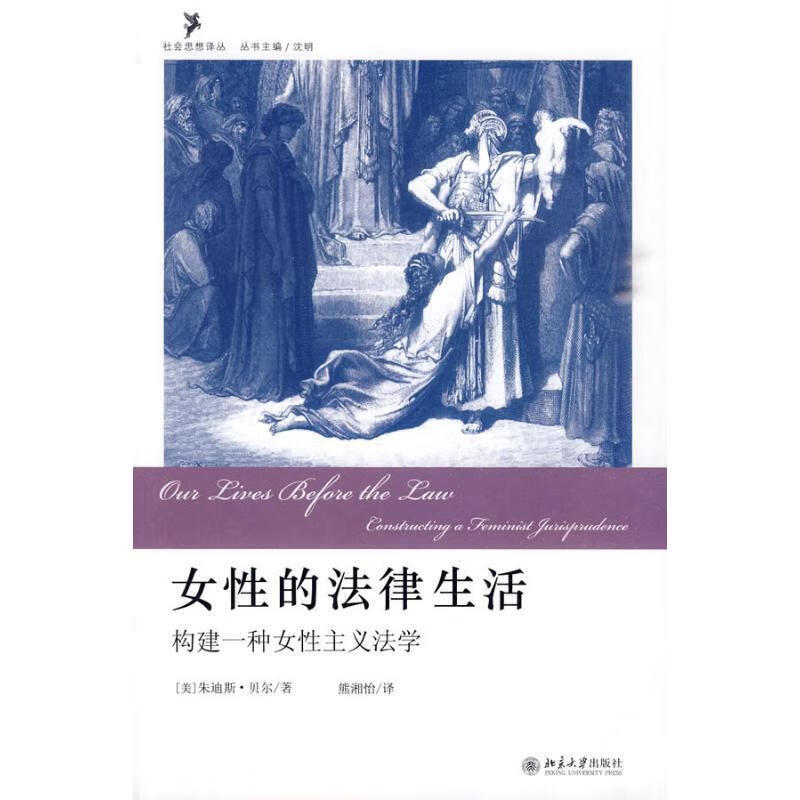
法學學者朱迪斯·貝爾曾經在書里分享過自己的一個經歷,她有一天獨自散步的時候身后突然冒出了一個大哭的孩子,身邊人陸續出現,開始指責她不負責任,直到孩子的真正母親出現,向公眾道歉。沒有人關心貝爾本身的感受;她什么都沒做,和她也沒有任何關系,突然被指責僅僅只是因為她是一個女性,照顧好孩子的責任理所當然地屬于她。我有同樣的經歷:坐著,什么都沒做,突然有陌生人向我走過來請求我讓座。哪怕我腿上放著十幾斤的書包,旁邊男性沒帶包、低頭在玩手機,我也并沒有坐在老弱病殘座位上。我會被視為是可以提供座位的合適人選的原因,僅僅因為是女性,人們會覺得我更容易答應請求。一個女性,想要假裝這不是性別問題,恐怕這才是不切實際的。
能脫離性別、中立客觀地看待這件事嗎?這句話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的預設和陷阱。
要客觀地承認,也許這會是我招致批評最多的一篇文章:畢竟,只有一百多粒藥物送出樣本的我無法提供更多的數據和規避偏差,沒有辦法保持更多的中立,假裝自己是一個不帶任何感情在客觀理性討論這個現象的、中性的人,因為在提供幫助的過程中我會更傾向于優先考慮女性(更安全、效率更高、收益更大)。
我看到那位完美受害者的女孩說,“我是一名醫學生,所以贈藥方面沒有特地去關注性別”。她和曾經的我一模一樣,這次她是我寫作的動力。我有一種幸運的超能力,就是每次去看醫生,醫生都會很喜歡我,侃侃而談,就像看到娘家人一樣松弛。這是因為我的家人全部都是醫生。我會投身在這幾年的這些互助活動里的機緣也正是如此,這不但是一種自助自救,也是我獲取疫情相關信息來預判和保護自己家人朋友的一種方式。畢竟我哥在兩年前就是急診科一線,現在仍然留在崗位上高燒著,父母早就退休但這次人手不足,我爸打了第四針直接上了一線,媽媽待命中。我從小是被當成醫生接班人培養,但是被父母認為更適合做醫生的我,反而最后是家里唯一一個逃離學醫安排的人,我沒有那么強大的內心。
因此我也非常敬佩做了醫學生的這個女孩。但我并不同意,這是一件參與時可以不去關注性別的事情。我以為,恰好因為是女性,成為醫生時才更應該注重性別。醫學行業里最厭女的領域之一,恰好就是婦科這種和女性最相關的科室,教科書里充滿了各種男性傳統偏見的女性的身體知識(熟悉醫學史的話會知道這算是長期的遺毒了),甚至很多婦科醫生本身就非常厭女。朱迪斯·貝爾是我喜歡的法學學者,她說:所有的女性主義法學家恐怕都會同意,法律如果有性別,那一定是男性。這句話換成醫學,也是成立的。美國的法學院里現在擠滿了女生,中國的醫學院里也不缺少女性,很多行業,我們都不再缺少女性的參與了,但是區別可能僅僅是,從此變成了一個更多女性從事的男性行業。
真正的善良,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罕見的高貴品質,人們通常容易低估它的難度——我也許確實做過點好事,但我絕對不敢輕易地奢談自己是善良之人。很多人的所謂善良,更可能只是因為他或她沒有條件和能力去作惡。
哲學上有一個專業的講法叫做“道德運氣”,簡單說,我能完成一些善舉,可能并不是因為我有多善良多經得起考驗,而更可能只是因為我足夠幸運(這篇文章的很多地方,我都在特意強調和解釋這件事),得以成功免于一些復雜的道德難題和拷問,沒有遭遇社會新聞里各種極端情況,比如我不需要去擔心扶老人會不會被訛詐,向人伸出援手的同時是否讓自己置于險境。否則,當我忘記為自己武裝上獠牙和尖刺時,我的善良只會被嘲笑是愚蠢和好收割。這確實令人難過。
但是,也正因為善良是如此的寶貴,在倉促地結束這篇文章之際,我還是想說,很小的時候我就讀過“子貢贖人”、“子路受牛”的故事,簡單說,孔子這樣的圣賢也同意和推崇,做了好事的人,是應該理所當然、理直氣壯地收獲答謝禮物的(無論是國家的補償金還是接受救助者送出的牛),孔子說,因為這樣才能倡導更多的魯國人去救落水的人。能在這些公益活動設計里更多地考慮保護好那些本應受到夸獎的人,無論性別,這本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