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劉夢霏丨數字時代的“歷史之用”:公眾史學與游戲研究
文 _ 劉夢霏(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
歷史學與公眾的關系,是歷史學在當代面臨的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挑戰之一。實際上,“歷史學之用”早就與公眾緊密相關。從山洞中的巖畫,到莎草紙與刻滿楔形字的泥板,再到龜甲與竹簡,歷史一直是人類積極保存自身記憶的重要途徑。我們很難跳脫出自身來書寫歷史;我們所寫的歷史總是不可避免地是“我們”自己的。這里的“我們”不僅是以個人身份在發言,更是我們受所在社會、文化、性別環境影響之后的一種“合奏”。
?在近代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確立之前,希羅多德等傳統史家曾是敘事的藝術家與文獻的綜述者。在19世紀科學化的歷史學的建設進程中,史家逐漸變為“專家”,成為檔案材料的收集者與研讀者。而現在,隨著公眾史學[1]的流行,我們也許可以見到史家身份的第三次轉化——成為“數字工具的評議者”,在專家身份的基礎上關注長敘事、大問題,在數字之流中為這個時代下錨。
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重談公眾史學,既是因為它在承擔著“面向大眾傳播歷史”的使命、具有“以歷史方法解決公共問題”的應用特性之外,在科研方面擁有可以向學院派史家提供助益的功能;也是因為它有了新的發展與新的可能性——這與數字技術息息相關。可以說,21世紀的公眾史學最“公共”的發展就是數字人文,這是歷史學對數字時代的回應,而數字化的現代世界也為史學提供了新的方法與視角。
數字人文潮流影響下的公眾史學,在研究對象與方法上都有所拓展。從傳統的以文本和文獻為主的歷史研究到“更加注意各種視覺再現的作用”,不少傳統史家忽略的新史料被加入到歷史學者的工具庫中。對這些新史料進行研究,有助于我們真正理解此前在精英史學中失語的“公眾”的歷史,因為“在一個并非全民識字的社會中,視覺形式發揮著重要作用”。[2]

歷史學為什么重要
林·亨特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
此外,數字人文也將數據庫列入史家的案頭工具中。古籍與檔案的數據化不僅為學者訪問第一手史料增添了便捷,更為新的研究帶來可能性:跨數據庫檢索使得史家可以在各種主題的數據中找到內在關聯,并揭示文化與社會的不同側面。不過,數字人文的潛力并不限于此。計量史學、量化方法、數據庫的使用都是新的“技”與“術”,而當數字人文變成了“數據庫人文”,無疑是對公眾史學帶來的新史料與新可能性的浪費。在數字時代,公眾史學最值得重視、能夠同時在“技”“術”“心法”方面帶來新的可能性的新大陸,是游戲研究。
游戲研究是針對數字游戲進行研究的專門領域。2001年,英文期刊《游戲研究》(Game Studies)的誕生以及DiGRA(數字游戲研究協會)的建立,使其得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領域在國際上蓬勃發展,并圍繞核心問題“何為游戲”“游戲對人、對社會能有何種影響”產生了大量成熟的討論。
該領域尚未取得國內史學界的關注,主要因為很少有中國史家將游戲視作一種史學對象——在大多數情況下,既不知道如何認識游戲,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游戲。而公眾史學和數字人文的視閾已經為利用游戲鋪墊了一條道路。“歷史遺跡的參觀者不僅想要閱讀銘牌、看展品、聽講解,甚至還會觀看有組織的表演;他們有時候還希望通過歷史重演和其他形式的虛擬體驗更直接地回到過去。”[3]從歷史遺跡探訪到歷史人物扮演,再到紀錄片的歷史實景節目,海外的公眾史家已在嘗試各種能“原樣重現過去的生活”的方式,比如“羅馬重建”項目等。不過,這些項目大多數在以較高的成本支撐一段較簡單的體驗。

Rome Reborn, VR Project ?Flyover Zone
具有前瞻性的史家已經開始關注到“數字建模”對歷史體驗與歷史表演的重要作用,但其對觀眾行動的期待往往與線下場景并無二致,即“來逛,來看展品說明,來截圖拍照”,沒有想到這樣的場景可以容納更豐富的行動可能性——為觀眾提供在歷史情境中做選擇、采取行動的機會,由此直接影響其歷史認同。
直接導向歷史行動,通過行動將被動的“觀眾”轉化為主動的“玩家”,為他們塑造專屬的歷史體驗,并在行動的過程中影響其民族、文化、信仰、社會認同,這是數字游戲能做到,而史家一直沒有意識到的。這里所說的“游戲”,并非出于教育目的專門制作的功能游戲,而是作為商品的游戲。筆者曾撰文論述過游戲的歷史性,以及游戲與歷史結合后可能產生的理論與實踐的多重關聯,[4]也曾從經濟模式出發,將游戲區分為作品游戲、消費游戲、賭博游戲。[5]期待這些研究能為史家提供一些利用游戲的思路。
簡單地說,游戲本身即一種史料。從物質文化史的角度來說,數字游戲是工業社會流水線與資本主義雙重作用下的產物,從策劃、創作到銷售,游戲、游戲創造者與玩家同處于物質文化網之中,受到具體的時間、空間、文化與技術的影響。厘清游戲的物質文化史,也是在為一代又一代玩家的童年與游戲環境作傳,有助于史家理解數字時代技術與文化、游戲物件與社會精神之間的種種關聯。當然,在游戲史流失的過程中,對游戲本身進行整理與保護,并從中發現中國游戲的特性,也是史家應當關注的重要方面。對此,筆者所建立的“游戲的人”檔案館[6]的若干實踐,應可為公眾史家提供一些拋磚引玉的理論與實踐的可能。
游戲也有著非常精神性的一面。宏觀而論,赫伊津哈在《游戲的人》中提到“人類文明產生于游戲之中……你承認了游戲,你就承認了精神”;微觀而論,人們玩游戲的動力既是它所帶來的心理滿足,亦是對它填補工業社會斷裂的意義鏈的期待。[7]游戲往往會像“時空膠囊”一般展現出所在文化的核心特性或社會的核心動力學邏輯。例如,從流行游戲的變遷來看,幾年前流行的以《魔獸世界》為代表多人在線角色扮演游戲(MMORPG),需要玩家與其他玩家并肩作戰、拯救世界;近年來流行的移動游戲,以《王者榮耀》為例,則代表著一種新的游戲類型——多人在線戰術競技游戲(MOBA)的崛起,這類游戲強調玩家對戰,單局游戲時間更短,目標只有“和隊友一起摧毀對方水晶”一條;隨后代之而起的“大逃殺”類游戲,則是一種玩家在險惡的環境中彼此斗爭的生存游戲,玩家中只有一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這一演變折射的是一個競爭越來越激烈,而玩家卻日漸無法對之造成有意義的改變的、主體性日漸減弱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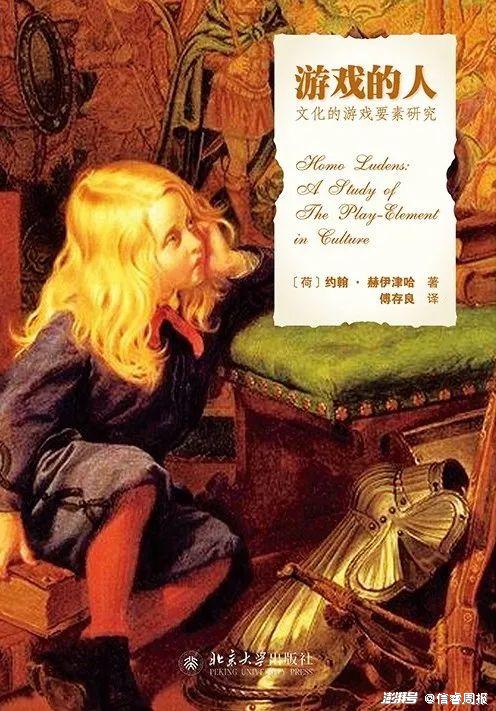
游戲的人
約翰·赫伊津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史家杰森·貝吉(Jason Begy)的研究涉及對幾個有關19世紀鐵路與帝國建設的桌面游戲的分析,他將桌面游戲視為一種物質文化的聚合體,其中展現了大眾對歷史的理解。[8]這種方法同樣應用于數字游戲研究。實際上,數字游戲的反饋環比桌面游戲更強,玩家自主行動帶來的移情更深,也更容易對在游戲中體驗到的內容和觀點產生認同,這些認同集合在一起,便構成了大眾對歷史的普遍認知。目前學界已有不少針對公眾在游戲中如何理解歷史以及形成集體記憶的研究,如關于波蘭[9]和納粹[10]的研究。游戲玩家、設計師與發行商都會受到社會與文化風尚的影響:流行的社會話題常常會成為游戲的主題,人們對社會現象及歷史的認識也會在游戲中得到充分展現。比如,游戲《軒轅劍漢之云》力圖展現的并非完人的諸葛亮形象,不同于儒家的傳統觀念視角,而與后現代史學、新文化史的發展帶來的新視角密切相關。
隨著2017年歷史游戲研究(historical game studies)發布專刊并組織專門的國際會議,其作為一個單獨領域被建立起來。海外學界對游戲的關注已不再聚焦于游戲是否準確再現了史實,而是將重點放在理解游戲的形式如何傳達及影響歷史之上。歷史被看作一個“跨越多種媒介形式、實踐、社會領域和利益相關方的共享的文化過程”,而游戲開發者與游戲本身“試圖建立起一種(針對歷史的)權威感和真實性,與此同時充分意識到在史學中借鑒史實與主觀性之間的沖突與相互作用”。這種對歷史的認識與新史學、后現代主義和數字人文等學術潮流的發展直接相關:一方面,史家的注意力不斷從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轉移,這也是劉北成老師所謂的“從宏大敘事轉向地方性知識”[11];另一方面,語言學的轉向與后現代主義都使“歷史的糖衣融入了歷史的蛋糕之中…….形式與內容常常彼此滲透、相互纏繞”[12]。
同時,我們以往提倡的線性發展的進步史觀對于歷史真實性的確信態度也受到后現代主義的挑戰,“單一的正確的過去”被無數種基于不同敘述立場且可能同時都正確的復數的過去取代,“從中心視角轉向多元理解”因此成為可能,歷史事實的建構性乃至虛構性開始得到史家的重視。這一變化對歷史游戲研究來說特別重要,因為游戲的推進依賴于玩家的主動參與,而這種主動參與往往會不可避免地在游戲復現的歷史空間中加入虛構的成分。正如杰斯帕·居爾(Jesper Juul)所說,游戲本質上就是“半真實”的;當真實性不被視為史家選擇研究主題的唯一前提時,針對游戲的建設性探索才能開始。
筆者曾在博士論文[13]中嘗試了一種不同于西方學界的歷史游戲研究方式。現有的歷史游戲研究主要側重游戲中折射的歷史現狀,是一種“自外而內”的研究,但筆者認為“自內而外”地研究游戲如何影響甚至形塑了現實,對公眾史學這一結合了理論與實踐觀照的領域來說更具參考價值。這篇論文并不針對任何單一游戲或某種游戲類型,而是對在桌面游戲與數字游戲中都會出現的一個職業(德魯伊)與復興的凱爾特宗教(德魯伊之道)之間的歷史聯系進行研究。[14]筆者不強調“游戲的歷史”,而是著重于“游戲入史”,即將游戲與更重大的社會歷史要素并置,使之成為文化潮流的一個重要部分。

《魔獸世界》中的大德魯伊瑪法里奧·怒風,他從半神塞納留斯那里習得了“德魯伊之道”
圖源:Wowpedia
在對德魯伊的研究中,筆者發現游戲確實既體現出“文化身份的符號具象化”,又從根本上揭示出社會的渴望。它不再僅僅是一種“再現”或“折射”,而是形塑現實、影響歷史的重要動因。游戲成了歷史實踐的一部分,也塑造了這個時代關于德魯伊的常識。德魯伊的復興史展示了游戲如何在更大的社會文化當中發揮重要作用,它不僅孕育了傳統的復興,培養了生態認同,還與精神性的信仰有所關聯。游戲的這些社會作用是此前的歷史游戲研究較少探索的,也是公眾史家可以利用游戲繼續去探索的。
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了一些數字游戲與歷史研究可以相結合的方向,并輔以行動指南。
? 歷史復現:這是最嚴謹的歷史游戲的形式,對玩家的要求較高,往往以“歷史模擬類”游戲的形態出現,即按歷史事實設定游戲的初始狀態,用一套游戲機制模擬相應時代的歷史發展規律,最終以再現或顛覆真實歷史過程為目標。比如,《全面戰爭》系列、《王國風云》(又譯《十字軍之王》)系列、《歐陸風云》系列、《文明》系列等。
? 以史鑒今:將虛擬的敘事與現實的歷史相勾連,通過高度抽象的游戲機制對現實做映射。例如玩家在Papers Please(《請出示證件》)中會扮演一個負責蓋章的邊境官員,該游戲過程是對官僚主義、移民問題與種種復雜社會問題的映射。
? 歷史游樂場:讓玩家在真實的歷史背景和人物的環繞下書寫屬于自己的傳奇。在流行的商業游戲中,“歷史游樂場”類游戲較多,可玩性相對較高,玩家容易入手,是歷史教育的重要入口。比如,《軒轅劍之云和山的彼端》、《刺客信條》系列、《皇帝的一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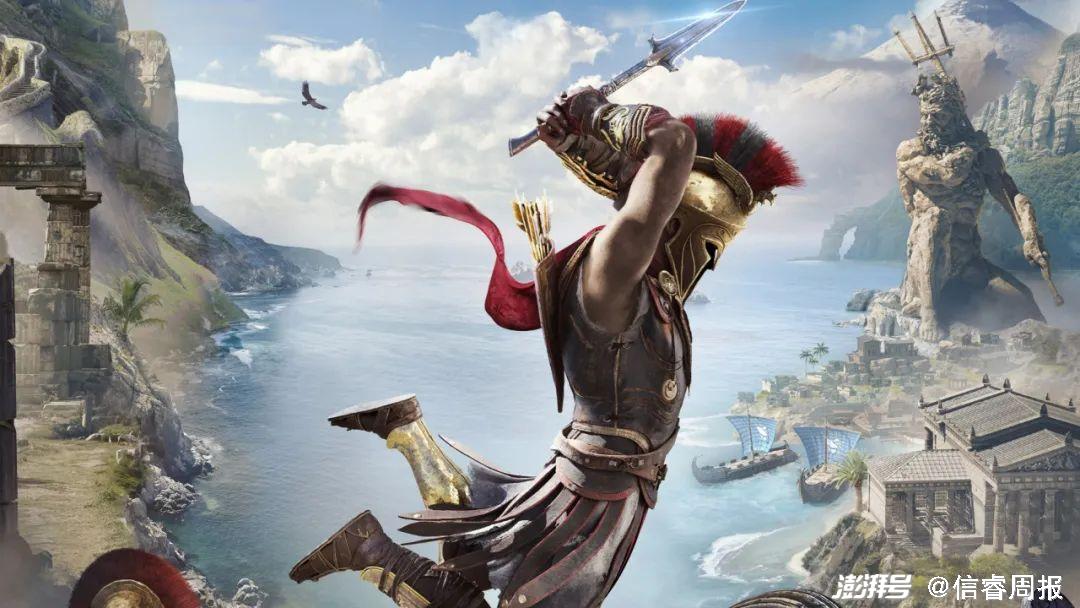
游戲《刺客信條:奧德賽》壁紙
? 歷史學者的技藝:通過提供歷史素材讓玩家自行拼湊歷史事件的原貌,體會利用歷史學者的技藝所得到的思維樂趣。例如,用模擬經營游戲《龍之崛起》來建造唐代城市;在視頻解謎游戲Her Story(《她的故事》)中通過鑒別圖像史料的真偽建構真相;此外,已有海外學者利用游戲JFK: Reloaded(《刺殺肯尼迪:重裝》)、紀錄片與論文三種不同的媒介資料探尋肯尼迪之死的歷史之謎——這是最能發揮玩家-用戶的創造性,也是最能令游戲發揮出實驗室般的作用、讓思想可以得到實踐、讓新發現有可能產生的方式。
當然,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游戲與藝術界限的逐漸模糊乃至“元宇宙”概念的提出,數字社會日漸被游戲填充。可以肯定地說,未來勢必會出現游戲與歷史深度結合的其他研究方向。彼時,游戲與歷史的疆界也許會完全消失:游戲的當下將迅速變為歷史,而歷史將成為可體驗、可學習、可試錯、允許玩家構建完整意義環并完成自我實現的游戲。當這種融合發生時,游戲帶來的新方法、新規則也會導向新的發現:在鏡花水月的清醒之夢中,存在著“超”真實之“真”,這些來自玩家的行動和互動所產生的認同將持續影響現實世界,將虛擬世界的歷史扮演變為現實中的歷史參與和歷史行動。
當公眾史學擁抱游戲時,歷史學者也許會發現,他們所獲得的不僅是一種強大的新武器,更是一種影響現實的可能性。數字游戲,正是在數字時代能發揮“歷史之用”,但在當下最被低估的公眾史載體。
參考文獻:
[1] 大眾史學、公共史學、公眾史學是Public History在不同年代的中文翻譯。其中, “大眾史學”用得最早, 經姜萌考證, 于1987年由朱孝遠在《西方現代史學流派的特征與方法》一文中提出, 并就此成為通用概念。“公共史學”出自1989年王淵明的《美國的公共史學》一文, 此后也擁有了獨立的生命力。“公眾史學”的譯法最新且最為普遍, 本文所引的多數歷史譯作亦采用了這一譯法,為避免造成概念上的混亂, 本文也沿用了這一譯法。
[2] 林恩·亨特. 歷史學為什么重要[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 139.
[3] 同上, 第32頁。
[4] 劉夢霏. 游戲入史: 作為文化遺產的游戲[M]//游戲研究讀本.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0.
[5] 劉夢霏. 游戲監管, 從分類開始[N]. 環球, 2020-07-21.
[6] “游戲的人”檔案館(Homo Ludens Archive)是筆者2018年發起的一個旨在保護中國游戲與游戲人的歷史的項目, 官網地址為: www.gamearchive.cn, 微信公眾號為“游戲的人檔案館”。
[7] 劉夢霏. 尋找游戲精神[M]//離線·開始游戲. 北京: 電子工業出版社, 2014.[8] BEGY J. Board gam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J]. Gamesand Culture, 2015.
[9] STERCZEWSKI P. Replaying the Lost Battles: the Experience of Failure inPolish History-themed board games[J]. Kinephanos, 2016.
[10] CHAPMAN A, LINDEROTH J.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Play: A Case Studyof Representations of Nazism in Games[J]. The Dark Side of Game Play:Controversial Issues in Playful Environments, 2015: 137-153.
[11] 劉北成, 張耕華, 彭剛, 等. 后現代主義與歷史學[J]. 史學理論研究, 2004(2).[12] 同上。
[13] 劉夢霏. 游戲入史: 自然祭司德魯伊形象的古今變遷研究[D]. 北京: 清華大學, 2019.
[14] 德魯伊(Druid)既是凱爾特宗教的祭司, 也是數字游戲中的一個可以變身為動物的戰斗職業。德魯伊之道(Druidry)是2010年得到英國官方承認的一種“崇拜祖先與自然”的信仰形態。筆者的論文即在論述圍繞著德魯伊這一形象而發生的這一切如何歷史地相連, 又與社會文化動力之間有何關系。
(原載于《信睿周報》第84期)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