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創造“世紀之交”:讀周嘉寧《浪的景觀》|新批評
原創 劉欣玥 文學報

無論是“地下上海”,還是電波里的“空中上海”,周嘉寧探入潛伏的城市人文地理脈絡,最想突出的,仍是城市文化的包容性。有如熱流在城市地層下方翻涌,時不時也能闖入公共空間展示自己。書中多次出現對于一代人“好運”思考。
從《密林中》一路寫至《浪的景觀》,周嘉寧終于抵達寫作風格的成熟時刻:內在的專注,明亮的美學,清潔、克制而精確的漢語表達,對于青年時代精神世界的熱愛與洞悉。
新批評
創造“世紀之交”:讀周嘉寧《浪的景觀》
文 / 劉欣玥
在21世紀快要走完第二個十年的時候,《鯉》做了一期“我去二〇〇〇年”的主題策劃。受邀撰稿的“80后”作家、批評家與媒體人,共同回望那個人人急于快步奔向新世紀的90年代,討論被匆忙略過的時代波動。求新求變的亢奮,全球化的近景,對未來的樂觀預期,穿透新世紀前后一代人的青春,也參與塑造了當時還沒有定型的世界想象與價值抉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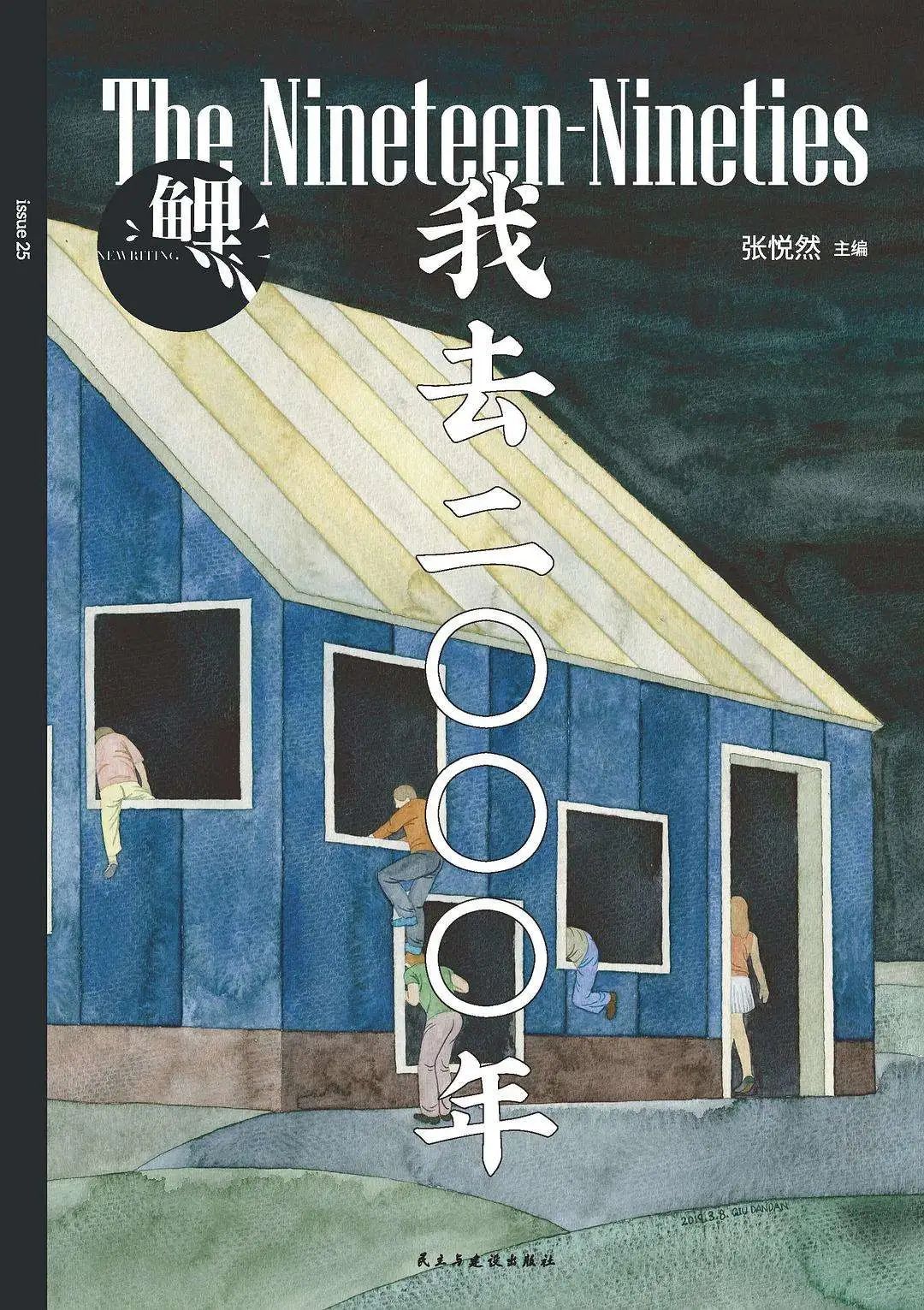
這一期里有周嘉寧的《風暴天》。寫的是上世紀90年代末她在上海的臺風回憶:高中的夏日,整座城市到處淹水的景象,讓原本紀律嚴明的軍訓變成了一場無人管束的校園狂歡。短文的語調明快、輕松,但周嘉寧要講的,其實是成長記憶里上海城市排水系統失調造成的影響。2000年以后,政府投入大筆財政預算,展開道路積水整治與城市下水系統升級工程,極端天氣來襲時的亂糟糟場面,從此徹底說再見,和18歲以前胡鬧的青春期一起留在了上個世紀。
臺風意象曾多次出現在周嘉寧早期的作品中,《蘋果瑪臺風》(2003)里有過典型的青春憂郁敘述,獨自等臺風來的女孩“感到整個世界都是如此憂傷地潮濕著”。到了《風暴天》,室內的孤獨個體變為集體流動的隊伍,城市史和社會現實底色的引入,顯然都為感性的青春心曲增加了發散的維度。對于這一點,周嘉寧自《了不起的夏天》《基本美》以來“走出自我”的寫作調整,有更為充分的展開。《風暴天》的文末寫道,“爾后,我們共同來到了干燥的下世紀。”

周嘉寧在近期思南讀書會舉辦的
《浪的景觀》新書分享會上
在一貫給人以多雨印象的上海,周嘉寧為什么會賦予其“干燥”的形容?“干燥”之感,是市政基建治理與改造升級的結果,更是感官體驗在文學層面微妙的轉喻。生活世界變得更加清潔宜居,如同霧障散去后,萬物遵守的法則變得清晰。但標準化的過程,勢必要整頓掉混亂與混沌感,也見證了諸多“另類之物”的曇花一現,而后消失。周嘉寧用幾年的時間,將這種觀察,寫成一系列以21世紀前后十年為背景的小說,從上一本小說集《基本美》(2018),到最新小說集《浪的景觀》里的“中篇三部曲”——《再見日食》(2019)、《浪的景觀》(2020)和《明日派對》(2022)。《風暴天》可以視作這個系列的題跋,行文雖短,卻具備了這些小說幾乎所有的核心元素:對世紀之交的凝神思考,價值多元且寬容的時代氛圍,年輕人的叛逆、合作與創造,秩序動搖時意外之美的降臨。

理想國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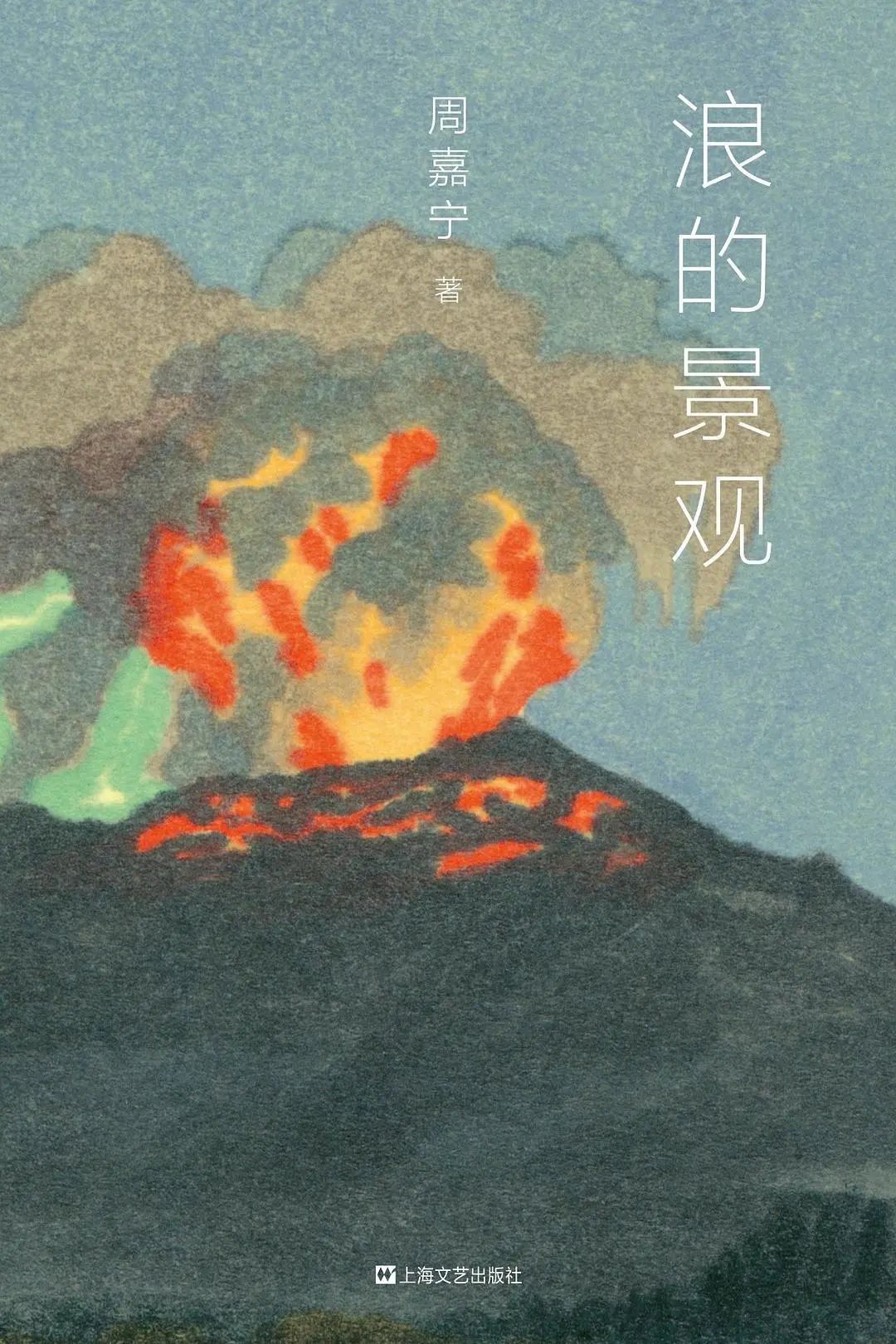
這樣看來,“臺風”是一則極佳隱喻——風停雨住后,世界趨于井然有序,周嘉寧想要用寫作追摹的,卻是規則尚未凝定時的遍地元氣。釋放出元氣的,正是那些在城市快速變化中被抹去痕跡的事物,它們曾從裂隙里涌出,但在當時缺乏有效的文學覺察或文學表達。經過時間的沉潛與空間的考古,周嘉寧使用記憶、語言與虛構,讓這些“另類之物”的細節與意義重新顯影。借用小說中最引人矚目的意象來說,那是時代的強風吹拂下出現過的形形色色的浪。在21世紀的弄潮兒眼前,再小的浪尖上都藏著未知的機遇,而每一個狀似小人物的沖浪手,都是自己的歷史書寫者,無論他們此后是否被更大的浪所吞沒。
同名作《浪的景觀》講述“非典”陰影下,從大專畢業后陷入無業狀態的“我”和群青,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接手了友人在迪美地下城的服裝檔口,成為上海最早的外貿服裝個體戶。如同一對攜手闖關的拓荒者,兩人熬過地下城興起時艱苦階段,直到交上好運,賺進第一桶金。地下城的審美與消費深受搖滾文化浸染,年輕人以衣著標榜叛逆與個性,“我”和群青在不知疲憊中度過了一段浪漫、驚險與財富齊飛的傳奇歲月。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是“我”與群青的引路人,服裝攤主老謝,他從華亭路、襄陽路,再到七浦路服裝批發市場的一路輾轉頑抗,直到徹底退出行業的心碎歷程。這段充滿江湖氣息的外貿服裝販售的變遷史,被周嘉寧寫得鮮氣淋漓。又是販假,又是斗毆,愈發慘烈的金錢搏殺中,老謝這樣富有情懷和才干的“外貿元老”相繼出局,“我”與群青的小檔口也最終被吞并。迪美地下城曾經作為小眾時尚淘貨樂園的精神已逝,只剩下一具供觀光客打卡的消費景觀外殼。故事的尾聲柳暗花明,2007年前后恰逢淘寶網興起,“我”與群青在結束實體銷售生涯之后,告別彼此之前,還意外吃到了網絡銷售最初的一波紅利。

《明日派對》同樣采用了雙主人公的結構,寫了兩個女孩在廣播電臺黃金年代里的友誼、奇遇與共同創造。故事從2001年轟動一時的羅大佑演唱會說起,“我”與王鹿相識于演唱會現場。兩人同為一檔電臺節目的忠實聽眾,后來因為參賽獲獎,以大學生的業余身份,在上海廣播電臺擁有了一檔專業節目。她們建立起音樂上志同道合的小團體,通過電波傳遞20世紀西方搖滾樂的異質之聲,也得到了素未謀面的聽眾的熱情回響,甚至親自采訪了羅大佑。在舉辦名為“明日派對”的音樂現場演出后不久,兩人的節目在洶洶來襲的電臺商業改制中被關停。這段聽覺共同體的存在時間盡管短暫,卻記錄下了同代人彌足珍貴的共鳴共振。

新舊世紀之交,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沖擊廣播電臺這樣的國營單位,為了效率和盈利,不得不割舍情懷,作出結構性的整頓與裁減。在《明日派對》和《浪的景觀》里,無論是空間被一再擠壓的小本經營實體服裝銷售,還是電臺這種傳統媒介形態的轉軌,都置身在這個價值趨于單向的進程中。但與此同時,小說里也出現了方興未艾的ebay、淘寶網,還有尚在胚胎階段的豆瓣網的身影。今天的讀者一定能會心一笑,像是看見了老友的童年照片。沒有人能拒絕技術革新與資本競逐,盡管告別總會伴隨著嘆惋,但那個時候,多的是繼續奮勇迎上下一個新浪潮的人。
對與自己經歷相近的城市文藝青年群體的造像,早已是“周嘉寧式的小說”的標識之一。她筆下的人物,多多少少偏離于主流規則,因為少數人的興趣愛好而聚集在一起,結下友誼,也總能搭建青春烏托邦般的同溫層與庇護所。《浪的景觀》一書,則尤其突出地以空間化的方式,復現了一系列匯聚文藝青年的實體“據點”:《浪的景觀》里的搖滾歌友會、外貿服裝批發市場,《明日派對》里上海的“指揮部”與南京的“防風林”、電臺節目、線上音樂論壇。《再見日食》的故事架設在更大的國際視野里,但位于北美中部的小城佩奧尼亞同樣具有“飛地”氣質。在那里舉辦的青年藝術家駐留計劃,為第三世界的年輕人提供了“身處世界進程之外”的避難所,在跨越語言、膚色、文化積習的碰撞中,摸索人生與藝術新大陸的入口。這些空間場所,都可以歸入前述具有“混亂感”的事物之列,其所內蘊的青年創造力和文化傳播能量卻不容小覷。無論是對城市垂直空間的重新發現,還是年輕人在中國與世界版圖上的跨境與流動,文藝青年的“空間創造”,都是《浪的景觀》所著力刻畫的。

小說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寫空間。公路、街道、市場、公園、河流湖泊,調用大量真實的上海、北京、南京、臺北等城市空間細節,閱讀時仿佛也穿梭在實地、歷史與想象的多重曝光的城市里。隨著21世紀前后城市文藝青年交往史的路線重現,周嘉寧也重繪一個半隱失了的“地下上海”地圖。“地下”在這里有雙關之意,既是主流之外的小眾文化角色,也是物質空間方位的地表以下——這些集群好像打游擊一樣,在隱蔽的城市夾層中開辟自己的活動場所。最典型的形態,莫過小說中出現的各式各樣地下、半地下的防空洞。《浪的景觀》中的迪美地下城、樂隊演出live house,《明日派對》中的青年俱樂部,還有吸引了大批搖滾樂隊的排練廳所在地,都是始建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防空洞,“墻上留著60年代的保衛標語,也貼著二十一世紀的唱片海報。”人防系統建設的遺留物、廢棄的學農基地,都在各類文化青年集群的手中得到新一輪的空間賦權。

無論是“地下上海”,還是電波里的“空中上海”,周嘉寧探入潛伏的城市人文地理脈絡,最想突出的,仍是城市文化的包容性。有如熱流在城市地層下方翻涌,時不時也能闖入公共空間展示自己。書中多次出現對于一代人“好運”思考。“好運”如同偶然與奇遇的同義詞,卻只會在一個布滿縫隙的社會頻繁地隨機掉落。用小說人物的話說,“難以想象,我們未經訓練的聲音和想法將被傳播到如此堅固有序的城市里。”這在無意中接通了情境主義精神和1960年代以來圍繞城市權力展開的行動。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明日派對》收束于“我”、王鹿與瀟瀟用充氣艇在蘇州河上劃船的率性行動。在聯防隊不緊不慢的監視步伐和手電筒光照下,這個游戲般的冒犯/冒險游戲,也許只會給這三個年輕人自己制造出一段“犯規”的難忘記憶,卻也在被城市規則板結化的空間區隔里,結結實實地劃開裂痕,釋放出解放城市空間的文學想象力。

周嘉寧的小說一向具有鮮明的城市性。作為生長于八九十年代的城市一代,長大成人的過程,恰好踩上了城市躍遷的發展主義節奏。作家多次提到青少年時期的上海是一座處處都在施工的“大工地”。《浪的景觀》里也有無處不在的城市工地:夜色下挖了一半的越江隧道,深入浦東腹地的新的地鐵站,機器噪音轟鳴,如同一頭霧中巨獸。調查記者小象的感受是,“覺得前方阻斷的淤泥被漸漸清除之后,通往的不是江的對岸,而是其他地方。”在隧道修了一半,還不知道要通向哪里的時候,人們被允許自行越界,擁抱歧路。無怪乎會產生通行無阻的空間暢想,“據說整個上海地下的區域與區域之間都是相互連通的,理論上可以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想象與行動可以穿透混凝土、廢氣與泥濘,同樣可以將個人聯結于他人。小說里刻畫的那個時期的人與城,都受到這種未知的放縱與滋養,處在如夢似幻的“現實中間狀態”。借用作家偏愛的湖與岸的比喻來說,“對岸”的魅力,在于或許什么也沒有,卻仍然保有所有可能。

所以,面對那些后來消失在半途中的痕跡,周嘉寧使用了“景觀”——這個鄭重到顯得理想化和浪漫化的詞語——以示對于多元、平等的有機社會的敬重。語詞的悖反,恰恰透露出對景觀化的消費社會邏輯的質疑。不過,與其說周嘉寧要那些時代的沖浪手樹碑立傳,不如說恰恰相反。比起三篇小說主人公的猶豫底色,泉、群青、小象、張宙和瀟瀟等人,代表了一種堅定前行的姿態。面對集體生活的落幕,美好時光結束的感傷,他們更多時候是清醒的,也是坦然的。馬里亞諾問,“你們還沒有年輕夠嗎?”群青說,“不然呢,要造一座紀念碑嗎?”借人物之口,同一個集體中不同聲音形成張力。盡可以由衷贊美,但也處處警惕懷舊,拒絕再次掉入景觀化陷阱,小心地避免落入自我感動和過分煽情。在某種意義上,周嘉寧專注“世紀之交”的出發點想來絕非懷舊和美化過去,而更接近于伯格森提出的“活的記憶”,“一種著眼于未來而對現在和過去所做的綜合。”未來已至,讓那些藏在年輕時代深處的“泉源時刻”重新浮出水面,是為了讓現在繼續在思考中往前走。就像那支在蘇州河劃船的小分隊,最后在該靠岸地時候堅定地靠岸,岸上的生活也同樣值得創造,“今天可能也是永恒的一天。”
從《密林中》一路寫至《浪的景觀》,周嘉寧終于抵達寫作風格的成熟時刻:內在的專注,明亮的美學,清潔、克制而精確的漢語表達,對于青年時代精神世界的熱愛與洞悉。像尼采所說的,“最深邃的洞察只會源自愛。”使人驚喜的是,城市文藝青年常常被貶義為“狹隘自我”、“逃避現實”、“過分敏感”,周嘉寧的創作卻能多年專注于此,耐心地向下掘地三尺,直到打通時代與城市變遷中潛在的文化脈絡。這樣的寫作者的真誠在于,“21世紀初的考古”從未完全脫離“自我”的蹤跡,而是以親身經驗讀入這段歷史,藉此反身更新自己深嵌其中的記憶與理解。小說對新世紀前后的每一次文學回收與精神反芻,都是對“城市文藝青年”更深層的歷史經驗的話語檢索。

在“80后”內蘊諸多的身份所指之中,“文藝青年”招來的聲音盡管褒貶不一,卻從來都是獨具時代癥候性的一個群體。這個以文學藝術作為世界觀乃至生活方式的集群,他們身上的指標性,還有大片尚未充分討論的空間:西方流行文化工業、傳統教育制度、以消費形式追求的個性化差異、互聯網進入后初代網民的文化交往、bbs論壇時期的文學……周嘉寧的創作,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他們的生活史、心靈史與文化實踐,從來都有機地內在于社會的劇烈重組,并且可以毫不遜色地對時代激蕩作出有力的應答。
盡管作家并不打算要證明什么。在這一點上,《再見日食》描繪的那場日食,和男作家拓對于泉的思念、虛構與安放,最接近于周嘉寧目前的小說觀念。在日食帶外圍看見的日食,隔著山的背面和湖的對岸聽見的歡呼聲,究竟算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日全食帶的“陰影”之于陽光直射的地方,一如“地下”之于地面,當然,也一如小說虛構之于現實。新舊千年交替時,洞開過多少入口與出口,小說家并不想占據風景的解釋權。她好像只是自在地逗留在虛構與現實的交叉地帶,好像只是和旁人無異,看一看風景。
原標題:《?創造“世紀之交”:讀周嘉寧《浪的景觀》|新批評》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