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訪談︱羅新:有所為有所不為,就做一個學者
【編者按】在我的印象中,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羅新教授上一次受到讀書人的廣泛關注,是因為他那冊薄薄的《黑氈上的北魏皇帝》,而最近一次“火”起來,是因為他去年年底出版了《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本訪談大體圍繞“學術旅程”和“讀書獻疑”兩個主題展開。“學術旅程”期望借此增進對其人的認識,“讀書獻疑”則基本上由《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引申開來。

澎湃新聞:您在《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前言里說,“我能夠較多地使用魏晉南北朝史料,全拜近二十年田余慶先生和祝總斌先生兩位恩師的教誨。”很想請您談一談田先生和祝先生在教書育人和治學風格上分別有什么特點,對您有著怎樣的影響。
羅新:兩個人性格很不一樣。田先生年紀大一些,資格老一些,我(在北大)入學的時候,平時也見不著他,一年大概見上一面、兩面的。經常能見到的是祝先生,我們幾乎每周跟祝先生在一起,一是在他家里讀《通鑒》,一是上他制度史的課。在研究生頭一兩年跟祝先生的接觸是很多的,到三年級的時候準備寫碩士論文了,我和另一位同學就要分開,各選一位導師,祝先生對我說,田先生讓我跟他,另外一位同學就跟祝先生。從那以后,我和祝先生的接觸就慢慢少了,好多都是禮貌場合那種見面。但是,我覺得祝先生對我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第一個是他怎么對學生,他對學生(的態度),用田先生的話,就是“菩薩心腸”,總是為學生著想。要是按照田先生那種嚴格的標準,有些學生不能招,有些學生不能畢業,有些學生中途就應該淘汰了。可是祝先生總是會替學生想,這是特別難得的。要是問他為什么(這樣做)——連我們做學生的都覺得,這個人就算了,中期考試讓他不過關,就讓他回家了,可是祝先生會覺得人家是真的愿意學習,一個人想學習,那一定要想辦法幫他。他是這種性格和心腸的人。這點對我還是有很大影響的。
另外,要說學歷史,入門,那是祝先生帶的路。我中文系畢業的,原來也讀歷史書,畢業之后好幾年都是在讀歷史書,讀筆記啊,讀正史啊,讀雜七雜八的著作啊,可是不大了解(文學和歷史)有什么不一樣。自從跟他讀了制度史,我才真的領悟了,哦,這才叫讀得懂歷史。上了他的制度史的課,再讀《通鑒》這種書,讀法不一樣了——過去都是從里面找故事而已。祝先生的課我都聽過,史學史、法制史、官制史,在我讀碩士和博士期間,他開的課我都聽過。這對我非常非常重要,特別是讀碩士時每周到他家里讀《通鑒》,真是很有收獲的。
祝先生今年88歲了,據說現在身體很不好,師母身體也不好。前不久張帆代表歷史系去看望祝先生,我看到照片,感覺很蒼老,跟我記憶中能量無限的,騎著自行車風風火火的,在未名湖邊不停跑步的,每天拉單杠的祝先生,那個記憶完全不同了。他現在真是老人了。
我認識祝先生比認識田先生的時間要長得多,因為我本科就上他的課——本科時中文系、圖書館系和歷史系的通史課是一起上的,他給我們上通史。我是因為他才進北大歷史系讀研究生的,因為我不認識別的歷史系老師——當然祝先生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他。所以我就給他寫了一封信,問您招什么(方向的)研究生。他說我招魏晉南北朝。那我就考魏晉南北朝。

祝先生在回信的時候說,我呢,是跟田余慶先生一起招生。我當時還想,田余慶什么人呢?這個名字肯定在哪見過,在報紙上、在雜志上看到過,但沒有任何印象,也沒有讀過他任何東西。入學之后才讀他的文章,那時候《東晉門閥政治》也出來了,就讀(他的)書讀文章,才了解他。當然田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不用說了。在我一生當中,我接觸最密切最多的、情感和思想上聯系最深的人,應該就是田先生了。我現在五十多歲了,我一生主要的時間在北大,我在北大期間主要是跟田先生在一起。而田先生也不僅僅把我當學生對待,我也不把他只當一個老師對待,所以,無論是在學業上、個人感情上、個人生活上,(田先生)對我都是最重要的一個人。
每個人讀書都是希望學老師的,像我從讀碩士開始,崇拜田先生,我的碩士論文簡直就是模仿田先生那一套來寫的。但是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你很早就會意識到,自己學不到(田先生)那一套東西。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治學風格。田先生常說“泥我者死”,機械地學是學不好的。事實上,我們這么多學生跟著田先生,都崇拜他,都想學習他,但沒有一個學得比較像。我也學不像。這一點,我早就意識到了。所以,老早就放棄了,就做自己能做的一點事情。這點田先生也是贊成的,他覺得不能機械地模仿別人,不然會失去自己的風格。當然,一個人很難形成自己的風格——即使沒有風格,也不需要去模仿別人。
我覺得,田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另外一些方面的,不是直接(反映在)學術上、寫作上、讀文獻上的,這些當然都是應該跟著老師學習,但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方面——比如說,對待學術的態度,對待人生的態度,在對人生和學術關系的處理上,這些方面(田先生)對我影響是最大的。在我認識田先生之后,我少年的那些想法都拋棄了。我猜想,如果沒有碰到田先生,我的人生會非常不同——我不敢說更好或更糟,但肯定會非常不同。因為,看著他,會覺得這樣的人生就是美好的,就應該過這樣的人生,就是做一個學者,不必做任何別的事情,不求別的東西。有所為,有所不為。我覺得挺美好的,至少挺適合我的最基本的價值觀。所以我心甘情愿過這樣的人生。

澎湃新聞:您當初為什么選擇北族名號這個專題進行研究?這里面涉及比較語言學這個很難啃的骨頭(當然這只是中古史研究的困難之一)。
羅新:我最早寫這類文章的時候,國外有些專家就跟我說:這些問題都是幾十年來人們拒絕再討論的,因為討論這些問題很危險,差不多都是在胡思亂想。但是,我是出于兩個原因走上這條路:第一,這些都是五六十年前學者們的工作,但五六十年來都不做了,不做自然有學術內部的道理,學科自身的邏輯,這個我們今天都能理解。我們當然反對名詞解釋那樣的研究,又是語言,又是歷史,東扯西拉寫一篇文章。但是呢,這是一大片應該開墾卻沒有開墾的荒原,特別是中古史料里有大量這方面的材料,契丹以后、元以后通過語言的比勘,用科學的方法去還原,是做得到的。但是在唐以前,相當部分會是眾說紛紜,如果有十個人研究,可能會有五六種、七八種說法,甚至各有一種說法,莫衷一是。在百十種說法的基礎上,又增添一種說法,有什么意義呢?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片應該利用的資源,不能因為前人的教訓就不敢觸碰它,就不敢用它。中古史資料那么少,而現有材料中有這么一個礦藏不開發,實在說不過去。這是第一個原因,使得我不舍得不去動它。
第二個原因,如果我想離開傳統的以中原史為中心的視角,換一種視角看那個時代的歷史,就必須處理這些材料,我的博士論文寫十六國,寫得很失敗,畢業之后好多年我一直在反省。田先生也認為我的博士論文寫得不好,他覺得我的碩士論文做得很好,那個路子他能接受,是因為跟著他那個路子走的,他的意思是我應該做點別的研究。這樣,就有點做不下去了。我就是有點不服,想了好多年,在去哈佛燕京之前跟張廣達先生聊過,張先生對我起了很大作用,他說這些問題應該做,但你的做法不對,因為你的做法,幾百年來傳統中國學者都是這樣做的,清代學者也是這樣看問題的,他們讀的書比你多,他們積累的材料比你豐富,還是照原來的方式,你超不過他們,說不出更多的話來。這一說對我觸動很大。的確如此,錢大昕都這么做了,我還能怎么做呢?你想比他們了解更多,就得具備和他們不一樣的能力和視野。這個視野,就應該是現代學術的視野。
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暫時放下了中古史,開始讀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比如中亞的研究啊、蒙古啊,讀突厥以下的東西。這對我觸動很大。我發現因為語言資料的寬闊,一下子視野就變了。這一變,你對北方的感受是不同的,你會發現傳統學者對這個是隔膜的,他們很信賴中文史料里的說法,你只要站在另一角度,就會深刻地懷疑這些說法。而且你一懷疑,背后的漏洞就非常清晰地呈現出來了。這個時候,我就覺得應該學習語言。雖然我們不知道鮮卑是什么語言,但我們知道古代阿爾泰語的基本規則,而突厥時代跟鮮卑時代有很強的繼承性。比如說在名號方面就有強烈的繼承性,突厥人把那一套東西都拿來用。而且,整個阿爾泰文化的繼承性都很強。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后,突然發現這個字原來是這個意思,這樣一來就做了不少工作。我和傳統的以語言來研究歷史的學者不同,我是這個時代的學者,具備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知識和追求,就是說,我的目的不是簡單地還原語言,我其實不在乎這個東西,而是希望借此恢復歷史面貌,發掘史料背后的政治構造和文化特征。即使我的一些具體解釋是錯誤的或不可靠的,或者說是永遠無法證實的,但沒有關系,我模模糊糊意識到那背后的道理,而那個道理是非常靠得住的,或者說,是有啟發的。這一點,使得我愿意做下去,但也沒有做多少年,因為我漸漸意識到這背后的關懷是有限的。如果只做技術性的工作,做多了也煩,我關懷的其實是(語言、名詞)后面的東西。后來我覺得可以跳出語言了,就做了《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一類的東西。

羅新:我們翻譯的那些論文都是歷史方面的,而丹尼斯·塞諾的厲害在語言方面。我們沒有選語言方面的論文,是擔心翻譯難度太大。當然接觸丹尼斯·塞諾本人,看他別的東西,對我影響很大。不過,那時候我在這條路上走得挺遠了,有點兒回不了頭了。
阿爾泰學主要是關注語言的,當然也會涉及廣義的文化,甚至政治,也會討論歷史問題,但國際上的主要參與者主要是做語言研究的,可以說是一門以語言學為中心的學問。我沒有資格去討論阿爾泰學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借鑒這些研究成果。就這一部分來說,我們還是做得很不夠。內亞研究跟阿爾泰學這兩個概念所指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好像阿爾泰學是更早的東西,是東方研究、東方學的一部分,內亞研究是現代學術的一部分。就像漢學和中國研究的關系,說它重合,確實是大重合,內亞研究本身不包含學科規范、方法,可是阿爾泰學是包含這些內容的,它的門檻很高。
澎湃新聞:國內有哪些學者涉足這個領域呢?
羅新:國內還是有挺多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不過主要是做突厥以后的,我們還有國際頂級專家,比如做蒙古的,過去有亦鄰真先生,現在有烏蘭、烏云畢力格等,在突厥學領域我們過去有耿世民先生,都是成就卓越、在國際上很有地位的學者,很了不起的。但是,用阿爾泰學的積累、規范與方法做唐代之前的研究的,好像還沒有。所以,我做這個研究,有點孤掌難鳴,沒有人說你好,也沒有人說你壞,確實是一個糟糕的事。大概是因為熟悉阿爾泰學的人對中古史不太了解,而熟悉魏晉南北朝史的人對阿爾泰學的方法也挺隔膜。希望今后會有較多年輕人勇敢面對。

羅新:我是參加過走馬樓吳簡早期的整理工作,這方面的論文寫得不多,大概有三四篇吧。做魏晉南北朝研究的人,學科上最大的焦慮就是史料太少了,可以說,魏晉南北朝史料你在讀研究生期間可以全部讀完。當然不是說讀完了就可以不再讀了,吃透它當然需要一輩子。在這種情況下,就有所謂拓寬史料的說法。要拓寬史料,出土史料是最重要的。在這方面我做的工作比較多,名號研究是一種,同時我也做墓志,還有就是當時出現了吳簡,我也很積極地參與了。當然簡牘整理的技術性很強,但是對于努力的學者來說這個困難還是能克服。而更重要的是看自己能不能利用這些史料。對我來說,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在這方面能力不夠。怎么說呢?我感覺我對吳簡的材料很隔膜——材料本身我很熟啊,因為是我參與整理的,可是要我把這些材料寫成文章,我不大會寫。當然我那時候也是把精力放在北方這些研究了。這樣,就很快主動放棄了。
澎湃新聞:讀這些材料,應該會刺激您閱讀文獻材料。
羅新:那當然。絕對的。因為很多文獻你根本就不讀,或者讀了根本視而不見。比如說,竹簡里面常見“屯田司馬”,這是我自己整理的,老遇到“屯田司馬”。很久以后讀《三國志》才發現曹魏那邊有這么一個規定,就是說,屯田民都帶有一定的依附性,就是半奴隸身份的人,罪犯或俘虜,曹魏把這種人每五百人設一屯,屯長官是司馬。當年做吳簡的時候沒有意識到,有可能孫吳學了曹魏的制度,就有了同樣類型的“屯田司馬”。也許長沙郡下的臨湘侯國規模不大,設一個屯就可以了。當然我沒寫過任何文章,也沒看到別人提這個事。我讀書的時候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哦,原來是這樣。所以,當你讀了出土的文獻,再去讀正史文獻,過去可能不注意,現在明白了。
澎湃新聞:迄今為止您自己比較滿意的論文有哪幾篇?
羅新:沒有特別滿意的。如果說寫得比較有意義的,文章本身寫得并不好,但是文章寫了之后對我后來的研究,對我后來的學術發展有意義的,大概有兩三篇這樣的文章。
一篇是《可汗號之性質》,通過討論可汗號,我突然明白了名號內部的結構是什么,而且對我來說是一個發現,因為過去沒有人這樣討論。我把名號區分成兩個部分,它們各有功能。而且我意識到這是一個通例,在任何級別的政治領導名號身上都有類似的結構。這個功能與結構的突破,使我后來所有這方面的研究成為可能。
另一篇是《王化與山險》,也是由一對概念所結構起來的,把它簡化為“王化與山險”這樣相對立的一對觀念之后,我就明白了,對于南方土著人群,一個大型帝國是怎樣采取政策的,以及這個歷史進程經過怎樣的階段性發展。如果回過頭來重寫,會寫得好得多,但當時寫得很草率,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后來想明白了,已經來不及了,前面寫了一大堆廢話了,但也舍不得扔。寫完之后的收獲,要比論文本身的收獲大。
其他的(論文),就沒有這種理論性的、方法論的意義。

羅新: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并不是往復,而是天涯上有一個關天茶舍,那是我創辦的。
往復最大的收獲,是陸揚老師的加入。我們這些人說的話,即使不算壞,對大家都不那么陌生,只有陸揚的參與,他說的話,他帶來的信息,他帶來的想法,是當年的中國學術界很陌生的,所以他的意義非常大。2000年左右的中國學者,對海外學界的了解,和現在相比,不是一回事。現在陸揚說個什么,大家可能也聽說過,但那個時候陸揚說的話,都是新鮮的,都沒見過。云中君的出現,是網絡學術生態的一個新現象。如果說往復(對中國學術)有貢獻,這就是一個貢獻。
因為我本家姓冷,我父親本來姓冷,但我奶奶帶著我父親嫁到羅家,這樣我們家都姓羅了。這個在傳統社會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傳統社會根本沒有所謂純正的姓氏。姓氏的文化意義要遠遠高于姓氏的血緣意義。認同反映的是文化意義。誰養我,我就姓什么,對不對?
澎湃新聞:您是個電影謎,一年大概要看多少電影?最喜歡哪種類型的片子?電影對您的史學研究有何影響?
羅新:我過去狂追電影和美劇。時間合適的話,我能沒完沒了地看。
我年輕時是愛文學的,也曾想當作家,更多的是看小說。但看小說需要時間,看電影,像看美劇一樣,比較省事。所以,看電影可以說是一種偷懶,你進入虛擬世界,它迅速就結束了,兩個小時之內就結束了。不像看小說,需要一周,甚至更長時間。真正看小說的收獲比看電影的收獲會大得多。
我經常在想歷史和虛構文學有什么不同。也許我們寫的歷史跟那些文學作品沒什么大的不同,只是游戲規則不一樣,歷史學要遵照一套自己的學理、研究和寫作規范。歷史和文學最大的不同是,文學從構想開始,就是有主人公的,有中心思想、故事主線,而歷史沒有,歷史哪有什么主人公啊,只有寫出來以后才有主人公,比如你把偉大領袖寫出來,他才是主人公,但是在他那個時代,主人公隨時都在死啊,隨時都有新的主人公出現。真正意義的歷史是沒有主人公的,是一團混沌,沒有主線,也沒有故事,——故事是寫作的時候,被歷史學家特意找出來的,圍繞一個主人公寫出來,放在有限的時空里講述。但是這樣做就抹殺了很多別的主人公,抹殺了很多別的主線。我覺得,對歷史學的這個敘事特征進行反思,可能對我們認識歷史有意義。我們自己的研究和寫作,我們會覺得我很重要,其實對歷史來說,只不過是萬萬千千的線索之一,你把這個線索單獨拿出來的時候,強調它的時候,意味著抹掉了很多其他的線索,而其他的線索也都是真實的東西,你抹掉了他們,是因為你認為他們在你的研究中不重要,當然也可能是你對他們認識的不夠多。對歷史研究者來說,要經常這樣想,經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別把你寫的東西看得多么神圣、多么重要、多么不可動搖。
澎湃新聞:您無疑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很好奇,您從大都到上都的路上還帶著什么書?
羅新:如果從背包客的角度說,不帶帳篷,不帶睡袋,不帶吃的、喝的,所以帶的東西不多。十來公斤,不到十五公斤。不重。露營的人,一般都得帶二十公斤以上。十五到二十公斤是一個跳躍,到二十公斤就很難受,走一步都很難受。十五公斤以下,多一點、少一點,差別不大。背負增重到近二十公斤,我去年經歷過,每一步都不是好惹的。我走之前,請社科院歷史所的羅瑋,他是張帆的學生,我請他幫我準備了相關史料的電子版,當然我還帶了幾本閑書,因為我還是喜歡看紙本。其實后來看不了。前一個禮拜還能看,后一個禮拜就看不動了。

羅新: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是把草原官號和古代華夏制度聯系起來討論。我那時候受了人類學的影響,在幾篇文章里都暴露出這一點,不愿意只說北方是這樣的,非常想說我做的這個研究具有一般性,也可以用來反觀其他文化,包括華夏早期文化。我那時候有一種這樣的觀念,后來我放棄了——認為北方的發展只不過是反映了華夏早期發展的一個階段,如果讓北方的政治繼續成熟發展,將來它會走到南邊的華夏這條路上來。這種預設,很可能是受到普遍歷史觀的影響,我們這代人都受這種歷史觀的影響,就是進步史觀那套東西。雖然嘴上不說,但始終想把北方和華夏搭上,碰到謚號這個東西,覺得好奇怪,生前有謚號,為什么改為身后有謚號。我想對這個問題給一個解釋,對這個解釋,有人說很有啟發,有的人沒有感覺。時間長了,我也想不清自己是怎么想的了。后來我就沉迷在名號的功能分析上了,不太敢跟華夏搭邊了。除了《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這篇文章,我后來再也不敢把北族名號和華夏傳統扯在一起,因為我覺得這種解釋還是很冒險。當然做先秦的人也不從這個角度想問題,所以有的人可能會覺得有啟發。
澎湃新聞:在史料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您對史籍中有關南匈奴的零星記載作出了獨到的解釋。在《匈奴單于號研究》一文中,您認為:“南匈奴歷任單于的單于號,都是死后獲得的。”這“是匈奴單于號傳統的重大改變,推動這一變化的力量,一定來自東漢王朝”。但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直接證據,我對這個論斷仍不免有所懷疑,畢竟內亞草原民族的名號傳統根深蒂固。我想請教的是,這篇論文發表之后已有十幾年,您是否有更多證據(包括旁證)進一步證明您的觀點。或者,您是否改變了原先的觀點?
羅新:這個就是普遍歷史觀的影響,既然到了中國文化環境下,匈奴慢慢就接觸漢朝文化這一套,所以匈奴名號就從生前變成死后獲得的了。如果能說明這一點,我當時所信奉的那一套歷史觀就起作用了,中國制度、中國文化這套東西就不是中國獨有的了,而是在某個社會、某個政治發展階段必然經歷的,是普遍的。北方之所以沒有,是因為還沒有達到這個歷史階段。后來這套我就不提了,我感覺這背后的預設可能是錯誤的,或者是有問題的。
相關材料就這么幾句,后來也沒有新的出土材料。別人要反駁也很難,因為沒有更多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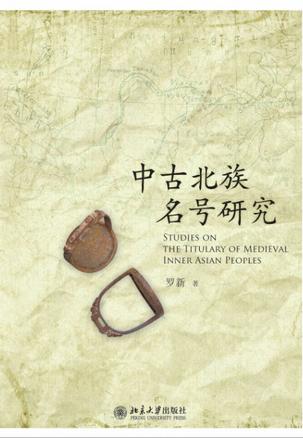
羅新:我當時推測賜名幾百個人,應該是有一個機構的,有一個賜名的班子,這個班子是秘密的。里面的成員級別可能不高,都是一些文人,讓他們弄清楚,然后以皇帝的名義去頒布。
我的一個學生寫論文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賜名是不是被受賜者家庭接受,接受程度如何,使用范圍如何,這還是不一定的。有些人家里可能沒有行用賜名,當然在正始場合是用的。近年所出的“元萇墓志”,元昶不見于史。萇不像是賜名,萇就是長,長命、長安,都可以換用萇這個字。元萇的萇,可能是長命一名的縮略。那時候“長命”是一個常見的名字,這個名字作為一個漢語詞早就連音帶義進入代北鮮卑語了,所以代北集團的人取長命做名字并不奇怪。書寫時按照漢語書寫習慣,簡寫為元萇。按照元萇墓志,知道他官居高位,是個重要人物,但正史里卻看不見。我的學生潘敦在他的碩士論文里考證,原來這個元萇就是《魏書》里的元儼。正史記他的賜名,家里安葬他時還是用他的本名,兩不相干。這樣,我們就知道,賜名不一定為家人所遵用。
澎湃新聞:您在《從可汗號到皇帝尊號》一文中提出,唐代的皇帝尊號制度根本上淵源于內亞民族的政治文化傳統,而武則天恰好借此自封“天后”,而后臨朝稱制。我的問題是,可汗號傳統誘發了皇帝加尊號,并且形成一套制度,但皇帝尊號本身(所謂“允文允武,乃圣乃神”)是否包含了宗教因素,比如說武則天的尊號是否有佛教的因素?
羅新:武則天的尊號里面帶有佛教的內容,有的可能帶有道教的內容,更不用說到了元代,那里面有太多宗教的內容。稱號就是美名嘛,才不分什么道教佛教,只要覺得是好東西,都可以拿來用。
澎湃新聞:唐太宗時期完成了《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的修纂,高宗時期完成了《南史》和《北史》,有學者指出初期的唐朝政權是個具有異常高度歷史意識的政權。今人研究南北朝史,必然要利用唐初編纂的這些歷史文獻,您覺得這里面有什么陷阱或值得時刻警惕的地方?
羅新:步步陷阱。但這幾乎是唯一的材料。除了現在出土的一些墓志,文學有些詩文,幾乎沒有別的。南北朝時代的文獻喪失,太嚴重了。
所以歷史觀很重要,得建立一套批判的歷史觀。你有了自己的問題,不要被這些材料迷惑住。學會從材料中讀出材料背后的意圖。我們的老師,周(一良)先生、田先生,最喜歡說的一個詞叫“讀書得間”,就是在字里行間去找背后的意思,我記得我做學生的時候,老師經常說這個詞。現在人們說的少了。那時候見面就說,要讀書得間、讀書得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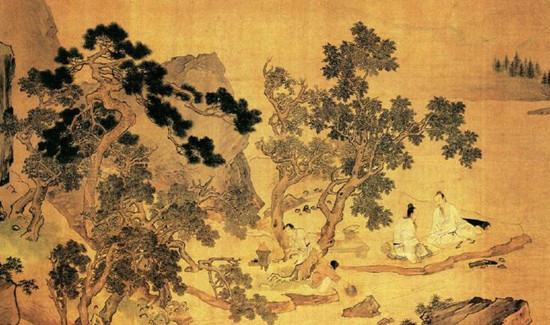
羅新:我們任何時候都在說某些時期變動特別大,當然有可能,但我們不能忘記一點,歷史本身一直在變動的。所有重大的變動都是前面的小變化積累的結果。有時候我們只注意到那個重大變化發生的瞬間,比如只注意到辛亥革命的那一場暴動,可能沒有注意到將近一百年來各方面的條件在往這方面指引。如果只注意到那場暴動,那是嚴重不夠的。拿魏晉南北朝來說,至少有些變化在東漢的時候就開始了,不能只看到五胡十六國、北朝發生的動蕩。歸根結底,歷史是寫出來的,發生的歷史跟寫出來的歷史不一樣。剛才說過,歷史沒有主人公,沒有線索。但是,寫出來的東西都有線索,都有主人公,都有“問題”——歷史自身是沒有“問題”的。我想說的是,歷史上是否發生了重大變化,是歷史學家的說法問題。他說這些的時候,是要表達某個目的。我們要注意他想說什么,想表達什么。
古代歷史的特點是只記載重大的政治變動,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事件和人物,就寫得很多,我們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熟悉的人物,應該超過兩漢。我們大概只記得漢高祖時代、漢武帝時代、兩漢之際、東漢末的人物和事件,東漢中期一百多年的歷史,就不大管了。就此而言,做魏晉南北朝史的學者是幸運的,因為這些政治變動都記錄下來了。但是,這也容易造成錯覺,你會覺得這個時候的歷史變化特別多,其實這些都是政治上的變動。很多重大的文化上的變動,如果不是因為有考古發掘和其他傳世材料,我們幾乎看不到。比如佛教,如果不是因為有石窟,有大量的造像碑,我們不知道那個時候最大的變化可能是文化上的,民眾生活、社會形態的變化,可能出現了新的結社方式,人們有了新的交往方式,女性因為宗教而獲得了一定的解放,她們有了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價值空間,是過去所沒有的。而史料在乎的是誰和誰打了戰,誰贏了,并不關注更重大的變化其實是發生在另外一些方面。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日本的北族史、內亞史研究有什么值得中國學界關注的地方?
羅新:我覺得日本學術挺有意思的,一方面日本學者跟西方學界關系非常緊密,另一方面它自有傳統,它自己的研究傳統非常深厚,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問題、方法、資料整理等方面,它自有傳統,甚至有一些東西比西方要強得多,比方說他們的蒙古研究和滿文研究,特別是滿文研究,是世界上最好的,獨一無二的好。就這一點來說,姚大力老師開過一個玩笑,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這個玩笑當真,他說,你用滿文材料,不需要懂英文,不需要懂滿文,只需要懂日文就可以了,因為日本學者整理得很好,很可靠。
當然他們的傳統也在變動發展中,比如早先比較重視與中國對立的游牧世界,把這個叫作樸素主義、文明主義,相當于羅馬文明世界與蠻族世界的對立,這是一種研究方法;但是,現在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不再把蠻族世界、游牧世界看成是跟中國歷史相對立而存在的,他們是跟中國歷史發生了關系,但更大程度上它們是自我存在的,而它們的自我存在是跟后面更大的內亞世界、甚至歐亞世界相聯系,我覺得這是學術的新發展,不是什么分裂中國的政治陰謀。這個發展值得關注,因為阿爾泰語言和芬烏語言在空間上的確是連續分布的,因此它是一個廣大的世界,過去我們只注意到中國周邊,只注意蒙古高原,以為已經看得夠遠了。日本學者是一直往西,看到烏拉爾以西,一直到波羅的海,這樣一個廣大的世界。我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所以他們再也不把內亞史看成是東洋史的一部分了。這在學理上有它的道理。
澎湃新聞:您在《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前言中指出,一切歷史視野中的所謂民族都是政治體,另外還提到文化體的概念。那么,文化體和政治體之間是否會有矛盾和沖突?如果有,一般會有怎樣的措施予以調解?
羅新:我覺得文化體和政治體是不同層面的問題,我們對某種結構進行描述的時候,因為觀察的東西不一樣,就有不同的區分。政治體(這個概念)強調的是用政治關系塑造出來的,文化體強調的是用文化關系塑造出來的,或者說是通過文化聯系起來的。比如說,漢字文化可以構成一個文化體,包括整個東亞,甚至越南,但它從來不是一個政治體,相對來說文化體的連續性比較強,空間比較大,而政治體的連續性很不強,可能幾十年就換一個王朝,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上時有發生。所以,政治體、文化體當然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危險的是,政治體比較喜歡把自己描述成文化體。過去我們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對兩者不加區分。當我們討論一個王朝的時候,我們就以為這個王朝代表了某種文化,其實它只是這個文化中的一部分,它有政治邊界,它想把邊界之外的說成跟它在文化上也沒關系,甚至是敵對關系,而事實是,那個是它所屬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它不能在政治上征服人家,納入到自己的體系里邊,就把人家推出去。另一方面,有的政治體無視別的政治體,人家明明是一個政治體,但你總是聲稱那是你的一部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至少我的研究傾向是,我們始終要重視政治體,因為政治體有不同的利益,雖然文化體、社會體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政治體有它特別的利益,它的利益是王朝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只有明白它的利益,才能理解它的政策、手段和統治方式。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