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消除知識缺陷?公眾如何參與科學傳播
編者按:長期以來,科學知識的大眾傳播一直面臨著諸多局限。除去知識本身的復雜性外,科學界所青睞的“知識缺陷”模式,即將公眾視作知識匱乏的群體、認為公眾應該成為科學知識的被動接受者,也導致了傳播上的不對稱關系。單向的、自上而下的傳播,以及缺少問責的制度使得公眾對于科學界產生了不信任。本文作者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哲學教授卡塔琳娜·迪蒂爾·諾瓦斯(Catarina Dutilh Novaes)與都柏林大學學院的哲學助教西爾維婭·伊萬尼(Silvia Ivani)指出,在遏制錯誤信息傳播、消除反科學環境外,我們更應該鼓勵公眾以不同方式參與科學政策的制定,建立雙向的回應、參與和問責制度。本文原載于《波士頓評論》,中譯略有刪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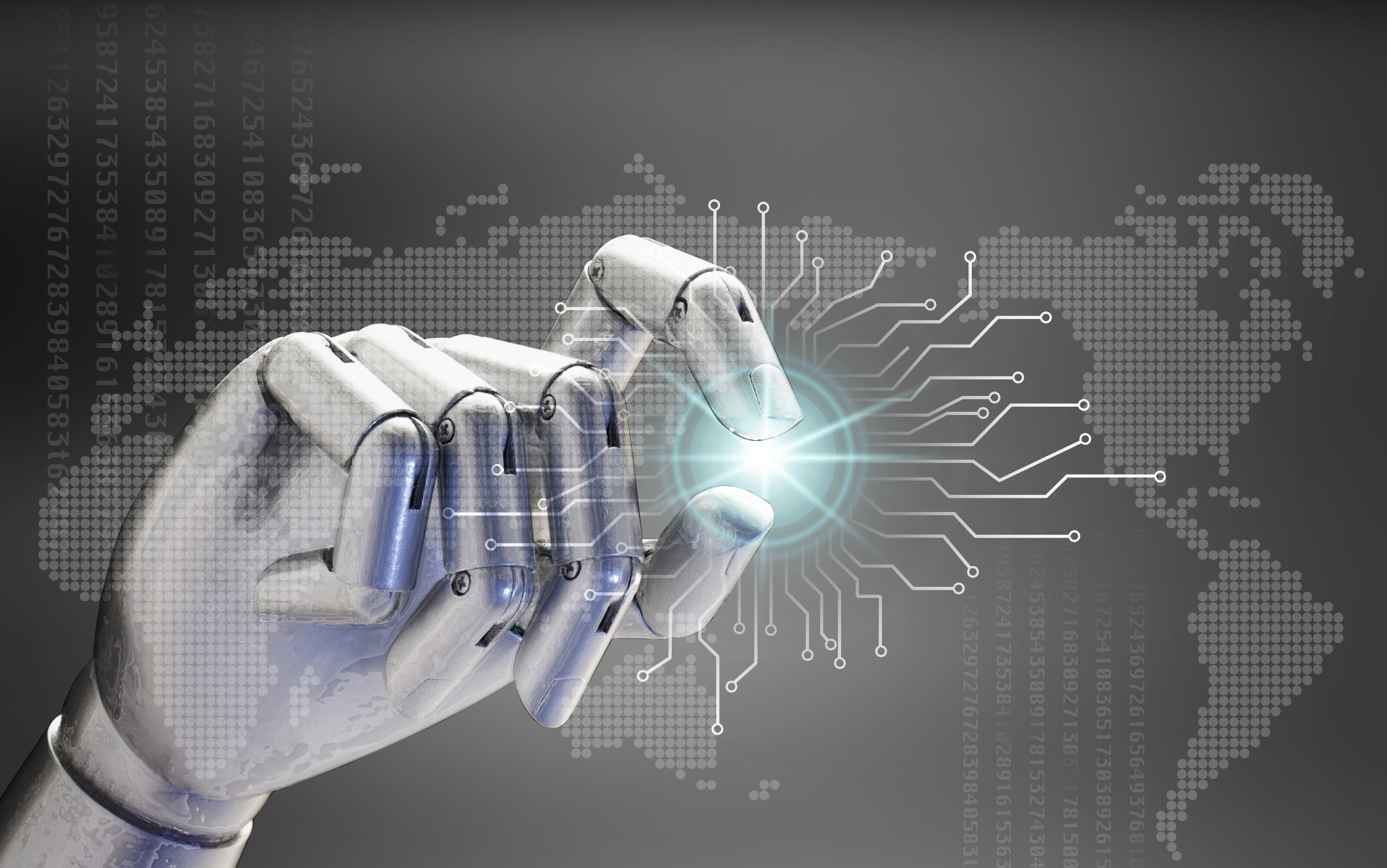
1985年,世界上最古老、最杰出的科學機構之一的英國皇家學會提出了以下問題:“如果公眾能更多地了解科學的范圍和局限,了解科學的發現和方法,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嗎?甚至會變得不同嗎?”由遺傳學家沃爾特·博德默爵士(Sir Walter Bodmer)擔任主席的委員會對此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是的,一個具有科學素養的公眾將使世界變得更美好,能夠促進公共決策,并提高國家的繁榮程度。
在40年后,這一觀點依舊非常流行,專家之外的群體也非常接受這一觀念。普遍的觀點認為,公眾對科學知之甚少:他們不僅對科學事實知之甚少,而且對科學方法論,即進行科學研究的獨特方式也一無所知。公眾的無知被認為是普遍的反科學態度的主要來源,產生了對科學家、科學創新和據說是“遵循科學”的公共政策的恐懼和懷疑。從反對轉基因食品到歐美的反疫苗運動,這種態度帶來的后果簡直隨處可見。
這種“科學與社會關系存在某種具有影響力的聯系”的概念促成了科學傳播的“知識缺陷模式”(knowledge deficit model)。該模型假定科學家和公眾之間存在一種不對稱的關系:非科學家被視為科學知識的被動接受者,他們應根據科學專家的安排,或多或少且不加批判地接受科學知識。正如科學傳播學者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指出的那樣,“這種模式采用了一種單向的、自上而下的交流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擁有所有必需的信息的科學家們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填補了‘對科學一無所知的’普通大眾的知識真空。”
從這個角度看來,公眾對科學的支持問題有一個明確的解決方案:我們需要更好、更廣泛的科學教育。教育和知識機構必須更好地教授科學,而科學家則需要更好地向公眾傳播他們的發現,以及他們得出這些發現的方法。簡而言之,挑戰在于提高大眾的知識和推理能力。一旦公民對科學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能更好地進行推理,強大的公眾支持就會隨之而來。有了大眾共識的支持,科學進步就能免受非理性或無知的攻擊,同時更自由地為社會帶來益處。
最終,這些觀點都是關于社會世界的經驗論斷;因此,它們的有效性可以被檢驗。而事實上,在過去20年中,證據證明“缺陷模式”表現不佳。首先,這種方法根本沒有帶來“公眾能夠廣泛支持和接受科學”的預期結果。盡管學界在科學教育和傳播方面做出了集中努力,但在美國和英國,針對公眾對科學的理解和態度的定期調查表明,多年來公眾的科學素養幾乎沒有變化。特別是在歐美反對疫苗方面,以提供科學證據來駁斥疫苗接種謬論為基礎的干預措施基本上已被證明無效。
鑒于其自上而下的、技術官僚式的科學傳播觀,缺陷模式也被批評與平等、自治和參與等民主價值觀相距甚遠。一些人認為,既然公民作為納稅人為研究和創新提供資金,他們就應該對這些資源的管理和使用有發言權。此外,由于在科學背景下做出的決定可能對社會產生深刻、具有破壞性,甚至具有差異化的影響,公民應該有機會就研究和創新是否會(以及將如何)擾亂他們的生活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偏好。
鑒于缺陷模式的明顯失敗,在過去20年里,各種科學傳播的替代方法紛紛涌現,其靈感來自于解決反科學情緒需要改造我們的科學和政治機構。根據缺陷模式的觀念,科學機構不需要進行轉型;關鍵是要通過教育和交流贏得無能的公眾的支持。相比之下,這些替代方法認為,科學研究和創新應該更加貼近社會——放棄單向的指導,建立雙向的回應、參與和問責制度。
這些報告主張,除了培養科學素養這一狹隘的目標外,我們也應該著眼于促進科學家和公民之間的合作這一更廣泛的目標(同時我們也在努力改善科學教育)。他們呼吁從鼓勵公眾理解科學轉向促進公眾參與科學。他們認為公眾不是無知的源泉,也不是科學啟蒙的被動接受者,而是“當地知識”的蓄水池,他們具有源于個人經驗的專業知識。此外,他們的洞察力足以且應該為科學實踐提供信息。
當代學術界中的一些流派強調了從關注科學教育,到聚焦研究人員和公民之間互惠的權力分享、合作和交流可能帶來的好處。一些學者,例如哲學家希瑟·道格拉斯(Heather Douglas),主張科學的民主化。由于許多科學決策對社會有重大影響,因此它們不應該僅僅由少數精英決定,無論他們多么訓練有素或知識淵博;相反,它們應該讓所有受影響的人都有機會參與(盡管方式不同)這一進程,并接受其結果。此外,正如哲學家皮爾路易吉·巴羅塔(Pierluigi Barrotta)和埃莉奧諾拉·蒙圖斯基(Eleonora Montuschi)所主張的,科學本身應該對社會作出回應:采用一種協同的方法,允許不同的人用他們不同的經驗和當地知識做出貢獻,讓提出和解決新的重要研究問題、收集相關數據和獲得新知識成為可能。科學技術研究學者希拉·賈薩諾夫(Sheila Jasanoff)則建議采用“謙遜的技術”來加強公民參與,在問責制方面改善科學治理。
另一些人強調,社區參與具有舉足輕重的實際意義。與公眾的接觸甚至可能被視為科學家無法逃避的道德義務。正如科學史學家娜奧米·奧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在提到氣候變化時表示得那樣,科學家“負有哨兵的責任,要讓社會警惕普通人無從知曉的威脅”。為了更好地理解社會所面臨的挑戰,以及發展能夠意識到這些挑戰研究,從而為社會需求服務,科學家必須與社會不同階層接觸并讓他們參與進來。
將這些想法付諸實踐的框架是“地平線2020”(Horizon 2020),這是歐盟在2014年至2020年間成立的研究和創新資助計劃,該計劃管理著近800億歐元的預算。“地平線2020”采用了“負責任的研究和創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下稱RRI)”的政策框架,該框架“要求所有社會行為體(包括研究人員、公民、決策者、企業、第三方組織等)在整個研究和創新過程中共同合作” 。在這個方案中,科學應該與社會合作,為社會服務;研究和創新應該是科學家和公民共同努力的產物,應該為社會利益服務。為了推進這一目標,“地平線2020 ”鼓勵采用對話式參與做法:即在科學過程的各個階段(包括在科學項目的設計和研究重點的規劃中)建立專家和公民之間的雙向交流。
那么,進步是否已經到來?我們有理由懷疑這些努力是否代表了科學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積極轉變。首先,“地平線2020”的繼任者“歐洲地平線”最初被批評將RRI框架擱置在一邊。此外,大量證據表明,缺陷模式在科學界和政策制定界依舊根深蒂固。例如,莫莉·西米斯(Molly Simis)及其同事在最近一篇題為《理性的誘惑》(The Lure of Rationality)的論文中認為,科學界的很大一部分人仍然傾向于將公眾視為“不懂科學的”,而且“將公眾視為不屬于科學界的‘其他’實體”。杰克·斯蒂爾戈(Jack Stilgoe)和他的同事們同樣感嘆,公眾參與的范式已經變成了一種“程序性”的策略,目的是“為預先確定的方法贏得信任”,而保證現有的權力結構不受動搖。綜上所述,這項研究表明,公眾參與敘事的作用更多地是“修辭”,而非現實。
許多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釋缺陷模式為何持續存在。一是知識確實存在缺陷,然而是科學家方面存在知識缺陷。科學家很少學習科學傳播,通常很少或沒有接受過關于如何成為優秀傳播者的正式培訓。因此,他們并不了解個人如何形成對科學問題的意見,無法支持、設計、計劃和實施超越科學教育的科學傳播戰略。博德默報告(The Bodmer report)強調了為科學家,而不僅僅是為記者或指定的科學傳播者提供此類培訓的重要性。
缺陷模式持續存在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它特別有吸引力。它為反科學態度提供了一個相對簡單的解釋,并提出了一個相對簡單的解決方案。至少,它對科學界和政治機構本身的要求相對較低。斯坦福大學的報告《錯誤信息時代的科學教育》(Science Education in an Age of Misinformation)展示了如何促進人們更好地理解科學,以此作為對抗科學錯誤信息的方式。這是一個善意,但可以說是較為受限的方法。
除去該現象背后的原因,缺陷模式的持續存在同樣令人擔憂,因為它過度承諾了科學教育和單向科學傳播所能實現的目標。我們目前面臨的最緊迫的兩大危機:疫情的大流行和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都需要大規模的社會協調和廣泛的公眾認同。我們需要了解和遵守適當的公共衛生措施,如接種疫苗和戴口罩。我們還需要更加可持續的個人選擇和對政府機構施加政治壓力,以大幅減少碳排放。
因此,當務之急是找到可行的方法來替代科學傳播的缺陷模式,并加以實施。這項工作不僅僅是關注認識論層面,即公眾對科學的了解以及科學如何運作,而是需要更直接地思考對科學和政府機構的信任的性質和來源。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討論的那樣,這種“信任缺陷”主要不是由認知上的擔憂引發的(比如,公眾認為科學家的無能)。相反,公眾的不信任往往是由對虛假利益的擔憂引起的,例如認為金錢或政治動機會損害科學知識主張的可靠性或合法性。
哲學家瑪雅·戈登伯格(Maya Goldenberg)在新書《西方的疫苗猶豫:公眾信任、專業知識和科學戰爭》中探討了包括西方反疫苗浪潮在內的諸多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對疫苗的懷疑確實可能是由基本的誤解引起的。但正如戈登伯格指出的那樣,歐美對于疫苗的猶豫可能是對醫療和科學機構不信任的標志,而非誤解或科學知識和專業知識戰爭的結果。她指出了造成合理猶豫的兩個主要因素:科學或醫學種族主義的遺留問題,以及生物醫學科學的商業化。事實上,多項研究表明,歷史上的醫療虐待:包括未經同意的醫學實驗和將某些群體排除在臨床試驗之外,這些歷史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一些群體仍然對科學干預深表懷疑。簡而言之,雖然部分公眾可能會認可科學專家的能力(在某一科學領域擁有適當水平的知識和技能),但他們同時可能會懷疑科學家的善良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來自科學權威機構的單向溝通可能不足以恢復公眾的信任,即使它極力試圖證明為什么某個特定的科學主張并非是違法的或屬于歧視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障礙并不是不愿考慮新信息的非理性意愿。而是信息本身被認為是不可靠的,部分原因是對于某些傳遞信息的人或物的道德評估不佳。或許,要解決這些被認為是科學或醫療機構的道德過失,需要的不僅僅是技術信息的傳遞。

歸根結底,信任意味著脆弱。如果我足夠信任你,讓你的意見影響我生活中的重要決定,我就給予了你一定的權力來控制我。在這方面,衛生保健決定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而對于邊緣社區而言這種風險更加嚴重。正如哲學家凱瑟琳·霍利(Katherine Hawley)所指出的,“那些生活在舒適環境中的人更加容易信任別人,因為他們在犯錯后更容易恢復過來。”當然,不信任也會帶來風險;未能接種疫苗會顯著增加患嚴重疾病的風險。但是,從信任和脆弱性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就能闡明為什么僅僅從知識缺陷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是有誤導性的。正如米歇爾·莫爾斯(Michelle Morse)和布拉姆·威斯佩爾韋(Bram Wispelwey)醫生去年在《紐約時報》上表示的那樣,“我們沒有探究如何去應對或彌補過去的傷害,才能讓我們的機構值得信任,而是把責任推給了邊緣化的社區,分散了人們對不信任的根本來源的注意力。”
當然,詆毀傳統權威知識來源的錯誤信息運動也助長了對科學機構的不信任,尤其是在民粹主義興起的背景下。這些行為讓科學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暴露在一個敵對的、不受歡迎的環境中。歐美的疫苗政治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遏制錯誤信息的傳播和反科學話語需要的不僅僅是精心設計的科學傳播計劃,或強有力的事實核查。在政治權力斗爭的背景下,我們必須注意到科學和政治話語如何交織在一起,以及科學傳播和普及本身所能達到的目標的局限性。
最終,知識缺陷模型失敗的原因,是因為它將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和接受視為一個認知問題,認為公眾知識太少。相反,我們需要的是能夠在塑造科學與社會的關系時,尊重同等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因素的方法。我們必須培養和贏得社會對科學的信任,這一過程既取決于知識,也依賴于權力。即使在理想的情況下,關于科學事實或知識生產機制的共識再多,也無法消除我們作為一個民主社會關于應該奉行的政策產生的分歧。這是一個不可避免地影響價值觀的政治和道德問題。
為了更好地培養信任,社會和科學界究竟需要進行什么樣的制度變革,這是一個經驗問題,值得辯論和借鑒社會科學的經驗教訓。但認識到問題的本質:它既是知識的問題,也是道德和政治的問題,是找到解決方案的第一步。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