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化之都與國際城市:邊緣城市墨西哥城是如何實現(xiàn)全球化的
我究竟歸屬于何方?全球化已讓我們開始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我們的地理和文化定位。在城市里,尤其是在那些超級大都市里,這一問題就讓人更生好奇之心。換句話說,在這些大都市里,我們原先對于地方的理解變得模糊不定。它們已不是邊界分明的同質(zhì)區(qū)域,而成了一些相互聯(lián)系的空間。在這些交互的空間里,文化認(rèn)同和歸屬感的構(gòu)成則包括本土的、國家的以及跨國的物質(zhì)和文化資源。
當(dāng)人們問起我們現(xiàn)居何地之時,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也很難作答。如齊格蒙特·鮑曼所稱,“有意義的棲息地”是那些既能伸展又可以收縮的空間。我們都生活在“充滿機遇和自由選擇的棲息地”(Bauman,1992:190;Hannerz,1996:42—43)。當(dāng)然,有時我們也無法如此自由,但還能夠接收到各種各樣的信息,了解來源于諸多地域的各種藝術(shù)風(fēng)格。這些信息與風(fēng)格元素不是“棲息地”固有的,卻賦予“棲息地”多元性和靈活性。我們在自己的居住地和游走于不同城市的過程中想象并構(gòu)建著我們的歸屬地。
將歐洲、美國和拉丁美洲的城市進(jìn)行對比,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各大城市的內(nèi)在差異,以及城市的本土性、民族性和全球性之間差異的多種多樣。根據(jù)阿馬利婭·西尼奧雷利所述,美國許多城市“都已逐漸演變成了貧窮或富裕猶太人聚居區(qū),各社區(qū)相互分離,不存在依賴,卻都只要存在,便難斷與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體系的關(guān)聯(lián)”,并常由“并不一定屬于該城市的指揮總部”領(lǐng)導(dǎo)。因此,猶太人聚居區(qū)內(nèi)部合并的過程和組織機制“就慢慢地局部地區(qū)化,越來越微型化,并在其內(nèi)部只擔(dān)負(fù)單一區(qū)域的功能,由此就更加突出它的獨立和分離之特點”(Signorelli, 1996b:54—55)。理查德·森尼特指出,美國城市內(nèi)按照種族和階級分離而居的狀態(tài)以及那種總要“跟同類一起”的思維,是造成對外來人口多疑、低容忍和充滿敵意的根源,而這情況又由于美國人對于秩序感的偏執(zhí)追求而進(jìn)一步強化(Sennett,1996:101—109)。齊格蒙特·鮑曼同樣評論道:在極端同質(zhì)化的城市或社區(qū)內(nèi),要“培養(yǎng)出能夠正視人類之間的差異性和各種形勢的不確定性的品行和機智”是極其困難的,因此占主導(dǎo)地位的態(tài)度傾向是“對他者抱有恐懼之心,僅因其為他者”(Bauman,1999:64)。
在歐洲以及借鑒了歐洲模式,特別是西班牙、葡萄牙模式而形成的拉美城市中,城市發(fā)揮著推動各類移民完成現(xiàn)代化并相互融合的功能,這些移民不僅包括外國人,也包含了同一國家不同地區(qū)的外來人口。雖說存在窮人區(qū)與富人區(qū)、中心區(qū)與郊區(qū)之別,但城市依然促進(jìn)了多族群的和睦相處。這一模式具不均衡性,然而整體上并未將“本地”和“外地外國”的標(biāo)簽分得過于清楚。
在最近二十年間,巴黎、柏林、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圣保羅等城市移民數(shù)量的增長以及社會治安問題的惡化,使得人們采用街區(qū)封閉并設(shè)立各類監(jiān)控系統(tǒng)的方式加強防衛(wèi),這種土地使用方式和交互的片段性越來越像美國的分離模式。然而一體化的城市規(guī)劃仍是主流觀念,也就是說,無論是對于中產(chǎn)階級還是對于廣大民眾,大型城市是跨文化實現(xiàn)的場所。或許,“要實現(xiàn)信息傳播,并在一個足夠廣大的人群之中對不同體驗進(jìn)行比較,從而形成一個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盡管這一網(wǎng)絡(luò)對于全球性社會系統(tǒng)并不重要,大型城市是唯一可能的空間”(Signorelli,1996:55)。示威者的游行,還有工人、學(xué)生、婦女和居民的抗議,社區(qū)廣播以及跨國電視臺都是城市重大事件,它們在城市里發(fā)生,同時主要反映城市里或不同城市之間的問題。即使是在美國,上述活動也屬城市行為,上述網(wǎng)絡(luò)成為各類運動的城市基點以及克服分離問題(雖只是偶然成功)的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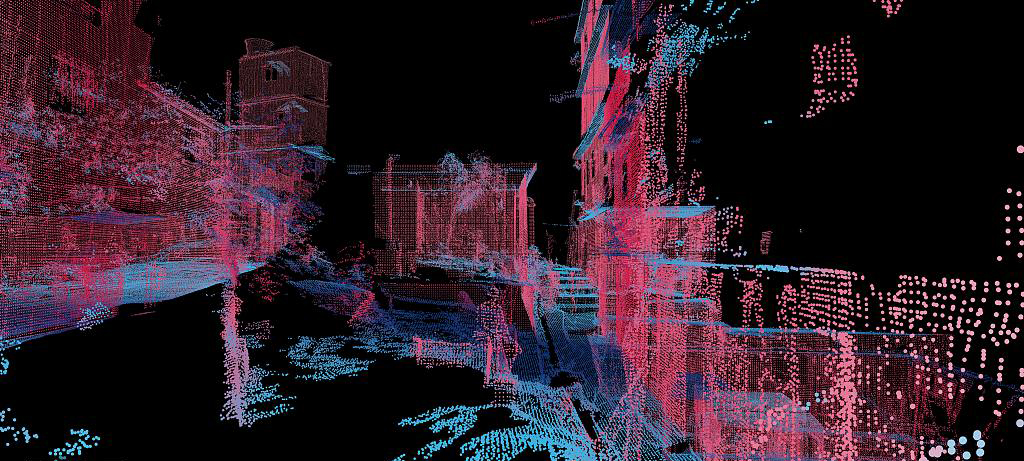
當(dāng)?shù)貢r間2022年8月3日,巴西里約熱內(nèi)盧,麻省理工學(xué)院的可感知城市實驗室使用3D激光掃描數(shù)據(jù)來觀察巴西的貧民窟。
城市復(fù)興
我想再具體探討一下從何種意義上說大城市是對全球化進(jìn)行想象并將全球化與民族的和本土的事物關(guān)聯(lián)起來的空間。實際上,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就有學(xué)者做過研究,當(dāng)時主要涉及第一世界的大城市。薩斯基亞·薩森以對紐約、倫敦和東京的分析開啟了這一研究方向。曼努埃爾·卡斯特利斯、霍爾迪·博爾哈和彼得·霍爾則聚焦歐洲城市,并改變分析角度,摒棄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學(xué)界流行的對城市衰退的警示視角。全球化的都市主義回避交通堵塞、環(huán)境污染以及犯罪行為等城市災(zāi)難,轉(zhuǎn)而表達(dá)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人口下滑趨勢局部得到控制以及技術(shù)的創(chuàng)新。為佐證此般日新月異的變革趨勢,還提及一些城市出現(xiàn)的“回歸市中心”現(xiàn)象。保羅·佩魯利將巴黎和柏林列入城市復(fù)興的范例。巴黎是因其前幾十年的大規(guī)模建設(shè)政策今日已結(jié)碩果,而柏林則得益于東西歐統(tǒng)一的實現(xiàn)。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區(qū)域性的大都市,尤其是那些歐洲偏南部的城市,諸如巴塞羅那、慕尼黑、里昂、蘇黎世、米蘭和法蘭克福等,在朝著這一方向的發(fā)展中扮演著新的角色。這些城市的經(jīng)濟(jì)和文化重啟,就業(yè)率增加。這個增加不僅僅發(fā)生在第三產(chǎn)業(yè),也發(fā)生在長期不景氣的工業(yè)領(lǐng)域:新型非物質(zhì)網(wǎng)絡(luò)的基礎(chǔ)建設(shè)在形成規(guī)模,宏大的公共工程也得以推動。相似的現(xiàn)象也在紐約城中得到印證:紐約這個曾因暴力問題與社會墮落被某位城市規(guī)劃學(xué)者定義為“西方文明的終點站”(Koolhaas,1994)的城市,近些年的兇殺和搶劫案件不斷減少(也許得歸功于監(jiān)控攝像頭的投放?),開始興建新型藝術(shù)和商業(yè)中心,此外還成了眾多知名出版社、100多家報社、240多家雜志社以及160000多家網(wǎng)站的總部所在地。
成為全球化的城市究竟需要哪些要素?上文提及的學(xué)者們指出需要以下條件:一,跨國企業(yè),特別是從事管理、研究和咨詢的機構(gòu)能夠發(fā)揮強大作用;二,國內(nèi)和國際人口的跨文化混合;三,聚集一批精英藝術(shù)家和科學(xué)家而獲得國際聲望;四,國際旅游人數(shù)居高。(Borja,Castells,1997;Hannerz,1998;Sassen,1998)
可能有人要問:“城市復(fù)興”到底是否真實?又是誰能在超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過程中獲利,畢竟大多數(shù)人都只能作壁上觀?這樣的批評是針對上述提及的幾個城市的。我曾于1998年10月參觀了柏林市中心的修繕工程。當(dāng)時25萬名勞工夜以繼日趕工,要讓諾曼·福斯特、倫佐·皮亞諾、貝聿銘及其他知名建筑師設(shè)計的大樓拔地而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德國人能那么快速地就把波茨坦廣場上曾將柏林一分為二的柏林墻舊址留下的歷史傷疤掩蓋好。彼時,僅有些許建筑物尚存,其中最顯眼的便是那口巨大的井,因當(dāng)時還在修建中,不允許人進(jìn)入工地。但還是可以登上InfoBox——那個巨大的紅色塔樓,樓上一直播放著關(guān)于該工程完工后的樣子的概念短片。此外,還有一家售賣各種“紀(jì)念品”的商店,出售之物包括電腦合成的各類建筑完工后的“照片”、宣傳畫冊、裝飾物、T恤、影音產(chǎn)品、海報和印有未來建筑工程圖片的紀(jì)念杯,甚至還有組裝虛擬建筑的拼圖游戲以及互動式光碟。游客能夠“親身體驗”這個歐洲最大的商業(yè)中心,并且還能作為觀眾象征性地參與戴姆勒奔馳和索尼等大型跨國公司的建設(shè)工程。全球性的現(xiàn)代化對于局外之人來說不過是一出戲,而對尚未存在之物先制作“紀(jì)念品”,以此來構(gòu)建一個新的融合與記憶想象體,卻是合乎情理的。
全球化的城市與傳統(tǒng)的非多元融合城市之間的差距,在第三世界的特大型城市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事實上,幾位研究此問題的專家都將既定的全球化城市和“新興城市”區(qū)分開來。前者包括紐約、洛杉磯、倫敦、巴黎、柏林、法蘭克福、東京和香港,這些金融、保險、咨詢、廣告、設(shè)計、公共關(guān)系領(lǐng)域以及音像和信息產(chǎn)業(yè)管理的老牌中心。與此同時,“新興的區(qū)域中心城市”則涵蓋巴塞羅那、圣保羅、墨西哥城、芝加哥、中國臺北與莫斯科等城市,那里的全球化服務(wù)業(yè)與傳統(tǒng)行業(yè)、非正式或邊緣化的經(jīng)濟(jì)活動、低效的城鎮(zhèn)服務(wù),以及貧困、失業(yè)和糟糕的治安狀況等現(xiàn)象同時存在。
第二類城市,即“新興城市”,正處于傳統(tǒng)的極端方式與全球性現(xiàn)代化的對立之中。此般局面為全球一體化提供便利,然而同時也為經(jīng)濟(jì)文化領(lǐng)域的不平等和排外現(xiàn)象提供了土壤。這樣的問題尤為明顯地表現(xiàn)在年輕人就業(yè)困難上:或因經(jīng)濟(jì)條件的不平等,或因教育培訓(xùn)的缺失,他們在勞動市場上難以立足。
分裂和不平等,即存在于全球化的城市和本土的、邊緣化的、不安全的城市之間的二元對立,是阻礙許多城市在這個新的發(fā)展時期中重新找到自我定位的主要因素。博爾哈和卡斯特利斯指出全球化的一大風(fēng)險是變成服務(wù)于精英階層的全球化:“城市的一部分被打包售出,另一部分則處于被雪藏或是被拋棄狀態(tài)”(Borja & Castells,1997:185)。許多美國城市曾在早年遭受過治安和暴力問題的困擾,使得其城市形象受到極大損害。于是,當(dāng)時這些城市采取了專項政策實行強化整治(其中有些是不民主的),又開展藝術(shù)文化活動構(gòu)建有吸引力的城市空間。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特大城市中,經(jīng)濟(jì)危機、金融危機和政府執(zhí)政力的削弱使得提升各類服務(wù)、改善社會治安、調(diào)動新的經(jīng)濟(jì)文化資源以革新城市生活以及擴展城區(qū)向外輻射等目標(biāo)難以實現(xiàn)。同時,失業(yè)問題不斷加劇,年輕人就業(yè)尤其困難。
邊緣城市的全球化
正如對城市(如柏林、巴黎和維也納)的研究能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現(xiàn)代化一樣,我們可以思索一下是否今日對城市變革的探討有助于一些全球化理論問題的解決。若我們一致認(rèn)定特大城市(或至少是其中幾個)是全球化運動在工業(yè)、金融、公共服務(wù)和傳播等領(lǐng)域得到體現(xiàn)的場所,那么公共空間的轉(zhuǎn)變則能給予我們理解全球化趨勢及其與本土文化互動的密鑰。下文中,我將著重分析在一些拉美城市中發(fā)生的文化代表意義與城市視覺形象的變化,墨西哥則是重中之重。此般分析是為理解在政治經(jīng)濟(jì)上相互依賴的“艱難”過程中,對于全球化的想象構(gòu)建發(fā)揮著何等作用。這就要我們重新認(rèn)識全球化,同時也促使我們?nèi)ヌ骄吭谒^的全球化城市中,如何重新界定城市屬性和公民身份。

墨西哥城
與其他殖民城市一樣,布宜諾斯艾利斯、利馬和墨西哥城曾是該區(qū)域的重要首府,也是與西班牙連接的樞紐城市。此類跨越國境的交往聯(lián)系,在民族獨立運動之后和現(xiàn)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仍在持續(xù)。大型的港口城市從二十世紀(jì)初起就一直保持開放,而當(dāng)?shù)氐膫鹘y(tǒng)則和與之進(jìn)行貿(mào)易來往的大都市的舶來文化相糅合。比如,大西洋沿線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加拉加斯、哈瓦那和里約熱內(nèi)盧,同西班牙、法國和英國有來往,而哈瓦那與里約及非洲大陸有密切的聯(lián)系;與此同時,利馬和巴拿馬則與美國以及亞太地區(qū)往來甚密。在這些城市中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的雛形,只是它受限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邏輯——必須優(yōu)先與某一個大型城市保持密切往來。而直到二十世紀(jì)中葉,上述拉美都市的城市結(jié)構(gòu)和城市生活意義主要取決于它們作為其所在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但當(dāng)今,墨城和圣保羅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化城市并非因為它們是區(qū)域的中心抑或與某個“宗主國”有密切聯(lián)系,而是由于它們成了世界級的經(jīng)濟(jì)和傳播網(wǎng)絡(luò)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心。
從十九世紀(jì)中葉到1940年,墨西哥城的人口從185萬激增到341萬,墨城的城市結(jié)構(gòu)卻仍然保持著十六世紀(jì)由西班牙殖民者所設(shè)定的方形結(jié)構(gòu)。直到大約五十年前,城市生活都還在劃定的區(qū)域里進(jìn)行,其地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位于老城區(qū)(位于今墨城市中心地帶),而老城區(qū)由殖民時期的老建筑、十九世紀(jì)的建筑以及其他一些能讓人想起史前歷史的考古地點構(gòu)成。
在這一時間段里,國家政府一直都是民族社會和城市生活的主要參與者。墨西哥的建立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諸如印第安族群之間的分化以及國內(nèi)不同區(qū)域之間的分隔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得益于國家成立后所建立的鐵路運輸系統(tǒng)、國家經(jīng)濟(jì)市場、一個以卡斯蒂利亞語言為基礎(chǔ)的教育系統(tǒng)、單一政黨內(nèi)的政治一致以及權(quán)力集中的工會。同樣,文化財富也促進(jìn)了此般大一統(tǒng)的實現(xiàn):通過手工藝術(shù)、現(xiàn)代造型藝術(shù)和電影藝術(shù),形成了綜合反映自身民族文化的財富。所有這些文化的想象體在國家博物館和國際博覽會上頻繁展出,在龐大的公共壁畫中來回呈現(xiàn),在鄉(xiāng)土記憶和城市情感交織的電影中重復(fù)演繹。隨著人口不斷向城市聚集(二十世紀(jì)初只有10%的墨西哥人住在城市里,而七十年之后這個數(shù)字就變成了70%),各種地區(qū)資源,如教育中心、博物館、有紀(jì)念意義的考古地點和墨西哥政府保留下來的殖民時期建筑,都越來越聚集一地——以首都墨城尤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的文化保護(hù)政策比其他任何一個拉美國家都要健全。
從半個世紀(jì)前至今,墨西哥城的公共空間、人們聚集和交往的方式又發(fā)生了怎樣的改變呢?早在1950年,墨城作為首都其面積也僅是現(xiàn)在的三個中心區(qū)(貝尼托華雷斯、夸烏特莫克和科約阿坎)那么大。那時人們的生活主要集中在城區(qū)內(nèi),倒是也有有軌電車,還有22000輛馬車、60000輛汽車以及1700輛負(fù)責(zé)日均百萬人流區(qū)際流通的公交車。市民步行就能走到老城區(qū),真要使用交通工具的話,行進(jìn)距離也不超過五公里。那時只有一小部分人會閱讀報刊來獲取信息,而更多人則更傾向于收聽電臺,并且人數(shù)開始不斷增多。人們常會去看電影,或去舞廳和公園消遣。那個年代沒有電視也沒有視頻。大學(xué)、書店和劇院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帶。
從城市空間到媒體領(lǐng)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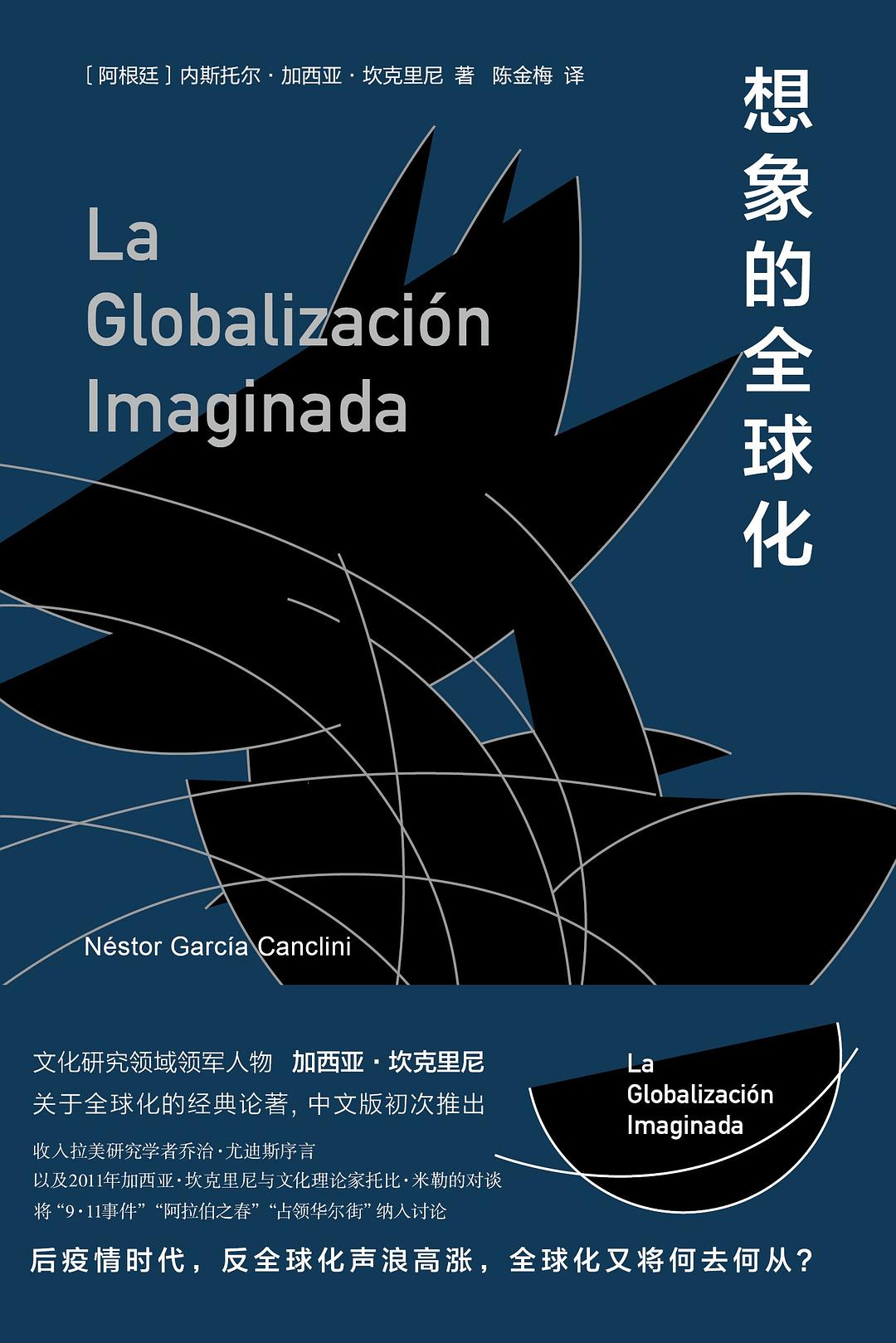
《想象的全球化》,[阿根廷]內(nèi)斯托爾·加西亞·坎克里尼 著 陳金梅 譯,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7月。
從一個三百萬人口的城市到一千八百萬人口的特大型城市的轉(zhuǎn)變,引發(fā)了涵蓋人口統(tǒng)計學(xué)、社會經(jīng)濟(jì)學(xué)、信息和娛樂領(lǐng)域的諸多變化,而對于這些問題,文化政策給予的關(guān)注較少。在墨城北部和東部的民眾居住區(qū),工業(yè)的發(fā)展并未能推動博物館、書店和劇場的創(chuàng)建,公園和娛樂場所的數(shù)量也少之又少。當(dāng)時只有電視電臺、斗牛,加上1985年后出現(xiàn)的影音俱樂部以及一些公立圖書館能為市民的閑暇生活提供點消遣選擇。直到大眾媒體的誕生,人們才開始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
而在最近二十年間,在公共空間里進(jìn)行重新分配的是什么呢?首先便是傳播網(wǎng)絡(luò),包括報刊、電臺、電視、影音和電子信息。其次便是圖書館、大型商場——有些商場舉行文化活動——以及最近興起的多廳影院。比如在波哥大、加拉加斯和圣保羅,跟“傳統(tǒng)場所”相比,傳媒領(lǐng)域?qū)π畔⒌膫鬟f以及對城市生活的想象體而言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此外,傳媒領(lǐng)域有時還能為人們提供更多碰面和相識的新方式:人們的交流可以通過電臺電視上的互動節(jié)目或者熱線電話完成;過去人們習(xí)慣約在老地方見面和散步,現(xiàn)在都習(xí)慣在購物商場會合。除此之外,許多此類的文化活動能夠使大部分公眾體驗大城市生活以及異國風(fēng)情。由此,城市作為公共空間的性質(zhì)也發(fā)生了改變。上述的交流方式不僅方便了首都城市與國內(nèi)各生活層面的往來,同時促進(jìn)了首都城市與跨國財富和國際信息的互動。因而,特大型城市便成了信息集中、國際化演出云集、大型外資企業(yè)分支遍布、資本運作機構(gòu)扎根以及全球化的革新與想象進(jìn)行的場所。
墨西哥城仍有不少大型的本土文娛盛會吸引著眾多人群。每年會有三百多萬朝圣者在12月12日趕到維拉城區(qū)來朝拜圣母瓜達(dá)盧佩,還有兩百萬人則在復(fù)活節(jié)前往依茲塔帕拉帕城區(qū),更有一大群人習(xí)慣聚集在市中心的索加羅廣場參與政治集會,或是前往各大體育館觀看比賽。以上種種都是不可不提的實例。還有很多未被納入文化產(chǎn)業(yè)化范疇的文化活動仍在進(jìn)行著,如主保圣人節(jié)、沙龍舞會以及居民聚居區(qū)街上的狂歡和當(dāng)?shù)氐膫鹘y(tǒng)活動等。如此之大的墨城仍存留著一些村落之人,他們繼續(xù)踐行其本土習(xí)俗和源于鄉(xiāng)土的慶祝活動,他們的名字由天主教圣徒之名和納瓦特爾元素合成,昭示他們的西班牙和印第安血統(tǒng),同時,他們在工作和消費時與這個現(xiàn)代城市發(fā)生聯(lián)系;除此之外,墨城至今還存在著一些建于十七十八世紀(jì),有某些自治特色的社區(qū),那里還在重現(xiàn)屬于十七十八世紀(jì)的活動和慶典。很顯然,在從社區(qū)中穿腸而過的高速路以及呈現(xiàn)后現(xiàn)代想象的高科技建筑物中,這些活動并沒有顯得格格不入。最近的一些人類學(xué)研究在對不同居住模式和促成多元化區(qū)域形成的各種想象體進(jìn)行比較之后發(fā)現(xiàn),那些居住在村鎮(zhèn)的人習(xí)慣認(rèn)同“我是某地人”,而那些生活在現(xiàn)代區(qū)域(比如小區(qū)和公寓樓)的人較多使用“我住在某地”這樣的表達(dá)(Portal,1997)。
上述研究所展現(xiàn)出的差異性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正如我們在另外一個研究中所分析的,必須要承認(rèn)這些新型的歸屬認(rèn)同方式促使居住不再專屬個人行為,甚至擴展至跨國維度(García Canclini,1995)。不管怎樣,大多數(shù)人持續(xù)且成系統(tǒng)規(guī)模地參與的活動,投資最為密集、創(chuàng)造最多就業(yè)機會的領(lǐng)域,以及公共場域(esfera pública)的發(fā)展中最富有活力和影響力的空間,總是集中在新聞、電臺、電視以及那些覆蓋不同城市和跨越國界的大眾娛樂(如電影和購物)行業(yè)。
如同在其他拉美國家以及墨西哥別的地區(qū)一樣,墨城也正在經(jīng)歷去工業(yè)化的進(jìn)程,面臨著由于國際競爭導(dǎo)致的工廠關(guān)閉,或出于生態(tài)原因工廠轉(zhuǎn)移至墨西哥其他地區(qū)。另一個原因則是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重組將重心傾斜到第三產(chǎn)業(yè)(Nivón, 1998)。差不多二十年前時興城市化理論,強調(diào)城市與鄉(xiāng)村的不同,以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勞動力轉(zhuǎn)移到了第二和第三產(chǎn)業(yè)。現(xiàn)如今,發(fā)展的最強推動力不再是工業(yè)化,而是電子信息技術(shù)發(fā)展和金融資本運作。由于這些服務(wù)必須要有相應(yīng)的基礎(chǔ)設(shè)施,就連流動性最強和解域化程度最高的產(chǎn)品也緊緊扎根于那些技術(shù)資源豐富和人口素質(zhì)較高的城市里。全球化互動交往的地理布局與戰(zhàn)略地帶緊密結(jié)合,分散于全球的多個點位,以使得信息在廣闊空間傳播,即傳播的空間化(espacializar las comunicaciones)。
在全球化的經(jīng)濟(jì)模式中,各大城市已變?yōu)槎鄧?jīng)濟(jì)聯(lián)通之地,它們與其說是工業(yè)生產(chǎn)的中心,不如說是提供服務(wù)的中心。在紐約和倫敦,制造業(yè)所雇的勞動人口占據(jù)經(jīng)濟(jì)活動人口總數(shù)的比例不到15%,并且在可預(yù)見的未來,即在二十一世紀(jì)初,此數(shù)字最終會降至5%至10%之間(Hall, 1996)。如果說幾十年前大都市的標(biāo)志性形象是煙囪和工廠街區(qū),那么現(xiàn)在的大都市留給人們的印象則是各國巨大的廣告牌充斥(甚至造成視覺污染)所有的高速公路以及后現(xiàn)代風(fēng)格的建筑物——各大公司使用反光玻璃裝飾的辦公大樓。這些場景正在改變整個墨西哥城——上至改革大道、波蘭科和圣塔菲(均為墨西哥城商業(yè)繁盛區(qū)),下至城市最南端——的城市風(fēng)貌。
同樣也需看到各大、中城市里的大型購物商場所發(fā)揮的文化功效。它們在擴張房地產(chǎn)和商業(yè)資本、集中調(diào)整投資結(jié)構(gòu)、創(chuàng)造就業(yè)和讓小型商業(yè)(他者)消失的同時,也為消費大戲的上演提供了空間,使得高大的建筑群與信步和休閑聯(lián)系到了一起。它們還成為社會上層和中產(chǎn)階級象征高雅的符號,并提升了跨國品牌產(chǎn)品在滿足消費者需求上的重要性。許多購物中心都設(shè)有特定的文化活動設(shè)施,如多廳影院、書店、唱片行、電子游戲、音樂演出、藝術(shù)展覽及其他娛樂中心。憑借有吸引力的設(shè)計、衛(wèi)生又安全的環(huán)境,它們能夠超越其商業(yè)目的而成為約會和社交的場所(尤其受到年輕人的青睞)。文化和商業(yè)屬性的糅合使這些商場變得比純粹的文藝場所更加誘人前往,同時又比一般只供購物和閑逛之地更加值得信賴。這種糅合獲得成功的一個文化秘訣在于能夠?qū)⑼怀龅纳矸菹笳髋c個人舉止自由融為一體。對顧客的采訪報告表明在這些地方購買衣物和商品更能體現(xiàn)顧客的身份和品味,此外,這些場所提供現(xiàn)代化和國際化文娛活動以及高質(zhì)量的展覽,同時還能接受人們輕松隨意地享受這一切,比如可以穿牛仔褲入場,還可以邊走邊聊(Ramírez Kuri,1998)。
城市空間的使用和消費(包括文化消費)方式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并沒成為關(guān)于城市的議題的一部分,更別提被納入文化政策了。在墨西哥城,只有奎庫爾科商場曾引起過社會爭論。人們認(rèn)為建造這一商業(yè)中心和配建一座大廈會影響鄰近的同名古文明中心,那一歷史遺址可是整個墨西哥谷[1]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始于公元前二世紀(jì)),此外還會污染水源并造成路面交通擁堵。然而,當(dāng)休閑活動的市場化進(jìn)一步擴張以及城市面貌發(fā)生改變之時,人們應(yīng)當(dāng)考慮的公共利益難道只限于與歷史古城之間的沖突嗎?
由于大量人流前往購物商場以及商場將公共資源私人化的特點,商場的建造其實可以作為從公共角度入手的研究分析對象,而非只著眼于商場對古老建筑的影響。國家除了行使調(diào)控和制約職能,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大型購物中心對于公共空間利用上的可取之處。正如這類商業(yè)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們回歸電影院并促進(jìn)人們對唱片和藝術(shù)展覽的消費一樣,也值得探討在此思路下商業(yè)中心是否同樣能促進(jìn)其他一些與公共文化相關(guān)的活動,以傳播文化、分享信息并鼓勵人們參與。巴塞羅那、柏林、倫敦以及其他一些歐洲城市的大型商場在這方面已大有作為。(Borja & Castells,1997)在那里,除了可供消費的場所,投資者還需要設(shè)置一些并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場所,比如兒童活動區(qū)以及一些文化和社會服務(wù)場所。
在墨西哥,管控商業(yè)電視的法律規(guī)定,各個電視頻道必須保證有12%的時段用于公共信息的傳播。此外,聯(lián)邦立法院也為保護(hù)重要歷史遺址和維護(hù)城市的和諧發(fā)展,確定了一些開發(fā)受限的特殊地區(qū)(Zonas Especiales de Desarrollo Controlado)。如果有人想在這些地區(qū)進(jìn)行超出規(guī)定范圍的開發(fā)(占用土地或開啟建造工程),則應(yīng)當(dāng)在該地區(qū)建設(shè)一定的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以促進(jìn)城市資源的再生和改善。
制定法規(guī)讓企業(yè)家在建造或擴建商場時必須騰出一定空間專用于發(fā)展非營利的文化業(yè)務(wù),如演出、藝術(shù)工坊、由墨西哥電影檔案館(Cinecteca)管理的電影播放廳,以及面向社會大眾的電子信息服務(wù)等,難道不是可以實現(xiàn)的嗎?就像評估大型建筑在建設(shè)過程中對環(huán)境的影響一樣,也應(yīng)考慮其文化影響,并要求所有的營利性投資都應(yīng)拿出其部分收益來回饋社會。或許,重新思考這類具有社會屬性和消費特點的新型空間所產(chǎn)生的公共價值,將推動墨西哥效仿很多其他城市(正在修改它們城市規(guī)劃)再將城市建設(shè)寫進(jìn)其討論議程(Holston & Appadurai,1996)。
雖說墨西哥城在最近半個世紀(jì)的發(fā)展全靠工業(yè)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規(guī)模國內(nèi)移民潮,然而自從其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初經(jīng)濟(jì)對外開放起,這個城市里最具發(fā)展活力的城區(qū)還是那些建立了外資企業(yè)或是完成了墨西哥企業(yè)的國際化的區(qū)域。墨西哥城及其周邊都市區(qū)域現(xiàn)已成為世界上二三十個超大城市區(qū)域(megacentro urbano)之一,實現(xiàn)了經(jīng)營管理、發(fā)展創(chuàng)新和市場營銷的跨國融合。這一發(fā)展所帶來的變化非常明顯,尤其可見于圣塔菲區(qū)——惠普、奔馳、丘博保險、Televisa等大型公司的辦公樓以及大型商場和高端住宅區(qū)就占用了650公頃的土地。同樣,變化也可見于墨城其他幾個地方,如改革大道、波蘭科部分區(qū)域、起義者大道和南環(huán)城路的建筑修繕中;變化還表現(xiàn)在大型商場和新型國際酒店不斷涌現(xiàn)、電信和衛(wèi)星通信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信息科技的發(fā)展、有線和數(shù)字電視的出現(xiàn),以及之前我們已提及的多廳影院的誕生等。這些舉措中的一部分直接導(dǎo)致了文化和傳播發(fā)生變革,另外一部分則重新定義了城市生活以及將空間據(jù)為私用的傳統(tǒng)模式。這兩類情況的共同之處在于,國家都將其領(lǐng)導(dǎo)地位讓給了私有企業(yè)和跨國集團(tuán)。
為使城市生活全球化的根基穩(wěn)固,而非簡單淪為房地產(chǎn)、金融、媒體等行業(yè)的斂財路徑,我們有必要重新闡述文化政策與公共場域和公民身份之間的關(guān)系。若藝術(shù)和手工藝傳統(tǒng)、博物館和歷史老城區(qū),能夠與先進(jìn)通信技術(shù)和信息化手段一道,成為城市或國家發(fā)展計劃的一部分,那么它們將會是解決社會分化與不平等問題的新路徑,或許還能改變一個城市或國家的對外形象與競爭力。
注釋:
[1] 即Valle de México, 是位于墨西哥中部的一個高原,大致與現(xiàn)在的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州東半部相連。墨西哥谷周邊是數(shù)個哥倫布時期文明,包括特奧蒂瓦坎、托爾特克和阿茲特克的中心。
(本文選摘自《想象的全球化》第七章,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刊發(fā))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