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風情 | 我愛多倫路 | 劉湘如
原創 劉湘如 上海紀實

我的住處離四川北路很近。在上海虹口區和楊浦區的交界區域,有一條坐落于虹口區的小馬路,很多人不知道它叫天寶路,而我十分熟悉,因為這條小路上有我的蝸居,很小,室內邁步只可以走幾步,我給她取名叫“十步齋”,含義有“十步芳草”的意思,言其小而溫馨。不過要說這里的地理位置,那就是上等地標黃金地段了。這里不僅交通便利,生活更有難以企及的方便,周圍的超市,菜場,書店,學校,公園,可以說是應有盡有,對于居家過日子來說,她擁有無窮的方便。
而對于我來說,最大的興趣和獨特的優勢,在于一個偏好,它離一個我喜歡的地方很近,那就是多倫路。順著天寶路和祥德路,過山陰路,甜愛路,穿過魯迅公園,就到了這個舉世聞名的風水寶地了。在掛著汽車禁行標牌的街口,一座新建的具有民國裝飾風格的牌坊,上綴有“海上舊里”四個大字,這里便是“多倫路文化名人街”的北入口處了。這里距離我居住的地方約一兩公里,這正是散步的最佳途程。在閑暇時,我常常一個人散步到多倫路,在小街上靜靜地溜達一番,或者東張西望欣賞一番各類文化用品和各色古典文物,特色連連的別墅和舊居,而后再慢騰騰的一路散步走回,這真是我的最大的特立標識的文化享受了……
一

提起多倫路,人們立即會想到上海,想到虹口,想到民國風情,想到三十年代,想到魯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葉圣陶等中國文學巨匠,以及丁玲、柔石等左聯作家在這里開展左翼作家革命文學活動的往景。其實,早在清朝末年,這條多倫路已經開始繁華。在這里更有孔(祥熙)公館、白(崇禧)公館、湯(恩伯)公館、薛氏宅等中西合璧、風格各異的老宅,以及豐樂里、永安里、景云里等近代上海傳統民居石庫門住宅群,這些綜合因素,更使得多倫路成為海派建筑中的“露天博物館”。
多倫路位于上海虹口區四川北路街道,北接東江灣路,東臨四川北路,南接東橫浜路。這條路的形狀成“L”型,長550米,寬10-13米的多倫路文化街,是上海的一條著名的文化坐標和休閑街。因為街短而窄,路曲且幽,不大的多倫路文化街在中國地圖上,甚至難以具體標示,但在中國近現代上,特別是中國文化史上,多倫路卻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
此路最早叫竇樂安路,修建于1912年,因為小街曲折幽靜,街邊的小樓風格各異。夾街小樓,櫛比鱗次,更顯出風格各異,令人矚目。20世紀初葉,這里是上海寶山縣一條荒蕪冷僻的小河浜。隨著西方列強炮火而涌入中國的淘金者隊伍中,有一個叫竇樂安的英國傳教士,此人曾受到清朝光緒帝的接見,他在當時虹口公共租界地塊上,象征性地花了些錢,買下了這片土地。竇樂安看中這里中、美、日三不管的寬松環境、便宜的地價和淞滬鐵路近在咫尺的交通,填河造路,干起了招商引資的營生。于是,路名便叫竇樂安路。從清宣統三年也即1911年,直到民國7年的1918年,此路有了最初的變革,與今多倫路201弄以北的北四川路相連接,形成現在的路況。20世紀二三十年代,此路兩邊屬華界當局管理,從建成到抗日戰爭時期止,周恩來、瞿秋白、張國燾、陳望道、趙世炎、魯迅、茅盾、郭沫若、葉圣陶、柔石、丁玲、馮雪峰、張之江、史良、陶晶孫、鹿地亙、陳愛蓮、王造時及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等大批中外知名人士,在這條五百多米的街道上居住過。一時間八方雜陳,四海云集,風云際會,風生水起。
民國32年,即1943年7月30日到8月1日,汪偽政權先后收回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同年10月1日以察哈爾省多倫縣(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縣)更名為多倫路。抗日戰爭期間,多倫路上大多為日本僑民或侵華日軍官兵居住,成為日本侵華海軍保甲制度區。
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初,多倫路先后出現了大批社團組織,像太陽社、基督教會、上海藝術劇社、中華藝術大學、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新中國劇社、自由出版社等各類社會團體與組織,紛紛亮相于這條路上。
與上海的豫園老街、靜安寺、南京路相比,這條路沒有他們奢華輝煌,顯得有點不起眼。然而這條外觀看似平凡的小馬路,卻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臥虎藏龍之地,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周恩來、瞿秋白、張國燾、魯迅、茅盾等一大批彪炳史冊的人物,臺灣作家白先勇也在這里的白公館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一兩個多世紀來,上海走過了從開埠時期的沙船漁村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十里洋場,直至形成今日東方大都市的滄桑歷程。多倫路及其周邊地區,從一個側面集中地展示了這個歷程印跡和文化縮影,從瞿秋白、陳望道、趙世炎、王造時、內山完造等等名流大亨到景云里、中華藝術大學、上海藝術劇社,名人故居、海上舊里,積淀成今天多倫路上濃厚的文化氣息,使人流連忘返。
可謂“一條多倫路,百年上海灘”。
二

1998年,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上海虹口區政府開始對多倫路進行一期改造,重點保護和修復了沿街的優秀歷史文化建筑。2001年,多倫路被上海市旅游局命名為 “上海市文化特色街”。2010年,被文化部授予“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稱號。
2011年,多倫路完成了整體環境改造工程,沿街老建筑的外立面經過“修舊如舊”的處理,路面整體鋪設成老上海的彈格路,從此告別了又臟又亂、污濁嘈雜的馬路菜場,還原出了海派文化獨有的優雅風情,變身為一個兼具“名人故居、海上舊里、文博街市、休閑社區”的特色文化街區。2012年,又邀請法國、美國、英國、西班牙、日本和國內的多家設計公司對多倫路二期改造進行方案設計,并制訂了詳細修建規劃,確定了保護地區內的文物建筑和優秀歷史建筑,保留對延續區域內歷史風貌有價值的歷史建筑及建筑符號,使原有歷史風貌和更新建筑肌理盡量保持協調契合,注重改善人居環境,打造特色明顯的文化社區。堅持“傳承與創新結合,紀念與休閑結合,古典與現代結合”的原則,通過加強歷史街區、名人故居的保護,及其功能的深度開發,進一步挖掘文化名人街的文化內涵和海派特色……

每年春節過后,春天才剛剛降臨,我會在不經意間散步到魯迅公園,那時進門后滿眼撞見的,竟會是迎春花以及紅的和白的夾竹桃,我想躲避她們都來不及,一般情況下,我或者剛剛從比較笨拙的電腦打字中走出來,對于艷麗的顏色特別敏感,我會一路散步走到魯迅像前,在那個小廣場的石墩上坐著,享受生活休閑的樂趣,我常常呆呆的望著那座古銅色的魯迅塑像,看著先生那雙特殊的眼神,揣摩著他會在想一些什么?據說當年魯迅也是常常散步到這里,在一個石墩上小坐,當初虹口公園是否就因這而改名的呢?有時候,或在櫻花紛飛的四月,或在槐花飄香的五月,我會在魯迅公園里逗留半天的時間,在這里的每一處,留意一些別致的景觀,有時樹林里,假山上,小湖邊,到處可以見到一群人圍坐在一起,或在唱京劇,或唱滬劇,或唱流行歌曲,一個個字正腔圓,聲音動聽,也有圍在一起拉胡琴彈唱的,清音繚繞,輕管細弦,能讓人聞之忘返。更有意思的是那些蘸著大拖把用水在地上寫字的老人,從他們的書法功底上看,不亞于名副其實的書法家,不知為何要在公園里寫字自娛?這里頭好像包涵著很難理出頭緒的社會現象,我感覺在中國所有的城市公園中,有些景觀是上海特有的。時候還早,走出四川北路公園西大門,拐過一條斜的街面,就一以貫之地到了多倫路名人文化街了,在這條L形的小街上,我對于以陳望道為校長、夏衍為教育長的中華藝術大學和中華藝術劇社故址產生了興趣,接下來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左聯”大本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在這里成立的。我常常站在文化街上浮想聯翩,遙想當年的“左聯”干將夏衍、馮雪峰、瞿秋白、柔石、許幸之、潘漢年、張愛萍等,他們的風格和他們當時的作為,都在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和故事里沉淀了。歷史皆已離去,人去樓空的多倫路最能引起文人的慨嘆,我每回在這里漫步時,常常有意識地去觸摸那些人的脊梁和手臂,我并不想和他們照一張像作為留念,我是想感覺一下他們那些人脊梁和手臂有多硬?雕塑家的匠心是偉大的,他使得每一個塑像都栩栩如生,形神畢肖。我和這些雕像握手時,我似乎感到了他們手臂的力量。
有一回我來到湯恩伯公館一棟歐式風格的三層小樓內。見到了先秦至民國的歷代錢幣大量品種,總計十多萬件,重量約有十噸之多。我有時也光顧另一些展館,諸如珍藏著世界各地旅游品的旅游品紀念館,有著大量中外藏書票,特別是魯迅、瞿秋白、丁玲等“左聯”成員的藏書票館,它們讓人想入非非。我還曾迷過一家奇石館。三層民居原為著名工人領袖趙世炎寓所,1927年這位早期共產黨人在此被捕,后慘遭殺害。現在這里住著一對夫婦,他倆以石定情,藏石50載,上萬件藏品叫人嘆喟。我體會到上海人為什么喜歡“白相相”了?在這里逛逛,無論是弘文書店、茶樓、棋室、古玩店、教堂、鐘樓等等,都是陶冶情趣的難得的處所啊。

當夕陽西下的傍晚時,我會沿著四川北路祥德路那條小街,一路悠悠地走回到我的十步齋,這時正是勞燕晚歸的時候,小區到處都是人,市聲和人聲混雜特別顯得人氣旺盛,我有過內心孤獨的時候,所以很喜歡這種氣氛。我在家里看書,看電視,寫文章,聽著外面熱鬧的世界心里特別愜意。不過這是暫時的,好就好在我的蝸居有鬧中取靜的優勢,當夜晚人們都進入夢鄉時,小區顯得很靜,這種靜是獨特的,不是無聲,或者正因某種細小的聲音更顯得靜寂,比如有幾個馬路上走路的腳步聲,窗戶外自行車騎過的聲音,遙遠的黃浦江一兩聲清細如弦的汽笛聲,那簡直不能叫聲音,而分明是夜間唱著的眠歌,是夢的伴奏。我有失眠的毛病,不過在離多倫路文化街很近的我的十步齋里,我常常是失眠也不覺得疲倦的。
三

多倫路是值得慢慢逛的地方。在這里漫不經心上走一走,你仿佛聽見曾經激蕩文壇的豪邁的吶喊;仿佛感受到這里曾經強勁跳動的中華民族的脈搏;你仿佛能領略到百年上海灘演繹的民俗風情。
現今的多倫路面清目秀,凸顯出沿街建筑的個性特色。兩側的博物館,展覽館,古玩字畫,書屋文苑,茶室吧廊,等等,無疑已經成為國內外賓客懷舊休閑、旅游觀光和文化消費的好去處。名人雕塑廣場、名人足跡路、民間收藏館等等。各種各樣的特色店吸引了各色的收藏者,以及各類私人收藏博物館包括集報館、古陶瓷收藏館等,真正是目不暇接。這里現在已經被評為“上海十大休閑街”,在街上,擁有全國第一家現代美術館,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畫家與畫廊。這里也是圖書的集散地,愛好書籍的人在這里流連忘返。
我有個癖好,喜歡淘書,特別是淘舊書,愛聞舊書的味道,那種略帶著霉味的有點兒濕濕的刺激味,是一種歲月流過的標識。父親是個私塾先生,每到夏天就搬出一箱箱舊書在烈日下暴曬,鄉村人叫“曬霉”。記得我小時候頑皮,常常會在父親曬好舊書裝箱后,偷偷跑去翻箱倒柜,倒不一定是為了讀書,而是好奇著那些舊書里頭到底藏著些什么寶貝?時間慢慢地過著,那些經過暴曬的書帶著另一種微燥的太陽味,成了我親切的記憶。等到我自己也讀書寫作開始藏書了,我依舊對舊書有一種異樣的情愫。
多倫路的舊書店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它們消磨了我的許多時光。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發現多倫路上一家不起眼的小書店。離小書店不遠處還有幾家小書攤。嚴格地說,有的小書攤并不能算是書攤,它不過是收舊書舊報的臨時攤點,特別是有一對殘疾人的攤點,他們連一個起碼的遮雨蓬也沒有,但每天到他們這里賣舊書舊報的人卻特別多,大約是同情他們是殘疾人的緣故吧?這個書攤也就是我光顧最多的地方,因為他們那里常常會有出其不意的舊書出現,是一些市面上很難見到的好書。讀書人希望得到的珍稀,被有些人把黃金當廢鐵賣了。所以,在這個舊書攤上,在成堆的舊書里尋找我所需要的書籍,是在沙里淘金,成為我生活中的一大樂趣。有一次,我因為眼疾問題在醫院醫治,一只眼做了激光,用眼罩罩著,愛人和孩子戲稱我為獨眼龍,我對于周圍的事物都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可是當我路過那個小書攤時,依然一眼就被吸引了過去。那里有一套《宋史紀事本末》,文言本,明代陳幫瞻編選,中華書局于五十年前出版影印本,五年后出版鉛印本,厚重的三大本,每本定價卻只有1.25元,我在一大堆舊書里把他們全部找到時,發現書后標有“文津閣和文溯閣本四庫全書與提要均作二十八卷”字樣,不禁竊喜自己的運氣,因為要搞到那28卷本談何容易?我當時正在寫朱熹和嚴蕊,亟需核證南宋史料,天天跑圖書館卻未見到這套書,真是老天幫忙雪中送炭。馬上掏出100元錢給那對殘疾夫婦,把這套書全部買回,那對夫婦對我感激不盡,殊不知我應該感謝他們呢!
在舊書攤上淘書,要處處留心。也是那次以后不久的一天,有一朋友請我在多倫路文化街上一家酒店吃飯,就散步過去,剛走到多倫路的拐彎處,就被一個舊書攤吸引住了。我走上去,在那些雜亂堆放的舊書中,發現了一套上、下冊《女仙外史》,我知道這是清代初葉呂熊寫的一部章回體小說,文學史家很少道及,但它曾被稱作“新大奇書”,是在《金瓶梅》等奇書之后被人們發現的,所以冠之以“新”,雖有神魔小說的某些特點,卻有深刻的思想背景。我曾于上世紀70年代在一個縣城中學的老夫子家見到過這部書,當時我想借去一閱他堅決不答應,還說這書是禁書,不想到此刻竟在無意中見到。書是上世紀50年代的版本,很舊很破,我當即掏出八十元把兩本書買下。這樣捧著書到了酒店,往桌子上一放,灰頭黃舊的,座中有人嘲笑我,弄的服務員也跑來看熱鬧。
四

多倫路最是顯耀的還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精心點綴的小品街景,街心廣場上姹紫嫣紅的花壇,古樸與現代、凝重與輕靈各異的千姿百態的文化旅游紀念品,在朝陽中熠熠發光的“百年老店、恒豐茶莊”銅牌,人們真切地感受到:多倫路文化名人街正從歷史走向現代,從現代走向未來。以交相輝映的故居舊街老弄堂,鱗次櫛比的畫廊文苑博物館,連片的古玩字畫收藏品,各色咖啡屋,特色的文化街氣氛十分濃厚。
多倫路的設計特色以文化、旅游為主線,帶動沿線相關商業的發展。在路面及環境整治、修繕原有人文景觀的同時,創造新的城市開放空間,形成多功能、多層次的集旅游、文博、商業、休閑為一體的環境,賦予文化以新的城市活力。
作為一條文化名人街,多倫路的開發與普通的商業街開發最大的區別在于:它著重于文化與展示的功能。沿線的一系列名人故居、遺址、美術館、博物館,充分體現了多倫路的文化特點;而與之相輔的各類特色餐廳、民俗商店、咖啡館、古玩店、書店、影劇院則為其增加了新的商業活力,使地區功能更為有機、豐富、多元和完整。現代城市設計理念更加尊重人的便利和舒適。多倫路文化名人街的設計中,從街道尺度、綠化的布置、開放空間的安排、小品的陳設、建筑的細部、直至地面的鋪裝,都意欲使購物、觀光者體會到“步行者的天堂”這一理念,并充分提供通訊、納涼、集會、休憩、公共衛生等服務設施,體現出對人的細致關懷。
還記得多年前的一天,我的家鄉來人,一行好幾人都是文藝界人士,他們要我帶他們找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但當時我不知道,問了不少人,終于在多倫路文化街201弄2號,找到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那是一個非常生僻的小弄堂,這里的各位成員都來過多倫路好多次了,卻從未發現過這個處在洋房之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那天我們早上八點就出發到達了多倫路,可是“左聯”實在是很難讓人找到,在多倫路的弄堂里,走了一遍又一遍,也是沒有找到。在這途中遇到了一位與我們有著一樣目的來到這里的老黨員,是一位退休的中學教師,看起來也有七十幾歲了。她與我們結伴一起尋找”左聯”,接著又與我們一起參觀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在這期間,我們發現這位老人不僅是一位老黨員,更是一位知識淵博的老人。在此后的參觀中,講解員一直帶領我們參觀并且講解,講解員都并不能講清楚的歷史背景,這位老教師卻能一口解釋清楚,我想也許她是單位的教授黨史的老教師吧?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是中國共產黨于1930年3月2日在中國上海領導創建的一個文學組織。目的是與中國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其思想。左聯的旗幟人物是魯迅,但實際在背后握權是兩度留蘇曾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這樣的一個組織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文學革命。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我們看到了整個英式風格的建筑。看到了當時開會的情景,很難想象那樣一個與一般學校教室差不多的地方,正是這個組織的重要地址。我們看到了帶著手銬的左聯五烈士,他們讓我們敬佩 ,他們帶著手銬卻依然挺立的姿態,昭示出我們的中國的精神和氣魄。我們還看到了左聯成員死前寫的文章手跡,他們那些認真不茍的態度,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讓我們的心也隨之震撼。
我愛多倫路,十分崇敬那段歷史。十分珍惜我們今日的擁有。對于多倫路文化街的珍稀和典故,都藏進了自己的知識庫存里,他們和其他書本知識一樣,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和文化范疇。我曾工作于外地,節假日回到上海蝸居,而今在這里定居,是一種緣分,也是精神的領地和地緣的收獲。所謂大隱隱于市,在這里生活,沒有人知道我是誰,來自何方,干什么的,甚至沒有人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曾經有過怎樣的失敗或者輝煌,這種天馬行空的感覺特別好,有時候我甚至想,比起上海來,我工作過的城市還是小了,有時候在城這頭說句話城那頭就有人聽到了,做人有時不得不小心一點,在上海就沒有這種感覺了,好大世界,無遮無礙,誰都管不著誰了。如果在這里想寫點東西,或者在寫作之余到多倫路文化街去逛逛,真是一項莫大的享受。
我愛我的蝸居,更愛多倫路,當然,最愛我的蝸居距離多倫路這么近,這是上天的賜予。更是人生和生活的饋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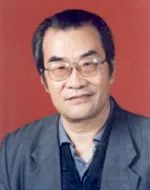
劉湘如,又名劉相如,筆名老象。安徽肥東人。1980年代加入的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散文學會理事,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中國名家書畫研究會副會長。國家一級作家。曾任安徽電視臺高級編輯。作品涉及小說、報告文學、散文、詩歌、影視劇等。迄今發表出版作品千余萬字,主要著作30多部。其散文集《星月念》《淮上風情》《瀛溪小札》,報告文學集《十步芳草》《共和國星光》《馬拉松大戰》,長篇小說《美人坡》《風塵誤》《朱熹別傳》,影視作品《山雨》《青樓情殤》等曾獲廣泛社會好評。作品獲國內外多種獎項,《美人坡》獲2006全國優秀長篇小說一等獎。《風塵誤》為八屆茅獎入圍作品。《星月念》獲首屆中國圖書獎。作品被譯多種文字至國外,選入《高中語文教材》《中國新文學大系》《大學語文課外閱讀》《百年中國散文經典》等。當代著名詩人公劉評價“筆尖上流著作者自身的真血,真淚,點點滴滴,必將滲入讀者的良知,一如春雨之于土地。只有這樣的作品興旺起來,散文復興的口號,庶幾可望變成現實。”(《星月念》序)。當代著名作家魯彥周稱其散文是“散文中的精粹”(《淮上風情》序)。
原標題:《風情 | 我愛多倫路 | 劉湘如》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