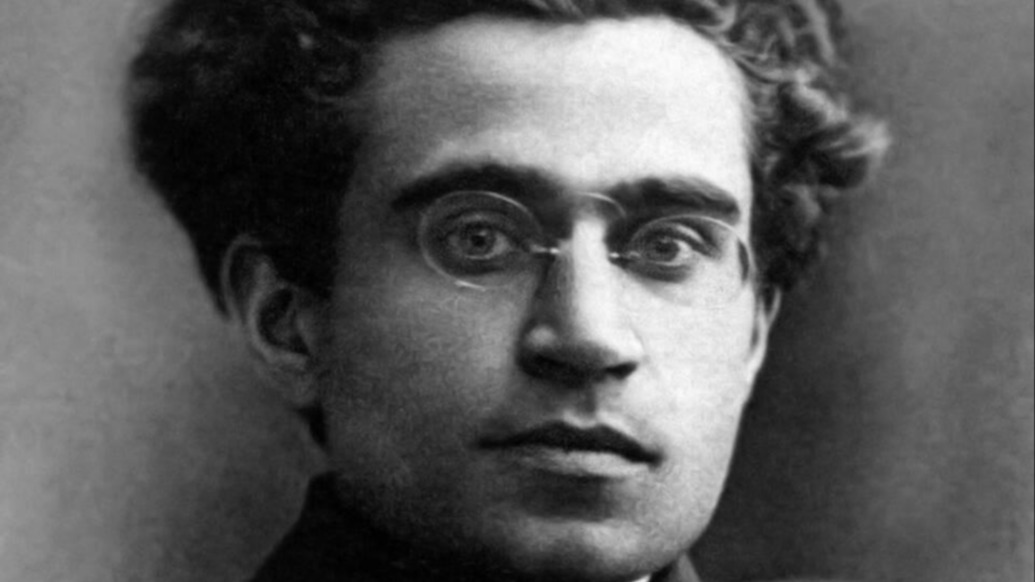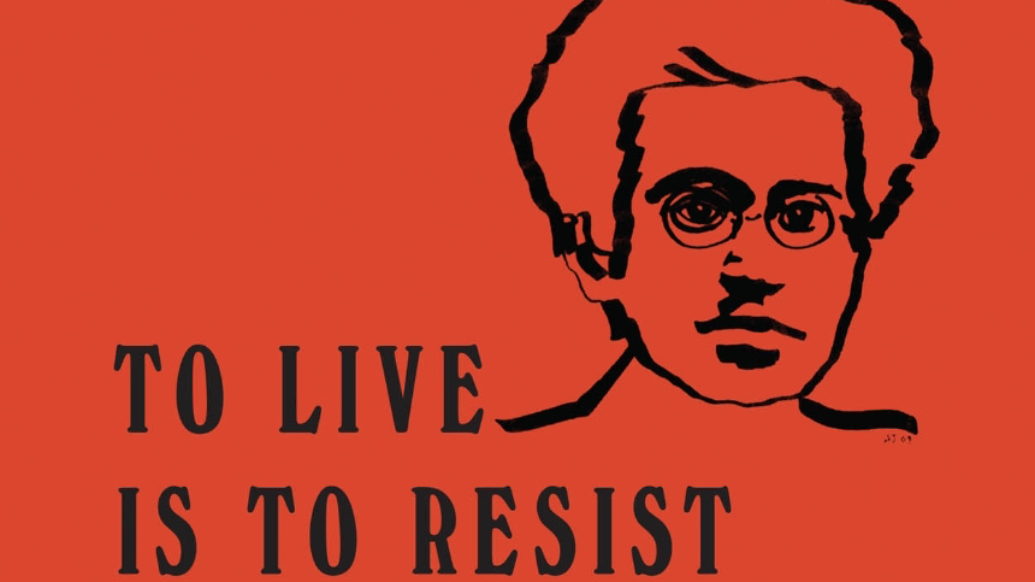- +113
光頭黨、電子樂、前沿亞文化:歐洲極右翼的“反抗運動”
斯蒂凡·弗朗索瓦(Stéphane Fran?ois)是一位法國的政治學、思想史學者,關注歐洲激進右翼和新右翼的文化策略。他的研究對象包括:作為亞文化的光頭黨文化,所謂“反抗文化”的微妙形態,一種稱為Gabber的電子音樂文化,新異教主義、秘契主義和歐洲激進右翼、新右翼之間的關系。針對歐洲極右翼的“反抗文化”形式,澎湃新聞特約記者李丹在法國對弗朗索瓦進行了專訪。

法國極右運動的政治光譜是復雜和多樣的,不同的陣營、團體間甚至表現出彼此對立的意識形態:既有新異教主義者,又有基督教徒;既有雅各賓派,又有地方主義者;既有反西方主義者,又有親西方者;既有支持經濟自由主義的人,又有反資本主義的人。
弗朗索瓦試圖呈現其中的復雜性,例如革命話語怎樣被移植到反移民的極右話語之中。艾約布(Serge Ayoub)在1987年創建了“國家革命青年”組織。他在經濟層面上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和反資本主義的,用這些主題來吸引脆弱的年輕人參與他的運動。失業的年輕人想要一個更左翼、更安全、更多福利的政權。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希望把所有的移民、外國人都排除在國家邊境之外。這就是弗朗索瓦所說的“怨恨的社會主義”:充滿種族主義、拒斥心理和對他者的恐懼,其宣揚的社會主義只保留給同一種族的國民,即白人。
對于最激進的組織來說,作為移民的法國人并不是真正的公民。在20世紀90年代,國民陣線的二號人物布魯諾·梅格雷(Bruno Mégret)想要建立基于”血統“的權利概念,禁止雙重國籍,“法國人”首先是一個“本土法國人”:他們對公民權和國籍的概念是基于種族的。有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的排外主義針對的是意大利人、波蘭人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種族主義開始污名歐洲以外的人口,而歐洲人口的流動不再被視為移民。
新一波的法國光頭黨運動扎根于巴黎地區、皮卡第、北加來、盧瓦爾河、阿爾薩斯和洛林這些老工業區,這些地區通常遭受了全面的去工業化浪潮。弗朗索瓦發現,這里的政治文化一方面是非常左翼和反資本主義的,一方面又是勒龐主義的。一方面人們充滿保衛工人、反對雇主剝削的愿望,另一方面拒斥移民,把后者看成“偷”工作的人。其成員通常是來自平民家庭的非常脆弱的年輕人,父母通常接受社會救濟。他們的文憑較低,屬于農村和城郊地區的無產階級。大多數情況下,成長于父母中只有一人工作的家庭。
在極右運動中,這些年輕人首先認為自己分享同一個意識形態,其次分享同樣的社群心理。他們處于一個相對封閉的社群,他們的“反抗文化”也是一種封閉的“反抗文化”,對周圍的世界不停發表暴力的言論,同時熱衷party、喝酒或吸毒。弗朗索瓦在皮卡第觀察了超過400個年輕光頭黨的博客,發現它們有著同樣主題:拒絕移民,“以法國人的自豪感和反資本主義制度來保護他們的兄弟、父母、家庭免受危機蹂躪”。

他們的音樂叫做Gabber,在荷蘭語中是“朋友”的意思,來自意第緒語。Gabber來自Techno,也被稱為是硬核Techno,從起源上來說是一種富有攻擊性的電子音樂,節奏感極強。Gabber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比荷盧經濟聯盟,但Gabber光頭黨在千禧年之際才誕生,并在法國的北部發展起來。弗朗索瓦分析了它的起源、意識形態的基礎以及和極右黨派的關系。這樣的音樂讓一些青少年參與政治活動,而不是相反。“一個Skrewdriver(“搖滾反抗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著名樂隊)演唱會比一個長時間的動員演講更有效。”從這個角度來看,“革命民族主義”者一直處于亞文化的最前沿。
弗朗索瓦在其著作《歐洲音樂:右翼亞文化民族志》和多篇文章中,不僅研究極右的音樂文化,還研究極右的文學、藝術、色情、電影文化的方方面面。事實上,極右運動與其他亞文化群體相似,但同時增添了身份認同:種族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意大利的CasaPound運動是觀察“反抗文化”場所的經典案例,他們在歐洲舉辦大量音樂會、表演、街頭藝術進行“反抗運動”,但這卻是一個極右組織。這個組織以詩人龐德(Ezra Pound)命名有雙重意義:他的“詩篇”為前衛藝術所看重,他的“殉難”為新法西斯所看重。弗朗索瓦稱,朋克一定是左翼的或極左的,也是一個常見的誤解。
以下是對弗朗索瓦的采訪。
澎湃新聞:你說極右有時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共產主義的,而是主張“第三條道路”的。 那么我們仍然可以使用傳統的左右劃分方式嗎?
弗朗索瓦:盡管某些右翼分子也接近革命民族主義思想——在此我特別想到的是阿蘭·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主義——但“左/右”劃分仍然運作良好。
“革命民族主義”創始于1962年3月4日在威尼斯召開的歐洲新法西斯主義團體大會。 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承諾成立“一體化的歐洲民族主義政黨”。 這個來自歐洲民族主義潮流的聯盟本來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探索“第三條道路”,既不同于蘇聯的共產主義,又不同于美國的資本主義,號稱打通極左和極右。革命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把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和社會主義的社會觀相結合的運動,拒絕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共產主義,因此也就是“第三條道路”。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反對自由主義,他們認為它傾向于打破邊界,混合民族和文化,使其獨特性消失。他們的思想在拉美和中東等民族主義革命中具有回響。
右翼激進主義的“第三條道路”首先是一種專制的、等級的反資本主義,從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運動中繼承下來,并混合了60、70年代的左派思想。 它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軍營社會主義”(socialisme des casernes),有時候被朝鮮所吸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歐洲和美國的“革命民族主義”組織不得不更新他們的思想資源和知識分子資源。他們開始向極左那邊尋求,特別是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議題。這并不新鮮。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些德國民族主義運動和理論家(比如恩斯特·榮格爾、恩斯特·尼采)就在觀察蘇聯對年輕人進行政治鼓動的方式。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些團體受到反殖民主義思想和民族解放的啟發,如古巴或切·格瓦拉。 今天,他們受到了查韋斯(Hugo Chavez)的啟發。
關于你的問題我想說,一個人必須在智識上誠實,明確地界定“左“與”右“的含義:不存在一個左派, 只有各種左派,就像不存在一個右派,而是各種右派。
澎湃新聞:你對極右團體音樂的研究是非常有趣的。極右亞文化的音樂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從60年代的ska,到80年代的朋克或Oi!,再變成硬核Techno(Gabber),這個過程是非常有趣的,你能再多談談嗎?
弗朗索瓦:Oi!是一種朋克音樂,原來流行的流行意識形態是工人階級的反叛,歌詞話題包括失業、工人權利、警察和其他當局的騷擾、政府的壓迫,還涉及街頭暴力、足球、性和酒精等不那么政治的話題。后來一些粉絲卷入了國民陣線(NF)等白人民族主義組織。“搖滾對抗共產主義”(RAC)是白人力量/白人至上主義運動的發展,與Oi!有相似的音樂和審美特征。

事實上,革命的右翼團體、革命民族主義者,一直在尋求創造自己的文化。音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一個理論化有時過于簡潔的環境中。音樂起著統一和團結的作用。這些活動積極分子一直在尋找節慶性的、充滿節奏的音樂,他們找到了ska(來自牙買加),然后是Oi!和搖滾對抗共產主義,然后從1990/2000年代起Gabber一統天下,這是一種節奏性特別強的Techno,時而充滿暴力。 從Oi!到Gabber的演變與Oi!提供的非常糟糕的形象相聯系,Oi!已經基本上被認定為是暴力和極右的音樂......今天,Gabber也受到這種負面形象的影響,Gabber的粉絲們把自己與極右區別開來,以此保住名譽。
澎湃新聞:在之前的采訪中,你說過,極右派組織已經摒棄了暴力的方式,旨在產生最大的媒體可見度。“法蘭西行動”這樣的老牌極右組織也在采用這樣的策略,“對身體對抗的贊美依然存在,但身體上的暴力被引導了,包括創建適合街頭格斗、拳擊等武術運動俱樂部。”我注意到在Antifa也有類似的拳擊俱樂部,在法國、意大利都存在,Antifa的音樂也同樣是嘻哈,這意味著Antifa運動難以創造出自己的政治語言嗎?
弗朗索瓦:不,事實上恰恰相反:激進的極右團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模仿Antifa組織,試圖創造適合自己的文化。這在“革命民族主義”團體那里尤其明顯。最好的例子是意大利的CasaPound,可以看到一個革命民族主義對左翼占屋運動的挪用置換。

革命派極右群體對極左文化非常感興趣。 正如你所說,他們往往有相同的音樂文化。 在1960-1970年間,極右激進分子與Antifa和托派激進分子有著相同的“外表”:長發。
我回到你的評論的第一部分:整體而言,暴力事件已經被拋棄,轉而支持媒體行動主義,換取媒體曝光度,而一些“行動”能帶來被禁止的快感,但并不會妨礙他們裝滿犯罪記錄的事業。
澎湃新聞:有人指責德國當前的Antifa運動更多是一種時尚風格、音樂場景和俚語,發揮著反主流文化的作用,卻并沒有成為在更廣泛社會中根植于民眾的運動。左翼亞文化和大眾社會運動不是一碼事。你怎么看?法國Antifa運動有什么特點?
弗朗索瓦:反抗文化總是一種邊緣化的運動......一種反抗文化,不能成為一種群眾運動,因為反抗文化在其實踐和理論上總是有非常激進的一面。如果我們要吸引更多的積極分子,成為群眾運動,就必須抹去這些因素,達成共識。當一個人聲稱有革命思想時,這是不可能的......然而,這種共識在思想和姿態的重新組合中是必要的,音樂、衣著和語言方面只是非常次要的。
第一次反法西斯運動是20世紀30年代在法國出現的,在法國共產黨影響下的那些地區出現的。今天,反法西斯主義來自極端左翼運動:當代法國的Antifa運動是多元的,包括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自由派的共產主義者、另類運動分子......Antifa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對國民陣線崛起的反應。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它是圍繞著兩個主要的組織的:Ras l’Front和No Pasaran。今天,它不再是結構化或統一的。除了這些差異之外,還有一些共同點:反法西斯運動者,拒絕與政府中的左派有任何聯系,等等,但是這種運作更具“親和力”。
澎湃新聞:Antifa在馬賽和“法蘭西行動”(L'Action fran?aise)這樣的極右組織之間的緊張關系還在繼續,你如何看待馬賽的局勢?該怎樣理解極右中的君主主義者?在后革命語境中,君主主義聽上去反動、不可思議。
弗朗索瓦:Antifa組織和極右派組織之間的矛盾趨于增加。漸漸地,我們回到了20世紀80年代的緊張狀態。經過一段時間的平靜(1990 - 2000年)之后,又出現了一系列活動和對抗的復興,這一代的活動和對抗已經與上一代不同。新一代更具侵略性。
君主主義者試圖恢復法國的君主制。他們可以劃分為兩種:1、正統派(légitimistes),那些希望重新回到正統家庭王位的人——即路易十六的后代,也就是最后一個“正統”國王查理十世的后代。2、君主主義者,那些只想要返回君主制的人(查理十世的后代或波旁王朝)。它是一種君主制鄉愁。
跟第二種相比,第一種堅持更明確的王位繼承關系。
法國主要的君主主義組織是由查爾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于1898年創立的“法蘭西行動”。這是一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組織,當然也是法國最古老的極右派......我借此機會提一個觀點:當君主主義者,并不一定就是反動的。有一些君主主義流派,比如《紅百合》(Lys Rouge,一份君主主義刊物,最初與1940年Jean-Marc Bourquin領導的君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有關,后來1970年代又再出現)或者“新法蘭西行動”(Nouvelle Action Fran?aise,1970年代試圖建立君主立憲制的政治運動,《紅百合》是其刊物)。他們懷念君主制,同時并不敵視左派政治。他們想要一個國王,同時想要左派政治。包括上述團體在內的一些人是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的選舉的。我認識其中一些變成了社會主義活動家的人。
另一方面,把極右派武裝分子視為反動派是正確的,“法蘭西行動”的“革命”傾向已經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老實地講,保皇派不過是今天的軼事......他們的動員能力并沒有那么強。只是有幾個他們的活動家特別的吵鬧,被賦予了關注度。法國在激進權利方面的主要趨勢,還是“革命民族主義”和認同方面的。
澎湃新聞:怎么講?
弗朗索瓦:歐洲的極右主要有兩股潮流,具體到法國也是如此:一股是革命民族主義者,是法西斯主義的演變,融合了一些極左的元素+反猶主義; 一股是身份認同主義者(identitaires),是把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堅持的那些認同方面的主題(文化、民族、種族)加以演變。
澎湃新聞:總的來說你對現在法國極右的狀況怎么看?
弗朗索瓦:首先,距離20世紀30年代的那些重要運動還有很遠的距離,所謂重要運動包括“法蘭西行動”在內的同盟、法西斯團體或準軍事組織。其次,現在跟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規模可見的極右暴力也是不能比擬的,那時有“新秩序”(Ordre Nouveau)或“西方”(Occident)這樣的新法西斯組織。

凱爾特十字勛章是新秩序的徽章,新秩序的信條是“愛國主義的復興、價值的等級制度以及家庭和教育的恢復”。曾在1973年發起“阻止野蠻的移民”行動,和左翼共產主義者發生暴力沖突。

“西方”同樣使用凱爾特十字勛章,1960年代的極右組織,強烈反共,也反戴高樂當局,一些成員后來成為右翼黨派的著名成員,甚至獲得了部長職位。
我得說,法國的極右還算不上崛起。 只有幾百名激進分子非常喧鬧,有時非常暴力,尤其是個別人士。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