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跨界共學實驗室 | 閆梓萌:讓“天坑專業”帶我認識這個世界
以新聞為軸,丈量不同學科的精神氣質;以共學為旨,打破專業分類的固有邊界。
這是一個沒有局限的共學實驗室,在新聞的底料里加入不同學科的調味,煎炒烹炸出各具特色的跨界大餐。我們等待著各專業大廚們來“掌勺”,我們期待著斑斕色塊的相遇、碰撞與炸裂,我們渴望著純凈靈魂的真誠、勇氣和吶喊。
實驗室邀請兩位熱愛新聞的主理人,邀請十余位不同專業背景的朋友,組成共學小組,分享與體驗多學科交流的魅力。
/專業分享/
2022年7月10日
主題:讓我的“天坑專業”帶我認識這個世界
分享人:閆梓萌
就讀于北京語言大學西班牙語專業,目前于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學語言學系交換。副業是獨立作者,業余鼓手。

廣義:對大眾而言,通用語一般是指英語,其他語種則是非通用語言,統稱“小語種”。
狹義:外語語種可分為通用語和非通用語。其中,通用語是指聯合國的6種通用工作語言,即漢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阿拉伯語;非通用語則是聯合國6種通用工作語言以外的語種,這些語種為嚴格意義上的小語種。

小語種專業在國內高校各學科中屬于比較新的專業,并且主要集中發展在一些外國語類大學。
以西班牙語專業為例,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專業創建于1952年,是國內第一個西班牙語教學單位;1979年招收全國第一個西班牙語專業研究生班,1981年成為碩士學位授予單位,1996年又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授予權。
其他小語種專業發展較早的高校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南京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等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設西班牙語專業。
一些綜合類院校則起步較晚,如四川大學于2010年開設西班牙語專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之前與拉美國家的外交關系等原因,臺灣地區的西班牙語專業起步也并不晚,如臺灣輔仁大學于1964年就已開設西班牙語專業。
關于課程設置,以我在北京語言大學的學習為例。大一和大二兩年比較注重基礎,專業課設有“西語精讀”、“西語聽力”、“西語泛讀”、“西語口語”等注重培養語言能力和對語言對象國的普遍了解的課程。

閆梓萌的學期課表
大三這一年我選擇了出國交換,學習的課程則可選擇性更大一些,我基于自己的興趣選擇了兩門西班牙方言課程:加利西亞語言文化及加泰羅尼亞語言文化;此外我還選修了意大利語、西班牙文學史、歐洲文學人物等課程。大四的課程則是根據我們自己的發展意愿選擇,有西語口譯、拉美國別研究、西語文學選讀、經貿西語、語言學等課程。

閆梓萌的學期方案計劃

近幾年小語種似乎成為了一個許多人“勸退”的“天坑專業”,豆瓣上的“大學后悔學小語種”小組已有三萬多組員。而小語種專業被稱為“天坑專業”的原因主要有:
適用對象國有限,有些專業如緬甸語、尼泊爾語等對象國專一,會導致就業范圍局限,甚至容易受到社會問題、政治動蕩等多因素影響。
學科發展時間不算太久(尤其一些新興語種)導致教學體系成熟度不高,一些同學會對學習內容感到困惑。
國內研究生招生名額極少,競爭激烈。
部分相關職業存在報酬與付出不成正比的情況,如書籍翻譯。
我所學習的西班牙語專業在小語種專業中算是發展相對成熟,就業范圍也相對更廣的“幸運”專業;不過從就業及其他實用性的角度來看,小語種確實并不是一個百分百盡如人意的專業。
但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我毫不后悔并且非常慶幸我選擇了這個專業,大學四年以及更遠的以后我的人生中會發生很多事情,我會不斷改變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也會不停習得新的能力。因此我個人更多是把大學本科四年選擇的專業,當作一個我了解這個世界的切入點之一,而不是有利于我去適配某一項工作的培訓課。在我的學長學姐中,有一些成為了專業領域的佼佼者,但也有一些最后做了和專業關聯不大的工作,譬如有法語專業的學姐讀碩士去了法國讀藝術、有意大利語專業的學長在校期間負責學生會宣傳部的攝影工作,畢業后去國外做了攝影記者、有酷愛研究游戲的西班牙語專業的同學現在去了游戲公司設計游戲……

我在大學期間接觸過的語言有西班牙語、日語、蒙古語、意大利語、加利西亞語、加泰羅尼亞語和阿美語,了解這些語言文化的過程也對我的許多方面產生了影響。
(一)西班牙語
因為很喜歡文學,所以大學期間除了校內的課程以外,我接觸西班牙語語言文化的主要途徑就是文學閱讀,而這也對我目前在做的工作產生了影響。
大二時我很愛讀波拉尼奧的小說,無論是他的文筆還是其中的情感都令我產生很大共鳴,恰好那時我剛剛失戀,情感豐富,就寫了一篇受波拉尼奧影響很大的短篇小說,后來發表在了澳門日報的鏡海版面。第一次寫作就得到了發表的機會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后來我繼續進行小說和詩歌的寫作,并多次發表在澳門日報、臺灣聯合報等華語媒體。
大三時我加入了“Babel巴別塔官方”公眾號的文學部門,負責撰寫介紹拉美當代作家的文章。后來我發現一些優秀的拉美作家在社交網絡上也很活躍,就試著用西班牙語給他們發私信,邀請他們做一些對話采訪,對他們的作品做更多的解讀,并且請求他們授權給我翻譯他們的作品呈現給中國讀者。很多作家都爽快地答應,我也很開心以這種方式去做一些能夠打破國別邊界的交流。
部分采訪文章鏈接:
先鋒 | 專訪:弗蘭克·巴艾斯——「自加勒比寫作」
先鋒 | 專訪卡洛斯·格里格斯比:海邊的少年詩人
先鋒 | 專訪英格里·布林加斯:于暴力與愛中作詩
先鋒 | 「混沌與桂冠」——拉奎爾·薩拉斯·里維拉
(二)蒙古語
大二時我選修了蒙古語課程,老師是蒙古人,上課經常會提到許多我未曾聽聞的蒙古族文化;也有許多少數民族的同學選修了那門課。在這樣的課堂環境里,我關于民族的理解也跳出了我此前僅有的“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只花”的印象,有了更多的思考。當時結課時我自己寫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我是這樣回憶第一堂課的:
“而后就開始了看名字認民族的環節。蒙語老師是蒙族人,所以一眼就識出班里的蒙族同學,親切地說:“這是我們蒙古族的孩子。”我難免心頭一動,意識到我從來沒被人說過是“我們漢族的孩子”,或許是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的多數,對民族的概念反而弱化起來了吧。老師用蒙語與他們挨個交談,我越發無聊起來,已經從椅子上挪到了床上躺著。當然我無聊并不是因為對蒙語不感興趣(不然就不會選這門課了),我的無聊是因為,我感到這一切在慢慢與我無關。望著天花板,聽著電腦里不斷傳來的蒙語會話,我在想,當我在內地與漢族同學聊著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時,一旁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同學,會不會也偶爾心生與我此刻類似的無以歸屬感呢?”
快要結課時,我選了一個周六,起了很早從北京坐車到呼和浩特,去親眼觀察我學了一學期的語言背后的文化。在那之后我沒有繼續學習蒙語,但是每當我遇到少數民族的同學,聽到與少數民族相關的事情,我都會心生一種親切感,也會更加在意他們在內地有時需要面對的不安與陌生感。
(三)加利西亞語
大三這一年我一直在西班牙加利西亞大區的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學語言學系交換學習,我也在系里選修了一年的加利西亞語言、文學、文化課程,對加利西亞的語言、歷史、人文都有了更深的了解。而這些學習給我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我意識到我抑制不住地對這個地方產生了認同感,和別人介紹它時我是帶著些許的驕傲和歸屬感在講述,而當它發生一些新聞事件時,我也不是以一個外鄉人的視角,而更多是以一個故鄉人的親切在看待它。
選取一段我之前寫的留學分享文章里的話在這里分享一下:
“加利西亞人的祖先是凱爾特人,至今在許多地方都能見到凱爾特人留下的戰壕。十九世紀時,加利西亞曾興起方言文化保護運動,來抵抗卡斯蒂利亞語的侵入導致的加利西亞語的衰退,這場運動便是被命名為“凱爾特主義運動”,來提醒加利西亞人不要忘記自己的文化。這場運動的代表人物Eduardo Pondal也是加利西亞頌歌歌詞的作者。
加利西亞的文學資源很豐富,有許多堅持用本土語言寫作的優秀作家,其中Rosalía de Castro最為著名。我也想向大家推薦一個加利西亞音樂組合:Milladoiro,他們許多歌曲的歌詞都是加利西亞一些優秀本土詩人作的詩。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的歌,是上課時老師給我們放的“Moraima”,曲調悠揚溫柔,在圣地亞哥下雨時播放這首曲子,歌手深情地唱著“Lévame, Moraima(帶我走吧,莫萊瑪)”,是我最愜意的時光。”
還有許多其他語言學習的體會,譬如我從加泰羅尼亞語言文化的學習里理解了這個總是要鬧獨立的地區的人民的自由與平等精神、從臺灣土著民族的語言學習里了解到了不同的歷史觀、從日語的語言學習里感到了他們的禮貌謹慎……我想,對于我來說,這也是學習冷門小語種的意義:這些收獲不會讓我直接得到能夠適配一項工作的能力,但是已經化成我思想里的一部分,并在我以后工作生活的每個瞬間無聲地顯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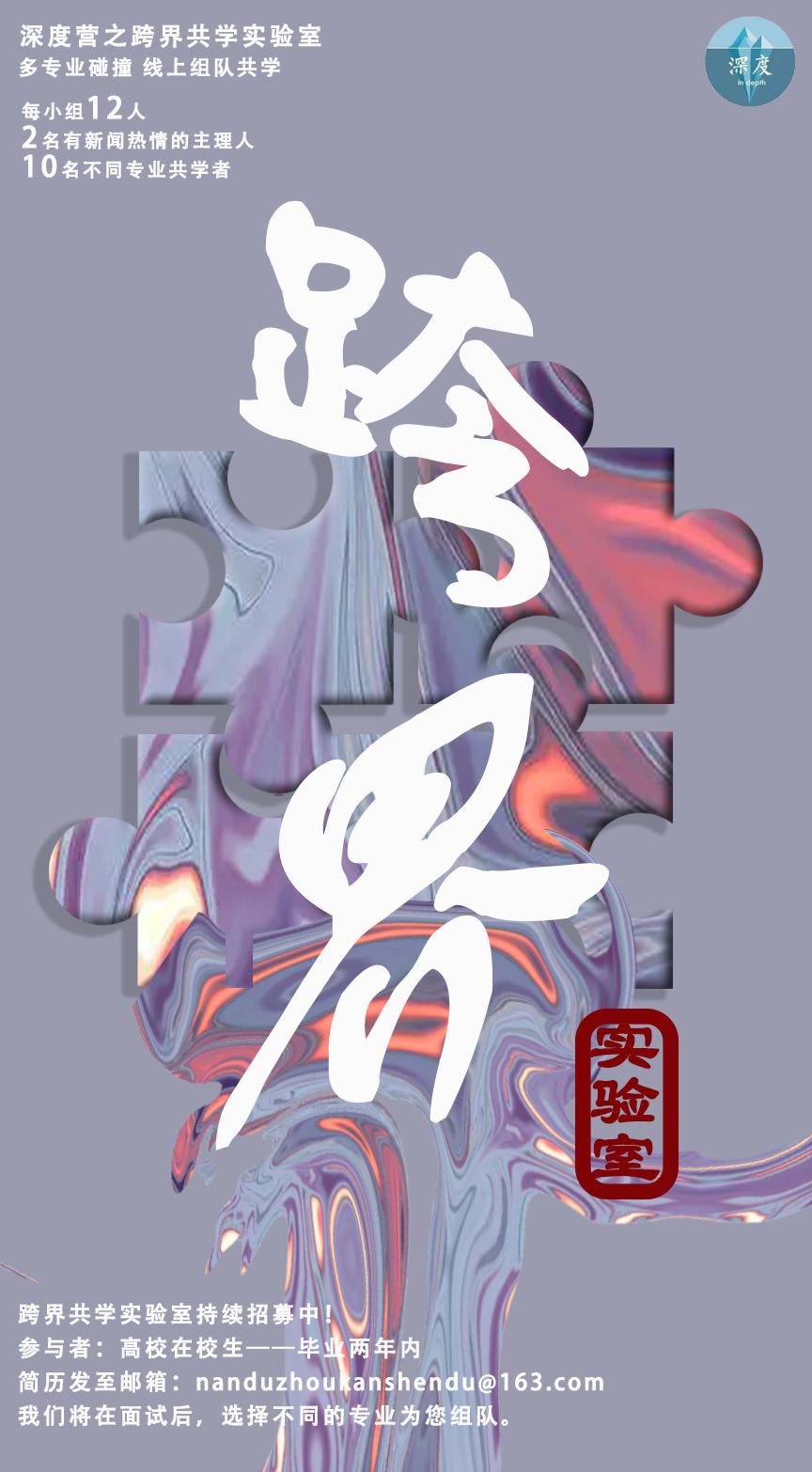
原標題:《跨界共學實驗室 | 閆梓萌:讓“天坑專業”帶我認識這個世界》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