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咖啡之“惡”——越南,黑暗的中心
20世紀80年代,越南是位居世界第42位的咖啡生產國,前法國殖民地的咖啡莊園里種植著大量優質的羅巴斯塔咖啡。后來新政府將這些咖啡種植園收歸國有。越南出口的67000袋咖啡相對于咖啡的世界出口貿易總量來說,微不足道。
2001年,越南咖啡產量達到1500萬袋,躍居世界第二。這種大幅增長被認為是全球咖啡價格暴跌的原因。極力否認任何估算錯誤的世界銀行也由于曾為迅猛增加的咖啡種植籌集資金而受到指責。同時還出現了一些無法證實卻又持續存在的謠言:咖啡作物可能遭到了二噁英的污染,這是美國在越戰期間大面積噴灑橙劑留下的后遺癥。咖啡黑暗的歷史又重演了,越南就是它的舞臺。

越南婦女采摘咖啡
無聲的陰謀——越南的橙劑之痛
1859年,法國攻陷西貢,這標志著越南殖民地化的開始。這次襲擊是拿破侖三世時期法蘭西帝國侵略成性的資本主義戰略的公然宣示。沒有一個道貌岸然的歐洲國家不曾卷入在亞洲的殖民行動,法國也不例外。數年之內,法國已經控制了被他們更名為印度支那的整個地區,到1887年,又將今天的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一同置于印度支那聯邦的統一管理之下。法國在很短時間內建立了殖民統治的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鐵路、運河、港口以及法國人控制的管理機構,從而坐享印度支那的礦物、煤、稻米和橡膠等自然資源和農產品,但其中并不包括咖啡。咖啡雖然在1887年被引進越南,但法國殖民時期種植的咖啡似乎僅僅是為了滿足當地的消費。印度支那似乎為法國的制造商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但那里的經濟并沒得到多大的發展,因為法國投資商人只想取得快速的回報,很少將所得利潤用于再投資。
法國人和他們的越南走狗侵吞了通過建設灌溉系統開辟出來的稻田。盡管從1880年到1930年,越南的水稻產量增長了3倍,但農民平均水稻消費量卻在減少。和穆爾塔圖利在《馬克思·哈維拉,或荷蘭貿易公司的咖啡拍賣》中對貧困的描述一樣,無地的農民被迫去做沒有報酬的工作來抵償法國人因為資助越南的基礎設施建設而強加給他們的稅收,而這些農民根本就沒有從這些基礎設施中獲益。普通民眾并沒有因為受到殖民壓迫而得到教育、公平或衛生保健等方面的補償,而且越南人民被排除在參與新經濟活動之外,因而無法改善自身的生活狀況。總而言之,對于歐洲殖民列強的由來已久的種種指控,都可以從法國對待越南的方式中得到證明。
在這種情況下,毫不奇怪,民族主義運動不斷興起,又不斷被鎮壓。直到1930年,胡志明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之后,民族主義運動才得以持續展開。胡志明早年是一名水手,遍游各地,后來定居在巴黎,并在那里加入了法國共產黨,最后回到了越南。盡管共產黨最初的幾次起義遭到殘酷鎮壓,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們的活動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而就在那時,整個印度支那變成了由法國人管理著的日本占領區。作為法國維希政府投降政策的東方翻版,越南的法國人與日本人相互勾結,允許日本人駐軍印度支那,將印度支那作為日本擴大“大東亞共榮圈”的跳板。只有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在二戰中通過暗中傳遞情報等方式,協助盟軍反抗法國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1945年,日本戰敗,越南出現權力真空,胡志明趁機在北方掌握了實際權力,而法國殖民者則控制著越南的南部。這種分裂局面奠定了后來越南戰爭的基礎。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同溫斯頓·丘吉爾的戰時協商中,曾經堅持認為英國應該放棄他的帝國體制。雖然美國總統聲稱這是出于道德考慮的要求,但其目的明顯是為了給美國的商品開辟新市場。在他建議英國撤出的地區中,當時并不存在真正的共產黨掌權的威脅,后來只有馬來亞成為一個“例外”。但是,美國并沒有期待法國人放棄他們對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因為,很顯然,如果法國人從那里撤出,胡志明就會掌權,并且因為胡志明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所以他“沒有資格”協助擺脫殖民主義枷鎖。此外,胡志明是一張潛在的多米諾骨牌,能引發一系列準備就緒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于美國說來,那完全可以構成開戰的理由。法國由此從美國那里得到了援助和武器支持。經過一段充滿摩擦的共存時期之后,法國發動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結果,這次戰爭造成了越南的正式分裂,北方正式成為越南民主共和國,胡志明成了這個新生國家具有西方化與現代化意識的統治者。他公開稱贊美國,并將美國憲法的一些內容納入自己國家的制度之中。而南越卻落入極權統治之下,該政權很大程度上利用北方對它的威脅而向美國乞求援助、贏得好感。盡管在越南,咖啡不是驅動性的經濟力量,但曾在戰后的中美洲造成巨大災難的模式也還是出現在了越南。南越對異己力量的無情鎮壓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支持北越的政治力量,各種援助和起義者紛紛從南方流向北方,在那里尋求越南的重新統一。1963年11月1日,肯尼迪(John Kennedy)總統授權發動軍事政變,暗殺了南越的吳庭艷總統,繼而任命一幫腐敗無能的將軍執政,并通過越來越多的援助和武器裝備來扶持這個政權。只要這個政權能夠被用來對付北方,美國對這個政權內部的所作所為一律聽之任之。1963年年底,17000名美國軍事顧問被派駐到南越,去支援處于外部武裝力量和內部的人民民族解放陣線雙重壓力之下的南越政權。
1965年,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下令轟炸北越,當年,有75000名美國陸軍進入了越南南部。到1968年上半年,進入越南的美軍人數達到了50萬。美國國民對此強烈不滿,從而改變了此后幾十年間美國戰略的走勢。約翰遜意識到自己無力對付這一局勢,于該年5月開始在巴黎舉行和談。那一年是大選年,而且最近才浮出水面的一個事實是,共和黨的候選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經暗中破壞這些和平談判。尼克松向南越政權許諾,如果他當選總統的話,他會給南越政權更多的支持。然而尼克松當選后的共和黨政府并沒有履行承諾。越南戰爭又持續了3年,損失了3萬名美軍士兵和不計其數的越南人的生命。從越戰爆發到1973年美國顏面盡失地從越南撤軍,美國向越南投放的炸彈數量甚至超過了美國在二戰中投放的炸彈總數,平均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攤到了1枚500磅的炸彈。這場戰爭奪走了200萬越南人的生命,從另一個角度看,十年越戰美國耗費了至少2500億美元。戰爭代價沉重,卻毫無意義。
越戰的失敗在美國人心頭罩上了一層此前美國為建造美利堅帝國而采取的所有干涉行為都不曾造成的濃重陰影。也有人認為越戰的失敗并不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至少實現了確保越南不再出現一個另類政治體系的戰略目標。越南被戰爭摧殘得滿目瘡痍,直到最近仍被看作是一個經濟問題叢生的國家。
戰爭的陰影不僅困擾著美國人的心靈,許多美國退伍老兵由于接觸了橙劑,健康受到了實質性的損害。美國軍隊決心要阻止北越的共產主義者進入南越,認為越南茂密的叢林和濕地紅樹林為北越共產主義者提供了掩護。他們幾乎不假思索地判定,只要把這些植被清除,就能除掉自己的對手。這就導致了1961年到1973年間發生在南越的綜合性化學清除植被事件。這種戰略會引起何種后果從來沒有被充分考慮。橙劑被隨意地灑到叢林和農田上,明知道這會導致平民的痛苦。即使這些藥品對平民的影響不是直接的,只是造成平民生計資源的破壞而不是對健康的摧殘,難道這種噴灑行為沒有違反禁止化學武器條約么?隨后有大量證據表明,橙劑對人類健康會造成迅速和直接的危害。但問題是,我們竟然說不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這種化學品究竟是不是違法的。這個問題對于我們當下的時代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因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部分地以它配置有化學武器為理由的,美國在哥倫比亞的所謂“反毒品戰爭”也一直使用了化學武器(有諷刺意味的是,那次行動再次涉及世界上最出名的化學制劑公司孟山都)。關于美國蓄意使用化學武器并持續這么做的看法,并不僅僅是出于學術興致而提出的。

1966年5月,越南戰爭期間,一架美國空軍C-123運輸機沿著公路低空飛行,在道路兩側的叢林中噴灑化學脫葉劑,以防敵軍隱蔽在密林中發起伏擊。
橙劑因其包裝的圓筒上標有橙色條紋而得名,是由陶氏化學(Dow)、鉆石三葉草(Diamond Shamrock)和孟山都等公司生產的。它是二氯笨氧乙酸和三氯笨氧乙酸這兩種除草劑的混合物。很久以來,一直有人指責說,在制造橙劑的過程中有一種名為TCDD的二噁英污染物濃度嚴重超標,但孟山都及其他制造公司卻不予承認。二噁英是許多和氯有關的工業過程(比如廢物焚化、化工生產、紙漿及紙張漂白)所產生的副產品。20世紀80年代早期,有消息披露說,咖啡過濾過程中使用的含氯漂白紙可能被二噁英污染,咖啡產業于是陷于一片混亂之中。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從1997年開始就認為,效力強大的二噁英(2,3,7, 8-TCDD)是一級致癌物,即“已知的人類致癌物”。如果接觸到二噁英,就會引發嚴重的生殖和發育問題(這種影響的程度要比它的致癌作用低100倍),破壞免疫系統,擾亂荷爾蒙分泌。而且,二噁英極其頑強,在自然環境條件下分解極為緩慢,會對整個食物鏈造成影響。二噁英是脂溶性生物沉積物,會在魚類、家禽和牲畜之類的哺乳動物體內大量累積起來。越南人最喜愛的食物——鴨子,也易受二噁英類生物沉積物的感染。
孟山都公司全力挑戰支持二噁英有毒這一判斷的科學證據的可靠性。有報道說,有一場關于橙劑的針對包括孟山都在內的7家公司的訴訟,最后以這些公司向原告賠償1.8億美元和解。這些公司先前曾經否認使用橙劑會導致健康問題。美國有許多組織致力于調查有關橙劑的信息,并為那些證明接觸橙劑與引發疾病之間有直接關系的病例提供幫助。根據前面提到的那項和解的標準,美國退伍士兵每個月可以獲得2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補償金,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越南政府每月給受害士兵的補償為7美元。然而,美國軍事主管部門仍然盡力壓制關于接觸過橙劑的退伍老兵的人數的消息。更重要的是,他們否認橙劑曾經對越南人民造成了或者正在繼續造成任何健康問題。為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橙劑是兩國外交談判中的一個禁忌。有人曾推測,在20世紀80年代末舉行的兩國之間的首次對話中,如果有人提到有關橙劑的問題,美國會立刻退出談判。飽受戰爭蹂躪的越南人民現在終于發現,為了重建經濟秩序之類的目標,自己和他們的先烈們陷入了一個無聲的陰謀中。橙劑問題對越南人來說是個禁忌,對美國人來說也同樣如此。發現其中的原因并不困難,新聞界早就在廣泛地暗示:越南正在拼命重建國家經濟,因而極大地依賴于向世界市場出售本國的農產品和水生有殼動物。如果證明了這些出口產品中含有二噁英,越南就很可能再次遭受重創。
據估計,越戰期間約有5700噸或者說1200萬加侖橙劑被噴灑到南越地區,摧毀了那里14%的森林及50%的濕地紅樹林,紅樹林曾是價值頗高的木材來源。有450多萬英畝的植物遭到毀滅,給野生動物和生態環境帶來了災難,更不必說那些被噴灑到的可憐的越南人了。農場和小塊農田也沒有逃過厄運,從而引起了大范圍的貧困和饑餓問題。噴灑過橙劑的土地至少要10年之后才能重新長出植物。至今仍沒有一項徹底的調查完整地估算出噴灑橙劑帶來的健康代價。不過,加拿大海特菲爾德咨詢公司(Hatfield Consultancy Ltd.)的一項深入調查研究表明:在越南噴灑橙劑大約造成了4萬例死亡和一些嚴重的病例,還有50萬越南新生兒具有先天生理缺陷。二噁英通過污染土壤或水源進入食物鏈,并逐漸在人體組織中積累——這是對某個受到監控的“備受關注地區”進行調查得出的結果。這意味著,橙劑或二噁英導致的問題正在變得越發嚴重,而不是在逐漸消失。二噁英的諸多有害特性之一,就是它分解得極為緩慢。
有“毒”的咖啡與被奴役的第三世界
二噁英的問題是被悄悄地揭開面紗的,因而毫不奇怪,一直以科學面目而自豪的咖啡業早就已經調查過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大量涌入世界市場的越南咖啡中可能殘留有二噁英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對氯漂白過的咖啡濾紙中可能殘留有二噁英的恐懼曾突然導致咖啡產業陷入癱瘓。二噁英曾對咖啡意識產生過負面的沖擊,這使咖啡業的專家對相關信息小心回護,人們難以全面了解有關二噁英的信息,更促成了今天人們疑慮重重的心態。其實,所有證據都表明二噁英不是水溶性的,即植物并不能吸收二噁英,包括咖啡樹。但是,咖啡貿易仍對該問題倍感恐慌。2002年,一個咖啡科學家組織對該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報告說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據傳曾經呈交了這樣一份報告,因為,“一旦判定沒有什么可憂慮的,他們也就沒有理由不公開宣布了”。這個報告沒有被公布。這種自我防衛心態可能也是由美國一向存在的擾亂民心的現象造成的。根據美國咖啡協會的說法,有一伙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出于無人知道的原因,經常向媒體披露咖啡里含二噁英的消息。有一段時間,他們甚至散布完全虛假的謠言,說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已經開始對越南咖啡進行抵制。不論這個神秘組織的目的何在,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存在一個解決當前咖啡生產者所面臨的問題的方法,那么這個方法一定會是把整個越南的咖啡產業踢出咖啡市場。一旦這樣,咖啡價格就會迅速飆升。因此,這些神秘人物的存在是商業恐怖主義的跡象。它帶來的疑問是:遭受低價格沖擊的咖啡生產國會孤注一擲去捉弄市場嗎?或者,是某個胡作非為的財團想要趁機在紐約咖啡市場上大撈一把么?
美國本可以在使用橙劑造成的后果中汲取教訓,但是它卻再次重復了它所犯的這種錯誤,這令人難以理解。正如我們所見,在哥倫比亞的所謂“反毒品戰爭”中,除草劑的使用日益增加,造成了和使用橙劑之后類似的環境和公共健康問題。盡管美國一些科學家和辯論小組大聲疾呼,國務院向國會提交的報告(根據法律,這個報告必須在撥款之前提交國會)是片面和不充分的,報告中沒有做出“根除哥倫比亞古柯時空撒的化學制劑不會對人類健康安全和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的保證。但是該行動還是實施了。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想象中的地緣政治需求凌駕于所有其他考慮之上,而且無論結果如何,最終都由貧困的哥倫比亞農民來承擔負面的后果。有跡象顯示,一種使用最廣泛的除草劑——“蕩滌劑”會對咖啡作物造成污染。如果是這樣,美國國務院將來就得面對他們自己把毒藥從拉丁美洲引進給他們自己的公民的后果。

越南達拉特的咖啡田
有趣的是,咖啡產業總是不斷重現一種令人沮喪的歷史模式。咖啡喜在高原地帶生長,而熱帶高原是原始生態的最后一片凈土, 那里有茂密的森林、眾多野生生物和土著居民。因此,這三者總是咖啡種植面積擴大時的犧牲品。最近,在咖啡生產不斷擴大的越南內陸高地定居下來的柬埔寨族人抱怨說,他們不僅被從原來的居住地驅趕出來,而且被從紅河、湄公河三角洲地區遷居到此的越南人潮給淹沒了。一些人認為這是一種心機很深的政治策略,是故意讓他們遷移到柬埔寨邊境附近地區來構成阻隔柬埔寨對越南入侵的“安全帶”。就像我們在中美洲地區看到的那樣,將印第安土著居民從高原居住地驅逐出去的做法和咖啡產業的繁榮緊密相連,而越南似乎正在重復這種可悲的做法。
越南咖啡快速膨脹的生產規模和世界銀行有很大關系,盡管世界銀行極力否認這種關聯并發布措辭激烈的新聞來否定任何指責。和橙劑事件一樣,官方的內幕很難被揭開,原因是金融機構和越南政府本身都不愿意承擔造成世界咖啡市場價格暴跌的主要責任。假如從政府借款的咖啡小農的處境的確得到了改善,無論貸款是不是從世界銀行那里得來的,畢竟還算是一種安慰。然而,正是由于咖啡小農自身的“成功”,他們現在正不得不以只相當于生產成本60%的價格出售其產品,并陷入無力償還貸款的困境。此前,他們對咖啡業前景的盲目樂觀確曾刺激他們從政府那里貸款去種植咖啡。曾經一度欣欣向榮的越南咖啡產業正在快速萎縮,咖啡種植者已經意識到,以前認為十拿九穩的發家致富其實是不現實的。種植咖啡對高地脆弱的環境、遭到侵擾的野生動物、被驅逐的土著居民和沒有收入但債務累累的低地移出民所造成的摧殘,是難以估量的。不出所料,沒有人愿意為此承擔責難。
越南是“善意”發展計劃關注的焦點之一,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就是通過發展咖啡產業來促進越南的發展,目的則是改變與美國長期戰爭帶來的混亂和破壞。越南的主要資本是廉價勞動力,而這是越戰的直接產物。通過部署廉價勞工并將其納入發展規劃中,越南政府可以吸引世界銀行之類的金融機構對之進行投資,而世界銀行則為越南預示了一條進入全球貿易體系的切實可行的途徑。這是當今時代的殖民主義形式:富裕的債權人為了第一世界消費者的利益,通過投放貸款來榨取其他世界的廉價勞動力。世界銀行當然受控于擁有51%股份的美國財政部。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一樣,都是決定千百萬人生計的、未經選舉的華盛頓共識三巨頭的組成部分。這三個組織都受意識形態的驅使,沉迷于美國式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以及它被預期會帶來的收益。就越南及其咖啡產業的事例而言,世界銀行并沒有履行它的責任,從而造成了全球范圍千百萬人的苦難,而這對于那些在過去十幾年中追隨過它的指引的人們來說毫不奇怪。1999年,前任高級經濟師約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經大膽地建議世界銀行處理事情的手段不要過于強硬,結果被撤職。約瑟夫·施蒂格利茨的例子再次表明,對于世界銀行的那些最嚴厲的指責似乎都是真的:它給尋求貸款的國家開出“包治百病”的經濟藥方;為了西方大公司的利益而去賄賂政府的部長,使其將公共財產低價出售;向外國投資商開放金融市場,從而導致客戶信心動搖,當地銀行發生擠兌;由此造成的社會動亂又需要用強力手段去壓制;幫助當地銀行渡過無法償還西方銀行貸款的危機;在堅持給第一世界的農業提供補貼時卻不厭其煩地重復自由貿易的咒語,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施蒂格利茨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解決某國經濟問題的方案比作高空轟炸:一些人“在豪華酒店里冷酷無情地制定解決問題的策略,而任何一個知道這樣做等于在毀滅他人生活的人都會在制定這種策略時躊躇不決”。這種轟炸的比喻揭露了全球政治、經濟權力的掌控者是如何逃避對其采取的行動承擔責任的。在強權政治古怪、迂回的言辭中,對平民的蓄意殺害——在另一種語境中是指戰爭罪行——被說成是對戰略目標進行空襲時必然要帶來的完全合法的不幸損失。與此類似,在全球經濟運作中,金融機構為了堅持某種意識形態目標而對一個個國家造成的生命和生計毀滅并沒有被看作恐怖性行為,而是被說成由輕微的導向錯誤造成但從根本上說是善意運用正當原則的悲慘結果。
咖啡產業對這些經濟政策的反應是多樣的。許多咖啡生產國設有咖啡銷售局,負責購買所有農民的產品。雖然這些機構常常是腐敗的,而且過于官僚主義,但農民至少知道他們能夠賣出他們的咖啡并能拿到錢。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實施的結構性調整使許多這類機構解體,從而使市場對私人貿易商開放。結果由于跨國公司通常控制著整個咖啡貿易,咖啡農根本沒有機會自主選擇買家和商定價格,也無法保證這些買家能夠回頭來更多地購買他們的咖啡。結構調整帶來的這類影響正在蔓延開來。
咖啡業過去雖然有明顯的缺陷,但是一個從事咖啡業的人可以認為自己從事的是一種誠實的職業。但是現在,和其他行業的商人一樣,咖啡商人不時會覺得自己實際上是在購買被盜竊來的東西,并且成了奴役第三世界的人。良知越是浮現于他們的腦海,他們就越會奇怪,這一切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大多數咖啡商只好把他們的良知囚禁在黑暗之中。
咖啡期貨交易中心大樓對面的世貿中心一號樓的頂層曾有一家名為“世界之窗”(Windows on the World)的飯店,從那里可以欣賞到曼哈頓及其周邊的美景。可能會有這樣一位歷史學家,站在這與奧林匹亞山一樣的高度向下凝視,憑借淵博的知識去猜測:1776年8月27日,喬治·華盛頓在長島被人數眾多的英國步兵擊敗,隨后率領他的軍隊撤退到伊斯特河對面的布魯克林高地上的要塞里,那些要塞坐落在哪里呢?幾天之后,“9000名或者更多的喪失信心的士兵——他們國家最后的希望——陷于進退維谷的境地,身后是大海,前面是耀武揚威的敵軍”。世貿大樓頂層的這位坐在扶手椅上浮想聯翩的歷史學家小口抿著沙布利白葡萄酒,想象著華盛頓如何回避英國驅逐艦的追擊,使部隊成功有序地撤退到了曼哈頓。這樣一個敦刻爾克式的撤退不僅拯救了這個國家,也為他的國家卓越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現在,就像一幅畫面,那家雙子塔酒店,以及我們關于歷史的令人安慰的幻想都消失了。剩下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使我們在看待過去的時候把自己看作是例外主體的現代西方文化傳統的大廈垮塌了。那些曾被認為已經永遠成為過去的歷史要素——帝國、奴隸制、宗教戰爭、壓迫、災荒和瘟疫——在我們充滿驚懼的雙眼前又重新展現,使得我們不堪回首。“我們”現在無所遮掩地站在世人面前,顯得并不比過去的“他們”更好,不同的只是,面前這個舞臺的規模更大了。
(本文選摘自《黑金:咖啡秘史》,[英]安東尼·懷爾德著,趙軼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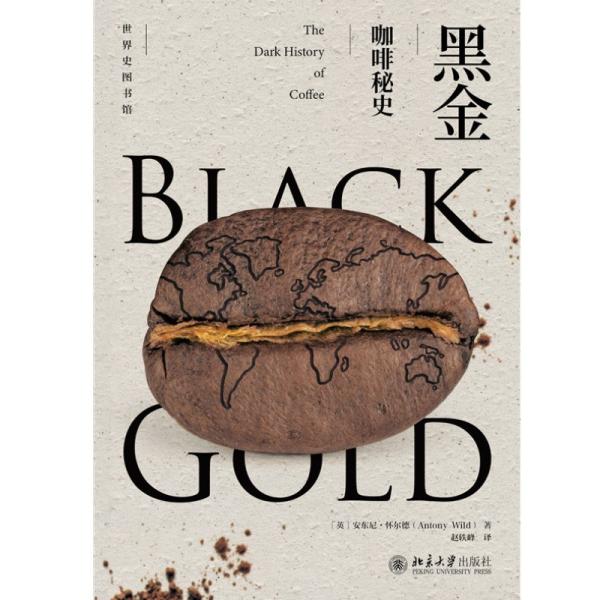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