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路內(nèi):小人物的命運往往是后置的(下)
在42萬字《霧行者》出版2年以后,小說家路內(nèi)又寫出了一部長篇小說《關(guān)于告別的一切》。小說首發(fā)于《收獲》長篇小說2022年春卷,剛剛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單行本。
故事的時間線從1985年延伸至2019年,講述了一對父子在不同年代的一場場以告別為終的愛情。小說主人公李白是一個談過十幾場戀愛的過氣作家。他的母親在他十歲時與人私奔,不知所終。他的父親李忠誠曾是農(nóng)機廠副廠長,救火英模,也是未來的阿茲海默癥患者。故事的開頭是李白與其初戀在2018年重逢,而重逢猶如單行道上的車禍,讓往事“接二連三地追尾”。
在某種意義上,《關(guān)于告別的一切》可以被看成是《花街往事》的姐妹篇,它追溯了父輩一代的愛情故事,還試著將故事脈絡(luò)伸向了出生于新世紀的下一代。它也是路內(nèi)目前所有小說里距離當下最近的一部。
“我也想寫一個2022年的故事,可是等到寫完時,2022也就過去了,仿佛立即作廢。那就不是追著時代,而是被時代追著跑了,非常狼狽。其實寫近處的,講老實話,容易得很,太容易了,怕失之輕率。”今年4月,疫情宅家期間,路內(nèi)就新作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因篇幅關(guān)系,專訪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里,路內(nèi)從他的愛情故事接受史談到了他對愛情的理解、他對新作的構(gòu)想、他與小說主人公的關(guān)系、《霧行者》對新作的影響;在下篇里,他講述了他對父輩一代愛情的感悟、他對今天愛情故事的觀察、他對時代與“懷舊”的理解,以及他對個人命運和大歷史關(guān)系的審視。
此為下篇。

路內(nèi)
面對愛情,父輩一代就像是沒機會玩的小孩
澎湃新聞:《關(guān)于告別的一切》里,李忠誠這個角色也很有意思。有時我感覺這對父子的經(jīng)歷疊在一起,是男人面對愛情時各種笨拙的集合體。我很喜歡看李忠誠的故事,尤其是他在失去妻子后的中年愛情生活,甚至覺得這部分還想看得更多一點。寫這個故事時,你怎么想到也寫寫李忠誠?
路內(nèi):我對上一代人研究得還比較多的,不恭敬地說,有點像時代標本。好在我也快變成時代標本了,這話可以用來批判自己。李忠誠很像我一個朋友的父親,過去年代人家罵“壽頭”的那種。一直想寫這么個人物,沒什么機會,作為主人公他有點太單薄,作為次要人物又失去了深刻討論的可能。現(xiàn)在這位置正好。
澎湃新聞:你怎么評判一個男人情感上的成熟?有什么標志嗎?
路內(nèi):夸張地說,男人成熟的標志是死掉。
澎湃新聞:男人至死是少年嗎?
路內(nèi):少年這個詞太美好了,事實也可能是混賬、山炮、活在幻想里的人。好吧,我收回我的話——不否認有的男人相對成熟些,做事情比較理智些,個體差異還是有的。
澎湃新聞:寫父輩愛情那部分,也讓我想起了《花街往事》,當然它們是不同的故事。我想問的是,你怎么理解父輩一代的愛情?
路內(nèi):我們對父輩一代的愛情,體感差異很大。正如李白所說,他父母離婚時才三十來歲,在他看來是非常成熟的成年人了,但實際上,等他自己活到35歲,發(fā)現(xiàn)不是這么回事。中年人仍然可以很幼稚。因此這種理解隨著我年齡增長,也會變得更深入些,更寬容些。他們最好的年齡上,時代很苛刻,或者很窮,必須立刻建立家庭來維持生活,而不是享受或理解愛情。以前覺得這是天經(jīng)地義的,等我這個年紀,回想他們,覺得很是不忍。似乎他們也只是一群小孩,卻沒有給他們玩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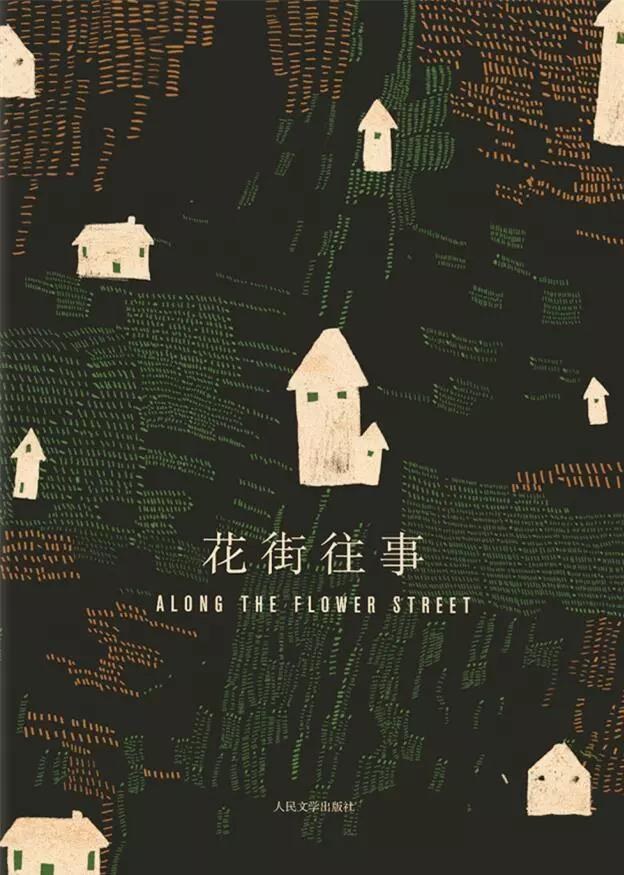
《花街往事》
澎湃新聞:有沒有看過《父母愛情故事》,或者是之前很火的《人世間》?談到父母愛情吧,有一陣很多人會想到那首《從前慢》,覺得過去的愛情就是比現(xiàn)在的純粹、簡單。你覺得呢?
路內(nèi):都沒看過,但我肯定不會覺得過去的愛情比現(xiàn)在純粹。所謂純粹也不見得是好事,是被壓制的結(jié)果。
愛情雖然更多地被女性書寫,但純粹的愛情更像是一種男性化的理想說辭。這種純粹并不那么平衡,有點單向。當代女性對愛情的要求,現(xiàn)實來看,復雜得多吧。比如說,指向婚姻和生育的經(jīng)濟支撐、至少是平等的話語權(quán),不一一例舉了。因此純粹這個詞在我看來,是帶有一點壓迫性質(zhì)的。不一定是男性壓迫女性,也可能是環(huán)境壓迫個人,甚或話語術(shù),變成一種索要的借口。它可能是個案,很美好,但它必須在對等的基礎(chǔ)上才能討論。
另外,純粹的愛情似乎只存在于書面語里。在現(xiàn)實生活中,誰會評價某人的愛情是“純粹的愛情”?我是沒遇到過。然而小說家似乎還是愿意寫寫,純粹的愛,無條件的愛。好的小說家會寫出另一種指向,我希望我也能做到。
當下的愛情,滲入了方法論和成功學
澎湃新聞:《關(guān)于告別的一切》也把故事脈絡(luò)伸向了李白的下一代——出生于新世紀的李一諾。這代人從小對網(wǎng)絡(luò)和手機就很熟悉。特別打動我的是小說里寫:“我們擁有了一切即時的聯(lián)系方式,最終仍可能出于某種原因而決裂,永不再見。此后年代,沒有命運安排的失散,只剩你想要的決裂,這將是李一諾他們面對的世界。”也很想聽你聊聊,你怎么看待這個時代的愛情?
路內(nèi):其實這句話也像是借口,過去時代并非沒有決裂,李白就是從父母的決裂中走出來的。只能說,他的人格不愿意承擔這種決絕,決絕并非不好,也許他內(nèi)心決絕,只是逃避這種態(tài)度。
我不太能討論當下的“純粹的愛情”了,連純粹的意義都在變。現(xiàn)實地說,不同階層在用各自的方式詮釋愛情。打個比方,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我看到的是大部分人都不再支持跨階層的愛情了,人們不相信這個,覺得必遭報應(yīng)。但這一趴,一直是過去文學作品里樂于書寫的。我們討論的都是愛情的“周邊”,對嗎?
澎湃新聞:“大部分人都不再支持跨階層的愛情了”,意思是,愛情要門當戶對?
路內(nèi):也可以這么說,但門當戶對這詞挺難聽的,跟上一代有關(guān)。實際可能是,大家對自己的階層身份認識得更為清楚,以這個為基礎(chǔ)在建立愛情觀。如果愛情失敗,不討論愛情本身,首先討論階層差別。那么它就變成一種話語了。或者說,在愛情之中,當下的方法論、成功學的滲入,也是挺多的。過去也有,但不是目前這一套理論。你也不能說這是錯的。
澎湃新聞:如果一場愛情失敗,大家會說鳳凰男就是不要找,或者鄉(xiāng)下妹就是心眼多,類似這樣的。
路內(nèi):是啊,這種簡陋的話語實際上……看上去挺像辦公室政治的。
澎湃新聞:之前聽陳福民老師說過:“假設(shè)愛情也是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知識之一,它的穩(wěn)定性在今天遭到了完全的侵害。可假如一個時代的文學不能處理愛情,這份文學也是非常可疑的。”你認為愛情的穩(wěn)定性在今天這個時代受到了侵害嗎?
路內(nèi):陳福民老師講得很好。如果不去處理愛情,文學是會失色的。但我的看法,這種穩(wěn)定性,所指的是感情層面還是社會學層面,還需要陳老師再解釋一下。我個人對單純的社會學層面,興趣比較缺乏,因為太多媒體話語。說白了就是,營銷號讓人聊什么,人就聊什么。這太可怕了。我們還是要有一些詩意上的追求。
不要標榜當下,也不要標榜年代
澎湃新聞:你怎么看待“懷舊”?
路內(nèi):這不是個好詞,它已經(jīng)被當代互聯(lián)網(wǎng)話語定義成中年男人的神經(jīng)官能癥,緊跟著懷舊的就是猥瑣。其結(jié)果是,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在共享這個詞,而兩者的意義是有落差的。我們可以找到無數(shù)這樣的詞,它不一定是代際差別,往他者臉上敲圖章是很爽的,而且不需要為此負責。小說是這樣一種東西:它無法越過大眾而強行使用一個已遭貶斥的詞,因此,我們只能無奈地認定,懷舊是個糟糕的東西,懷舊是一種嘲諷。
再比如,驕傲這個詞也有歧義。一種是自尊,一種是傲慢。但我們總是用驕傲這個詞。我們讀喜馬拉雅的時候也會有錯覺,它不喜,也不雅,它的意思是圣母或女神。連圣母都變成壞詞了,對吧?這就是現(xiàn)實,詞的異質(zhì),意義的變化。
澎湃新聞:這種現(xiàn)實給小說寫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路內(nèi):詞的變化會使作家慎用意義,更多地去描摹,或者避開一些很大眾的概念。比如說方言小說忽然好用了,有些詞因為很偏僻,不但有新意,也避免被大眾解構(gòu)。這可能不僅是小說,電影的鏡頭語言也是這樣。二十年前我們看電影,一顆子彈慢鏡頭飛過空中,覺得很酷,現(xiàn)在就是爛俗的鏡頭語言了。但有時候,往往是關(guān)鍵時刻,總還是會被一個壞詞帶偏。

《關(guān)于告別的一切》
澎湃新聞:你又怎么看待這樣一種對小說家的描述,叫:“往事的拾荒者”。
路內(nèi):拾荒者這個詞要追溯到程德培先生評論吳亮老師長篇小說《朝霞》的一篇文章,題目叫《一個黎明時分的拾荒者》,然后我去查了一下,深夜或黎明的拾荒者,是一個很穩(wěn)定的意象,居伊·德波好像也談到過。回到深夜來看,那是一個人人都在沉睡的城市,拾荒者是孤獨的,他撿拾他人棄置的碎片物,這些碎片不僅無用,而且無意義,但有時也會出現(xiàn)誤棄的金子?這個人將碎片物打包,分類,估算其價值——這個形象具體描述出來確實像小說家。不過,往事的拾荒者,看上去更像一個口述者,喋喋不休講述過往的人。
澎湃新聞:我可以這么理解嗎:其實你本人并不反感講述過往,你也相信有時會出現(xiàn)誤棄的金子,但你對“懷舊”這個詞很無奈?
路內(nèi):懷舊確實容易讓意義固化。瞬間的、個體的懷舊也許還好,那不應(yīng)該是一種思維方式。講述就是講述,每一次講述都是在重申或覆蓋意義,找到新的出路。這想法比較受德勒茲的影響。
澎湃新聞:我在你的小說里還是能感受到很強的年代氣息。
路內(nèi):我希望自己也能寫好當下。當下這個詞也快變成壞詞了。
澎湃新聞:其實你的講述也蠻經(jīng)常提及“年代”的,比如:“以后年代也許就沒人要看(愛情小說)了”;“東愛這故事現(xiàn)在也有人看,只是放在當下年代,就不那么動人。”我也想聽你說說你的年代觀。
路內(nèi):我有點不太理解,何謂年代觀。我寫過一些這樣的小說,經(jīng)常被問。寫作的人對于年代是比較“貪婪”的,像一個預(yù)算無限的電影導演,他想要在故事中復原場景,有些是當年的實物,有些是仿制品(偶爾穿幫)。通過鏡頭,這些東西構(gòu)成了場域。一個寫當代的作家,一個寫古代的作家,當然也有建立場域的想法,也可能穿幫。寫的時候,實際是雙重價值觀,一種是當時的價值觀,作者不能全然否認,得呈現(xiàn)出來;一種是當代價值觀,隱藏在文本里。大體來說就是這樣。
澎湃新聞:《關(guān)于告別的一切》寫到2019年,是你目前所有小說里距離當下最近的一部。想過再往前寫嗎?比如2020、2021、2022……是不是越近越難寫?
路內(nèi):會的,想寫一個2022的,可是等到寫完時,2022也就過去了,仿佛立即作廢。那就不是追著時代,而是被時代追著跑了,非常狼狽。其實寫近處的,講老實話,容易得很,太容易了,怕失之輕率。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標榜當下,也不要標榜年代。
澎湃新聞: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你會對這個時代感到無所適從?
路內(nèi):我起初估量的是,等我老了可能會無所適從,這是靠經(jīng)驗得出的,上一代人總是會落后的。現(xiàn)在倒也不這么看了,個人問題先放一邊。確實,借用齊澤克反駁福山的概念,歷史沒有終結(jié)。如果時代向前跑,我不太會無所適從,我也許還能跑得比時代更進步些。如果倒退,就很難說了。
澎湃新聞:《關(guān)于告別的一切》里也有一種對時代的茫然與感傷。
路內(nèi):兩種不同的茫然。作為人物,李白在變動流逝的時間中,總是呈現(xiàn)出茫然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是回溯的,我們經(jīng)歷過的人早已替他看到了結(jié)局。作為作者,我對未來有點……用個俗詞兒:講不清道不明。
澎湃新聞:你現(xiàn)在會怎么思考個人命運和大歷史之間的關(guān)系?其實看你的小說,也能通過小說人物看到一些隱藏在文本里的觀點。
路內(nèi):有一種歷史觀認為,歷史往往依靠大人物的決策,之所以不用偉人這個詞是因為也出現(xiàn)過希特勒這樣的。這種決策無論對錯都是前瞻的。而小人物的個人命運往往是后置的,得經(jīng)歷過了才能看清,甚或只有旁觀者能看清。這種前瞻后置之間的反差和互相拉扯的力,一直是我寫作的主題。智者和愚者,強者和失能者,廣大世界和微渺路徑。不過以后,我也許會寫點別的。
澎湃新聞:小說最后一章寫到“豆瓣罵戰(zhàn)”,這部分也很有意思。你怎么評價現(xiàn)在的“豆瓣生態(tài)”?
路內(nèi):那一段更像個寓言。過程是,一個過氣作家在豆瓣被大V罵了,他居然親自下場還嘴,作為“群眾”主體的大V招了幾百個人過來罵作家,顯然,作家作為權(quán)威主體,需要群眾批判一下,這也無可厚非。然后作家忽然發(fā)現(xiàn),匿名大V不是群眾,是某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也就是權(quán)威評論家體系。這個體系為什么要去豆瓣充當“推翻權(quán)威的領(lǐng)導者”?這好像也是他的個人自由吧。那么作家也獲得了自由,他的干女兒帶了一群中學生上去罵大V,還都冒充外國人,用英文罵。于是,這兩個權(quán)威體系全都糊涂了。正確的爭論是把對方整明白了,這叫討論問題。那如果目的是想把對方整糊涂了,怎么辦?
澎湃新聞:你覺得我們文學圈,現(xiàn)在有爭論嗎?如果有,都是什么樣的爭論?
路內(nèi):真的不多,文學圈都是高手過招,一回合也就結(jié)束了,敬個禮,再見。但娛樂時代,人們喜歡看爛戰(zhàn)。
【后記】
上一次采訪路內(nèi)是在2020年春天,因為《霧行者》。我們還說那本“大部頭”特別合乎疫情時期灰蒙蒙的心情,小說里蕓蕓眾生“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面貌也猶如現(xiàn)實的鏡像。當時路內(nèi)已經(jīng)開始寫《關(guān)于告別的一切》了,但他應(yīng)該沒想到等到這部新作在2022年春天面世,又一輪疫情暴發(fā)了。
采訪不得不改在線上進行,穿插其中的,還有各種有關(guān)疫情的消息。路內(nèi)的小說人物經(jīng)常在其所處的時代變化里有著這些那些無法解釋的情緒。在一個特殊的時間點談?wù)撍男≌f,談?wù)撔∪宋锏拿\和時代的關(guān)系,本身也是一件很魔幻的事情。
我印象很深的是這一次他談到自己有點想寫2022年,不是報告文學,而是寫已經(jīng)常態(tài)化了的疫情生活。身處其中,素材似乎遍地都是。但這個念想并不容易,按他自己的話說——“影視轉(zhuǎn)化不會順利,拿文學獎也無望,還可能被罵,再就是外面的段子比小說更精彩”。
另一方面,時間總在流逝,而真正的寫作需要時間的發(fā)酵與冷卻。即便單從技術(shù)上來說,與時代同步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長篇。我能理解路內(nèi)說“不想追著時代跑”,追逐當下如同逐月,小說家在追逐的時候,月亮也在前行。這里似乎冒出一個悖論了,遠了會少一些切膚之感,近了又像是戴了放大鏡,目不見睫,不容易看到整體的輪廓,也不容易保持文學必要的心理距離和觀察距離。
但我想,一個有想法的小說家不會把選擇的權(quán)利完全交給時間——因為所謂時間的選擇,仍然是一代代時間中人的選擇。(羅昕)

路內(nèi)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