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簡牘學與內亞學的會面:不同時空下移民的“交流”
2017年8月12日下午,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四十九場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舉行。本次研習會和“清朝與內亞工作坊”合作舉辦,主題為“帝國·邊疆·移民——簡牘學與內亞學的會面”,主持人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孫聞博、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孔令偉,希望以“移民”的話題為橋梁,跨越領域與斷代的鴻溝,促進簡牘學與內亞學兩大領域的青年學者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對話。
秦朝洞庭郡遷陵縣的移民
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游逸飛根據近年最重要的出土簡牘之一——里耶秦簡,探討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里耶古城遺址的移民問題,亦即戰國楚國舊地、秦朝洞庭郡遷陵縣的移民問題。游逸飛2012年曾親訪里耶古城,深深感到其僻處深山、交通不便。科技發達的今日尚且如此,二千年前的遷陵縣只會更加閉塞。然而游逸飛研究里耶秦簡所見洞庭郡遷陵縣的駐軍、官吏,驚訝地發現他們全是外郡人,本地人竟然無法在家鄉擔任小吏,修正了我們對秦漢史的既有認知。當地平民與刑徒亦有大量外地人口。“深山里的外來移民”現象不僅吻合杜正勝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歷史脈絡:“秦分置天下為郡縣,派遣守令治理,郡守縣令都是秦人。在山東人看來,這些秦吏都是征服者,是外國人。”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洞庭郡遷陵縣幾可視為秦朝在楚國舊地、深山之中設置的殖民地。
循此脈絡,游逸飛注意到完整的里耶古城可能只是面積約四萬平方公尺的小城。若無里耶秦簡出土,考古學者只會將之納入”軍事堡壘”的分類,將無人知道兩千年前秦始皇在湘西山地筑城置縣。換言之,里耶古城并非一般的縣城,其軍事性質不容小覷。而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縣官吏與編戶齊民的數量有限,亦反映當地自然聚落缺乏置縣的經濟、社會基礎,秦始皇在此置縣的政治、軍事考慮更加突出。
不管里耶再怎么偏遠,當地終非一片空白的處女地。秦始皇在湘西山地設置遷陵縣,對當地土著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呢?游逸飛指出里耶戶籍簡里“荊不更”等楚爵記載,反映遷陵縣的編戶齊民里存在一定比例的楚人。里耶秦簡9-2307則反映濮人、楊人、臾人等當地土著不能住在遷陵縣城里,大多應被驅趕到更偏遠的深山之中。秦朝區分移民與土著的政策昭然若揭,但其中仍有更多細致的區分值得我們深究。

孫吳長沙郡臨湘侯國的移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凌文超指出,隨著湖南長沙走馬樓吳簡陸續刊布,臨湘侯國這個即使在孫吳境內也不太重要的地域,逐漸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以本次研習會探討的“帝國”主題來說,過去我們的研究不是重視中心,就是關注邊疆,中心與邊疆之間的內地,反而常常被不經意地忽視。其實中心與邊疆都過分特殊,最能真實體現國家統治普遍狀況的地方,很多時候既不在中心,也不在邊疆,而在最平常、最一般的內地。那里往往有最能體現國家統治力及其治理效果的日常行政秩序,也正是那些凡常而廣袤的內郡縣,支撐著中心的繁華興盛,也影響著邊境的伸縮消長。相較于里耶秦簡反映的邊疆小城,走馬樓吳簡呈現的臨湘侯國更適合當作內地的代表。孫吳歷史的發展,不僅體現在中心如建業、武昌的盛衰,邊疆如江淮防線的攻守和交州的經營,更體現在整個江南地域的普遍統治情況,尤其是人口管理、經濟開發、物資征集等情形,這些從根本上決定了孫吳的進退存亡。
吳簡中所見孫吳長沙郡臨湘侯國的移民,其身分主要有新占民、私學、州軍吏、師佐、叛走者和生口。相關簡例分屬于《隱核新占民簿》、《舉私學簿》、《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兵曹徙作部工師及妻子簿》、《郡縣吏兄弟叛走人名簿》、《生口買賣簿》等簿書。
隱核新占民的目的在于將方遠客人占著戶籍,既加強對流徙吏民的管理,又增加孫吳編戶民的人數。流民占上戶籍是漢代以來的例規,然而,這次隱核新占民卻由太常府發出指令,由勸農掾臨時清查。事實上,隱核新占民是“舉遺脫為私學”的預演。因為兩者針對的都是遺脫、流民,在隱核新占民的過程中,各級官吏自然會有意識地隱匿其依附民,致使即將到來的舉私學難以順利而有效地搜括出更多的遺脫。
舉遺脫為私學,是孫吳安置流民的另一項措施,背后更反映孫權企圖追奪將吏、官屬的部曲、私客,借以削弱雄踞地方的豪將勢力。孫吳向郡縣下達了選舉遺脫為私學的政令,具體由選官系統執行。孫權還規定要發遣一定數量的私學送詣宮,這樣就確保能將一定數量的投附者從豪將、官僚那里剝離開來。此措施既然會導致官僚的依附者離去,損害其利益,官僚自然會有所抵制。于是我們看到官僚將臨湘侯國領有的遺脫選舉出來,回避了自身的依附者,由官府負擔了絕大部分由舉私學帶來的損失。
隱核州、軍吏父兄子弟簿是根據“保質”的需要而制作的名籍。州、軍吏不僅來自編戶民,也來源于遺脫、流民、方遠授居民,其中不少是北方南下者。以方遠客人任州、軍吏,且對其人身并無嚴格的控制,可能是孫吳建國過程中為招徠流民而實施的優待政策。正是因為不少州、軍吏本為“遺脫”,孫吳官府需要經常對其叛走、物故、疾病等情況進行調查和統計,制作相應的簿書,以加強人身控制。
兵曹徙作部工師及妻子簿是臨湘侯國兵曹負責調徙長沙郡中部臨湘、下雋、醴陵、建寧、攸、永新、羅、劉陽、吳昌、廣興、安成、茶陵等縣的師佐,為征討武陵蠻而制作兵事器械所編制的簿書。作部對師佐有嚴格的人身控制,且師佐按指令強制調徙。
郡縣吏兄弟叛走人名簿顯示,郡縣吏男性家屬多在始役年齡和征役時叛走,主要是為了避役和解除吏家的束縛。鄉吏在核查叛吏時記錄了叛吏的大致去向,供有關部門有針對性地進行逐捕。孫吳對諸吏、士卒父兄子弟叛走的懲罰十分嚴厲,不僅籍沒其家產,還將他們傳送大屯耕種限田,交納沉重的限米。
吳簡中有不少官方生口買賣的記錄,由兵曹出售的“夷生口”很可能就是俘獲的武陵蠻夷。如何處置這些蠻夷生口,據《吳書》所載,主要是“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前者即吳簡所記的“部伍夷民”、“夷新兵”;后者是否直接成為戶下奴婢并登入戶籍,是需要再考慮的,至少有蠻夷生口部分成為了屯田民。
整體而言,孫吳對待新占民、私學、州軍吏、師佐、叛走者、生口等移民,雖然采取了不同于編戶齊民的控制手段,但歸根結底仍然是企圖從事役和賦稅兩個方面實現官府的最大收益。官府讓他們落籍、遷移、遣送或出售都是從賦役收益的角度來考慮的。

明清河北地區的孔氏“圣裔”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建以“北孔氏‘圣裔’源流考”為題,指出宗周以還,“華夷之辨”屢經士大夫階層渲染,形成中國歷史長河中的波峰,而“北族漢化”未經稍歇,構成波濤下的潛流,非爬梳文獻、深入基層,難辨其本色。居住河北獻縣,被孔府承認為“圣裔”的孔氏即是一例。孔氏其家本為馳騁塞上的故元武人,被明朝封為“達官”,調入近畿,捍御蒙古。明清鼎革,孔氏族人永吉投效清朝,藉助家族關系招撫山東,又聯絡孔府投清。清廷酬庸其功,編入八旗漢軍,為“世管佐領”。后嗣幾經修譜,竟成為兼具“圣裔”與旗人身份的豪族。直到辛亥之后,彼等才完全融入漢人。孔氏的傳奇經歷體現北方胡漢融合的全面徹底。可知研究“北族漢化”,不可囿于一朝,而須自長時段入手,打破斷代的局限;北族政權治下的“漢化”決非單向,往往伴隨著“胡化”;北族選擇“漢化”,與其說出自文化感召,不如說是現實需要的驅動。“華夷之辨”作為文化概念,對“北族漢化”的影響并不顯著。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是由胡漢共同締造而成。

十八世紀的土爾扈特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孔令偉報告“流散于歐亞之間:十八世紀土爾扈特移民與西藏及清朝的交往”。他運用托忒蒙古文、藏文、滿文及漢文等多語種史料,指出居住在中央歐亞地區的土爾扈特蒙古,曾經在清俄兩大帝國的博弈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十七世紀初,原居于今日新疆北部一帶的土爾扈特人,因準噶爾人的興起,遷徙到今日俄羅斯境內伏爾加河流域。而十八世紀下半,土爾扈特人又因與俄羅斯政府的齟齬以及清朝的招撫,而徙回新疆境內。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這段期間,游移于歐亞大陸兩端的土爾扈特人不僅廣泛地溝通了中俄雙方的交流,更深刻地促成了歐亞大陸的全球化。不僅如此,依違于清俄兩大帝國之間的土爾扈特人,其主體本身可以深化“離散”(diaspora)的概念,藏傳佛教與帝國勢力的互動亦對“離散”概念產生重要的影響。十八世紀土爾扈特移民社群是深具意義的研究個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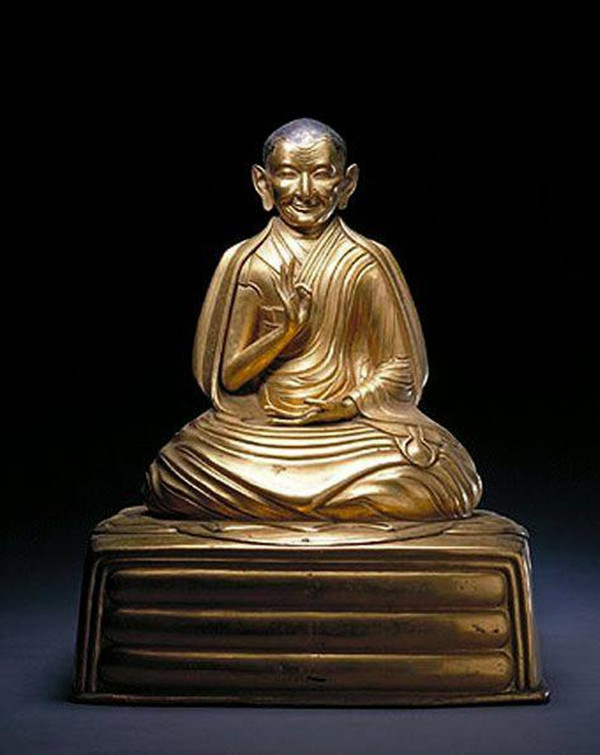
結語
隨著四場天南地北的移民研究報告結束,簡牘學與內亞學初步達成了“會面”的目標。與會學者彼此之間均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下次會面、更深入的對話、交流與合作打下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都是探討移民,但游逸飛與凌文超兩位簡牘學者較為重視國家對移民的控制。他們即便關注移民本身,研究也必須從國家控制移民的手段切入,仍不脫從制度史切入社會史的研究范式。這可說是研究簡牘、研究地方行政文書,必然面臨的深層限制與挑戰,無所逃于天地間。相反地,張建與孔令偉兩位內亞學者,參考資料雖然不乏官府檔案,但對移民本身的主體性、移民自己在想什么,顯然著墨更多。兩相比較,簡牘學者不宜以缺乏史料為遁辭,必須正面應對移民主體性缺失的質疑與挑戰,讓簡牘學研究不限于制度史,更能深入社會史,使整合國家與社會的整體史書寫成為可能。但內亞學者似亦可更加重視制度框架,將移民的主體性置入制度框架底下思考。畢竟人生于天地間,亦生于制度之間,無所逃于天地的同時,亦無所逃于制度。對制度框架的重視,或可以引發我們更多的思考,像胡恒等清史學者對“皇權不下縣”的老命題提出了精彩質疑,類似現象未必不能發生于內亞學之中。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