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從經典到同人,原著黨的天使還是魔鬼
“首相大人,我們能拿熊貓換卷福嗎?”
時隔四年,這條留言仍讓人莞爾。畢竟,可以驚動時任首相在訪華途中還要幫忙操心拍攝進度的,非BBC新版的《神探夏洛克》莫屬了。
嚴格說來,《神探夏洛克》是一部時下流行的“同人”劇。一方面延續了柯南·道爾原作的人設,一方面對原著的部分故事進行了二次創作,讓福爾摩斯穿越至21世紀的倫敦。雖然“同人文化”興起于日本,最初局限在動漫文化的領域內,但提煉故事內核至現代設定中重新包裝,卻是大家并不陌生的編創技巧。幾乎是同時期的“福爾摩斯系列”,華生則在美劇《基本演繹法》中變身為夏洛克在紐約城的戒毒陪護。更魔性的是,華生不是軍醫,不再跛腳,甚至都不再是位大叔,由美國華裔女演員劉玉玲扮演,不得不嘆服腦洞多大,舞臺就有多大。


不過,原著黨們似乎還是更青睞BBC的那一套,畢竟出品自原產國。即使快要磨蹭出一段義務教育的長度,不少鐵粉還是早早地搬好了小板凳,伸長了天線,時刻準備接受腐國有關第五季的好消息。作為世界上最賺錢的劇目,《神探夏洛克》劇本的成功,無疑為文學經典改創范圍內,舊瓶裝新酒的正確姿勢做了場典型示范。
原著黨的期待,是一種很微妙的分寸。既不能改編到毫無新意、一秒劇透,又不能面目全非、活像領養。最好隔一層窗戶紙的距離,不捅時霧里看花,捅破了也只是場美麗的誤會。原著是條底線,考驗的就是改編者在內核和假想間拿捏的功力。
于是,大部分人通過《神探夏洛克》認識了編劇史蒂文·莫法特和馬克·加蒂斯,他們被親切地稱為魔法特和麥哥。魔法特曾為斯皮爾伯格寫了第一部《丁丁歷險記》電影,后來又與麥哥同為《神秘博士》的編劇,那是“世界上最長的科幻電視系列劇”。如果還有什么共同點的話,他倆都是福爾摩斯的死忠粉,《神探夏洛克》的改創計劃就是在若干趟前往卡迪夫制作大本營的火車旅途中萌發的。他們自言,如何讓福爾摩斯在現代安身立命,是一輩子都愿意做的事兒。
某種程度上,原著黨恐怕是比柯南·道爾還要珍愛福爾摩斯。這位率直的蘇格蘭大叔1887年在《河濱雜志》上開始連載這一系列的時候,應該不會料到,六年后的某一天,當他準備親手結果筆下這個形象時,讀者會寄來毫無溫情的子彈。其實,早期對夏洛克的很多演繹,仍創作于柯南·道爾在世之時。20世紀初,美國人威廉·吉列屢次擔綱主演,他曾公開寫信給道爾,請求準許上演福爾摩斯的舞臺劇,道爾也公開回信說:“親愛的朋友,當然可以。你盡可以讓他結婚或者殺了他。隨便你想怎樣,都可以。”

就連你今天能夠從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版卷福身上感受到的,足以心花怒放的智慧和性感,也極有可能來源于最早一批原著黨的杜撰。福爾摩斯在《血字的研究》中被明確描述為奇高奇瘦,像根巨笛,還長著鷹鉤鼻,根本不是一個迷人的男子。《河濱雜志》的插畫家悉尼·佩吉率先以自己的美男哥哥沃特作為描繪原型——自此,福爾摩斯就必須英俊了。
至于我們早已習慣的福爾摩斯和華生形影不離,事實卻是,華生一角在1939年之前的電影中并不那么重要。巴茲爾·雷斯伯恩和奈杰爾·布魯斯搭檔過后,華生才和福爾摩斯平等地站在了一起。雖然奈杰爾飾演的華生歡樂到有些可笑,得罪了當時部分原著黨,cp人設卻保留了下來。
2010年,這位渾身散發強烈優越感的年輕人,帶著他那動輒腎上腺素飆升的同伴繼續無案不歡。你仍然熟悉他陰晴不定的心情,盤腿、手擺成尖塔狀置于下巴的姿勢。不過這次,他們開始熱衷發短信、寫博客,擅長利用衛星定位,鑒證科學不再是維多利亞式的新奇,推斷演繹更加奪目。
撇開剪輯技巧和拍攝手法的獨到,相比魔法特和麥哥將《神探夏洛克》的成功歸因于他們對道爾作品的尊重,以及其將角色描繪栩栩如生的功底。福爾摩斯這個經典IP,歷經層累演繹后的豐富和流動,才是更重要的一個勝利。
像一場曠日持久的愛戀,讀者先入了坑,才會想方設法為所愛續命,作品不斷在接受與改造中傳播,經典永遠呈現出開放式生態。《神探夏洛克》第三季開頭,劇組模擬了現實中部分網友對夏洛克跳樓之后的猜測,也復刻了道爾時代讀者集體焦灼后的拯救意識。自從被“死”過一次后,道爾應該也會認同,福爾摩斯這條命分明是靠眾人截胡來的。如今以季為單位的拍攝方式,便直觀了這種文本與讀者間的互動過程。
問題是,經典的封閉要透過讀者來打開,但將個人對角色或作品的好惡充當普遍真理來面對,反而是對真相的扭曲。正是深諳此道,霍加斯出版社,就是由伍爾夫夫婦創立,曾退稿喬伊斯《尤利西斯》的那家出版社,在莎翁逝世400周年,發起了改寫莎士比亞經典劇作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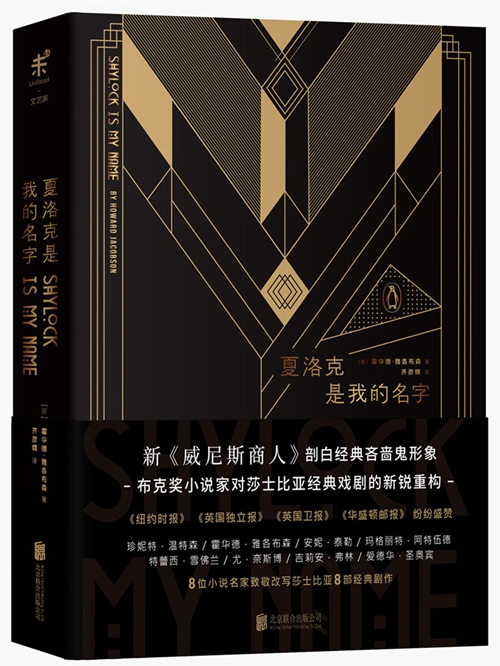
這是一個大膽的策劃,雖然從娛樂消遣攀升至文學頂峰的這一路,莎翁的戲劇已經歷過太多改創。珍妮特·溫特森首先受邀將《冬天的故事》改寫成《時間之間》,母本是一個棄兒的故事,而溫特森本人從小就被領養;《威尼斯商人》的情節大家再熟悉不過,在霍華德·雅各布森筆下也有了新的演繹——《夏洛克是我的名字》(雖然一不留神還以為是福爾摩斯的又一部同人),雅各布森曾以喜劇作家的身份榮獲布克獎,此外,他還是一個猶太人;飽受女權詬病的《馴悍記》被擅長家庭題材的安·泰勒反轉為《凱特的選擇》,她自己都說,接受邀請完全是出自于對莎翁的厭惡;有魔法師人設的《暴風雨》則由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接盤,改寫為《女巫的選擇》,而最新的坊間流言是,傳說她有女巫血統,傳說她可能今年得諾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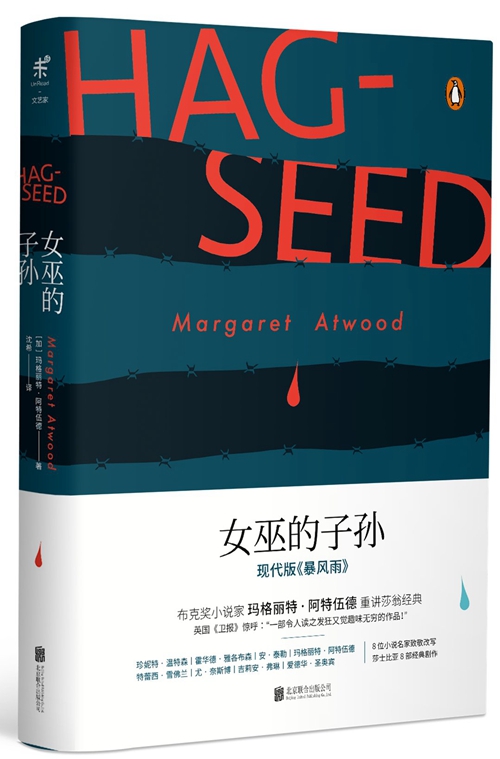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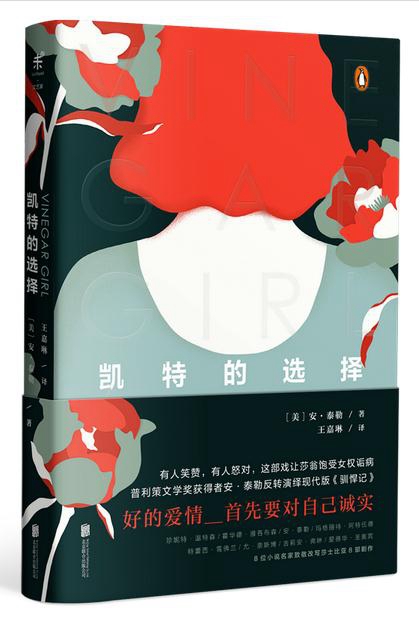
之后,還會由尤·奈斯博改寫《麥克白》;吉莉安·弗琳改寫《哈姆雷特》;特雷西·雪弗蘭改寫《奧賽羅》。即使經典拒絕定義,但這陣容,更像是復仇者聯盟,所以出版社才預言,這次將由經典產生出經典嗎?
文學作品人物間的互相顛覆,大多是讀者重新創作時的事兒,可能會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跨度。但自己為自己洗白這件事兒,歷史上倒真的發生過。比如《大義覺迷錄》,就是雍正在遭遇鄉野塾師曾靜詆毀之后,把原文與自己撰寫的一系列洗白文,合為一處,刊行流布的奇書。它在形成、流傳和禁毀過程中的部分橋段還被二月河略加改造,收進了自己的小說《雍正王朝》。而更多枝節,都可以在史景遷的《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中翻檢查閱。
對一則文字獄來說,雍正的對應之策很是奇特。除卻背后的政治功用和歷史動因,細節仍然值得玩味。一是政府十分明白,文人只能靠文人來說服。好像前文中的霍加斯出版社,邀請一流的作家改編一流的原作,未讀之前,想想就心服。二是雍正本意是以端正臣民的視野,使流言不攻自破。卻也實實在在,為尊古貶今、華夷之辨的老思路提供了另一種旨在維護各個族群文化特質,包容多元的文化觀。而這則自帶翻案情節的歷史邊角料,好看就好看在兩種異質的價值觀,是如何在你來我往、人各言殊的歷史公堂上互不相讓的。文學世界里,我們人為地對作品進行解構或制造沖突,就是為了避免普世價值觀上的極端,因為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往往只有在這樣的碰撞中才開始豐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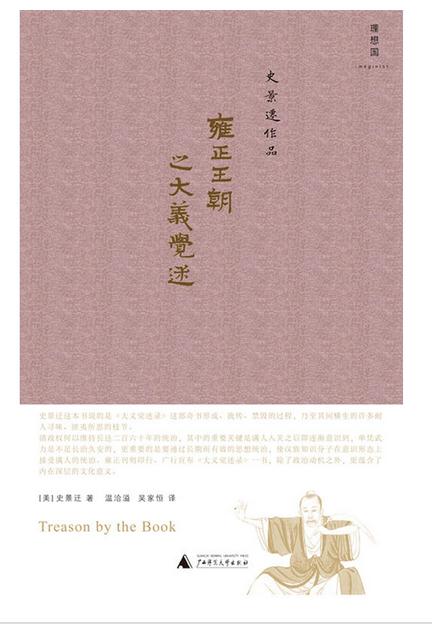
知乎上不乏“同人逼死官方”或“改編毀原著”之類相愛相殺的問題。生活哪會清淺到一覽無遺,或許更該相信,閱讀和想象是手中的萬花筒,我們認識這個世界永遠有很多的角度,而每個角度都可以讓我們到達不一樣的真理。腦洞還是要有的,萬一哪天就成經典呢?
比方《金瓶梅》,西門慶不僅在《水滸傳》外活了回來,還和潘金蓮過上了小日子。此書外表極歪,骨子里三觀卻極正。全書沒一個好人,所有人都拼盡全力,逃不過的,是欲望。《金瓶梅》還是我國第一部標題成熟的章回體小說和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白話長篇。
再說《西游記》。據不完全統計,被改編成電視劇的有20多部,改編為電影的至少8部。最近的一部,要數《悟空傳》了。明代《西游》就有三大續書,分別為《西游補》《續西游記》和《后西游記》,極盡奇幻曲折之事。
“續”、“后”、“補”都是我國古代文學創作的傳統,若算進“同人”,那高鶚所續的《紅樓夢》當然是“同人”中經典。
但“同人小說”畢竟是個新詞,從日本和美國發揚光大。美國最著名的科幻作品《星際迷航》就向粉絲開放了版權,優秀的同人作品甚至擁有被原著采納的機會。日本向來是尊重知識產權的典范,卻只對“同人小說”格外寬容,應該也是看到了“同人”反哺原著,互相成就的功用。
但是,這種鼓勵或包容,并不等于“同人小說”的現代合法性,即便原作者沒有狀告侵權。迪斯尼的《獅子王》山寨手冢治蟲的《森林大帝》,就是一段跨國侵權的公案。一部文學或藝術作品,只要著作權權利保護期終止,就進入了公有領域,再無侵權一說。前文提及的《神探夏洛克》和“霍加斯-莎士比亞系列”,改編的都是這個領域內的作品。公版之外的,就得麻煩遵守“同人圈”的潛規則:未經原著者授權,不能牟利,否則就可能會侵犯《不正當競爭法》。所以,多數“同人”作品都是免費公開在網絡上,某些作者還會聲明,作品的經濟利益屬于原作者。
像《武林外傳》那樣人物改名換姓以向武俠致敬的,也就是打了個擦邊球。畢竟周星馳也要為《功夫》中使用過金庸小說中的六個名字付版稅。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