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翼虎·山河·尋路胡煥庸線上的中國︱紅岸:以父之名

那是在1957年的家鄉杭州,27歲的新娘婁利玲,朝著遠方露出微笑。此時,她對新郎章元泗即將奉命奔赴的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還幾乎一無所知。但不出兩年,她就會拿到調令,離開北京的藥檢所,來到齊齊哈爾的富拉爾基,與丈夫團聚。
“上海抽了五個工程師,其中有他一個。他說,你怎么辦。我說,你去吧,我也去。結果,我們就在這兒待了五十多年。”
若非章元泗三年前去世,今年應是他在富拉爾基工作生活的第六十年。
當你一個人,完全是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才能成為兩個人。而隔壁的兒子和媳婦早已沉入夢鄉。而你沉浸在世界上最美好而輕松的回憶之中。
這就是婁利玲的快樂。

家事
時光把床頭的木頭磨得光潤,也在新娘的臉上刻下皺紋。章元泗和婁利玲在這張廠里配的小木床上睡了三十多年。彼時開荒艱苦,簡樸實用是榮耀,也是工程師的品格。
誰知多年以后,這種品格化為他人的重負。婁利玲總后悔,退休時沒加上職稱,不然工資就能高一些。“那時,他爸在這里,說算了算了,夠花就行了,別去了。職稱就沒加上。”婁利玲明明想要埋怨,卻又不知怎么地,對我笑了起來。
媳婦劉秋娥反過來勸她:“我說媽你不要這么想,活著就挺好了,不要糾結職稱。你們藥局的,比你年輕的,比你老的,都過世了。我這人說大白話。”
婁利玲希望兒子媳婦過得好一點。“他們到這,也是受苦了。”

她生了三個孩子。只有一起住的大兒子章鷹在這里出生成長,接了自己的班,成了重機廠的工人,剛退休不久。
頭一胎是女兒,特地回杭州生的,“因為我可以看看我的媽。”女兒被姥姥帶大。小兒子也在杭州生養。“放在他奶奶家,他奶奶帶的。”直至章元泗家人零落,無人看管,婁利玲才把小兒子帶回。至于那時小兒子多大,是四五歲還是十幾歲,婁利玲竟已不太記得。
這不失為家族策略。彼時南人初來東北,趕上艱苦建設,生養不易。但兒女難免生出心結。
“姑娘也不太來。她爸有病的時候來了。住了沒幾天,就回去了。她還得伺候她的公公婆婆。公婆是在上海的。”婁利玲拿著最后一張全家合影。
那是在病房里,暗淡的淺藍色木門襯著白墻。面色蠟黃的章元泗倚在床上。婁利玲的右手扶在他背后。二人身后是三個三口之家,人人表情肅穆。
你低聲地嘆息。那時候,想法和現在不一樣,好像到艱苦的地方去還是對的。那時候,就是為了建設嘛。那時候,身邊的工程師,多年之后的勞模,還是英姿勃發,眉清目秀。就像相冊里的照片上那樣。
舊事

當初來這的還有許多轉業軍人。自朝鮮戰爭局勢穩定,蘇聯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對中國援建的第一批大型重點工程項目,開始大量投入建設。
從1950年到1954年,中蘇分批議定的百余項蘇聯援助重點工程——被后人稱做“156項重點工程”,成為中國“一五”時期的重工業基礎。其中有三項落在富拉爾基,使得這個小鎮變成了工業城市——富拉爾基熱電站、富拉爾基特殊鋼廠、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又稱第一重型機器廠,就是如今一重集團的前身。
“他們那些人的青春就到這了。”劉秋娥說。她父親是傘兵,家鄉在河南。抗日戰爭結束后,其所在部隊被調往北大荒開荒,而后進入第一重型機械廠,工作了一輩子。
婁利玲有時在電視上看見西湖。“現在的西湖,那不像以前的西湖,現在人多,亂七八糟的。以前多清靜啊。”記憶似是非是。章鷹拿出一張照片:“這是我媽年輕的時候,挺好看的吧。”清清靜靜的西湖邊,婁利玲梳著大辮子。從紹興搬到杭州的章元泗一家,那時住在婁利玲家前面。那時,西湖邊人挺少,都是情侶,一對一對的。
“他在杭州上學,浙江大學。”婁利玲講著杭州話的語調,仿佛不愿融入周遭世界。章鷹想起父親,他口音標準,要是不注意聽,聽不出是南方口音。“我媽不行,第一句人家都聽出來了。她總覺得她說的口音挺標準的。”在東北長大的章鷹夫婦,一口東北話抑揚頓挫。

劉秋娥對自己公公的專業技術印象深刻。她記得,“文革”時章元泗被下放到專門煉鋼的七車間。那時工人面對有故障的天車,不會維修,只知敲打。章元泗便告訴工人,電怎么看,圖紙怎么看。“他笑話我們,回來和我說,工人怎么怎么樣。我說是,我們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的。”
婁利玲翻看相冊里章元泗的工作照,不記得他那些同事是什么人。
章元泗和婁利玲最后一張盛裝二人照,名義是“綠寶石婚紀念”。婁利玲看著這張照片:“這是他去世的前兩年。”沒說完,便被兒媳糾正:“不是兩年,頭幾個月。五月份照的,八月份就走了。”
當時家里似乎對老爺子瞞著病情。“媽說的,給老年人照相不花錢。”劉秋娥又補充:“其實洗的、拍照的,也都是那些南方人。”
婁利玲有時給北京的同學打電話。那頭的老太太,一月工資七八千元,每年攢錢去一個國家。而婁利玲自己的退休工資是兩千多元,她感覺腿腳不好,連南京藥學院的同學聚會也不想去。
最讓婁利玲苦惱的是記憶力下降。“以后就變成阿爾茲海默癥了。”她把病名說得清楚,卻記不清近期的事。
“九月份?”聽到兒媳提到九月曾送自己住院,婁利玲不禁反問。兒子無奈笑道:“不用記著啦。”
你的時間以想念為界,被分成兩截。你想要接近時間軸上幾個飄忽的亮點,它們卻越發模糊混沌。你以為影像不致丟失,自己卻漂泊在遺忘之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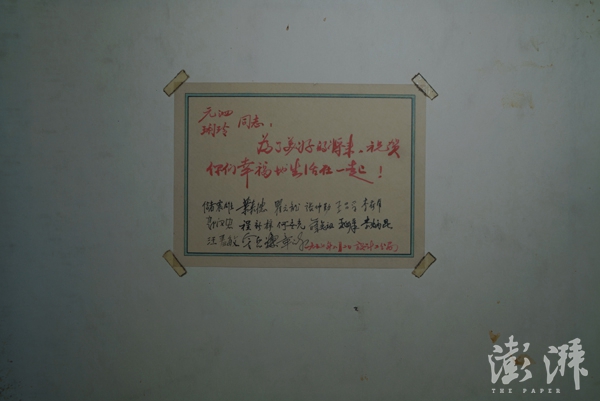
工廠
工人住宅是規整的兩室一廳。廳里掛著褪了色的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
大房間是書房,兼做章鷹夫婦的臥室。大書架上堆滿中英文的書,有用藥手冊,也有文藝小說。章鷹不太看書:“不像我爸和我媽那時候,像老學究似的,天天翻著書。”
父母都是大學生,章鷹自己卻是初中畢業。他18歲接了母親的班,進入五車間當維修工。五車間有上世紀六十年代一重自主建造的12500噸水壓機——這是一臺飽含著榮耀與使命的機器。早年填補了諸多國內鍛件的空白。而一旦這臺將近三層樓高的水壓機作業時卡了殼,章鷹就得爬上去維修,水壓機溫度高,他的工作服全部濕透,身上也到處是機油。
“一天能出你們一年的汗,出得一點勁兒都沒有。還特別埋汰。”
章鷹2000年便轉了崗。隨著年紀增大,他怕自己失一腳掉下去。

車間作息精確,工人們精神緊張,難有再學習的時間精力。技術卻在進步。2006年,新的15000噸水壓機投入使用。它打破了國外核電鍛件的壟斷——之前全靠進口,價格不菲。那臺章鷹服務多年的老水壓機,2010年也進行了改造,操作更加自動化。
2016年12月,55歲的章鷹正好退休。
章鷹不抱怨少讀了書。他對父親墓碑上的字引以為榮:“為一重獻身,終身奮斗。”這樣的獻身,似乎把自己兒子包含在內。
婁利玲卻想不起來,問:“誰寫的?”
為一重獻身的章元泗,經歷了一些重要的搬遷決策。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為了謀求更大的發展,一重設計產品研發、核電石化容器制造的部分業務逐漸轉移到大連和天津。章元泗也曾參與關于拿地的商談。
之所以機構搬遷,一方面考慮設備出海發運方便。另外,苦寒之地對人才的吸引力終究有限。到了2005年,一重只有生產制造的職能和企業總部還留在富拉爾基。
這已不再是章元泗和婁利玲來的時候。工廠走得比人快。

章鷹感慨,原本自己父母,在北京,在上海,都行。“但最后把我扔這兒了。”
那時都講究奉獻精神。但后來,章鷹和工友們發現,自己的收入與勞動強度不匹配。章鷹有點羨慕早年從重機廠去上海的連襟,“他還做這一行,加一個班400元,但在這邊,一個班15元,加班得隨叫隨到,不然扣錢。”章鷹感覺,連那點15元加班費,當年也是糊涂賬,不知記到哪去了。
章鷹說:“現在工人跌跟頭,打把式,往外跑。”
但章鷹也不無驕傲:“重機廠的工人,出去都是一把好手,什么活都能干。”作為中國重工業的搖籃,這里的工人有更多類型的車床可以操作,技術全面。只是,如今重工業總體不太景氣。跑到外頭也不好干。
眼下對一重而言,需要更多人才,但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去年5月新上任的領導雷厲風行,在上個冬天,搞了全員競聘。“干部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薪酬能增能減。”320名中層干部縮至190人。對營銷、高科技研發、苦險臟累差、高級管理人員等提升激勵。并制定了員工安置辦法,控制人員總量。此前遺留的集體職工的問題一并解決。
與此同時,去年定下的訂貨八十億、回款八十億的“雙八十”任務,當初看著遙遠,最后竟也完成了。今年任務是“雙一百”。后來,我們得知,從2017年1月起,一重便已扭轉了自2015年以來連續24個月虧損的不利局面。
近幾個月,廠里的工作量明顯多了起來。又因許多工人辦了內退,在崗的工人有時比以往更累。一個人得干好幾樣活。但工資不見得增加。因為任務多了,如果完不成,還得扣錢。
不過,比起之前沒活干的時候,這樣還是好得多。
章鷹感覺,“現在這廠子,正在爬坡階段,這個坡爬過去了,可能就好了。現在這個爬坡挺費勁。”
“國家好,小家才能好。”他又說道:“但要說,對重機廠有沒有感情,其實俺們說句心里話,我沒啥感情。”
劉秋娥急了:“也有,咋沒有。”章鷹回她:“你有,我沒有。”媳婦眼眶紅了:“我有。”
婁利玲從旁看著他倆,呵呵笑了幾聲。
劉秋娥平靜了一會兒,說:“咱們在這生,咱們在這長,咋能沒感情呢。”
章鷹還是覺得,這里沒有給自己帶來更好的人生。往年,與父親坐在一起嘮嗑,要是說重機廠不好,老人可不讓。
退休后,章鷹與工友一道旅游,拍拍照片。但不能走太遠,因為家里有老人。他每天清早六點醒來,已習慣了上班的作息。

你并不是為了重機廠而來。上世紀九十年代,廠里的藥劑科整體并入醫院,那時兒子已接了自己的班。如今老伴去世,與重機廠最重要的關聯也消失了。
城市
一家人不斷勸我喝水。自打幾天前進了一次五車間,我的咳嗽就沒斷過。
五車間的外墻上,掛著職業危害告知牌:“長期接觸生產性粉塵的作業人員,當吸入的粉塵達到一定數量時,即可引發肺病,還可引發鼻炎、咽炎、支氣管炎、皮疹、眼結膜損害等。”因此,必須佩帶個人防護用品,保證除塵設施運轉正常。
職業病難以避免。工廠生產中的排放物,連同干燥、寒冷的氣候,一并在人們的身心烙下印記。

建于1958年、曾興旺一時的黑龍江化工廠,去年忽然破產。此前,這家工廠收到齊齊哈爾環保局的二十九張環保罰單,累計三千多萬元,已然交不起這些罰款。與它同期建成的黑龍江玻璃廠、富拉爾基紡織廠,破產得更早。
章鷹為此挺高興,黑化可算黃了,要不夏天總是有味兒。“黑化周圍的房子,立馬能值點錢。”
但不久就傳來消息,富拉爾基簽下紫金銅業總投資40億元的十萬噸電解銅項目。人們還記得,這家企業曾發生瞞報廢水泄漏重大事故9天的事件,導致福建汀江部分水域污染。見慣了工業排放的富拉爾基人,對其宣稱的嚴格監管,一度不敢信任。去年夏天,劉秋娥也跟著大家,轉發抗議紫金銅業落地的消息。

“不管親戚朋友,我都介紹,齊齊哈爾有鶴,富區的大米也很好吃。水要是被污染,以后還能說什么呢?”
劉秋娥的話音帶著肺部的混響。她因身體不好早早內退,之前在一重的焊接車間開天車,后來整天咳嗽,她感覺,車間的有毒氣體向上飄。
劉秋娥去年還得了風濕,右手五個手指四個疼,腿也不好。風濕是這座城市的常見病。
章鷹不免擔心。“這地方,兩千多塊錢工資,要是沒有病,完全過得去。挺安逸的。因為物資便宜。但要是有病,就嘩嘩嘩一筆錢,又嘩嘩嘩一筆錢。”
早三十年,這里的人還年輕,不為這些擔心。這座在規劃圖上看起來猶如大飛機的風沙之城,看上去充滿榮耀。自1957年起,直到1990年代,幾乎每年都有中央領導,來到富拉爾基,視察那些牽系國家重工業命脈的工廠。

章鷹記得,那時街上能聽到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口音。人們身上有錢,看不上那些做小生意的。“來這里打家具、擦皮鞋的,都是南方人。”
現在情況早已不同。與章鷹的父輩同時來到富拉爾基的機構早已撤退。1958年從哈爾濱遷來的東北重機學院,1997年搬去河北秦皇島,即如今的燕山大學。齊齊哈爾醫學院也在世紀初遷至齊齊哈爾北市區。
正在老去的人,在富拉爾基的“大家庭”商場,追溯逝去的時光。在邁入2017年的那晚,商場頂樓的花園,搞了一場晚會。人們穿著亮閃閃的衣服,輪流拍照、嗑瓜子、換裝候場,在屬于自己的集體舞里回味青春,就像年輕時在車間換班那樣。“南方人可能覺得我們窮,但窮有窮的過法。”劉秋娥說。

章鷹和劉秋娥得照顧老人。劉秋娥常與北京的親戚交流養生,替婆婆求醫問藥。但或許擔心這邊醫療水平不行,對藥的用法用量不能及時調整,親戚沒有提供藥名。
大家庭的使命是守望相助。元旦那天的年夜飯,章鷹去了丈人家,兄弟姐妹坐了一桌。章鷹坐在九十歲的老丈爹身旁,不停為他夾菜。媳婦在家照顧母親。他們是兩家人的大兒子和大女兒。
而你總感覺,老伴要在大城市,還不至于去世。大城市有辦法治病。要是自己還在北京多好,在上海也行。
未來
冬天天黑得快。四點鐘已是傍晚。婁利玲趴在窗口望著。對面是一重車間。夕陽下的廠房,與章元泗去世前相比,沒什么不同。早幾年,每到換班時間,從這個街區涌出的人,會匯入更大的浩浩蕩蕩的上班隊伍之中。如今,周圍一重廠區的房子空了不少。

“這兩天冰少一點,這種冰上面走啊,怕摔一跤。”婁利玲望著樓下,似乎惦記著路上的歸人。
“老伴走以前問我,我死了你怎么辦,我說我也死。”
我嚇了一跳,忙說:“奶奶,這不行啊,還有活著的呢。”
“我說,你還有什么話要跟我說。什么也沒跟我說。我總想著他,好像總覺得,他應該在我面前。他退休以后,到大連去,有人請他在那工作,差不多七八年吧。我也去,住在大連。他回來以后,我就陪他出去走一走。溜達溜達。問他什么都懂,都會告訴你。他走了好像,活著沒意思。”
不知她是否聽到我的話。

她念著杭州:“多少年沒有回杭州去了。我的老家人現在都去世了。剩下我這一輩的,就有一個嫂子。也不去杭州了,因為別人都是小輩了。我的歲數也大了。出去要有人能陪著去。”
窗下亦有親人,給老人帶來驚喜。孫子回家時,把車停在下面。他眉眼有些像自己的爺爺,會開車帶著奶奶去街里轉。他在齊齊哈爾做公務員,因為不想當工人,也不愿離家太遠。
“兒子可能隨我,重感情。”劉秋娥有時想到,這是孩子懂事。要是去大城市打拼,北上廣,或者是杭州,靠家里這點在富拉爾基的積蓄,怕連房子都買不起。
富拉爾基的第三代大多遠走。“我們就這點好,把這幫孩子全都培養出來。有一部分上大連的,一部分上天津的。把孩子都整走之后,就跟著孩子去了。”劉秋娥說起兒子公務員考試考了第一,也很驕傲。自己早早內退,栽培孩子的精力不白費。
“我們的第三代,基本上沒有在重機廠的了,就重機廠,我們也不讓他們進來了。”章鷹見過最初的熱火朝天,見過后來的甩包袱,以及如今的周期性調整,感慨道:“現在工業這玩意兒,它沒準。”
屬于自己父親的時代終究已遠去。
五點多吃晚飯。兒子搟面烙餅,媳婦炒菜,是家常東北風味。婁利玲說:“我現在一點兒都不挑剔,有啥就吃啥。”以前她喜歡做八寶飯。
幾個月前,章鷹家附近的書報亭消失。婁利玲抱怨,自己訂的雜志拿不到了。但找不到書報亭的人了。打電話給郵局,郵局也沒有辦法。
客廳里擺著電子琴。家里只有婁利玲會彈。我們請她彈一首《送別》。老人起初推辭,后來拗不過。她的手指仍然靈巧。章鷹也露出笑容,給老太太拍照。“我老婆婆,很久沒彈琴唱歌,今天挺高興。”兒媳樂呵呵地,給自己的弟媳打電話。大家庭是這里的情感模式。

元旦過后就是春節。街區樓上樓下都是鄰居、工友、同學。章鷹的游園券直接送到了家里。“園”就是閑置的百貨商店和庫房。工會準備了套圈、丟沙包等游戲,獎品豐富而廉價。鬢角斑白的人們,倚靠著舊日的柜臺,在笑聲與驚呼中,觀看彼此的戰果與皺紋。工廠是一個更大的家庭。
退休的藥劑師婁利玲坐在書房的窗前打字。窗簾上的花紋是飛機形狀,一重廠前也有一架飛機形狀的涼亭。一重生產的重型設備,便用來制造飛機、火箭、航母上的裝備。為了這些國家使命,章元泗沒少出差。那天婁利玲拿著一捧絹花,去機場迎接老伴,回來就把花一直擺在寫字臺上。現在紅色的花上覆了一層灰。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