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口述︱國博研究館員李維明:跟鄒衡先生學習考古
【編者按】今年是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1927-2005)90周年誕辰,澎湃新聞采訪了鄒衡先生的高足、國博研究館員李維明先生,請他講述跟隨鄒先生學習考古的部分往事以及他自己的求學經歷。

大學前:管我們叫“知識青年”并不確切
我是1956年出生在河南洛陽。父親是黑龍江人,解放戰爭時期第四野戰軍的南下干部,后轉業到河南洛陽,參與第一拖拉機廠建設。他一直很正統,作為干部兩袖清風,一心撲到工作上,不怎么顧家,做事很認真。母親是拖廠醫院小兒科醫生,那時候誰家小孩生病了,隨時抱到我們家來,即使是吃飯的時候,母親會放下飯碗就給人家看病。據說兒科醫生很難當,因為小孩不會準確表達,有的嬰兒連話都還不會說,所以病情主要是靠醫生的判斷。父母的為人對我的成長有著重要的影響。
作為五零后,我們趕上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當時物質非常匱乏,身體缺營養。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又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很多學校都停課鬧革命。怎么上課呢?農村的學校是貧下中農來講課,城市的學校是工人來講課。我當時在第一拖拉機廠的子弟學校上學,曾經歷工人教師走上講臺,工業課主要講抽水機、拖拉機、發電機;農業課是講果樹修剪;政治課就是“反帝反修”、“巴黎公社”這些內容。到高中以后好一些,有歷史、地理等課程,數學、物理、化學、外語這些課,還會找廠里的技術員來教,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的。那時候“讀書無用”嘛,所以就是應付應付。
1974年,我作為知青“上山下鄉”到河南方城。現在回想起來,管我們叫“知識青年”并不確切,大概是與當時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相比而言,但其實沒有學到我們那個年齡應該學到的知識。

三年半后,招工回到拖廠,當機修工人。我在的那個車間生產拖拉機外殼,機器特別大,沖床有兩三層樓那么高,還有地下室,有個大滑塊往下壓。有時候修機器要鉆進大滑塊里或登上機器頂上,當時螺釘都這么大(李維明比劃,直徑大約十幾厘米),我印象中需要好幾個工人來上緊螺釘或松卸螺帽,先拿個套子套住它,上面有個桿兒,像推磨那樣推著讓螺釘松緊。當工人非常辛苦,三班倒,機床壞了就得白班連二班,二班連三班地修。
后來我調到拖廠二中——我的母校——當了美術老師,因為那時候我能畫兩筆畫,這是小時候的興趣。其實除了學校的圖畫課,我也沒學過畫畫,小時候家里連買畫材的錢都沒有,當時一個雞蛋2分錢,一張糊窗戶的棉紙5分錢,而一張圖畫紙是2毛錢,2毛錢是什么概念呢?一斤豬肉是4毛錢,一張圖畫紙相當于半斤豬肉。那時候家庭人口多,生活都勉勉強強。所以我在當學生幫老師撤展覽的時候,就把揭下來的廢紙帶回家翻過來用;學工勞動的時候,看到人家灑在地上的宣傳粉,就搓起來拿回家兌點水當顏料用,就那么個條件。當美術老師以后我還是買不起畫夾,曾經撿了塊三合板,我姥姥用舊床單幫我糊了一個,后來廠里的俱樂部又獎了一個。我當時給自己規定每天畫五幅畫,如果白天畫不完,晚上回到辦公室接著畫,所以那時候進步比較顯著。

讀本科:只要有一個學習的機會就行
1977年恢復高考,我已經年齡很大了,相當于別人大學畢業的年齡。但是我覺得這么多年終于有一個可以學知識的機會,其實對我來說學什么不重要,機會是人生中更難得的。我就開始復習考試,第一次就報考美術專業,素描都不怎么會,現學。我后來聽說洛陽市報考美術專業的初試有400人,進入復試40人,而這40人中就走了一個,去了當時的開封師范學院。我進入復試了,當時填了三個志愿:第一,中央美術學院;第二,廣州美術學院;第三個才是開封師范學院。后來知道第一志愿不錄取,第二、第三志愿也就完了。

當年高考科目有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沒有外語,我考了225分,過了文科分數線錄取線,但是沒報文科學校。后來我感到考美術這條路太窄了,就改考別的去了,原則是只要有一個學習的機會就行。1980年,我被鄭州大學歷史系錄取了。
為什么選擇歷史系呢?當時文科可選的不多,就覺得中文和歷史咱還知道是干啥的,其他一些學科都不大清楚是干啥的,就這樣去了歷史系。當時歷史系有個考古班,我覺得考古挺有意思的,就去聽考古班的課,也跟著他們考核,成績還不錯。考古班有的授課老師認為,這個同學學考古還不錯,就把我要到考古班。
本科時,開始翻翻課外書,但很多書看得都不太明白。比如說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當時買了一本,因為知識的欠缺,看不大明白;另外看鄒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覺得特別深奧、特別枯燥。隨考古班到洛陽偃師二里頭、安陽殷墟參觀學習,看到考古專家拿起陶片就能說出這是什么年代的,覺得他們特別神。當然我也清楚,人家這些知識都是下功夫來的。
讀碩士:鄒先生不看好我
1984年,我報考了北京大學俞偉超先生的研究生,結果專業成績過了,外語沒過。當年本科畢業,我被分配到洛陽市文化局文物科,主要負責管理報批、安全檢查、接待客人、起草公文等工作。我在那兒工作了兩年,其實同事、領導對我都不錯,但我總覺得大學知道的那些知識跟實際工作相差太遠了,于是就想再讀個研究生提高一下。
1986年,我報考了北大鄒衡先生的研究生,所有科目都及格了,但都不高,在六十分到七十分之間,就這樣考上了。后來我聽說,那年鄒先生想要一個來自長江流域的學生,培養他來做長江流域(楚文化起源)考古研究。他那年要招的學生專業成績很高,可惜外語沒過,被研究生院給卡掉了。
所以我考上研究生的時候,鄒先生對我這個來自黃河流域的學生很不以為然。有一次,就我們兩個人,鄒先生說,“我想要的沒考進來,我不想要的卻考進來了。門門都及格,這就是萬金油。”加上我的基礎不太好,缺課很多,田野考古也不行,所以鄒先生對我不看好。不過我從來沒怨過先生,我覺得應該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先生對你不滿意你就努力唄。
在學校我就是“三點一線”:教室、寢室、圖書資料室。只要在鄭大沒上過的課,都要補,那時候大概一周有二、三十節,我當時右手腕做了一個小手術,縫著線,即使這樣也不敢拉一次課。在北大上過的課有: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漢唐考古,還有一些公共課,另外還去中央民族大學聽民族學等。研究生選本科生的課特別吃虧,本科生拿2學分,研究生只拿1學分,盡管如此,還是把這些課都補下來了。聽北大所有老師的課,我都覺得非常棒、非常好,當時就覺得這是老師應該的嘛。我那時候很少跟老師打交道,為什么呢?我覺得要跟老師打交道,首先得有問題,要向老師請教,必須有準備。
其實我跟鄒先生接觸也不多,因為我覺得他不滿意我嘛。1986年研究生入學的時候,我都30歲了,那年剛剛結婚,家在鄭州。有一次,鄒先生帶著我們兩個碩士生到鄭州選發掘地點,同時到開封參加學術研討會。我們三個一起坐火車,上車以后把東西一放,鄒先生就拉著那個研究生補臥鋪去了,我留在那兒看行李。到了鄭州,鄒先生就讓我在鄭州待命,他帶著那個他覺得有培養價值的同學去開封開會,汽車就把他倆接走了。等他們開完會回來再會合,一塊兒做考古調查。有時候想想,還是會覺得老師有偏見。
鄒先生喜歡跟別人聊,到他家去的人也特別多。每次我去他家,不會超過15分鐘就會有人來。我一般一學期就去三次:開學了到他那去一次,說我來了,先生有啥吩咐沒有?學期中間去一次,給先生說我上半學期都做了什么事。到快放假的時候,去跟先生說一聲放假了,我走了。
假期的時候鄒先生一般都給我們安排實習,還讓我們寫實習報告,一假期別想閑著。比如說第一學期讓我們去山西曲沃曲村實習,報告中要寫發掘了多少座墓、多少灰坑、多少遺物、怎么分期等等,寒假20多天我大概整理出數萬字厚厚一本報告。當時每天只感覺太陽升起來了,太陽落下去了。春節期間都不敢和家人一起看電視。報告拿給鄒先生,他也就是淡然地翻一翻,就算過去了。

1987年春夏,我在河南密縣曲梁遺址發掘,發掘完大家都走了,我一個人留下來整理資料。整理工作在縣電影院會議室進行,房間很大,但窗戶是木頭的,多已經松散了,非常破敗。三伏天的時候特別熱,我就穿個褲衩子,掂了桶涼水,把兩個腳放在水桶里,撈一個濕毛巾搭在身上,把干毛巾墊在胳膊肘下,怕弄濕圖紙,就這樣繪圖。還有兩卡車陶片要統計,一片一片地數,開始還戴手套,手套都磨破了,后來就不戴手套了,手指皮膚磨破又長出新皮膚。最后像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陶片特征就熟悉了,這時候才知道為什么那些考古學家一摸陶片就知道它們是什么年代的緣故。
整理期間我每天晚上睡在一塊用于修復、繪圖的門板上。資料整理完要走的時候,把那塊門板掀起來,才發現下面堆放著發掘出土屬于商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尸骨,原來我每天就睡在這些尸骨架上方。所以說我們做考古的,有時候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讀博士:做考古確實非常艱苦
1989年我碩士畢業,分配到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當年鄒先生到河南淇縣指導研究生整理出土遺物,我就過去看他。當時他們在一個很大的破舊房子里整理出土遺物,房子漏雨,蚊蟲叮咬也很厲害,還要自己做飯。他那時候60多歲了,每天汗流浹背地在那兒干。我在那里觀摩部分陶器并繪了圖,晚上聊天,我就說,鄒先生我考您的博士吧。他說,考我的博士都排著隊呢,你排吧,大概你排到第三年。他每年一般只招一個博士生。

于是,我1992年考了北大博士。剛一入學,鄒先生就給我制定任務,讓我的博士論文做豫南地區考古,沒有什么可商量的。第一年時間,我收集南陽、信陽、駐馬店以及襄樊等地的材料,做了一萬多張卡片,然后背著這些卡片下去,不管到哪兒晚上我都要看卡片,看哪些是沒有的材料,把新的材料補充進卡片。

豫南地區以往的考古基礎很薄弱,我用一年多時間查看了采自340處遺址的陶器標本,后來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為了后人查閱資料方便,我把收集到的材料信息都放進論文了。比如豫南地區考古的目錄索引,豫南地區的學術史,我當時的調研日志。論文是有時效性的,也許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材料的補充就過時了,但是這些材料信息以后還是有用的。
博士研究生這三年有四千塊錢經費。我留下來一千塊錢,用作論文打印等答辯之需,用三千塊錢用于考古調查,像火車、長途汽車、住店、雇用民工在南陽淅川、方城和信陽的固始平寨進行了三次發掘等都要靠這些錢。我在豫南一共待了425天,行程10500公里,攤下來每天平均不到八塊錢。當時一個人,晚上能住辦公室就住辦公室,有時候也睡在教堂或者別人家的過道上。說實在的,外出時跟系辦公室主任告別的時候,都想說,也許這次出去可能就回不來了。

在外辦事,我的風格是堅持。有同志陪著我去調查遺址,中午喝點啤酒,下午就想休息,我說不行,時間有限,繼續調查。有時因伙食不好,有同志提出來,咱們能不能改善一下?我說不行,地方老百姓怎么吃,咱們就怎么吃。他們怎么咽下去,咱們就怎么咽下去。誰要是受不了,誰就走。我覺得你在那兒,老百姓都看著你呢。
在南陽淅川發掘,我們在一個五保戶家里用飯,本來說好一頓飯給她三塊錢,但是她太困難了,我們一頓飯就給她五塊錢。后在條件較好家用飯,一次給我們上四個菜,其中有一盤青菜,其余三盤是臭豆腐、干辣椒和咸蘿卜絲。每次我們四個人都把那盤兒青菜吃光,這三盤菜端下去拿報紙蓋著,下次再端上來,加一盤兒青菜,說起來也還是四個菜。
在信陽固始平寨古城遺址發掘的時候,我住的地方離工地有4里地,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往工地跑,晚上回來天都黑了。那地方水很少,每天只有半盆水用。發掘工作行將結束的頭天夜里下了雨,有幾根地層線還沒有測量繪圖,本想第二天再測繪,結果第二天仍然下著瓢潑大雨,那個發掘坑有五米深,黑漆漆的,旁邊的黏土都往下掉,隨時有塌方的危險。有同志好心,為了安全勸我不要下去,用目測估計把地層線連上。但我是一個北京大學的博士生,如果我這么做,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我說不行,穿上雨衣,讓一個人給我打傘,撐個大長竹竿子下去,把那幾根地層線測繪在地層剖面圖上。此時,雨轉為雪。來接我們的汽車,由于路窄雪滑進不來,就用拖拉機把我們拉出去,包括陶片。接應我們的同志說,我在那兒等你幾個小時,聽老鄉說了你不少的好話,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中央有這么好的干部。
離開發掘工地后,我因病毒感染病倒了,在地方醫院的病床上躺了十六天,什么藥都治不好,每天周而復始地高燒,后來不知道為什么慢慢就好了。病好了以后就趕到信陽去整理出土遺物,一間簡易房子就是整理室。十二月河南多冷啊,屋頂是一層薄薄的石棉瓦,窗戶是紙糊的,也沒有爐子取暖,我就穿著棉大衣、棉鞋、棉帽,每天早上七點到晚上十一點工作,終于把這些材料全整理完了,獲得一批有科研價值的新材料。做考古確實非常艱苦。
畢業后:和鄒衡先生“不僅是師生,而且還是學術上的朋友”
鄒先生是個嚴師,上學的時候我聽說他厲害,就躲著他,盡量少見他。而且也覺得他顧不上我。其實這段經歷反而讓我們倆之間的關系特別平等。博士畢業后,我到首都師范大學教書。鄒先生退休了,原來簇擁他的人有很多,退休以后身邊的人慢慢就少了。有一次他跟我感慨:“以前我身體還好,不需要人攙扶時,卻有那么多人殷勤相攙;現在老了,需要有人攙扶時,卻少有人這樣做了。”
那時候我剛到首師大,收入很低,生活也很艱難。但我想得明白,吃苦人過來的嘛,也不講究,專心學術,不斷有學術成果發表。鄒先生有時候看到我發表的學術成果,就給我打電話。為了節約電話費,只要他打進電話來,我就騎自行車到他家去陪他聊天,他家在中央黨校附近,騎過去大概需要五十分鐘,一去就聊一上午或者一天。有些車轱轆話,不知道已經聽了多少遍。
2001年,我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有一次說起先生退休后來往的人較之前少了很多。我就很直白地說,先生沒有用了,這句話惹他不高興。第二天,他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說了一些很不愉快的話,其中有一句,他說要跟我斷絕師生關系。等他說完,我說:“先生,我們是師生關系,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是誰想改變就能改變的。先生一生都說真話,為什么學生說了一句真話,先生就這么受不了?先生是不是也要學生說假話?”他在那邊沉默了。隔天上午九點,他又打電話給我,說昨天態度不好,他知道我當時正在評正高職稱,在準備外語考試,希望不要影響我的職稱考試。我說先生不會啊,你的話我都這耳朵進,那耳朵出去啦!
鄒先生是研究鄭州商文化專家,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學術觀點:鄭州商城是商代的亳都,是商代的第一首都,這填補了安陽殷墟之前的早商都城與文化的空白。先生找了很多證據,其中文字證據就是鄭州出土東周時期的“亳”字陶文,結果有人就質疑說亳字陶文是東周的,不能證明鄭州商城是商代的亳都。我在鄭州商文化的學習上投入了很多精力,最大的收獲是在1953年出土于鄭州二里崗的一件商代牛肋骨刻字上補識出一個“乇”字,可以說是我學術人生中最重要的發現。這個發現就給鄒先生“鄭亳說”提供了一個商代文字的時證,他很高興,先生對我這個發現非常認可,反復對我說:“沒想到啊,我當年在學校瞧你不起,沒想到你有這樣的進步。我身邊有你這樣的學生很欣慰,我們不僅是師生,而且還是學術上的朋友。”

鄒先生提出鄭亳說這個學術觀點以后,有幾位學人(包括他曾經教過的學生),從20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一直到2005年先生去世,不斷地發表文章跟先生爭論。鄒先生生前我沒有替他說過什么,先生去世以后,那幾位學人還在寫文章,而且是用尖刻的質問語氣來寫,我曾經告誡說,你有不同意見正面表達沒有一點問題,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如今他都不在了,你還用質疑的方式發難,人家怎么回答你呢?如果是這樣的話,作為學生,我就要回答了。有的人就是這種心態,先把鄒先生說成泰斗,然后蹦到他肩膀上批駁這個泰斗,整個批駁的過程,就覺得鄒先生是個阿斗。其實,這些人對相關材料并不十分熟悉,多為意氣用事。后來我就開始寫文章反駁了,代鄒先生講學術道理。他當年帶了我這么個學生,現在在學術上捍衛他創建的鄭亳說,這也是一種學術上的延續吧。

鄒先生學術體系做的很大,我做的很小。我以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只要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一點兒學術收獲,我生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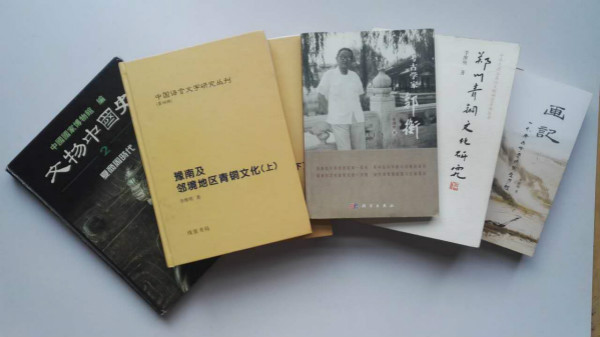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