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金瓶梅|李瓶兒:一只空空茫茫的流浪瓶
原創 蘭藉文化 紅樓夢研究 收錄于話題 #詳看金瓶梅 54個

作者
陽關
李瓶兒是個流浪的女子。
出生那天,有人送一對魚瓶兒來。這種瓶子,造型雅致,寓意吉祥,有文化內涵,有審美情趣,說明她的出身應該不差。
一張白紙等待書寫,一個命運即將展開。
是何緣法,第一嫁嫁與了大名府梁中書為妾?這是個一配多的老少配,而正室蔡氏暴虐嫉妒,一個個婢妾被打死了就往后花園里埋。
李瓶兒,于最為蓬勃鮮艷的年輪,只在梁家的外書房里住,承受著日逐一日的臨深履薄,空空落落。

第二嫁,名義上嫁的是花子虛,實際上嫁的是花子虛的叔叔花太監。
花太監想必不是嫪毐,在這個鬼畜事件里,子虛烏有的花子虛不過是個幌子。
花子虛不壞,只是缺少男兒氣概。沒辦法,叔叔有錢,便可以全方位無死角占用他的名分,以大質已缺之身,代行他對李瓶兒的一切權利和義務。
也許,在無數個另屋獨臥的夜里,聽著間壁的假鳳真凰,花子虛的胃里也曾倒海翻江,心里也曾摩拳擦掌。
而此時的李瓶兒,時不時,還要把他罵個狗血噴頭;好不好,還要老公公拿他打趟棍兒。
花子虛的宇宙一定是崩塌的。他,于血氣方剛之時,已無可挽回地衰頹了。
李瓶兒,在如斯的悖謬和顛倒里,也許有幾分對這個幌子的恨——好吧,你就心安理得做你的縮頭王八吧!

但基本上,看她后來對病勢沉疴的花子虛、對落水狗蔣竹山的那些釜底抽薪、冷水潑送,這個不幸的女人,也不是個善茬兒。
花子虛難做,李瓶兒更難做。然而她挺住了。走過那些雷聲暴虐,滴雨不落的歲月,她沒有枯萎,也沒有發瘋。
讓她挺過來的,除了花太監的年紀,還有花太監的銀子。基于這些銀子,她一輩子對這位老公公都是感念的。
花太監終于死了,然而某些記憶是死不了的。
花子虛每日只在三瓦兩舍里行走,他幾乎無法直面李瓶兒白花花的身體——這里那里,深淺高低,都有他叔叔花拳繡腿的印跡。
李瓶兒也已放下了對花子虛的期許。
她和他,相看兩生厭。
相比今天的富婆養鴨,李瓶兒終究只是個固有模具里陶出來的瓶子。不管多么靚而多金,多么漂泊不定,骨子里總是那個時代的傳統。她空空如也的身心,總需要一個合法的男人來填充,她的人生,總需要一個合法的家庭來支撐。而不是止步于逾墻鉆縫的偷情。
也許,中書府帶出來的那些珠子和寶石、老公公留下的這些體己,可作為她贏得一個健康好男人的資本。

沒有娘家人的她,盤算著,翹望著,多少個不眠之夜的點染勾畫之后,這一天,她遇到了她的瓶芯——西門慶。
經過了梁中書之懼內,花太監之妖魅,花子虛之雖有還無,乍遇上西門慶之狂風驟雨,李瓶兒,這朵流浪中的女人花,終于一塌糊涂地盛開了。
西門慶瞬間充滿了她。這場甘霖,澆開了她心身一切塊壘,澆開了她作為一個女人的全部溫婉、柔善、癡情和天真。這,就是她后來拼命嫁入西門家,似乎變了個人,如此那般溫良恭儉讓的原因。
不過,命運是個頑皮的孩子,于漫長的跌宕坎坷之后,還要第N次捉弄李瓶兒一下。
為西門慶做小的熱望幾度撲空,李瓶兒在平生最難將息之時,第三嫁,慌不擇路地嫁給了外直中空的蔣竹山。
關于這蔣竹山,李瓶兒后來對西門慶說:
你是個天,他是塊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
然而且慢,與西門慶登峰造極的敗壞相比,蔣竹山真有這么不堪么?來聽瓶兒原話:
你本蝦鱔,腰里無力,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吃臘槍頭,死王八!
原來,這蔣竹山只不過 “腰里無力”,而已。可是,因著這點無力,已足以被李瓶兒打入九十九層地獄。

而另一面,李瓶兒對西門慶的癡迷,則達到膜拜之境地。這膜拜,相當程度上,拜的就是西門慶的強有力,一睡之下,不計其余。
那么,好與壞如何劃分,愛與性誰為先聲?
有人說,李瓶兒性格前后不一,是近古文人創作女角的一個普遍性bug。
其實,李瓶兒的形象,從刻薄兇悍到馴順懦弱,從冷酷絕情到仁厚宅心,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的,其線索和軌跡也是清楚的、牢靠的。
從中書府到廣南鎮到清河縣,一路漂泊過來,李瓶兒啊,像奔命一樣盼著一個港灣。這個港灣里,律呂調陽,惠風和暢。
她之嫁西門慶,起碼有幾哭幾求幾跪、幾送銅不響。事實證明,古往今來,通過張愛玲指出的那條路,被撬開心靈大藏的女人,就是如此這般地把自己送進烈火煉獄的。
沒辦法,被肉體擊倒的靈魂,時而四仰八叉,時而俯首跪爬。
先是第十四回,人沒過來,三千兩銀子、四箱子珍寶已經過來了。李瓶兒一廂情愿地說:
“到明日,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
致命的戀愛腦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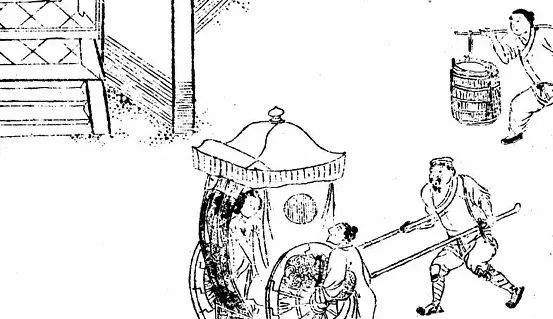
第十六回:
婦人遞酒與西門慶,磕下頭去說道:“拙夫已故,舉眼無親。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與奴作個主兒,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與官人鋪床疊被,與眾位娘子作個姊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說著滿眼淚落。
婦人因指道:“奴這床后茶葉箱內,還藏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著你蓋房子使。你若不嫌奴丑陋,到家好歹對大娘說,奴情愿與娘們做個姊妹,隨問把我做第幾個也罷。親親,奴舍不的你。”說著,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
“你早把奴娶過去罷!隨你把奴作第幾個,奴情愿伏侍你鋪床疊被。”說著淚如雨下。
應該說,經過這些連環套式的哭求跪請和財產轉移,李瓶兒的志氣已經低到了塵埃里。
接著,過了門,被冷落三天后,第四嫁的第四天,西門慶賞了她一頓鞭子。
這頓鞭子打在她的細皮嫩肉上,她當然是疼的、怕的。
然而真正讓她服帖的,文本作證,有一說一,不拔高不貶低,主要是西門慶的另一根同名利器。
“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
一宿綢繆,讓李瓶兒通體安泰。她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拿出許許多多的首飾金銀,試圖鎖定這遲到的幸福。
于此,我們看到,這個曠日持久、空空茫茫的流浪瓶,終而充實和停靠下來了。停靠下來的李瓶兒,寬忍,退讓,友善,溫良,認敵為朋,安于現狀。

如果說之前的她,是進取的,之后的她,則是守成的。昔日的革命要求在西門慶的隆隆炮聲中,很快土崩瓦解。
后來有了官哥兒,這個女人一發認為自己的人生業已功德圓滿。
面對著大群的母狼環伺,她一發伏牙蜷爪,幻想著通過綏靖來維持和平。
這里有一個不被主流認可的尷尬:有一種流浪叫性流浪,有一種安頓叫性安頓。前者最風雨飄搖,是諸多動蕩之所由生也;后者最固若金湯,是諸多靜好之所由系也。
不滿足,則抗爭,身心沒有著落時的李瓶兒,也是一頭斗志昂揚的母狼;既熨帖,則繳械,安頓了的李瓶兒,賢妻良母,垂眉低目,像艷陽下一彎百柔之水,盡顯女性之光輝。
她對西門慶始于肉欲的愛戀,也漸漸超越了身體層面,升華為對舉案齊眉相濡以沫的單向渴盼。對手下諸人的慈憫,也愈發深沉厚重。
孟夫子說:
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為這只瓶兒捉急。她千條水的漂流,萬座山的尋覓,這停靠的地方,卻不是個岸,只是個淪陷。而她已經自廢武功,丟掉了救生圈。
淪陷中,李瓶兒對自己的人生做了思省。思省的結果讓她發現并放大了自己的罪過。在窮途末路中,在懺悔中,她徹底回歸為一個內斂賢淑、溫謹謙卑、忍辱負重的傳統好女人,并被動而主動地拱手讓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官哥兒和她本人的生命。

說到官哥兒,作為媽媽,李瓶兒理應為他拼命。然而,孩子之于娘親,是一種雙向的加持,爭和忍都是母性。她久已習慣了忍氣吞聲,便有過些刀鋒,也都已經銹鈍得拿不出手了。
我們看到,這只瓶子上,是有那么多的,人我所加的傷;這只瓶子,盛不下西門家浩蕩的欲望。所以不止要被淹沒,亦且要被粉碎。
李瓶兒最后的日子,是凄楚的,但不倉皇;是沉痛的,但不冰涼。
她,打開箱子,拿出財物,分與眾人,以這個世界最流行最有效的方式,和大家做了一念兒。
她,到死都放不下西門慶。西門慶被她喚起的那些人性溫暖,也令人動容。
李瓶兒,這個倒貼了巨量財產、臨了還念念不忘西門家事、還在為他省錢的女人,受了西門慶一副三百二十兩銀子的桃花洞。
應伯爵喝彩道:
“嫂子嫁哥一場,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夠了。”
這里,我聽到紅塵之上,一聲長長的太息:
這個啊,讓人欲哭無淚的人世啊!
李瓶兒,付出了,原諒了,平靜了,要去還債了,世界欠她的,一筆勾銷了。
這只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一度被充滿的瓶子,魂銷夢散,復歸于茫茫大荒。

據說女人是精神的,男人是物質的,女人比男人更耐得住貧窮凄涼。相好的,牛衣對泣也安之若素;不相好的,金屋藏嬌也造事生非。
相好不相好的奧秘在哪里?
李瓶兒的故事告訴我們,女人,是精神的,更是肉體的,然而終究是精神大于肉體的吧。
大道至簡,真理不蔓。器之廝連,心之相牽。從精神到肉體是一條路,反之亦然。更可能,兩條路交互作用,不可二分。
曹雪芹說,才子佳人等書,作者不過是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這篇文字,碼到后面,我心里悲傷涌動。在此,截幾句話找補找補:
倘若他不是他你還是你,
你們會不會相逢在如彼的午夜里?
會不會減你三分雀躍,一段歡喜?
那么靈與肉,
誰是誰的主義?
他和你,
誰是誰的唯一?
可惱當年相思雨,
紛亂凄迷,誤了佳期……
原標題:《金瓶梅|李瓶兒:一只空空茫茫的流浪瓶》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