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偏向雪山行 | 與動植物為鄰的35年,守山人的野性呼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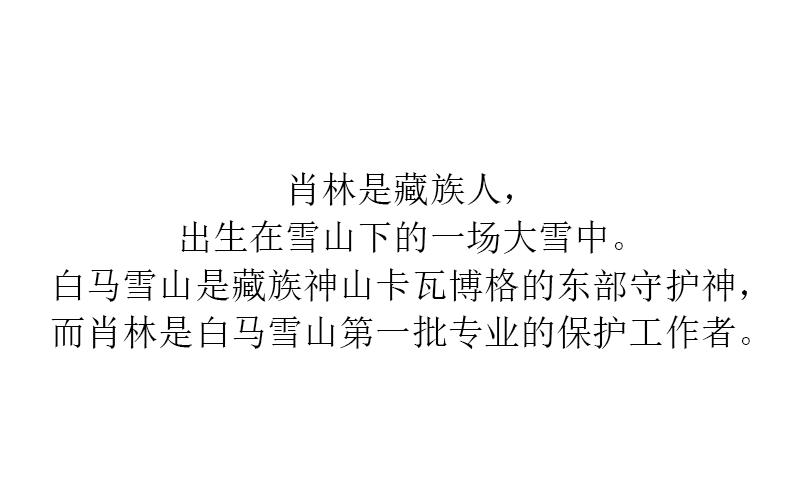
白馬雪山位于云南省德欽縣境內,1979年中國科學院昆明所的科學家在這里發現了滇金絲猴的存在。肖林是白馬雪山第一批專業的保護工作者,為雪山整整工作了三十五年。從十六歲到現在,他無數次上山勘察,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他怎樣是進行工作的?如何打敗孤獨?守山這件事,對他意味著什么?回歸正常的生活軌跡后,他有什么不適?2020年由樂府文化出品的《守山》,是肖林與作家王蕾共同撰寫的傳記作品,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對兩位創作者進行了采訪。
——編者按
每當故鄉飄起了雪,肖林就會感到濃厚又難言的鄉愁。那是老家鄰居拍下的紛紛揚揚的雪,群山一片白茫,雪山下的村子也覆蓋在蒼蒼白雪之下,如同童話中的小屋。看到這樣的景象,他心里就泛起無限的渴望,想驅車千里回家,回到他出生長大的地方,德欽縣佛山鄉江坡村。1967年的秋天,他出生在這里,出生在那年的第一場大雪中。
肖林,藏族人,原名昂翁此稱,小時候家附近駐扎的軍人們嫌麻煩,稱他父親“老李”,他便成了“小李”。久而久之,那演化成他的漢語名字“肖林”。那時候,在遙遠雪山下的“小李”不會想到,有一天他會走出家鄉村落,去到另一座名為“白馬”的雪山,將一生奉獻給它,也獻給雪山里的珍稀動物——滇金絲猴。他將與雪山、滇金絲猴糾葛一生,建立起深刻的羈絆關系,“一生無法分離”。

白馬雪山保護區內,一片少有人去的“世外仙境”曲宗貢。?攝影/肖林
多年以后,他堪稱傳奇的一生記錄在名為《守山》的書里,他和兩名隊員在海拔4300米的白馬雪山上駐扎三年的經歷得到還原。那是非比尋常的駭人經歷,他們時常背著被褥、鍋碗和糧食在野外一呆半個月,睡在大樹下、牛棚里和巖洞中,只為追蹤猴子們的行跡,尋找和確證滇金絲猴的存在,觀察它們的生存方式與習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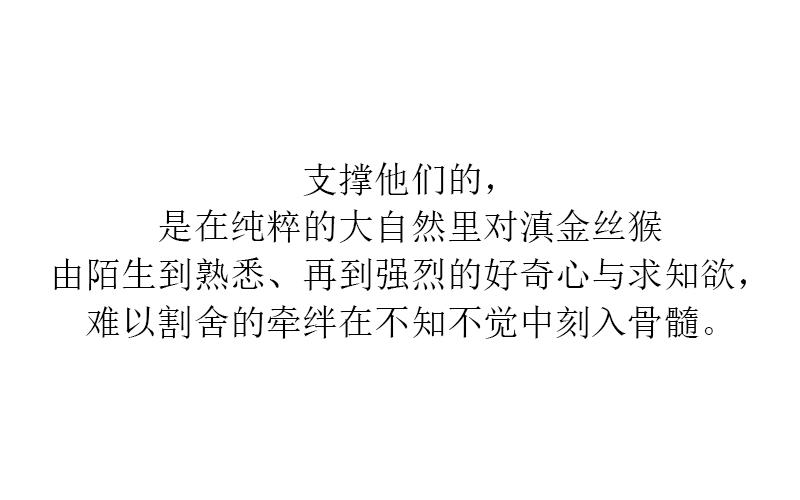
三年與世隔絕的生涯,他們經歷了極端的孤獨與艱辛,以致下山后患了幾年的失語癥。支撐他們的,是在純粹的大自然里對滇金絲猴由陌生到熟悉、再到強烈的好奇心與求知欲,難以割舍的牽絆在不知不覺中刻入骨髓。直至從白馬雪山保護局德欽分局退休,他都未曾離開過保護滇金絲猴和野生動物的前線,拒絕了職位升遷。
一切如同書里所寫:“野外三年正是我脫胎換骨的深深一眠,我在山里的時候便明白:這輩子如果和這些野生生靈斷開聯結,我將是個被剩下的可憐鬼。”
白馬雪山,我們的神山
肖林出生在大雪中,那是母親唯一記得的時間印跡。她不知道那是何月何日,只知道那天下起了秋日的第一場大雪。這也是那個時代藏族人的傳統,肖林在《守山》里說:“長輩們沒有一個人刻意記我的生日,因為我們藏族人不會去在意這些。老輩人甚至說不出生在哪一年,被問到年紀,他們只能含糊地說,‘七十歲了吧’,‘好像八十了’,然后疑惑地看著問的人。在藏族人心中,生死‘閘門’下,年輕幾歲,還是老了幾年,需要那么在意嗎?”
母親說:生在雪山下,便是一輩子的藏族人。出生在大雪里的肖林,更是和雪、雪山之間有著詩意而深刻的聯結。以至于他每每看到雪花從天而降,“內心深藏的秘密便會隨之萌動,仿佛只有大雪才能讓我煥發出別樣的能量與光輝……”

肖林的家鄉,雪山下的江坡村。?攝影/肖林
他在家鄉長到16歲,收到德欽縣政府將舉行公務員招考的消息,便和村里的小伙伴走路、搭車,歷經兩天抵達縣城參加考試。很快,他就收到了縣里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成為白馬雪山自然保護所的第一批員工。
一切源于1979年中國科學院對橫斷山的綜合科學考察,昆明所的科學家發現了滇金絲猴的存在,讓近百年的疑惑有了定論——原來滇金絲猴群還活躍在白馬雪山的層林之中。這直接推動了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的建立。1983年,中國政府又專門成立了白馬雪山保護所,以保護滇金絲猴等珍稀野生動物。
在德欽縣城培訓后,肖林和同伴們一起去往位于山下小鎮奔子欄的保護所。途中,翻越到海拔4329米的埡口,司機如同所有藏族人一樣,按照民族習慣停了車。肖林看著遠處“敦實厚重的雪山”,第一次和白馬雪山迎面相遇。

阿爾金山的盤羊。?攝影/肖林
白馬雪山,藏族神山卡瓦博格的東部守護神,相比藏區其他雪山利韌般的卓爾不群,它顯得“平易而厚重”。站在埡口的獵獵風中,肖林和藏族伙伴們高揚“風馬”,念起頌詞,念到最后把氣息提到高處,面對天地、山河高喊“拉索啰……”,那是古藏語中祖祖輩輩相傳的咒語,意為“神必勝”!他們的聲音在山谷中回蕩,就好像大山大河也在喊著‘神必勝哦’,風馬迎風飄揚,五彩顏色充滿整個天地。

一次巡護后的戰利品。@公眾號:樂與永續
那時候,這群16歲的少年不會知道,“我們這輩子的悲歡離合都再沒有離開過這座山,一直到老。白馬雪山就是我們的‘日達’(山主人),我們的神山,我們這些自然保護者這輩子的主人!”肖林“恨過他,愛過他,回頭來已為這座山付出了整整三十五年”。
他不是沒有過動搖,曾經差一點就離開了白馬雪山,申請調回離家更近、更能照顧到家人的農業局。但在最后一刻,得知將加入三年野外考察、尋找滇金絲猴的時候,他只思考了三分鐘,便決定放棄調回農業局的機會,加入野外考察小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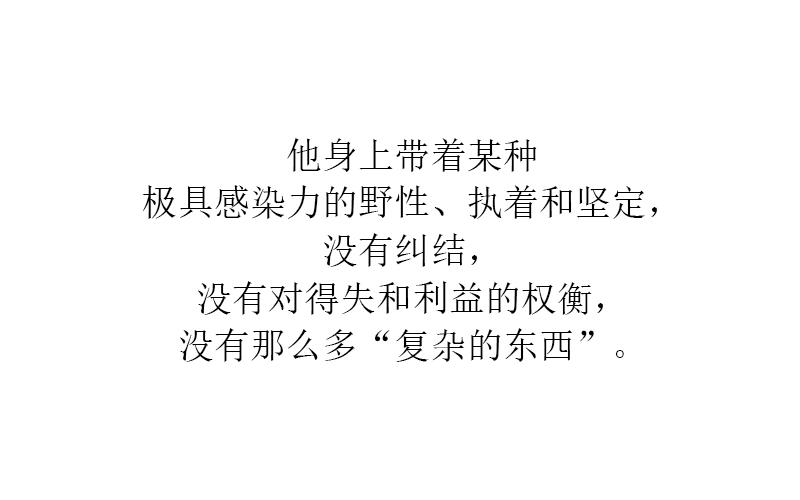
在保護所10年,肖林和同事們開展了種樹、巡山、抓捕盜獵分子等事務,卻始終沒見到滇金絲猴。“這個單位的成立就是為了保護滇金絲猴,但我卻連見都沒見過……人生能有多少個10年啊。”他說,“除非家人的日子非常困難,那我應該不會放下他們不管。但大家過得也不錯,有吃有喝,不算富有,但也可以了。而我選擇了這份職業,核心就是滇金絲猴。沒有它,就沒有我的工作,沒有我每個月的工資。我拿了10多年固定工資,卻連這個瀕危物種都沒有見到,心有不甘啊。”
生活的舒適,與家人的團聚,似乎都無法與他的職業使命相抗衡。他身上帶著某種極具感染力的野性、執著和堅定,沒有糾結,沒有對得失和利益的權衡,沒有那么多“復雜的東西”。那種不以務實為要義、“為瀕危物種付出一生的激情”,顯得稀少而珍貴。
山中三年,
被滇金絲猴撫慰的孤獨
他的一生,都被那三年改變了。人生從此以“山上三年”為界,分為上山前和下山后。那實在是異乎尋常的三年,也是《守山》里極為動人的篇章。

晴天的白馬雪山。?視覺中國
他和同事鐘泰、美國人老柯完全生活在野外,與雪山、森林、野生動物們相處,長年見不到人。每個月有15天,他們在高山森林中行走、奔跑、追尋滇金絲猴,另外15天做植物樣方,以弄清楚猴子們身處的環境、以何為生。
做滇金絲猴的15天最為辛苦。他們需要帶上15天所需的糧食、各自的被褥和鍋碗,肖林和鐘泰每人的背上至少會壓上60斤。不能帶帳篷,否則太沉,于是睡覺只能找露營的地方。他們睡過老鄉的牛棚,可以遮風擋雨,附近還有水源,他們把這稱為“三星級賓館”。
而另一處“五星級賓館”就更不得了了。那是一個看來普通的巖洞,“巨大的巖石下端凹進去,像一只慷慨保護的大手,雨水冰霜阻隔在外,我們只管放心躺進去。最絕的是洞里厚厚一層鬣羚的糞蛋,結實圓滾的小糞蛋墊了足足半米厚。躺上去,無數溫柔的‘小手’就趕過來給你按摩,酥麻的感覺直鉆到骨頭縫里。糞蛋還吸潮,睡上一夜,長期露宿在外帶來的風濕關節痛全都消失。”

肖林和同事在用望遠鏡勘察。@公眾號:新周刊
他們睡得最多的地方還是參天大樹下面,“在樹下直接鋪上塑料布,鉆進單薄的睡袋,頭枕大地,眼望星空,閉上眼睛就是一夜。半夜,被寒冷凍醒過,被急雨澆醒過,被大風吹醒過”,但也有過美好的夜晚,有時偶爾醒來,看見漆黑的夜空中閃爍的星,星光下的樹,疲憊得到安撫,整個人很通透,不知不覺就沉入夢鄉,醒來神清氣爽。
那樣艱苦危險的條件,后來年輕的同事們已不敢相信、無法想像。誰都會想要問一句:你們是如何堅持下來的呢?整整三年啊。
三年之初,肖林的妻子獨自在老家,挺著大肚子。那年冬日大雪,是德欽縣60年未遇的雪,一夜之間屋頂就積了五六十公分的雪,十分危險。若屋頂吸水過重,便有垮塌的可能。肖林后來才知道,是隔壁的幾戶鄰居們趕過來幫忙,把屋頂的雪弄成團后推了下去。“人的一生呢,左鄰右舍非常擔心你,都跑來把你的屋頂清掃干凈,這種純真和情感是很難得的。”他說。

白馬雪山的秋天。?圖蟲創意
而那時呆在白馬雪山上的他還在努力堅持下去。時間是慢慢變得不再難熬的,轉變的核心來自滇金絲猴。
觀察滇金絲猴的前一年,他和鐘泰都覺得非常無聊。除了第一次發現滇金絲猴感到興奮以外,此后他們都失去了耐心。還能有什么花樣呢?“一會兒跳來跳去,一會兒傻傻蹲在樹枝上,剩下的行為就是睡和吃。它們居然每天睜開眼睛就吃,直到閉眼睡覺,一直就在吃吃吃!睡覺的時間也長,上午十一點就開始午睡,有時甚至睡到下午三點半,晚上天一黑又接著睡。”
實在無聊,他和鐘泰兩人就開始互相推托那唯一的一架望遠鏡。“我說你看吧,他說你看吧,甚至兩個人因為太累了就曬著太陽打起了瞌睡。”肖林說。


上圖:母猴抱著小猴。@公眾號:白馬雪山滇金絲猴
下圖:小猴在玩樹枝。@公眾號:白馬雪山滇金絲猴
他們誰也沒有想到,一年后,兩個人就爭起了望遠鏡,誰都想把持著那個高倍望遠鏡不放。他時不時要推推鐘泰,“你累了,休息一下吧,我來看。”輪到他的時候,鐘泰也一樣,在一旁等不及地催他。
一切都是因為:之前認為“大姑娘繡花”一樣無聊的事,他們竟看出了門道。他們分辨出了幾個完整的猴子家庭,一個家庭有一只大公猴,兩只或四五只母猴,再加上嬰猴和幼猴。吃食、宿眠、轉移都是以家庭為單位。母猴甚至幼猴對大公猴恭讓三分,行為中不乏討好。這是一個無須質疑的“男權”家庭組織體系。
肖林說,觀察得越深入,就越會想要知道個體之間的區別、家庭之間的比較,想知道的東西就越來越多。但他們只能看出猴子家庭內部的關系,卻無法對猴子的社會形態得出結論,只是隱隱感到,它們的社會等級嚴格,家庭與家庭之間因大公猴的地位而有等級高低。直到最后,他和鐘泰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滇金絲猴中沒有猴王!那一結論,后來也得到其他科學家的認可。

肖林和同事們人工孵化、養護的白馬雞,被放歸山林前,生活在曲宗貢大本營的救護站。?攝影/李攀
1993年7月14日,肖林收獲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那天,他跟蹤著猴群,一路來到山巔。當他把自己塞進懸崖中的V字形縫隙、將相機舉在胸前后,猴子們來了,停在離他七八十米遠的大石頭上。竟是一個完整的猴子家庭!
六只猴子齊齊出現在那塊裸露的巖石上,那是他追猴生涯的第一次!他按捺住滿心的激動,鎮定地按下了快門……那是他們第一張成功的滇金絲猴照片,也是迄今唯一一張滇金絲猴純野生狀態下的完整家庭狀況呈現。
找塊干凈地方,
把骨灰灑在雪山里
山中歸來,肖林得了失語癥。“身體變成一口枯井,無論怎么使勁都抽不出一滴力氣”,“極其怕冷,手上沾一點涼水,雞皮疙瘩就立刻從手背一路蔓延到肩膀”。情緒消沉,不愿說話,就連單位組織匯報,他沒說幾句,眼淚就止不住,連話都說不清,只能哽咽道:“事情就是這樣……”匯報就結束了。

2013年,肖林與昆明動物研究所的龍勇誠、美國加州大學的科瑞戈、同事鐘泰一起完成了對滇金絲猴較為系統的生態生物學研究。@公眾號:新周刊
他后來才知道,經歷過極端環境的人,往往都很難重回原本的生活軌道。輕者失語,重者精神失常。“在4300米的冰天雪地里,連鳥叫都聽不到,就那么三個人,也沒話講了,互相看著都煩。”他說,他用了幾年時間,和愛人孩子在一起,重新體會溫暖的親情,融入單位,才慢慢回歸人間。
但那段經歷,終究對他們意義深遠。有時候,他會想起在雪山夜晚聽到的陣陣狼嚎,還有迎面相撞的那只狼。“它來得悄無聲息,當我們發現時,和它的距離已超過人與動物間的安全距離。可再仔細一看,它的步伐搖晃,最吃驚的是它的肚皮只是薄薄一層,緊貼在腹腔,與其說是在走,不如說在地上蹭。見到我們兩個‘肉塊’,卻沒有任何力氣捕食,只是帶著濃濃的弱者的自卑,默默離開,承受將死的命運。”
從此,肖林對狼的印象改觀。它不再是“狡猾奸詐”的野獸,而是歷盡艱難也無法填飽肚子的可憐生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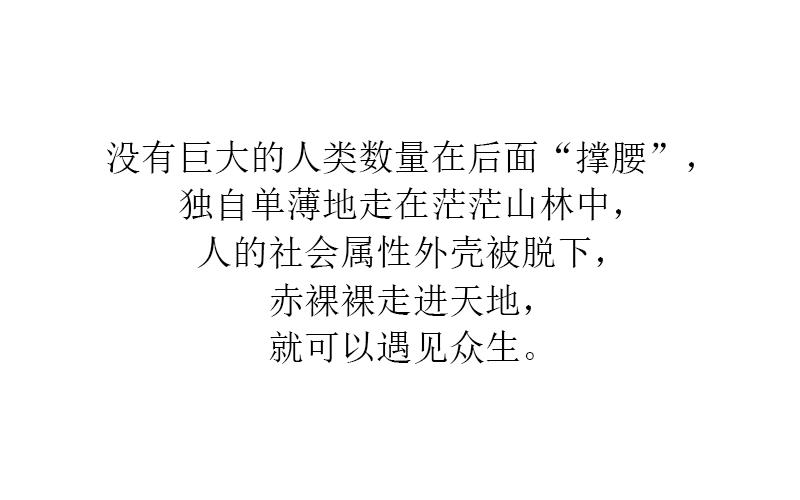
那三年讓肖林意識到:“白馬雪山里,恣意生存在大自然里的野生植物和動物,千百萬年來早已形成相互依賴又相互制約的生態系統,人在這里反而是孤單的。沒有巨大的人類數量在后面‘撐腰’,獨自單薄地走在茫茫山林中,人的社會屬性外殼被脫下,赤裸裸走進天地,就可以遇見眾生。”


上圖:生長在云南白馬雪山海拔4500米以上巉巖的雪兔子。@公眾號:樂與永續
下圖:綠絨蒿屬中個兒最高,開花最早的全緣葉綠絨蒿。@公眾號:樂與永續
他身上的“野性”,也在那三年里徹底地融入骨髓,一生無法消除。那也是《守山》的合著作者王蕾對肖林的深刻印象。王蕾至今記得,她第一次被肖林震撼到,便是2016年野生動物攝影師奚志農在大理為肖林舉辦攝影展的時候。那時,王蕾為肖林拍攝的野生動物寫圖說,還在藏北拍攝的肖林通過語音為王蕾發來解說。“他吃著肉,喝著酒,然后在山坡上找一個有信號的地方給我發一段語音。那些東西特別打動我,很簡單的語言,卻有種打動人心的力量。”王蕾說。多年后,她將他身上那最為動人的東西,總結為——“野性”。

在野外的肖林。
“他身上很有力氣和力量,踏踏實實做事情,坦蕩,大氣。包括他們整個白馬雪山保護局氣氛都是如此。”王蕾說,“跟自然打交道的人都有這樣的特點,遠離名利,很可愛。”
那也是王蕾在《守山》里想要表達的:把人類精神性的高度呈現出來,或許能給現代人的內心帶來鼓舞和安慰。
這便是肖林和白馬雪山的故事。有時候,肖林和同事們一起喝著青稞酒,笑著說:“以后要把我們的骨灰一起撒到白馬雪山最干凈的地方。”每每想到此,肖林都會熱淚盈眶,那是他一生的注解和情誼所在——“坦蕩為人,努力做事,這樣的患難之交,白馬雪山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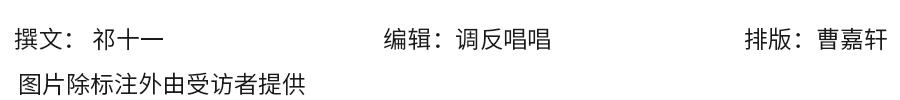
原標題:《偏向雪山行 | 與動植物為鄰的35年,守山人的野性呼喚》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