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專訪《羅曼蒂克消亡史》作者程耳:文學(xué)到電影是條喧嘩的道路
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上映以來,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和爭議。該片在豆瓣獲得了7.6的評分,然而,評價和口碑卻呈兩極化。在有些影評人眼中,本片散發(fā)著史詩氣質(zhì),堪稱中國版的《教父》,甚至是年度最佳的華語電影。然而,也有不少觀眾大呼“看不懂”,“不知所云”,“大型裝XMV”。對這些評價,導(dǎo)演程耳都一笑置之。
被問及有沒有向昆汀等導(dǎo)演致敬時,程耳說自己的電影沒有向任何作品致敬的意思,他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是出于本能,而他也強調(diào)自己不是民族主義者,他痛恨的,只是“那一代”的日本人。

其實,除了拍電影和寫劇本,程耳平時有了靈感還會寫小說。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就改編自程耳同名短篇小說集中的三個短篇:《童子雞》、《女演員》和《羅曼蒂克消亡史》,而小說的寫作也早于劇本。
他目前還沒有開始動筆寫下一部電影的劇本,但同題的小說已經(jīng)寫好一段了。
程耳在接受采訪時經(jīng)常會談到“一切事物的營養(yǎng)都來源于文學(xué),包括電影”,他把文學(xué)作為電影和電視劇創(chuàng)作的母體。
“同樣的一部電影,比如《羅曼蒂克消亡史》,有的人很喜歡,有的人不喜歡,說到底都是文學(xué)修養(yǎng)的問題。”
不過在他看來,“就中國現(xiàn)在的情況而言,從小說創(chuàng)作到影視創(chuàng)作可能是一條更加喧嘩和高調(diào)的道路,從電影到小說的道路肯定是寂寞得多,但后者可能帶有更多的反思。”
相對于影視的喧嘩,文學(xué)尤其是嚴(yán)肅文學(xué)要寂寞得多。但程耳并不贊同那些認(rèn)為嚴(yán)肅文學(xué)會消失的觀點。
“需要嚴(yán)肅文學(xué)的人雖然看起來沒有那么多,但是這些人都很精良。文學(xué)怎么會消失呢?嚴(yán)肅文學(xué)更不會消失。它們只是很寂寞,但是所有的反思還是得靠這些嚴(yán)肅的文藝和嚴(yán)肅的創(chuàng)作。”
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就嚴(yán)肅文學(xué)和電影在當(dāng)今中國的不同熱度、劇本的創(chuàng)作以及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一些相關(guān)問題專訪了程耳,以下為訪談實錄。
從文學(xué)到電影是一條喧嘩和高調(diào)的道路
澎湃新聞:您之前說寫小說的時候會注重畫面感,這和您拍電影有關(guān)嗎?
程耳:這個肯定是誤傳,我應(yīng)該沒有說過寫小說的時候注重畫面感這件事。因為這兩者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文本和不一樣的語法。但是文字本身有一種更廣闊的想象空間,我覺得這可能不僅僅是畫面感。
澎湃新聞:現(xiàn)在不拍電影的作家在寫作時也會無意用文字制造電影的畫面感,比如用文字制造一種王家衛(wèi)電影的感覺。您如何看待這種寫作的趨勢?是因為電影目前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一種比較強勢的表達方式嗎?
程耳:我覺得很難說這是一種趨勢,因為我還是認(rèn)為文學(xué)是基礎(chǔ),其實更多的是文學(xué)對電影的影響。當(dāng)然,我沒有太深入地思考過這個問題。如果是被電影影響的文學(xué),我認(rèn)為不會是太好的文學(xué)。
澎湃新聞:此前戲曲和話劇流行的時候,文學(xué)作品中有些描寫就會具有舞臺感,比如在小說的設(shè)定中讓人感覺有個舞臺,不同的人物來來回回、上場下場,在金庸和汪曾祺的作品中都能找到這種感覺。那您覺得電影會用類似的方式來影響文學(xué)嗎?
程耳:我覺得一定都是有聯(lián)系的。電影或許對文學(xué)有影響,但我覺得不會在文本價值這個高度或?qū)用嫔希矣X得這種影響是不太重要的吧。因為我還是認(rèn)為一定是文學(xué)更多地在影響電影。我覺得如果反過來,電影影響文學(xué)的話,那應(yīng)該都在很皮毛的層面。包括你說的舞臺感對文學(xué)的影響,其實如果我們退回到純小說的概念上,即便這種影響存在,也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澎湃新聞:有些情節(jié)在您的小說里只有一句話,比如“吃完就是操,操完還要吃,日復(fù)一日”這一句,但在電影里卻有不少淺野忠信和章子怡的對手戲來表現(xiàn)這一句話的內(nèi)容。在電影中,演員通過表演所表達的情緒也要比文字部分更豐富。那是不是電影也有文學(xué)所不具有的優(yōu)勢?
程耳:首先,我不認(rèn)為那段電影比那段文字更豐富,我認(rèn)為電影只是表達了那句話的一個方面。這還是表達方式和語法的問題,因為我也不認(rèn)為小說里的那一句話是單調(diào)的。文學(xué)是母體,是一個很寬泛的范疇。我們倆現(xiàn)在聊天,我和別人打電話,其實依托的都是文學(xué)的基礎(chǔ)。文學(xué)是包羅萬象的,從一對一的對話到小說至電影的創(chuàng)作都包含在其中。
澎湃新聞:那您覺得那句話沒有被電影表達出來的含義有哪些?
程耳:我沒有說沒被電影表達出來,我只是說我不認(rèn)為電影表達得比那句話更豐富。

澎湃新聞:您既拍電影又寫小說。在您看來,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影視創(chuàng)作的最大區(qū)別在哪里?
程耳:最大的區(qū)別還是語法和表達方式。因為當(dāng)寫小說的時候,我個人對自己的要求是會保持一個純粹小說的樣式,不可能是劇本或者是別的東西。它們用的材料其實完全不一樣,一個是鏡頭,一個是詞語。
澎湃新聞:您怎么看待有些作家目前放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投入影視創(chuàng)作的現(xiàn)象?
程耳:首先,人家沒有放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是否放棄創(chuàng)作,所以不能這樣說。就中國現(xiàn)在的情況而言,從小說創(chuàng)作到影視創(chuàng)作可能是一條更加喧嘩和高調(diào)的道路,從電影到小說的道路肯定是寂寞得多,但后者可能帶有更多的反思。
澎湃新聞:目前電影基本是輿論最關(guān)注的創(chuàng)作形式,相比之下嚴(yán)肅文學(xué)要落寞的多。嚴(yán)肅文學(xué)最終會因為不被大眾需要而消失嗎?
程耳:不是落寞是寂寞。這不會的。需要嚴(yán)肅文學(xué)的人雖然看起來沒有那么多,但是這些人都很精良。文學(xué)怎么會消失呢?嚴(yán)肅文學(xué)更不會消失。大家都在說嚴(yán)肅文學(xué)、嚴(yán)肅音樂會消失,但是都不會消失。它們只是很寂寞,但是所有的反思還是得靠這些嚴(yán)肅的文藝和嚴(yán)肅的創(chuàng)作。
“不是有感而發(fā)的創(chuàng)作怎能產(chǎn)生愉悅感”
澎湃新聞:看您之前的采訪,有提到最喜歡的作家,您說是博爾赫斯,能否說說文學(xué)給您的滋養(yǎng)和啟發(fā)?
程耳:像我前面說的,文學(xué)是一切創(chuàng)作的基礎(chǔ)。我覺得,不僅僅是文藝工作者和觀眾讀者需要文學(xué),即使是最普通的大眾也需要文學(xué)。在生活里你會發(fā)現(xiàn),有的人你特別喜歡跟他聊天,有的人卻完全話不投機,在我看來這取決于對話的雙方在文學(xué)上能否契合。
文學(xué)不僅僅是一個個的故事,它其實是你的審美和價值觀,這又反過來決定了創(chuàng)作者和欣賞者的“口味”。同樣的一部電影,比如《羅曼蒂克消亡史》,有的人很喜歡,有的人不喜歡,我覺得說到底都是一個文學(xué)修養(yǎng)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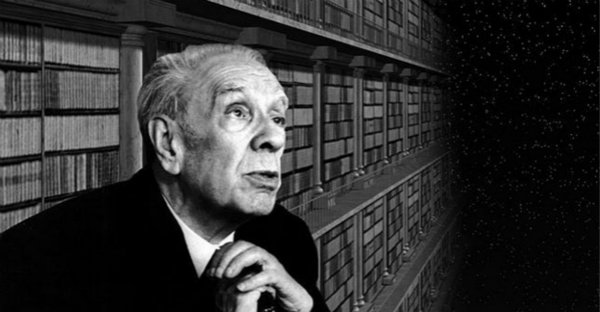
澎湃新聞:您的小說《童子雞》講述了一個很完整的故事,但為什么這條線放在電影里卻很短,在中間就停止了?
程耳:先和你說標(biāo)準(zhǔn)答案,因為我要留一個沒有消亡的羅曼蒂克。第二個答案:你明明看完小說了,還問我這個問題,你不是在給我挖坑嗎?
澎湃新聞:我只是比較好奇,看完小說后覺得您可能會拍《羅曼蒂克消亡史》第二部。
程耳:要拍也不可能拍《童子雞》。文學(xué)和電影還是不一樣,我們就拿《童子雞》那篇來舉例。很多人都說《童子雞》的后半段沒有拍出來太可惜了,但是我認(rèn)為后半段拍出來也不好看,而真正好看的就是拍出來的那一段。
澎湃新聞:您接下來會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影視創(chuàng)作還是小說的寫作?
程耳:就目前來說,我的劇本還沒動筆呢,小說已經(jīng)寫了一小段。從創(chuàng)作來說,寫小說會更自由,不用依賴于別人,想寫就能拿起筆來寫。
澎湃新聞:有報道說你下一部小說集還要保持7篇這樣的數(shù)量。
程耳:我的下一部小說集可能每篇小說都會再長一點,所以從篇章上來說不會有7篇這么多。但和這一部會有更完美的對稱方式,到時候你們就會知道了。
澎湃新聞:那您創(chuàng)作小說的興趣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程耳:其實也不是興趣,只是有的時候有寫寫字的欲望。寫作這種東西是很奇怪的,我在桌上放一張紙和一支筆,我可能有六個月都不愿去觸動那支筆。但突然有一天,你就可能想去觸動那支筆,那個時候就去寫,其實是特別簡單。我覺得真正的創(chuàng)作應(yīng)該是一個特別自然的過程,所謂有感而發(fā),無論是小說創(chuàng)作還是電影創(chuàng)作,這都是前提。
為什么有些作品,創(chuàng)作者自己痛苦,觀眾看著也痛苦。因為可能根本不是有感而發(fā)的內(nèi)容,怎么可能產(chǎn)生愉悅感呢。如果小說和電影有什么共性,那就在于它們那種流淌而出的方式,一個是文字的流淌而出,一個是畫面和聲音的流淌而出。
越來越多的人能去拍電影絕對是件好事兒
澎湃新聞:您是電影學(xué)院畢業(yè)的,學(xué)院派出身,您畢業(yè)的時候拍電影還是一個門檻很高的事情,但現(xiàn)在隨著技術(shù)的普及和資本的注入,拍電影的門檻大大降低了,很多作家都開始轉(zhuǎn)型做導(dǎo)演了,您怎么看這些作家轉(zhuǎn)型做導(dǎo)演后拍出來的作品?
程耳:其實我沒太看過他們拍的片子,所以我也沒法評論。但這事兒要一分為二地看,一方面,不要人為地制造壁壘。我覺得越來越多的人能去拍電影,這絕對是一件好事兒,只有電影越來越多,才會有競爭,才能大浪淘沙地留下一些好作品。
但另一面,現(xiàn)在很多人對拍電影這事兒越來越?jīng)]有敬畏了,我年輕時候喜歡的很多詞,比如“導(dǎo)演”,比如“藝術(shù)片”,現(xiàn)在都不好意思提了,都從所謂“高大上”的詞變成貶義詞了。我是覺得不管做什么事,都得拿出應(yīng)有的態(tài)度,多一點敬畏,別讓你這個行當(dāng)蒙羞。
澎湃新聞:相比香港的一些導(dǎo)演把自己定義為第三產(chǎn)業(yè)的員工來說,是不是內(nèi)地的導(dǎo)演還是有一種使命感和藝術(shù)家的抱負(fù)?
程耳:我覺得其實談不上一種抱負(fù),“抱負(fù)”這種詞還是太大了。我覺得一方面就是一種笨拙的自尊心。無論你拍哪一種電影,其實哪怕是你說的那種第三產(chǎn)業(yè)的電影,如果有笨拙的自尊心,也還是可以把電影拍好。因為人各有志,每個人想做的事兒和每個人能做的事兒是不一樣的。首先你要找到自己想做什么,然后真正冷靜地認(rèn)知到自己能做什么。所以稍微自尊一點,就可以把事情做好,其實沒有那么難。衛(wèi)星都能造出來,拍電影有什么難的呢。

澎湃新聞:電影出來以后,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覺得在電影里看到了昆汀的影子,但在我看來你的電影比昆汀的片子要節(jié)制很多,不僅僅是在演員的情緒控制上,也體現(xiàn)在鏡頭語言上。同樣,在《羅曼蒂克消亡史》里我也看到了類似諾蘭的敘事手法,但是又比他的電影更有歷史感和格局感,能否請你談?wù)勏矚g的導(dǎo)演和他們的作品?有致敬的意味嗎?
程耳:我拍這部電影的時候,沒有想向任何人致敬的意思,但是你之前喜歡的一些作品,總歸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你的創(chuàng)作,我的創(chuàng)作都是出于本能。要說給我影響最大的導(dǎo)演,其實有很多,比如黑澤明、比利懷爾德(代表作有《桃色公寓》、《日落大道》、《倒扣的王牌》等等)、恩斯特?劉別謙(代表作有《天堂可以等待》、《你逃我也逃》等等),還有很多很多。我還是受這些早期的、比較古典一些的導(dǎo)演們的影響比較多,昆汀的電影我當(dāng)然也非常喜歡。很多人說覺得昆汀的電影手法很新,其實換一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昆汀是一個充滿文學(xué)性、詩意的、傳統(tǒng)美學(xué)的導(dǎo)演。
“我絕對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澎湃新聞:之前我看到有人說這部電影是以“抗日劇”立項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程耳:這個我不太清楚,這是公司的行為。
澎湃新聞:在您的小說里,提到日本人往往都會用“日本賤種”這個詞,那您是不是很討厭日本人?
程耳:我前面是有三個字的,“那一代”。我絕對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我只是就事論事。與此同時你也一定看到我其他篇章里對日本當(dāng)代社會也有很多很細(xì)致的描述。我覺得應(yīng)該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反思戰(zhàn)爭本身,而不是說哪個民族的問題。我在那篇小說里也不只說了一個賤種,我也說了其他的賤種。就這樣,此處沒有坑。
澎湃新聞:有人認(rèn)為杜江扮演的童子雞其實就是杜月笙剛到上海的故事,您愿意回應(yīng)一下這種猜測嗎?
程耳:他們上次也都問我這個問題,怎么會這么想呢?我覺得這是最可笑的說法,給我一種乏味的感覺,有一種很表層的自作聰明在里面。但這不重要,也無所謂。我覺得這種想法首先缺乏邏輯性,因為我的電影里沒有任何這樣的暗示,而且從時空的角度來說,他和杜月笙是在同一個鏡頭里出現(xiàn)過的,所以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暗示。所以我覺得這種誤讀是非常不專業(yè)的,是一拍腦門的想法。其次這種誤讀沒有意義,我暗示杜江扮演的角色是杜月笙的過往有什么價值呢?在文本和意義的層面上都沒有價值。我認(rèn)為有的誤讀或讀解是有價值的,有美感和意義,甚至在邏輯上也能說得通。
澎湃新聞:片子的英文片名是“the wasted time”(被浪費的時光),我個人看完電影以后認(rèn)為這個片名似乎更“切題”,想問問您為什么沒有以這個為片名呢?
程耳:其實有點不知道該怎么回答這個問題,對于這部片子的片名,我想到的就是“羅曼蒂克消亡史”,翻譯到英文,我才決定變?yōu)椤皌he wasted time”。從我個人的角度,我覺得“羅曼蒂克消亡史”更有美感。
人生和創(chuàng)作最后都會回歸宗教感
澎湃新聞:在影片中有很多基督教的元素,這是您自己的信仰還是您認(rèn)為應(yīng)該有更高的關(guān)懷?
程耳:十字架的元素確實出現(xiàn)得比較多,在小說里對十字架的來源都是有交代的,包括葛優(yōu)的最后一個鏡頭,他的形體也是十字架的樣態(tài)。我覺得其實很多創(chuàng)作最終都會回歸到宗教,就好像牛頓研究第一推動力,其實最后也回歸到宗教。但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觸及到的也是一個很廣泛的宗教感,我在小說里提到“諸神”這個詞,甚至可以理解為一種神秘感。我覺得人生和創(chuàng)作最后都會回歸宗教感,才會找到真正的安靜和沉默。

澎湃新聞:您1999年從電影學(xué)院畢業(yè)到現(xiàn)在,17年間只拍了四部作品,絕對算不上高產(chǎn)。包括您的這本小說《羅曼蒂克消亡史》,您說也是在片場拍片的間歇寫出來的。我很好奇您在創(chuàng)作和拍攝這些作品之間的時間,都在做些什么。
程耳:我不算是那種對自己很有規(guī)劃性的人,不可能每一兩年一部這樣拍。說白了就是打發(fā)時光唄,想辦法怎么把時間打發(fā)得開心一點。比如創(chuàng)作這件事,我可能半年里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但突然有一天感覺來了我就寫個不停。對我來說,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如果是流水線批量生產(chǎn),那就沒意思了。我喜歡的是創(chuàng)作過程中,畫面和文字流淌而出的那種感覺。
澎湃新聞:沒錯,電影里有一段,閆妮和袁泉聊天的場景,袁泉說自己也不知道在拍什么,電影是派給下個世紀(jì)的人看的,我個人很喜歡這一段,覺得是您在自嘲,但我有朋友說他看完這段覺得很反感,感覺導(dǎo)演在故作姿態(tài),覺得自己被冒犯了。
程耳:沒錯,這就是我說的,你們對于文學(xué)的審美不一樣。大千世界嘛,什么樣的看法都會有。
澎湃新聞:看之前的訪談,您提到片子里有一些即興之作,比如第一幕開頭他們吃煎餅,還杜江和王傳君比腳的大小,都是原來劇本里沒有,但是在片場臨時起意拍下的。還有別的這樣的即興之作嗎?能否介紹一下?
程耳:還真就只有這兩處,我不太愛即興發(fā)揮,基本是按照劇本嚴(yán)格來拍的。
澎湃新聞:電影最后在票房上的表現(xiàn)不是特別令人滿意,對此會有些失望嗎?
程耳:辛辛苦苦拍了這么久,我自然希望票房的表現(xiàn)能更好一些。我不會過度地受票房困擾,票房表現(xiàn)不佳,我不認(rèn)為這是觀眾的問題,而是我們在電影的發(fā)行和宣傳這些環(huán)節(jié)上有很多地方是有缺失的,是值得商榷的。讓我有些失落的是,以這部電影在觀眾和影評人當(dāng)中的口碑來看,它的票房應(yīng)該更好一些,應(yīng)該更被更多的觀眾看到。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