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羅曼蒂克消亡史》配樂:什么樣的音樂能凝視流氓貴族的隕落
展現一件美好事物的毀滅能夠引起人的共鳴。哪怕是丑的,里面但凡有一點點美好,消逝了也抓心撓肺。
試想,關于舊上海黑幫家族的消亡史,應該用什么樣的音樂?是老上海的流行金曲,還是絲竹、評彈,或者歡場里的鶯歌燕舞?顯然導演不想太過沉浸在時代音樂里。
對《羅曼蒂克消亡史》來說,即便隨舊上海“流氓貴族”們一起毀滅的僅僅是他們自己和發展到極致的做派與禮數,即便他們非正義、不代表時代進步的方向,即便與他們一同覆滅的是更大的一座城,被命運車輪碾壓的幻滅感總歸是永遠的傷逝。

從整個影片來看,《羅曼蒂克消亡史》是一組很小的群像。把片名從《舊社會》改為《羅曼蒂特消亡史》,表明了導演程耳把視野從大歷史轉投向個體的意圖。
因此他做了種種努力,比如基本拍攝于室內,棄絕年代戲慣用大量群眾演員的做法;給每個角色同樣發光出彩的機會,因為每個人即代表了消亡的一種人;大量使用固定鏡頭,畫面對稱,人物放中間大特寫;不按線性時間剪輯,“強迫”觀眾在部分預知角色命運后更加關注他們的存在。
和影片中的大俯拍鏡頭一樣,這些個體的命運被置于上帝視角之下。他希望能夠以此跳脫出時代的禁錮,并借袁泉飾演的電影明星之口說出:“這電影是拍給下個世紀的人看的”。自然,音樂成為最合適表達這種疏離感的工具。
程耳對音樂的要求精細,日本配樂家梅林茂、中國作曲家郭思達、鋼琴家趙胤胤……整個過程中他找了數位音樂人參與原聲制作。大量的固定鏡頭中,音樂反而成為空間中最流動,最帶動情緒的介質。

影片由鋼琴曲開場,端莊、大氣、優雅,同時也非常克制和冷靜,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調。
三個不同年代的段落在音樂上也各有側重,以鋼琴為主的一錘定音,弦樂協奏更加靠近人物內心,單提琴的段落則是絲弦入肉,音樂與人心交纏在一起。
最點睛的是幾首人聲歌曲,分別是曾在兩次“兒子”被殺時出現的《Where Are You, Father》,渡部(淺野忠信飾)送小六(章子怡)去蘇州夜路上的《Take Me To Shanghai》,以及片尾曲《羅曼蒂克消亡史》。


科班出身的程耳在活著的電影大師中崇拜昆汀,也肯定閱片無數。和西方大師們一樣,對殺戮和暴力場面,他的處理沒有驚艷,但因遵循前人的做法而顯得恰當。陸老板(葛優飾)的兒子被殺及他指揮車夫(杜淳飾)槍殺渡部的兒子時,如同教堂音樂般的《Where Are You, Father》悠悠響起。
死亡的意義不明,戰爭像邪惡頑童咧嘴輕笑,這是宗教也難以拯救的殘酷現實。

渡部送小六去蘇州的車上,《Take Me To Shanghai》響起。小六是個很有意思的角色,別人都在演戲,只有她是“真花癡,真十三點”。這首歌是唯一一首貼近舊上海流行金曲的“靡靡之音”。在逐漸遠離上海的路上出現這樣一首宛如獨白的歌曲,令小六內心的向往自由與身在車中駛向未知命運間的矛盾愈發明顯。
比較難懂的是左小祖咒與尚雯婕合唱的片尾曲《羅曼蒂克消亡史》。
程耳和左小是老朋友。寫出這么一首歌后,他覺得很少有人能唱,就直接找到了左小。需要一個女聲,便請來尚雯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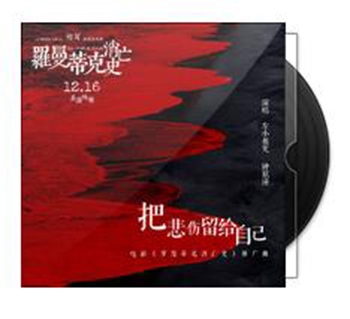
程耳在采訪中曾這樣解釋這首歌:“變化的東西很明顯,不變的東西就是那種精神,想表達的精神上的東西是一脈相承的,包括片尾曲,無非是表達了怎么客觀地看自己,怎么客觀地看世界,怎么客觀地從命運的角度去表現這種脈絡。”
落到歌里,就成了“仿佛他真的到來過世上/我們安靜地審視你/仿佛這一切真的有意義似的”。

一切被打回原形,記憶也一并被抹掉。所有遭到橫禍沒有活到壽數的人啊,注視著你的到底帝、魔鬼,還是電影院里隱在黑暗里的人們。
然而片尾曲看似絕對客觀,近乎虛無,導演本人卻在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恨這一代日本人”,因為他們打破了一個時代,一座城市文明繁華的巔峰。所以他的想法很簡單,把它記錄下來,讓永遠消失了的東西在甚至不在上海的影棚里不朽。
他努力還原,讓上海老爺叔、老阿姨們懷著對往昔的想象在電影院里笑出了聲,即使他們很明白沒有“流氓貴族”的潰退就不會有今日坐在影院品評的愜意生活。就憑這種奇妙感,《羅曼蒂克消亡史》也可躋身優秀國產片之列。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