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唐涯:致理想主義的最后余暉——關(guān)于“城市人”和“鄉(xiāng)下人”

我家有農(nóng)村親戚,我隱約知道“農(nóng)村人”很窮,和我們“城里人”是不同的。我舅舅家為了拼個兒子,一直在超生,被罰款,罰的更窮了,躲到長沙來偷偷的生,媽媽總是到韭菜園的一個小醫(yī)院去探望,回家就嘆氣。我媽媽最好的朋友叫陳靜,我們從小和她很親。靜姨的先生是個特別好的人,脾氣好,又能干,常買零食給我們吃。但是他有很多農(nóng)村親戚,常常到家里來,又吃又住還得帶點錢走。靜姨有時候會生氣跟我媽叨嘮,“我是沒女兒, 要是有女兒長大嫁人,第一條就是絕對不嫁給農(nóng)村出來的!”
很難說這些事情給我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關(guān)于“城鄉(xiāng)”差別的概念確實刻在了腦海里。 在學校里和小伙伴吵架的時候,盡管不帶惡意,但也會順口罵人“鄉(xiāng)里別”(這是長沙土話,大意就是鄉(xiāng)巴佬的意思吧)。在我漫長的青少年歲月里,農(nóng)村人是山的那邊海的那邊的藍精靈,我們不太一樣,中間隔著一個叫“城鎮(zhèn)戶口”的東西,因為這個東西,我們似乎擁有某些說不清楚的權(quán)利和優(yōu)越感。我沒有想過為什么,也沒有人告訴過我為什么,在很長很長的時間里,我將這一切視為平常的理所當然。
出國念博士的時候,開始接觸到一些農(nóng)村出來的男生,他們的人生軌跡大同小異:因為某些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特別會念書,是村里鎮(zhèn)上中小學永遠的第一名,到縣城里念高中,然后以縣狀元、地區(qū)狀元、甚至省狀元的成績考上了清華、北大、復旦、交大等名校,然后出國,碩士或者博士畢業(yè)后都找到一份很不錯的工作,走向人贏的道路。喝酒聚會的時候,我們也會淺淺的聊起遙遠的童年往事,然后我發(fā)現(xiàn),關(guān)于年代我們有著完全不一樣的記憶。大部分農(nóng)村出來的娃表示童年不可能整年吃白面或者米飯,主要以玉米面和紅薯為糧食;有的只有過年吃到過蘋果;有的甚至到2000年才用上自來水,大學假期回家還陪著媽媽從井轱轆里面吊水……有次回國和一個已經(jīng)是國企高管的兄弟吃飯,窗外有個滿臉風塵的農(nóng)民工在搬磚,一身Zegna西裝的他沉默了半天,指著窗外說,“我坐在這里是一點點偶然和僥幸,稍不留神,我就是他。”
我隱隱約約的感受到,這些從農(nóng)村走出的他們,內(nèi)心總有一塊地方,掙扎在“舊時代的魂與新時代的表”之間。我也模模糊糊的想起自己童年時那些往事,忍不住問自己,何為城?何為鄉(xiāng)?“城里人”和“鄉(xiāng)下人”是自然形成的社會群體,還是制度劃分的社會階層?“戶口”的屬性究竟是什么?她所衍生的特權(quán)究竟來自哪里?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公民有“遷徙”的自由。之后兩年間,中國發(fā)生了7700萬的人口大遷徙,包括大量農(nóng)民工進城。然而逆轉(zhuǎn)從1955年開始出現(xiàn),阻止人口流動的政策陸續(xù)出臺,1957年修憲,“遷徙自由”從憲法中消失,195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正式將“城鄉(xiāng)戶籍分割”制度化,城鎮(zhèn)戶口的特權(quán)地位實際上被確立,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形成,以廣袤的農(nóng)村反哺城市,尤其是國家重工業(yè)的發(fā)展,成為中國獨特的風景。從此,一張薄薄的紙,不小心劃出了幾億人口和他們后代一生的軌跡。直到1978年,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僅為17.9%,80%以上的中國人屬于“農(nóng)業(yè)戶口”,被束縛在幾畝薄田之上。這一年,人均收入為343元人民幣,2億人口處于饑餓狀態(tài),實際失業(yè)率在19%左右。
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歷程,其實可以用“農(nóng)民”這條線索串起來:農(nóng)村家庭聯(lián)產(chǎn)責任承包制將大量的農(nóng)村青壯年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在不允許人口遷徙流動的情況下,“離土不離鄉(xiāng),就地工業(yè)化”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興起;鄧小平南巡后,政策開始鼓勵“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向非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有序流動”,從此掀開了浩蕩的農(nóng)民工進城潮,民營企業(yè)崛起為中國經(jīng)濟的重要支柱力量;在中國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之后,數(shù)以億計的農(nóng)民離開土地,散落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工廠里,散落在全國每一個城市的角落里——我們所熟悉的“摩登中國、中國制造”——大到鱗次櫛比的高樓華廈,星羅密布的公路,鐵路,豪華寬敞的機場,火車站,還有那些維系著網(wǎng)絡(luò)世界運行的、埋在地下的電纜,小到手上的電腦和手機,電吹風,臺燈,電池,還有我們身上舒雅的內(nèi)衣,Burberry 的外套,MCM的書包——是數(shù)億農(nóng)民為掙得溫飽所迸發(fā)出的驚人忍耐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奇跡。
2015年,中國GDP總量全球第二,人均收入超過30000元人民幣。這一年,中國城鎮(zhèn)化率達到56%,中國擁有“城鎮(zhèn)戶口”的人口接近8億。仔細想下來,中國前面三十多年的改革,并不是神奇的傳說。中國增長就是城鎮(zhèn)化的歷史,是釋放人力資本的歷史,是大量勞動力從低收入的第一產(chǎn)業(yè)(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到較高收入的第二產(chǎn)業(yè)(制造業(yè))的過程,而已。
如果我們愿意將眼光稍微偏離當下,從過去的窗口看去,會發(fā)現(xiàn)歷史從來都驚人的相似。人類在15000前年前有了“鄉(xiāng)村”的概念,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隨著一些村莊人口的集聚,產(chǎn)生了簡單的商業(yè),逐漸有了“城市”雛形。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口的增長,社會分工出現(xiàn),復雜的交換和商業(yè)開始需要“秩序,規(guī)則”維持,王權(quán)統(tǒng)治從此“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居民”,城鄉(xiāng)分野,由此而始。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200年的時間內(nèi),從地中海沿岸的城邦林立到春秋戰(zhàn)國的城市群,東西方文明不約而同發(fā)生了規(guī)模化的城市興起,迸發(fā)出相似的璀璨。
更有意思的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歷朝歷代的城市化率:戰(zhàn)國期間15.9%,西漢17.5%,唐朝天寶年間20.8%,到南宋時期到達歷史頂峰22%,明清以后一路滑落,到1893年中國城市化率7.7%,僅為戰(zhàn)國時期的一半!城市化率的變化曲線恰好和中國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速度一致——這不是巧合,高速的經(jīng)濟發(fā)展,才會產(chǎn)生大規(guī)模的人口集聚,形成各種各樣的物質(zhì),文化,教育,醫(yī)療要求,從而產(chǎn)生更細的社會分工,加速城市和商業(yè)文明的演化。而人口集聚的前提是人口的自由遷徙流動。從元朝開始,人口自由遷徙流動的權(quán)利逐漸被剝奪,到清朝更是“編審人丁之制”,社會人口的流動性急速下降,直到大清滅亡。
回頭看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城市化和經(jīng)濟發(fā)展上走過的路,是不是多么熟悉?
沒有人的流動遷徙,就不可能實現(xiàn)人力資本的最優(yōu)配置,沒有人的集聚,就不可能有專業(yè)化,細分化的城市文明,就沒有我們所熟悉的一切文學,藝術(shù),建筑,醫(yī)學,科學的繁榮和發(fā)展。城市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搖籃,而人的自由是城市文明的基石。就像徐遠兄在他的新作《人?地?城》一書中所說的:
“人類演化的一條軌跡,是更多的人離開土地,匯成城市。”
徐遠兄來自蘇北農(nóng)村,和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出身學術(shù)男的人生軌跡一樣,考上北大,出國念博士,進入北美名校任教,又回國重回母校執(zhí)教。他的領(lǐng)域是宏觀和金融,然而土地問題,城鄉(xiāng)問題是他心中放不下,嚼不碎的情節(jié)。前兩周,他將《人?地?城》一書送到我手里,叮囑我寫點什么。當天我在回滬的火車上就一口氣讀完了。從城市的起源,到城市印象,到土地,糧食,人口遷徙,遠兄用一個學者的眼,從石器時代的“有容乃大”,寫到希臘羅馬和春秋戰(zhàn)國城市的興起,順著人類文明發(fā)展的線索去追尋城市的起源,追尋城市興起背后的經(jīng)濟邏輯;同時他也用一個農(nóng)村孩子的腳,一步步地丈量著從鄉(xiāng)村到城市的道路,追尋至今未能解決的土地問題的答案。十多萬字竟如行云流水,文淡如菊。
是夜我提筆想寫點什么,但腦子里翻來覆去還是汪丁丁老師的推薦語,“這是我讀過的中外關(guān)于人與城市的可讀性最強的好書,似乎沒有之一。”信矣。只得作罷。
直到昨天,讀到媒體報道“北京禁限低端產(chǎn)業(yè),累計減就業(yè)崗位約80萬個”,突然想到自己的鐘點工阿姨,原來住在離我大約騎自行車5分鐘的地方,因為屬于“低端”行業(yè),不配住在高大上的海淀區(qū),被“疏散”到了天通苑,現(xiàn)在來我家做衛(wèi)生路上要花費2個多小時,她辛苦,我自然也得提高點待遇——這么看下來,疏散“低端人口”除了增加“市場摩擦,交易成本”外,沒有看出太多好處。剛在尋思,這邊電話又響了,是學生打來的,說因為北京各區(qū)限制人口,今年“留京名額”特別緊張,一個帶著北京戶口的工作簡直成了博士生們心頭的痛。
放下電話,在北京海淀的一幢高樓里,我從緊閉的窗戶里看著霧霾籠罩的天空,突然想起了小時候那些關(guān)于“城市人”和“鄉(xiāng)下人”的記憶,忽然理解了遠兄要為自己,為他的父輩,為和他一樣的從泥土里僥幸走出的人們寫下《人?地?城》這本書的執(zhí)拗和情懷。
我什么也說不出來,僅以此文,致他們理想主義的最后余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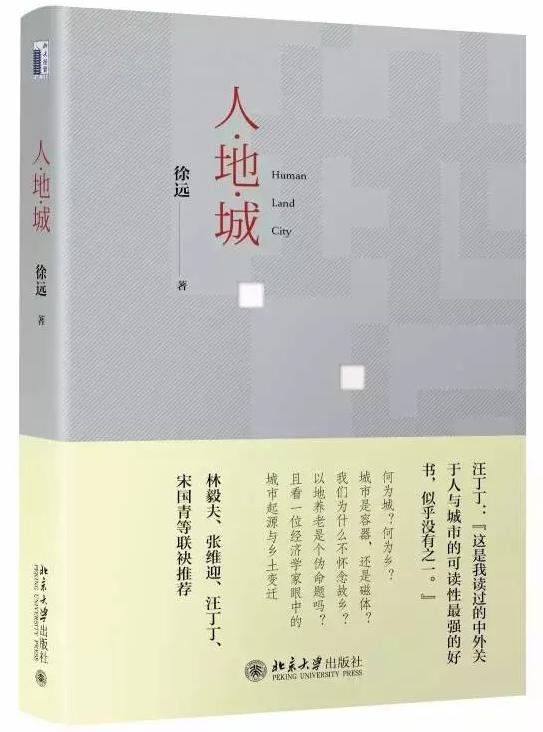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