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誰逃得過玲娜貝兒?
原創 看理想編輯部 看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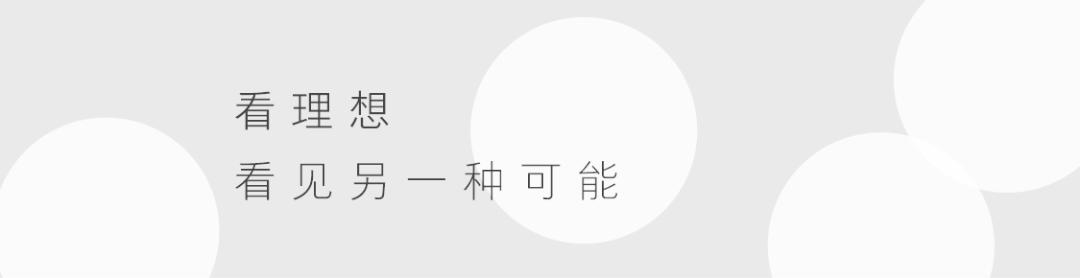

最近兩個月,和主題樂園有關的信息輪番占領熱搜。
9月,北京環球影城開園,各個平臺充滿了攻略和測評;10月,迪士尼新“頂流”玲娜貝兒引發全網狂熱,不少人連頭像都換成了這只粉紅色的小狐貍。
主題樂園究竟有怎樣的魔力,讓生活已經足夠疲憊的成年人連起大早、排長隊都不怕?
“小朋友,把樂園讓給成年人吧”,這大概是不少人卑微的心聲。
1.
被可愛的事物層層包圍的幸福感,
可以撫平成年人心里的褶皺
如果你問一個沉迷于玲娜貝兒的人“為什么會喜歡她”,那Ta多半會告訴你,“多刷幾個視頻就知道了”。
的確,沒有人能心如止水地走出玲娜貝兒的“飯拍”視頻。
視頻里,一只粉嫩嫩、圓滾滾的小狐貍,晃動著毛茸茸的大尾巴,用湛藍的長著長睫毛的眼睛望著你。
被表白,她就捂臉著轉過身去害羞;會生氣跺腳,會插著腰做出很霸道的樣子,也會扭著身體撒嬌;被叫了不喜歡的名字,就一根根數著手指教你念“玲、娜、貝、兒”……

動圖來源:微博@·光就在你眼里啊·
屏幕這邊的你,早已不由自主地露出“姨母笑”,甚至像被什么擊中一樣,心中涌起暖意,情不自禁地捂住胸口。
“好可愛啊”,這樣的感嘆似乎并不足以表達玲娜貝兒帶來的感受。
她身上有種用不完的,對這個世界的熱情,是我們早已沒有了的。看到她蹦蹦跳跳地上班下班,好像自己的內心也有一部分雀躍起來。
心理學家們發現,可愛的事物會喚醒一種名為“kama muta”(梵語,意為“被愛感動”)的特殊情緒。這是一種讓人感到溫暖、安全、精神振奮的積極情緒。
這種情緒,是都市人亟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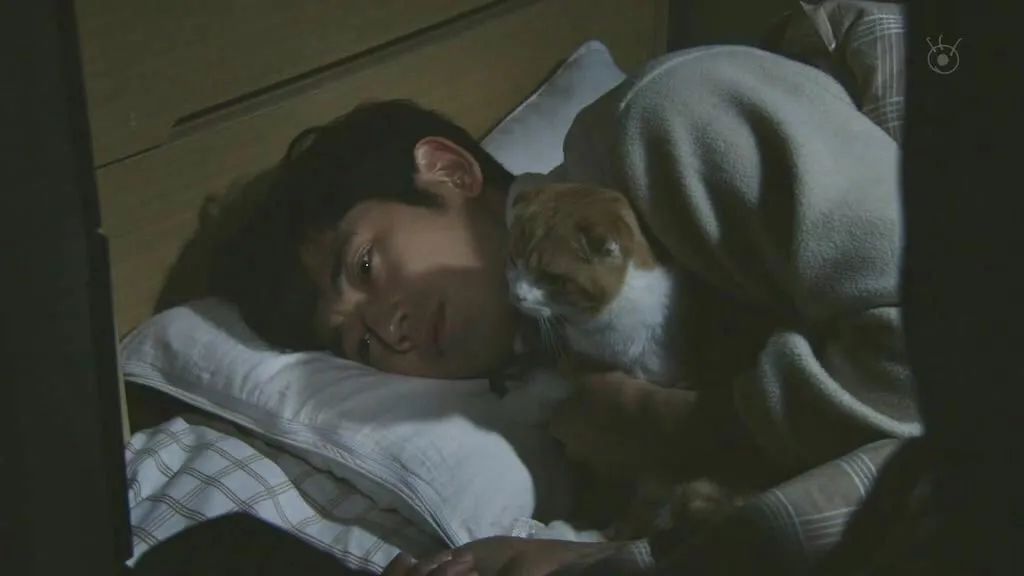
《最完美的離婚》
汪民安在《現代性》一書中寫到,“都市培育了一種獨特的器官,使現代人免于這種危險而瞬即的都市潮流的意外打擊,因此,這種器官必須麻木不仁。這就是冷漠、厭世和對對象的驚人的不敏感。”
生活在瞬息萬變的城市中,我們習慣于生出厚厚的鎧甲,用以抵御風險和不確定性。人與人之間,也總是趨于疏離冷淡,很難建立起真正深刻的聯系。
但人的內心,無法,也不能一直封閉。盡管在心里豎起了高墻,我們仍然渴望情感的聯結,渴望溫暖與歸屬。于是,這些可愛的事物就成了愛的代餐。
人類學家項飚曾說過:“很多年輕人在大的系統下工作和生活,個體也成為了一個封閉的‘系統’。我們為什么需要寵物來投射自己的情感?因為動物是能夠進入我們系統內部極少數的生命之一,在心理療愈上可能是有一定幫助的。”
孤身漂泊的人,養一只貓,家就有了情感內涵;加班到深夜的“社畜”,躺在床上看幾個可愛的視頻,帶著終于被熨燙妥帖的情緒入睡;懷抱一只玩偶,感受它的柔軟,內心也漸漸平靜下來。

上海迪士尼樂園,拍攝:汁兒
而樂園,是一個可以集中體驗“可愛”的地方。
很多動畫角色的設計,本身就符合奧地利動物心理與行為學家洛倫茲(Konrad Zacharias Lorenz)提出的 “嬰兒圖式” (baby schema)概念,具有高額頭、大眼睛、突出的臉頰、圓滾滾的身體、身體柔軟有彈性等一系列和嬰兒相似的特征。這些特征,是可愛的來源。
工作人員的生動演繹,則讓角色的可愛更加深入人心。
園區內,大到建筑的形狀和色彩,小到路燈、垃圾桶,都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和裝飾,營造出溫暖浪漫的氛圍。
這種被可愛的事物層層包圍的幸福感,足以撫平成年人被生活蹂躪出的褶皺,哪怕只是暫時的。
2.
在樂園,
度過一段坦然享受快樂的時間
在主題樂園能獲得的另一個寶貴體驗是,一段沒有罪惡感,坦然享受快樂的時間。
這是一個連抖音、快手這樣的短視頻平臺,都擁有倍速播放功能的時代。我們習慣于多任務、“全都要”,每天的生活,都被各種“必須這樣做”的事情構筑起來。
這些事,既來自外界的要求,又是一種自我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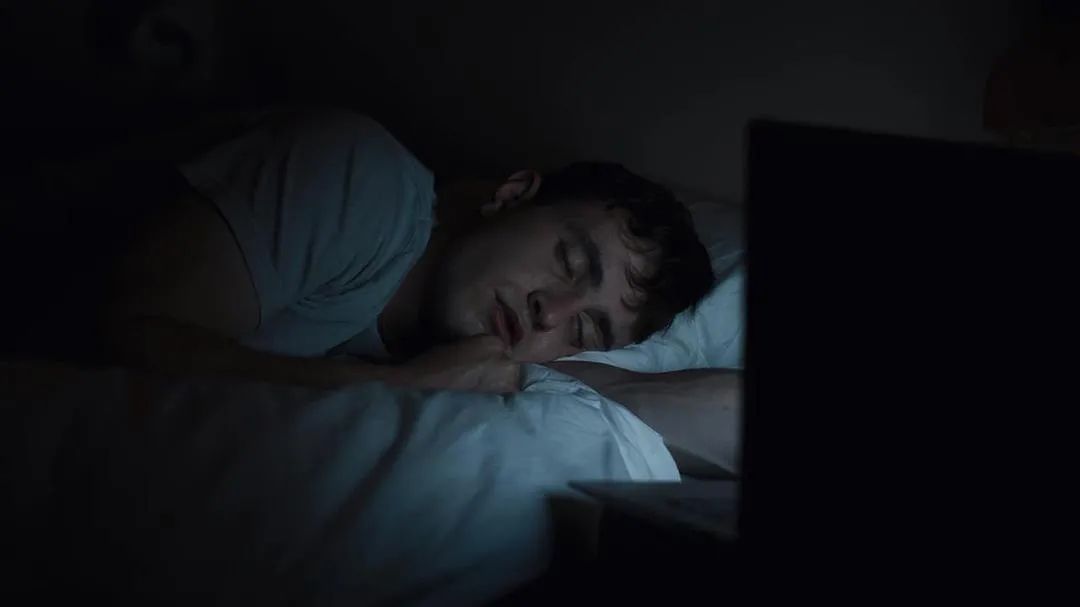
《正常人》
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提到,“功績主體投身于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
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
現代社會制造了這種“有罪的主體”。要做的事情很多,當一天結束,如果我們沒有完成自己的“要事清單”,就會產生罪惡感;當我們做一些無關乎效率的事情時,也會不由自主地產生,時間被浪費了的不安。
就連休息的目的,也變成了“使我們從疲勞中復原,以便我們繼續正常工作。”我們就這樣。日復一日地追趕著怎么也無法完成的清單。
可是,在主題樂園,快樂才是唯一重要的事。
主題樂園營造出的,是一個現實生活中的異世界。從走進大門開始,外部的時鐘就暫停了,煩惱也被丟在了門后。等待著我們的,是曾經在電影里出現的人物、場景,和工作人員臉上大大的笑。
樂園里的待辦事項,只有一個接一個的冒險。

上海迪士尼樂園,拍攝:蘇小七
在這里,我們的社會身份消失不見了。所有人都變得不重要,又變得很重要。
我們不再是畏手畏腳、生怕和別人不一樣的“社會人”,不論年齡幾何,都可以以輕松的心態穿戴夸張的衣服飾品,也可以隨便在路上蹦蹦跳跳,不用擔心別人的目光。
樂園愛好者袋米說,“迪士尼里的很多設定,會讓我覺得自己很重要。像‘星際救援’這種,能讓人實現一些平凡世界里不可能的暢想——我也可以拯救銀河系,這在迪士尼世界是被允許的,不會被嘲笑的。我自己,就是這段旅程的主角。”
這里不提供任何宏大的意義,也不能幫助你未來生活得更好,樂園只關乎快樂的體驗,只關于此時此地。
“看完煙花走出大門,走到地鐵站的時候,會有一種回到現實的感覺。”這可能是許多人離開樂園時的感受。
3.
那個曾經陪伴我們長大的世界,
就在樂園里
如果電影是在造夢的話,那主題樂園就實現了夢境。也有人說,樂園是夢想到現實的軟著陸。
看理想編輯部的汁兒直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在迪士尼和《玩具總動員》中的角色胡迪握手的時候,自己激動的心情,“好像終于觸碰到了那個向往的世界”。
那是一個我們曾經最熟悉和相信,如今卻越來越模糊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里,魔法理所當然地存在;故事的結局總是所有人“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善良終將戰勝邪惡;付出都會獲得回報;愛和勇氣是人生最不可缺少的。

上海迪士尼樂園,拍攝:汁兒
我們是懷著對那個世界的期待,興沖沖長大的,可是越長大,卻離它越遠了。
當倦怠和麻木逐漸成了生活的日常情緒,對于未來的感受,也從向往變成了焦慮,眼前的一切連同我們自己,都不再分明,只拉扯出糾纏的一團。
主題樂園將那個世界重新帶回我們眼前。
袋米說:“在這里,我可以被游戲項目的墻上亮起的,類似于‘人人都善良世界就會變好’的話打動,可以為一首伴著煙花放出來的《let it go》感動,不會被嘲笑中二,讓我感受到,做一個情緒飽滿的人真好。”

《佛羅里達樂園》
除了有關夢境的實現,整潔、有序、充滿歡樂的主題樂園,也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存在。恰如韓炳哲所描述的“平滑的世界”,沒有痛苦、不會受傷、擁有絕對積極性。
這并非全無問題。
美國的建筑學者邁克爾·索金(Michel Sorkin)在《主題公園變奏曲》一書中指出,主題樂園利用空間隔離的手段來排斥與周遭環境的互動,而且,主題樂園中只有對各種歡樂情境的無盡擬仿,真實世界中的貧窮、犯罪、臟亂、失業等問題在這里被忘卻了。
可是,它的積極之處在于也恰恰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們能夠“暫時脫離日常單調的生活,進入一個自由的烏托邦時刻”。
在《迪士尼、主題園與擬像的全球化》一文中,作者顏亮一提出,主題樂園“在單調、機械化、商品化的真實日常生活空間中,保留了人們對于都市公共生活的熱望,投射了個更美好生活空間的愿景。
如果使用者能夠在主題環境中看到這個愿景,再以之對比外在的真實空間,便有可能因為對于現實的不滿而形成批判的空間意識,從而促成社會的變遷。”
作為后現代主義消費文化的典型代表,學術界對主題樂園的批評從未停止過。
但問題并不只有一面。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主張,消費是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s)。
在文化經濟的領域中,商品是一個“開放性文本”,消費也成為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商品的意義可以被重寫。在主題樂園里,我們也可以描畫自己的故事。

上海迪士尼樂園,拍攝:汁兒
今天,“快樂”的供應量似乎很充足,搞笑博主的視頻、文字段子,各類喜劇節目,都在使勁“撓你的癢癢”。但生理刺激帶來的快樂似乎總是轉瞬既逝,很難在心里留下痕跡。
主題樂園給人的快樂,卻是能夠回味的。善良、天真、好奇、愛、勇氣,主題樂園里,藏著我們最初認識的那個單純可愛的世界,不僅讓我們快樂,更讓我們感到溫暖和安心。
選擇逃避和尋找快樂也許是人的本能,漫漫人生里,把頭埋起來一小會兒,也沒什么事兒。
參考資料
1.人類為什么喜歡蠢萌小動物,比如胖噠?| 南都周刊
2.迪士尼、主題園與擬像的全球化 | 顏亮一
3.《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哈特穆特·羅薩
4.《倦怠社會》 | 韓炳哲
? 兒兒祝你周末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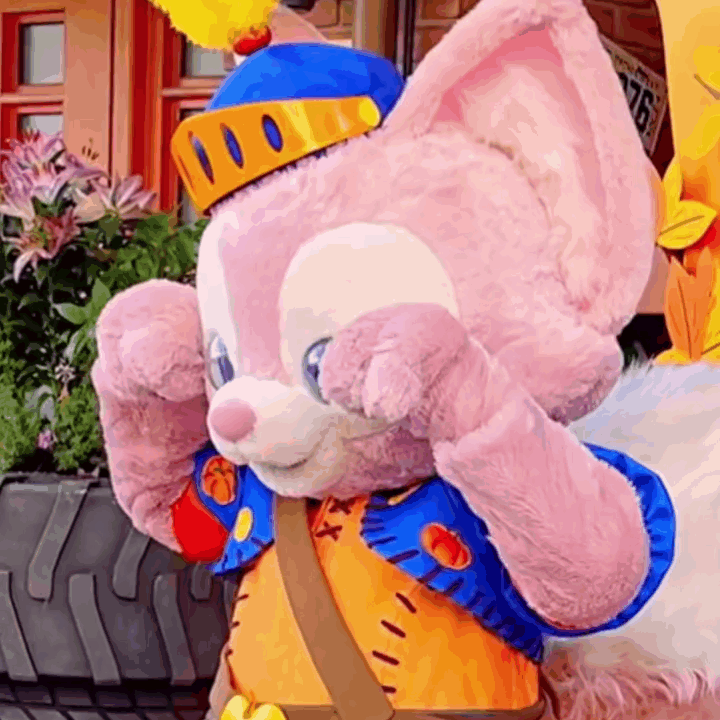
動圖來源:微博@·光就在你眼里啊·
撰文:Purple
監制:貓爺
轉載:請微信后臺回復“轉載”
商業合作或投稿:xingyj@vistopia.com.cn
原標題:《誰逃得過玲娜貝兒?》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