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訪談|中國人為什么偏愛俠客?

【提要】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武俠小說熱曾風靡一時,書中描述的精妙武功及俠義精神至今膾炙人口。然而,這些“成年人的童話”究竟與現實世界有多大的距離,歷史上的俠客是“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還只不過是魚肉鄉里的青皮、土豪?俠義精神在中國文化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中國游俠史論》第四次修訂版,作者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先生指出:游俠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從未被統治集團認可過,也很少得到主流文化的整體性肯定。但游俠敢任人所不能任,甚至不惜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脫人于待命刀俎的窘境,自然大得人心。游俠的人格與精神,應該仍對當代人的人格建構乃至文化建造有借鑒意義。
澎湃新聞:您對游俠是如何定義的,或者換句話說,該如何認識中國古代的游俠?
汪涌豪:關于游俠的定義,可能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許多。按通常的理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俠,仗義疏財、賑窮周急也是俠,但作為中國古代特殊的社會人群,游俠其實有著更為復雜的面貌。要定義準確,既需結合其崛起之初的具體構成,又必須兼顧其后不同時代的發展變化。
大體上說,游俠是伴隨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喪失與士的失職出現的。本來所謂的士大都擁有一定數量的食田,又接受過六藝教育,平時為卿大夫家臣,戰時充為軍官,是顧炎武所說的“有職之人”。后經春秋戰國以來的社會變動,雖具智、勇、辯、力而終不免“降在皂隸”,使其不得不既度人勢之廣狹,復量己德之厚薄,開始新一輪投輔明主的努力。其中長于文章辭令的成為游士,日后有些由宣揚禮儀教化而成為儒,有些由主張兼愛非攻而成為墨;長于射御攻戰的就成了游俠,也包括成為奮死無顧忌的“力士”、“夾士”和“勇敢士”。用馮友蘭《原儒墨》的說法,是一為“知識禮樂之專家”,即儒士,一為“打仗之專家”,即俠士。呂思勉《秦漢史》說得更為簡明:“好文者為游士,尚武者為游俠。”

汪涌豪:秦漢后游俠的來源變得復雜許多,成分更淆亂,不易究詰,是否都是士階層中人很難說。依司馬遷的分疏,是既有卿相之俠、暴豪之俠,也有布衣匹夫之俠與鄉曲閭巷之俠。前者大多有身份,富財貨,或權重王庭,或勢傾地方。這類俠以漢唐為最多,但宋以后也未完全絕跡。后者由戰國時市井細民任俠發展而來,以后或為中小地主,或兼營商業,更多則活動于城市鄉村,至明清兩代甚至還為醫、為僧。當然,無恒業恒產者更多。而一般士人,或少年意氣,熱腸在腹,或情懷廓落,投效無門,也有放而為游俠的。這種情況唐前有,唐以后要數明中后期為最多。今天幾乎人人都知道王陽明,但他及其學生輩如王艮等人均好游俠,乃或以任俠自喜,就未必為人所盡知。其時還有所謂“山人”為俠,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載之甚詳。他們以詩書為交游之具,以幕修贈與為生計之方,流品頗雜,不少人兼為商賈,或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顯于民而聞于鄉;或恃財行奸宄,為執政所深斥。凡此,都足證帝國晚期城市經濟發達導致的時代變化,以及“儒俠”、“儒商”翻為“俠儒”、“俠商”的復雜面相。
也正因為這個緣故,當后人討論游俠的源出,就很難形成共識。有的認為其出自平民,如勞榦、楊聯陞;有的認為其出自游民,如陶希圣、馮友蘭。但前者明顯不能涵蓋卿相暴豪之俠,后者特指喪失土地的流蕩無業者,他們既被舊有生產關系拋離,又為城市經濟所不容,因無所附籍而多靠富者庇蔭或官府賑貸,性質與卿相暴豪之俠全不相類,與布衣匹夫之俠也有不同,所以這兩種說法都未被學界據為定論。郭沫若以為其出自商賈,但例外太多,也無需深駁。
日人增淵龍夫和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以為游俠來自不同階層,各操生業,構不成一穩定的社會界別。其之所以好行俠,非為謀生,僅因受俠義精神的感召,故倡為氣質說。個人比較認同這個判斷。因為一個人為俠可以有各種原因,但基礎條件必是其天性中有一段難忤的俠性,隨其“人生精神意氣識量膽決相輔而行相軋而出”(陳繼儒《俠林序》),如“戰國諸公之意之氣,相與以成俠者也”(何心隱《答戰國諸公孔門師弟之與之別在落意氣與不落意氣》),是其典型。僅從所在階級、階層作推求,不免太過拘牽。當然,這并不表示我否認游俠會受從哪里走出來的階級、階層的影響。譬如他是平民,當然容易在性情中糅入蔑視權貴、反抗體制和劫富濟貧的意識;是富豪或權貴,則必然會多一份養私名以求仕進、蓄勢力以建功業的追求。
澎湃新聞:那么這一人群的群體特質是什么?
汪涌豪:最權威也最為人熟悉的自然是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中的論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班固思想較司馬遷為正統,故稱“意氣高,作威于世,謂之游俠”的同時,在《漢書·游俠傳》中不忘點出其還常“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但他對俠的上述特點是基本認可的,以為“亦皆有絕異之姿”。直到今天,人們對俠的特質的認識大體仍依此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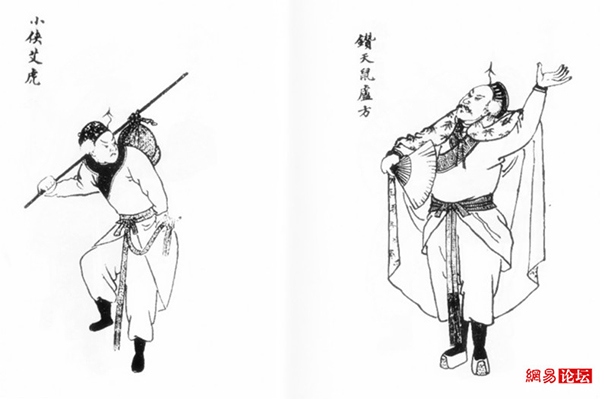
汪涌豪:確實,一說游俠就會想到《韓非子》中的這一句斷語。韓非在“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大爭之世,尤重張揚君權,所以《五蠹》篇明確反對“群俠以私劍養”,“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八說》篇又對“人臣肆意陳欲曰俠”與“棄官寵交謂之有俠”提出批評, 立場與后來荀悅《漢紀》所謂“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相同。后者將游俠與游說、游行并稱為“三游”,以為都“傷道害德,敗法惑世”,是“亂之所繇生,先王之所慎”。因標準絕對而明確,每為后世專制君主和正統士大夫所采納。其實,由兩人所說,再按之史實,可知歷史上“儒以文亂法”或有,“俠以武犯禁”則未必,不尚武力如郭解、朱家之流,有時更易觸犯世網。原因很簡單,為其令行私庭,權移匹庶,為患尤巨。所以我很同意你后半部分的判斷,即既稱游俠,主要特征或許正在其常游離于社會秩序之外。這里的“游”當然指“周游”和“交游”,但誠如楊聯陞所言,也有或更有“不受拘管”、“不受牽制”之意,故不應僅作“游蕩”解,還更應該理解為“游離”,一如西人所謂的“Free-floating resources”。它隱指其人可成為社會”自由浮動的資源“或所謂“游離資源”(《劉若愚:中國文史中之俠》,《楊聯陞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236頁)。用今天的社會學術語來說,正可構成一“非正式群體”(informal group)。但從統治者一方來看,你是“四民”之外一種脫序的存在,當然有悖王化;以后若再欺壓族黨,憑凌儒紳,起滅詞訟,喧鬧公堂,更不容于法禁。
此外還須指出,即使身在主流,也早有人對韓非提出異議。如明代事功卓著的汪道昆就認為:“文則苛細,文而有緯則閎儒;武者強梁,武而有經則節俠。二者蓋相為用,何可廢哉。”“韓子以亂法訛儒,犯禁訛俠,夫亂法非文也,何論儒?犯禁非武也,何論俠?下之為曲儒,為游俠,文武何謂?”(《太函集》卷四〇《儒俠傳》)他認為,俠事實上有上品與末流之分,不愿意人一概而論,所以稱犯禁之俠絕非節俠,正如亂文之儒絕非閎儒,又肯定前者的“不游而節”與后者的“不曲而通”。如此對待而論,更契合先秦以后游俠多途發展、各有偏重的情實。所謂“節俠”,指的是俠中能持操守者,他們與“輕俠”、“粗俠”不同,與“奸俠”、“兇俠”更有區別。以后,曾國藩因其“薄視財利”、“忘己濟物”、“較死重氣”而稱其為“豪俠”,認為“可與圣人之道”,雖精粗不同,“未可深貶”(《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第十四冊,岳麓書社1984年,442頁)。
澎湃新聞:游俠在先秦兩漢以及唐代,出現過讓人矚目的高峰,您曾指出,宋代以后不再活躍,全祖望更稱游俠“至宣、元以后,日衰日陋”,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汪涌豪:當年顧頡剛認為游俠自戰國迄西漢只五百年歷史,鈴木虎雄干脆認為唐時已不存在。我二十多年前初涉此題,尚少有檢索便利,只好遍翻二十四史,逐一查檢,發現居然無代無之,由此深覺社會史研究的余域尚多。當然,宋以后俠的活躍程度的確有所降低,不要說兩漢以降平交公侯、準與國事的際遇少有,即李淵父子占領長安后,召“五陵豪俠”與“俠少良家子弟”縻以好爵的事也再難見到(見《全唐文》卷一《授三秦豪杰等官教》)。
究其原因,自然與宋初懲五代之亂, 重文輕武,使人普遍內傾收縮有關,臺灣學者傅樂成和伊沛霞(Patricia Ebrey)都指出過這一點。按之其時汪藻所謂“迨宋興百年,無不安土樂生。于是豪杰始相與出耕,而各長雄其地,以力田課僮仆,以詩書訓子弟”(《浮溪集》卷一九《為德興汪氏種德堂作記》),以及葉適對“人心日柔,士氣日惰”的感嘆(《水心別集》卷二《法度總論二》),不能不說世道變化巨大。加以此后專制政體日趨完備,國家法與地方宗族習慣法的融合在事實上成型,游俠出入紳民兩界,沉入百業之中,活動空間漸被收窄,身份特征自不免日漸稀釋。許多俠因失去社會鼓勵而降低了對自身的要求,放棄操守者更竄身鄉閭,放濫成為霍布斯鮑姆(Eric J. Hobsbawm)所說的“社會盜匪”(《盜匪:從羅賓漢到水滸英雄》,臺北麥田出版股份公司1988年版,第5頁)。到明清兩代,許多俠與盜匪沆瀣一氣,作為“無賴群體”,活動尤見猖獗。日人上田信和川勝守研究江南都市無賴,都曾論及其時吳下有所謂“打行”,“大抵皆俠少,就中有力者更左右之,因相率為奸,重報復,懷不平”(葉權《賢博編》),有許多“里豪市俠”更趁社日節慶,“以力嘯召儔侶,醵青錢,率黃金,誘白粟”(王穉登《吳社編》),甚至還有招徒眾“習為健訟”的(見《萬歷通州志》卷二《風俗》)。
至于有的“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見丁日昌《撫吳公牘》),荼毒鄉里,更使其本來面目變得難以辨識。故明清兩代刑律都添入治地痞流氓的條款,其人所遭到的打擊是非常嚴厲的。以后有的散入民間為人保鏢,為武館教席,乃或入梨園班子為人練功說把子。是全祖望所講的“日衰日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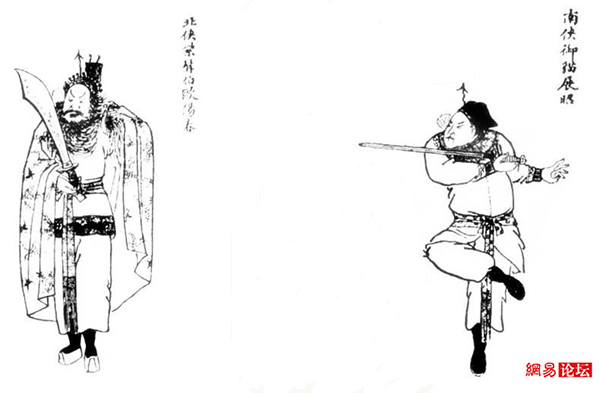
汪涌豪:確實如你所說。原因當然是晚清天崩地解的時局變化。先是康梁領導維新運動在全國展開,后有革命派擺脫立憲幻想,由愛國御侮轉向革命排滿。但無論維新人士還是革命派,手中都不掌握軍隊,這讓他們覺得吸納忠于信仰、敢于任事的仁人志士非常重要。游俠損己不伐,敢任不讓,明道不計功與正義不謀利的大義忠勇,在他們看來正可以引為同道,賴為號召。
此前,薛福成已痛感列強驟勝中國而呼求有“奇杰之士”出。至此,受西洋思想影響和日本崛起的刺激,再對照國人之局于傳統而了無生氣,整個社會迅速集聚其崇俠的共識。類似譚嗣同所謂漢匈奴犯邊被逐“未必非游俠之力”、康有為所謂“人相偷安士無俠氣則民心弱”、章太炎所謂“任俠一層與民族危亡非常有關”等為人所共識常談。盡管今天看來,有的話不無偏頗,非盡事實。
具體到學習西洋,梁啟超認為斯巴達人所以雄霸希臘、德國所以傲視歐洲皆因尚武,故作《論尚武》鼓吹“膽力”與“體力”,尤崇“心力”。自龔自珍提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壬癸之際駘觀第四》),時人每多言之。梁氏《意大利興國俠士傳序》稱歐洲人“雪大恥,復大讎,起毀家,興大國,非俠者莫屬”,或也受此影響。但其實,尼采唯意志論、詹姆士人格論和柏格森學說對他的影響也很大。另外,他還認為宇宙一切都由意識流轉構成,故備言“意力”對促進進化的決定作用,此“意力”就指“心力”。而所謂俠,在他看來也正“非膂力之謂,心力之謂也”。章太炎對中國人個性——他稱之為“我見”的缺乏痛心疾首,在《答鐵錚》中稱“所謂我見者自信也,而非利己也”,“尼采所謂超人,庶幾相近”,并認為這種“排除生死,旁若無人”,“上無政黨猥賤之風,下作愞夫奮矜之氣”,“于中國前途有益”。后編訂《檢論》,又稱盜跖為“大俠師”,比作“今之巴庫寧”,則認同俄國無政府主義“破壞的欲望也即創造的欲望”的立場無疑。其時,人們普遍推崇無政府主義,以為“今世界各國中破壞之精神,最強盛者莫如俄國之無政府黨”,有一原因就在它鼓吹暗殺,這方面議論可見后來蹈海自殺的楊篤生的《新湖南》。它很容易使人想到荊軻、聶政等人。以后,革命黨人學造炸彈,多謀行刺。如謀刺五大臣的吳樾,行前就寫下萬字長文《暗殺時代》。
再說學習東洋,我們比較熟悉的,如譚嗣同《仁學》就曾直言“與中國至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效,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氣概,出而鼓更化之機也”。唐才常與之并稱“瀏陽雙杰”,嘗亡命東瀛,也在《俠客篇》中稱贊日本俠的“義憤干風雷”。梁啟超《記東俠》認為日本之所以崛起,功在“一二俠者激于國恥,倡大義以號召天下”,為此借彼武士之名編成《中國之武士道》,意欲通過發揚歷代游俠史跡,來改變“民族武德斫喪”、積弱不振、外侮交乘的現狀。楊度在該書序中,對此意發揚也多。

汪涌豪:對。分開是為了敘述的方便。事實是,對三者的推崇,在他們是同時交叉的,因為他們視東西方俠者為同一類人,都樂以一腔熱血求一場好死。秋瑾素慕郭解、朱家為人,又好讀《東歐女豪杰傳》等書,自號“鑒湖女俠”,就如此。
其時,用“俠”為兒孫輩取名或替自己改字取號的人很多,這里的“俠”都不僅以中國古代的游俠為限,但古代游俠在其心目中所占的分量仍很重。故在作具體的推贊夸揚時,他們常有意識地突出其有信仰、具特操、能行動,富于救世熱忱和犧牲精神等方面。譬如章太炎雖認為俠出于儒,嘗謂“《儒行》所稱誠俠士也”,又主張“以儒兼俠”,但又認為不必深言道德,“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則可矣”(《革命之道德》),并尤力主去除“以富貴利祿為心”的“儒家之病”。他還特別尚勇,以為若“無勇氣,尚不能為完人”(《國學之統宗》)。
澎湃新聞:勇是孔子講的“三達德”,儒家應該是尚勇的吧?
汪涌豪:孔子當然尚勇,以“勇者不懼”為君子必備的質素。但請注意,他“惡勇而無禮者”,為其有可能為盜為亂。以后孟子更區分道德之勇與血氣之勇,重前者之“大勇”而輕后者之“小勇”,又強調以義配勇,推崇“不動心”,要人“持其志,無暴其氣”,并認為“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再后來,揚雄《法言》崇孟軻而貶荊軻,認為其不過“刺客之靡”,而游俠是所謂“竊國靈”者,簡直就是以義代勇了。所以章太炎要特別提倡勇,并認為游俠之勇可敬可佩,值得發揚。
以后湯增璧《崇俠篇》更倡言“舍儒崇俠”。還有人進而主張復興墨學。我們知道,墨學至東漢基本廢而不傳,然墨子貴義尚力,關心社會平等,有節制一己之欲而奉從主義的自律精神;墨家為赴天下急難,徒眾姓名澌滅,與草木同朽者不知凡幾,使時人覺得這種精神值得重作洗發。故譚嗣同好讀《墨子》,私懷其摩頂放踵之志。梁啟超雖以孔子為大勇,但《子墨子學說》仍稱秦漢俠風大盛是受了“墨教”的影響,“今欲救亡,厥惟學墨”。覺佛的《墨翟之學說》更全面肯定墨俠之于救亡的意義(見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三聯書店1978年,865頁)。
還可一說的是,1905年出版的《民報》創刊號卷首,也將墨子像與黃帝、盧梭并舉,以示革命前進的方向。
這里,我就此問題展開稍詳,是想同時究明游俠與儒墨兩家的關系。我覺得,這對認識何以游俠存而不亡又評價互歧會有幫助。
澎湃新聞:武俠小說中的俠客,幾乎個個都是蔑視官府或權貴的,歷史上真實的游俠似乎不是這樣的。
汪涌豪:天下事,想象與現實常有落差。事實是,游俠與官府權貴從來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魯迅《流氓的變遷》指漢大俠為求自保而多與公侯權貴相饋贈,是大家都知道的。白魯恂(Lucian W. Pye)《中國政治的變與常》一書說得更為徹底,他認為中國的文化,依附權貴是獲取安全感的最佳手段,游俠之與權貴,以忠誠交換保護,在雙方都覺得理所當然。錢穆早年作《釋俠》,稱俠是養私劍者的專指,而以私劍見養者,非俠,以后《國史大綱》承認見養者也是俠,也是看到兩者關系的密不可分。
兩漢以降,游俠已無“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的風光,但權臣養客仍很普遍,游俠與權貴的交往因此仍然密切。唐吳象之《少年行》詩有“承恩借獵子平津,使氣常游中貴人”這樣的句子,結合張九齡以“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勸諫正掌用人之政的姚崇(《全唐文》卷二九〇《上姚令公書》),可見兩者相與在那個時候正復不少。前不久,因電影《聶隱娘》引出不少俠的話題,雖是傳奇小說改編,但反映的歷史確是真的。還有一篇《紅線》,更與史實如合符節。唐代既有俠進入中央朝廷,也有退而入北衙禁軍的。又有一部分人驍勇剽悍,不愿老死牗下,遂投效邊庭,被強藩用為勾心斗角的工具,如此“塞上應多俠少年”,也是其人與官府權貴關系密切的顯證。這樣的情形要到唐末甚至五代后才發生變化,到那個時候,才有薛逢《俠少年》所謂“往來三市無人識”,或沈彬《結客少年場行》所謂“酒市無人問布衣”這樣的詩句出現。
要特別一說的是游俠與官府權貴交往所導致的多重結果。起初,他們可以賴此背景做出許多有利于人群的俠行,也可借以化解自身遭遇的各種麻煩。但以后隨門客向私客、奴客方向轉化,像戰國秦漢那樣享有隆盛社會聲名和自由度的好日子再難復現,其人的自主意識和獨立人格不免隨著身份的驟降而日漸喪失,有時障于恩誼,間或擺不開利誘,淪為后者的工具常在所難免。這種逆轉變化與宋元以后官府權貴對游俠態度由尊敬而禮遇,向為利用而恩接,乃至豢養以為驅使的方向過渡是正相對應的。

澎湃新聞:但游俠與官府處對立地位,應該說也是常有之事吧。
汪涌豪:這個當然。古代專制政體,從來追求“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漢書·刑法志》)。前也談及,如有人擅作威福,奪權朝廷,一定難為體制所容,一定會受到類似遷徙、從軍或被酷吏能吏鎮壓的制裁。并且,這種制裁貫穿古代社會始終。像遷徙一事,不僅常見于兩漢,《大元通制條格·雜令》中有“豪霸遷徙”條,其所遷豪霸中也多游俠。
但需要指出的是,游俠對抗官府有如下兩種不同的情形:一是本著俠義原則為民請命,目的是為了匡補其在錢、糧、刑、名等方面的闕失,這個部分,歷代游俠曾有過許多了不起的作為,既見諸載記,常感激人心,它們是后世小說中義俠形象的基本來源。二是為一己之私攻訐長吏,干犯法禁,這就不能視為蔑視權貴。如宋元以后,散入民間的游俠常常風聞公事,妄構飾詞,論告官吏,沮壞官府,有的甚至焚燒衙門,沖擊囚牢。不加分析,一概視作反抗權貴,就不免牽強。尤其這當中還有一種“持吏短長”,即抉發官吏隱私以為要挾,就更不能以反抗官府論了。如發生在漢武帝晚年那場“巫蠱之禍”,就起因于丞相公孫賀抓捕“京師大俠”朱安世,引來后者告發其子與陽石公主私通、又使人行巫蠱事。類似的事宋以后還可見到,今人不宜單憑想象作片面肯定。
澎湃新聞:我們讀武俠小說,會覺得那些俠客個個出手豪闊,而史書記載中,大多數的游俠是不事生產的,那么他們以什么為生呢?
汪涌豪:這類描寫確實不盡出于小說家的虛構。游俠之所以能妖服冶容,鮮衣美食,出入連騎,從者如云,接濟起人來更是傾囊而出,不留后手,是與其世家累富、多有田土有關。日人平勢隆郎指出,西漢游俠與富商聯系密切,其中暴豪之俠既壟斷坊市,又兼營商業、手工業,與其時周流天下的大賈有相似或重合的交通管道,大多還經商有成。宋以后,士商相混,紳商出現,許多“山人”兼為商人,許多商人又好為任俠,就更少物質方面的顧忌。
但盡管如此,依著這一人群的天性,大多不愿槁項黃馘,老死壟畝,故“不事生產”、“不樂常業”仍是其基本的生活狀態。這其間,有的游俠因為聲名在外,慕名而來者爭赴其庭,牛馬什物充牣不算,即頃致千金也非難事,但絕大多數游俠沒有這種待遇,平時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要維持豪闊的生活,就只有靠妄行非法了。《史記·貨殖列傳》所列“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可謂說盡其大概。
“攻剽”指以強力劫取,“椎埋”指椎殺后埋掉,此等劫掠行旅、橫搶市集是為財;偽托俠義,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圖報私仇,將人椎殺埋葬了事也可能是為財,“掘冢”更是所謂“向死人要銅鈿”。“鑄幣”即“盜鑄”,是自己開工造錢,凡此都給游俠帶來巨額的財富。此外,他們還沒少干“私煮”、“掠賣”等事,前者指制販私鹽獲利,其中許多著名的鹽梟都是由游俠充任的。后者也稱“略賣”,指用強力擄人以圖利,用今天的話就是綁票。唐宋以降,“坊市制”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開放式的街巷布局,商戶與居民雜處,極大增加了城市吸納外來人口的能力,造成社會上不在四民之列的冗者激增。游俠置身其間更如魚得水,靠山吃山,傍海吃海,尤其許多俠少與地痞游閑聯手,設變詐以為生計,在水陸兩道違禁走私成為常態。故明人姚旅《露書》稱古有四民,士農工商,自宋以后增加了僧、兵,變成“六民”,至此則有“二十四民”。他解釋其中“響馬巨窩”一類:“有閑公子,俠骨豪民,家藏劍客,戶列飛霞,激游矢若驟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羨其雄,官何敢問”,可見主要是干殺人越貨的勾當。
由于錢來得容易,愛惜也難。這才有許多俠者千金在握,頃刻間就可以緣手散盡。這其中當然包含許多游俠是在做劫富濟貧、賑窮周急的好事,如鄭仲夔《耳新》就記載有“潮惠大俠”嘗綁富豪子弟,出貼通衢,令其家人重金來贖。但從朝廷和地方政府的立場出發,這顯然是無法容忍的劣行。

澎湃新聞:游俠作為一個群體,在中國社會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汪涌豪:游俠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從未被統治集團認可過,也少有得到主流文化的整體性肯定。但社會上廣大的人群,憑著樸素的知覺與經驗,都覺得其可敬可愛,甚而忽視其有可畏可怖的另一面,多少是因為司馬遷那句不止說過一次的話:“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它很自然地讓人去想這“緩急”是如何產生的,既已產生,又有誰可緩解等問題。一個顯然的事實是,政治清明、世道祥和的時代,這種緩急不會常有,即使有也比較容易克服。因為在這種社會,國家綱紀不亂,人們安居樂業,間或有戶、婚、田、錢等方面的矛盾沖突,乃或道德人倫方面的糾葛與悖亂,也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明法和禮俗來解決。而當這個社會的弱勢人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無力自救,由國家出為主持公道自屬當然,即這個社會的其他成員也會秉一種良知,設身處地地分擔其痛苦。然而真實的世道常常反是。尤其易代之際戰亂紛起,或大災之年人不聊生,極易使強暴和不公正之事叢生頻發。有時即使未逢亂世災患,也有執事者亂政、怠政等問題。一旦不平事起,不要說民不舉官不究,即使民已舉而官不究也在在多有。這方面,我們不能太相信舞臺上的清官劇,看看史書所載歷代胥吏衙蠹如何橫行不法就可知道,即使專制政體高度發達的帝國晚期,吏治崩壞和司法腐敗之事有多嚴重,良懦之人又如何告訴無門,束身為魚肉。此所謂“江海相逢客恨多”。
其間又有一種情況尤其讓人驚心。那就是不要說許多人有遭遇緩急無法出脫的窘迫,有時候,這種緩急還正出自強權者的有意操控。《管子·君臣》篇就指出過這一點。他不滿“為上者”常讓身邊近臣,即所謂“中央之人”控制群下,認為“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但現在這些人出于私利的考量,常不能正確處置這類問題,相反,“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什么意思?就是為攫取威勢,憑手中權力把無足輕重的緩事硬辦成急事;又為了市私恩,把人命關天的急事拖成緩不濟急。這最讓人意氣難平。管子說這個的目的是警示“為人上者”,本來“生法者君也”,現在你“威惠遷于下”,早晚要出事。但他似乎忽略了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多少背公行私、草菅人命的事情發生,又會造成多少底層人的哀哀無告,冤無從伸。
那么,問題的根源在哪里?顯然不僅在“中央之人”。明方以智《任論》說得透徹,在“上失其道,無以屬民”。此時有游俠出來,敢任人所不能任,甚至不惜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脫人于待命刀俎的窘境,自然大得人心。所以緊接著他又說:“故游俠之徒以任得民。”這個意思,明清以來許多人都說過,后來梁啟超等人也說過。若要問為何游俠驕蠻悍頑、擅作威福,仍能得大眾信賴,原因就在這里。游俠在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之所以不能被忽視,就在于他可以濟王法之窮,去人心之憾。尤其當朝多秕政,敗亡之漸,他是無助弱勢最大的依靠。
澎湃新聞:您已提到,包括前面所說的晚清之士,歷史上許多主流中的文人士大夫都很推崇游俠,那俠的文化意義又是什么?
汪涌豪:簡單地說,其所起的作用已足以彰明其意義。我們知道,古代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權力依附和等級結構發育得非常充分的社會,又認同親族協作型的治理模式。用馬克斯·韋伯的話,為一“家族結構式國家”。因此素來重視由君主、官吏和平民構成的政治權威,由圣賢、士人和庶民構成的社會權威,以及由族長、家長和家庭一般成員構成的家族權威。因此它的社會穩定如勞思光所說,端賴四種權力:一為士人,其特性是教化的;二為家族,其特性是血緣的;三為民間組織,其特性是習俗的;再有就是政府,其特性是制度的(《中國文化要義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152頁)。由于傳統中國人從來以“集人成家,集家成國,集國成天下”為理之當然,一種如柯雄文(Antonio S. Cua)所說的將做道德自律的“典范個人”視為“持續無休止的修身過程”的觀念(《道德哲學與儒家傳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106頁),得到世人絕對的鼓勵。以后再由中庸調和的儒家學說與謙退尚柔的佛道思想的滲入,遂使一種重內省輕發露、重和合輕對立、重圓到輕伉直的處世方式,成為人們普遍照奉的準則。這樣行之日久,造成的極端后果便是人們社會責任感的消散與社會元氣的蕩失。每個人都拘執一種個人主義道德觀,潔身自好,束身寡過,而全無普遍主義的高上視鏡。看似從容中道,其實據于儒、依于道或逃于禪的背后,是安于守舊而不知拓新,謹于私德而昧于公義;是媚軟拘謹、飾智任詐。到最后,誠如明儒章懋所批斥的:“老成清謹者為上,其次只是鄉愿,下則無所放僻邪侈,無所不為。”(《楓山章先生語錄》)
類似對傳統文化由追求溫雅而趨于文弱,追求謹重而趨于保守,追求自我人格完善而趨于利群意識淡薄的批評,中國人自己說了許多,外國人對此也常有論及。我們比較熟悉羅素在《中國問題》中所做的批評,其實這樣的批評多了去了。如十九世紀,美國傳教士倪維思(J. L. Nevius)就對中國人“膽量不足而懦弱有余”多有譏評,他甚至稱“中國是一個冷漠遲鈍、不思進取、懶散懈怠、缺乏生氣的民族”(《中國和中國人》,中華書局2011年版,217頁),這是不是讓我們想到了林語堂?我們說,國民性的背后有文化與傳統在起作用,游俠的存在,某種意義上說,正照亮了這種文化的短板,也是對這種傳統的匡補與救贖。
他在認知方式上不講循例從眾,行為方式上不拘允執其中,情感方式上不尚拘謹自持,評價方式上排斥崇禮重序,無死容而有生氣,無空言而重實際,不避禍福,忘忽利害,有時還能充作勞氏所講的第三種權力,在民間處定是非,決斷生死;特別是他重人格平等,尚精神自由,愛無等差,義不茍且,這種敢于擔當又能擔當的精神,對從來講究察于安危,寧于禍福,明于去就,莫之能害的中國人及其背后的文化,顯然具有糾補意義。還有,他追求簡單的是非和簡明的人際溫愛,通過自身的努力與發揮,求得生命的高峰體驗,從而既超越儒家所強調的社會聯系和政治秩序法則,又超越道家所強調的自然聯系與心理秩序法則,最大限度地開顯了人的主動性,為消解這個世界的累累重負,疏浚堅強而飽滿的生命之源,提供了獨特而醒目的借鏡。
直到今天,為什么中國人仍喜歡這類人物,喜歡看武俠片和武俠小說?在人的心智結構常不免與世俗經驗相協調、與名利計較相適應的過程中,有時心憾于利害,間或又情變于存亡。這樣的時候,排開重氣輕死、任張聲勢的另一面,游俠的人格與精神,應該仍對當代人的人格建構乃至文化建造有借鑒意義。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