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企業如何為社會服務
1000億背后,或許蘊藏著騰訊找到的答案。
8月18日,騰訊再投500億,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投入到中國社會的基礎民生領域。看似巧合,實則水到渠成。
四個月前,騰訊即提出“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首期500億資金投向基礎科學、碳中和等前沿領域。
兩個500億,一者著眼未來,一者立足當下。
它作答的題面是,作為中國互聯網產業的核心力量,變大之后的騰訊將走向何方?
這個答案的起源,要回溯到十年前。那一年,騰訊提出了延綿至今的“開放戰略”。


倒逼出的“開放”
2010年的11月,注定是令騰訊刻骨銘心的月份。
在這個月里,“3Q大戰”到達戰事頂點,二選一、淚灑發布會、周鴻祎發公開信……技術戰、輿論戰、心理戰,戰戰相扣,步步驚心。
11月20日,工信部發布通報,同時批評了騰訊和360兩家公司,PC時代最后也是最殘酷的一戰“3Q大戰”宣告結束。而就在同一天,張小龍帶領著六七個人的小團隊,在廣州一個小角落開始研發一款名叫“微信”的軟件。
中國互聯網史上,迄今為止最閃耀的產品從此開啟征程。
新舊時代,在喧囂和寂寞中,悄然切換。
在接下來的十年里,“3Q大戰”自外,“微信”由內,一齊改變了騰訊,它開始脫胎換骨。
經“3Q大戰”一役,騰訊驚覺,這并非只是因惡性劫持而引發的一起競爭,環顧四下,自己此前想進入一切領域,掌控一切資源的做事邏輯遭到聲討抵制,已然成為了行業“公敵”。
十場“診斷騰訊”的專家討論會聽下來,騰訊管理層在痛苦反思中破繭蛻變。
2010年11月11日,是騰訊12周年司慶日,此時3Q大戰正酣。在內部憤懣與悲壯的氛圍里,馬化騰向全員發送了一封題做《打開未來之門》的郵件,提出了騰訊新理念的雛形。
馬化騰說,“我們將嘗試在騰訊未來的發展中注入更多開放、分享的元素。我們將會更加積極推動平臺開放,關注產業鏈的和諧,因為騰訊的夢想不是讓自己變成最強、最大的公司,而是最受人尊重的公司。”
半年醞釀,2011年6月15日,騰訊舉辦首屆“合作伙伴大會”,對外公布“開放戰略”,提出要在騰訊之外“再造一個騰訊”。
騰訊開始把能力向外輸出:共富,共創,距今整十年。

與中國互聯網共富
十年之間,每當騰訊財報發布,據此計算騰訊員工年薪,已成為一些媒體“例行”的報道熱點。今天,這個最新數字攀升到94萬元。盡管這一計算方式并不科學,但騰訊對員工的慷慨和高福利,“股王”的核心標的地位,已是業內共識。
騰訊不僅讓9萬多名員工和廣大投資者獲得了高回報,這種“共富”還延伸到開放平臺的伙伴身上。
2010年12月,“3Q大戰”平息不久,馬化騰在公開演講中提了一個愿景。他說,騰訊“希望讓天下沒有埋沒的才能。”騰訊希望可以通過開放平臺,“讓每個企業,甚至每個人都能夠成為價值貢獻者,并且從中獲益”。
騰訊的“共富”由此開始。
2016年9月,在騰訊開放戰略實施五年多之后,騰訊開放平臺累計分給創業者的收入超過100億元人民幣。如果統計排行榜最靠前的個人,到2015年,在騰訊開放平臺上已經誕生了50位億萬富翁,成長出20家上市企業。
今天,騰訊通過公眾號、小程序、微信支付、企業微信等共同構成的微信生態,帶動就業機會達到近3000萬個。一大批創作者和創業者,在微信生態里獲得了成功。
通過騰訊開放戰略“共富”起來的,還有騰訊投資的互聯網創業公司和員工們。
截至2020年1月,騰訊總計投資企業超過800家,其中70多家已上市,逾160家成為市值或估值超10億美金的獨角獸。
一大批創業者在騰訊的幫助下,實現了個人價值,富裕起來。而這些創業者創立的公司,又直接帶動了數百萬員工從事互聯網行業。
這是騰訊與整個中國互聯網的“共富”。

“共創”連接器
不止“共富”,還要“共創”。
在騰訊開放戰略的演進中,騰訊重新定位為互聯網產業中的“連接器”:成為互聯網基礎設施和能力的提供者,與行業中優秀的公司連接起來,幫助這些公司一起推出創新產品,一起成功。
當好“連接器”,源于騰訊的反思,更是騰訊變大之后,對產業產生的敬畏感。
2015年,馬化騰面向合作伙伴發出一封公開信,信中誠懇地說到,騰訊認識到企業再大,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行業都有很深的專業性,只有開放協作,才能創造出共贏的未來。
在“共創”思路下,許多新興公司推出了創新產品,外賣、共享出行、社交電商這些新興的商業模式,已經處于國際領先的位置。
十年前,BAT曾被視為中國互聯網不可逾越的大山,甚至一度有“BAT之下,寸草不生”的段子。而今天,中國互聯網的產業生態豐富,一大批新興公司冒頭長大。
包括騰訊在內,沒有一家公司被認為可以長期獨占鰲頭,沒有哪家公司被視為不可挑戰,中國互聯網行業的良性競爭氛圍開始形成。
這些逐步成長起來的互聯網公司,也開始投資和幫助更多中小創業者。“共富、共創”的“先富帶后富、先進帶后進”模式,呈階梯狀不斷延伸,催生著繁盛的中國互聯網生態。
2011年之后,開放戰略使騰訊成為中國互聯網“共同富裕”的引領者,騰訊也由此成為互聯網行業中令人尊敬的一家公司。
如果說“3Q大戰”從外部倒逼出騰訊的“開放”戰略,走向中國互聯網的“共富、共創”之路。在“3Q大戰”結束之時開始研發的微信,則從內部徹底改造了騰訊。

產品里的“中國”
2014年春節,微信“紅包”上線,一戰成名,此后多年仍是行業所津津樂道的現象級產品。
這個后來被從各種角度解讀的產品,卻往往被人忽視其中飽含的濃濃鄉土氣息——紅包,這是根植于中國傳統節日之中的文化儀式。
在騰訊發展史上,上一個與“微信紅包”可堪一比的是“QQ秀”——卡通、新潮。面孔是中式的,服飾、氣質卻偏西式和現代。
這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產品。以2011年為分界點,QQ和微信作為騰訊兩個時代的看家產品,形塑了騰訊不同的企業文化。
微信誕生之前,中國處在PC時代。互聯網源自西方,PC使用的高門檻又決定了用戶主體是中國相對年輕的用戶,他們更樂于接受西方舶來的文化。以QQ為核心產品的騰訊,因服務這些用戶,也充滿了新銳氣息。
“3Q大戰”之前,騰訊意欲獨霸一方的做法,很難說沒受彼時內外文化的影響,包括騰訊內部沿用至今的員工英文花名,都透著那一年代的印記。
今天,在中國有超過十億用戶每天都在使用微信,文化的底色就是生活,微信已經深深融入中國人的生活,與中國文化土壤融為一體。與其說微信改變著中國人的生活,不如說中國文化在悄悄改變著微信。
微信為外界所稱道的是“克制”,而另一種更貼切的說法,是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不偏不倚,中道而行。微信里那些看起來平常如水的功能,和中國人線下“熟人社會”的生活習慣,絲絲相扣。
從QQ到微信,騰訊的企業文化也因此而改變。中國文化在改變微信的同時,也深刻影響了騰訊。
與之伴隨的,是騰訊在活化傳統文化方面的文化自覺,這讓它屢有先鋒之作:《王者榮耀》的英雄多取材自中國歷史,打造“云游敦煌、數字故宮”等數字化文博窗口,讓傳統文化IP走入游戲、漫畫、電影……
騰訊近年來倡導“新文創”,力圖打造有世界影響力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透出它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雄心。
中國傳統文化改變了騰訊的產品,也悄然改變了騰訊的價值觀和商業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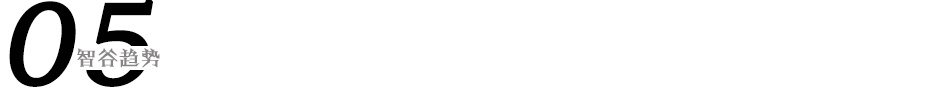
從商之道
2019年,騰訊將“用戶為本,科技向善”作為新的使命和愿景。
它帶有古典中文的色彩:兩兩對仗、朗朗上口。而更讓人聯想到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大學》開篇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是帶有中國文化底層印記的使命和愿景。
作為一家商業公司,在按照現代化公司運作的同時,遵從中國的傳統商業文明,“共富、共創”已嵌入基因當中,成為騰訊新的“商業之道”。
中國傳統文化鄙視為富不仁,恃強凌弱。騰訊提出開放戰略,甘作行業助手和幫手,和合作伙伴一起分享利益。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投資促創新,騰訊不謀求控股,不謀求控制合作伙伴,平均占股低于20%。關鍵時刻幫忙不添亂。相比之下,美國如Google、Facebook等則多數采取收購手段,將小公司的能力化為己用。
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回饋社會、敬老扶弱。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是中國第一家互聯網企業發起的公益基金會,截至2020年底,籌集捐款總額115.8億元,騰訊累計捐款64億元。
在內部運行管理中,也仍然可以發現中國文化的印記。比如被外界所熟知的“賽馬機制”,也契合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勝負已定,點到即止”,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現在,“共富、共創”思路為越來越多的創業者所認可。讓先進公司投資自己、賦能自己,已經成為互聯網創業者的一個優選項。
騰訊在幫助創業公司“共富、共創”的同時,也獲得了商業上的豐厚回報。在騰訊投資的800多家公司里,有15家公司創造了超過10億美金的回報,利人也利已。
馬化騰曾總結說,這種“去中心化”的開放戰略,讓“一棵大樹”變成了“一片森林”,現在看來這也是騰訊能長那么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半條命”的危與機
騰訊的“共富、共創”之路,并不平坦。
2018年2月,騰訊上線一款閱讀軟件“立知”,隨即被發現和一家合作伙伴開發的產品類似。很快,“立知”下線,馬化騰親自問責。在這樣一個細分領域里,騰訊都要痛下決心。堅持讓利于人,堅持克制沖動。
但過度開放,也給騰訊帶來危機。
“立知下線”三個月后,《騰訊沒有夢想》一文刷屏,文章直指“騰訊正在喪失產品能力和創業精神,變成一家投資公司”。
與之伴隨的事實是,把更多機會交給合作伙伴后,在信息流、短視頻等多個新賽道里,騰訊屢次失利。
對于騰訊的開放戰略,有一個“兩條半命”的通俗說法:通信社交和數字文化是騰訊的兩個命根子,騰訊自己來做,其它廣闊領域作為“半條命”交給合作伙伴。
通過開放戰略,騰訊把太多業務都作為“半條命”交給合作伙伴,限制了練兵機會,核心戰場打起仗來,能力匱乏問題就暴露出來。
和合作伙伴“共富”的“半條命”還在,而核心戰場的“兩條命”卻遭遇了危機。
“共富、共創”的前提,首先是自己要有能力、有資源去幫助別人。面對“開放戰略”帶來的能力危機,騰訊沒有選擇退縮,而是選擇了進一步“開放”來解題。
2018年9月30日,騰訊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架構調整。騰訊把大部分面向消費互聯網的業務整合成為“平臺與內容事業群(PCG)”,注重技術能力提升,大力開展“工業化”建設,重構內容力。
同時,騰訊新組建了面向產業互聯網的“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CSIG)”,這是騰訊新的判斷:行業趨勢在發生變化,消費互聯網正在向產業互聯網轉移。
騰訊將自己積累的經驗和能力系統性輸出,做中國傳統行業升級的“數字化助手”。面對傳統行業,騰訊的定位不是顛覆,而是依舊當好助手,一起“共富、共創”。
騰訊總裁劉熾平曾說:互聯網行業“顛覆了很多行業,讓很多人沒飯吃了”,這既不對,也不是騰訊真正的機會。騰訊的機會恰恰在顛覆的反面——“把技術分享出來,讓所有伙伴參與”。
從互聯網到傳統行業,騰訊的開放戰略并沒有止步,其“共富、共創”的思路正在加速。

中國社會的命運共同體
距9.30變革之后不到三年,2021年4月,騰訊迎來了第四次戰略升級,提出了“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騰訊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擴展到整個社會。
大背景是,隨著互聯網產業快速發展,以騰訊、阿里等為代表的互聯網大企業與中國社會的關系,正在發生變化。
一方面,互聯網大公司與中國社會已經結成命運共同體。
此前的二十年,中國互聯網公司從根本上,是憑借中國的人口紅利,以及社會提供的基礎設施獲益,得以迅速成長,而現在它們已經與中國社會融為一體。騰訊的用戶覆蓋中國絕大多數民眾;騰訊的部分產品,比如微信支付,某種程度上已經有了類似于“基礎設施”的作用。
從利益共同體進化到命運共同體,騰訊必須成為“中國社會的服務者”,才能再次發展。
另一方面,互聯網大公司也到了要向社會回饋的新階段。
互聯網公司身上積聚了巨大的數字能量,未來會走向何方,向善還是向惡?自己在國家和社會治理結構當中是一個什么角色,如何作為才能夠促進社會發展而非反之?這些問題既新又迫切。
2019年底,騰訊提出新的使命和愿景,“用戶為本,科技向善”,這是騰訊的一種主動表態:堅定走向善之路,堅定為社會服務。
在此基礎上,2021年4月,騰訊提出的“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則是將這種表態落到實處:基礎科學、教育創新、鄉村振興、碳中和、FEW(食物、能源與水)、公眾應急、養老科技和公益數字化……
首批500億資金準備投入的領域,看似與騰訊不相關,但卻與騰訊扎根的中國社會密切相關。騰訊選擇主動成為“社會的服務者”。
而8月18日,騰訊又將這一戰略推向更深,新的500億“共同富裕專項計劃”將關注當下的民生,在低收入增收、幫助醫療救助完善、促進鄉村經濟增效、資助普惠教育共享等領域持續投入,帶后富、幫后富。
未來與當下,相互呼應。兩個計劃共同構成了騰訊“科技如何為社會服務”的完整方案。
騰訊的“共富、共創”,延續了十年,也是一個正在進行當中的命題。
在過去短短二十多年里,騰訊和其他頭部互聯網公司一樣,成長為一種幾乎服務全民的新型科技公司。
作為一家商業公司,控制自身無限擴張的欲望,幫扶他者共同進步,并不是容易的選擇。
過去十年,通過開放戰略,騰訊承擔起行業“先富和先進”者的責任,幫助中國互聯網、傳統行業一同進步。
而今天,騰訊則在“變大”之后,意圖探索中國互聯網公司的獨特發展路徑:既然能量從社會中來,也必將到社會中去;將能量釋放到社會中,帶動社會一起成長,以社會的成功再次促進騰訊的成功。
這是富有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獨特商業之道。也是一家根植于中國社會、被中國傳統文化所浸染的商業公司,所做出的自然選擇。
再次回到2010年11月11日,騰訊12周年司慶日。在那天,馬化騰發送了的全員郵件中,他寫道,“當我們回頭看這些日日夜夜,也許記住的是勞累、是委屈、是無奈、是深入骨髓的乏力感。但是我想說,再過12年,我們將會對這段日子脫帽致禮。”
十年一瞬,時光已然給出答案。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