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6
羅伯特·達恩頓:18世紀《百科全書》印刷工人們的工作日常
印刷工和雇主
禁書在18世紀的法國通過地下渠道廣為流傳的時候,也許傳播了煽動性思想,但從那之后它們就被安放進了珍本室,在穹頂之下、高墻之內陷入靜止。它們已然成了老古董。書在剛剛印好的時候樣子很不一樣,但現在很難去設想它們原本的樣貌了,因為無論是印刷店還是18世紀出版業的發行體系,都基本不為我們所知。要想對這些書籍剛剛誕生時世界的樣貌形成一些認識的話,我們得回到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檔案中去,通過檔案我們可以觀察到印刷工工作時的狀態,聽聽老板們是如何談論他們的。
由于納沙泰爾印刷公司是從散落在法國、瑞士和萊茵蘭各地的印刷中心招徠工人,因此該公司的管理層形成了一張招聘代理網絡,他們調派計日工,通過源源不斷的書信往來討論用工市場,這些信件透露了一些有關舊制度治下的勞動狀況和工人的基本看法。其中信息最為豐富的書信往來在1777年,當時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規模擴張了一倍,為的是印刷四開本的《百科全書》,其時興起的“百科全書熱”耗盡了整個印刷業的資源。工人們借著這個暫時的用工緊俏時期,但凡能找到薪酬更豐厚、工作條件更好的機會就會不斷跳槽,因此就有了工人四處奔走的問題,這是貫穿那些書信往來的一個主題。納沙泰爾印刷公司招工最具吸引力的條件也許就是提供旅費,其金額約等于這個工人抵達工作崗位前在路上所花的時間若用來工作原本可以賺得的工資。同樣是10或12個小時,比起費力地推著印刷機,或埋頭在鉛字盤上苦干,工人們更喜歡行路,還能不時在路上的鄉村旅館停留一下。他們的旅程變成了一種帶薪休假,四處奔走成了一種生活方式,至少在計日工年輕時如此。
有時,我們可以根據信件的日期來追溯一個人的行蹤。他們通常要花兩天時間從洛桑行進70千米抵達納沙泰爾;從巴塞爾出發則有120千米,需要三天時間;從里昂出發有300千米,需要一周時間;而從巴黎出發有500千米,需要兩周時間。例如在1777年6月16日,百科全書之風最勁之時,一個巴黎的招聘人員派了六位工人去納沙泰爾,許諾他們一抵達就能得到24里弗赫的旅費。他們正好兩周之后向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報到,每天平均行路36千米。他們每周能賺10-15里弗赫,這樣一來旅費就相當于他們兩周的工資——這對于在初夏橫跨整個國家的一場徒步旅行來說是筆不錯的補償。但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在這些工人至少工作一個月之前拒絕支付旅費。招聘人員并沒有告訴這些工人這個條件;而且以防他們拒絕接受,他把工人的行李(hardes)作為一種擔保,之后才運到納沙泰爾印刷公司。這些工人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開始工作,排版、印刷《百科全書》。他們的名字定期出現在領班的工資簿上,八周以后他們才能拿到旅費和自己的行李——然后,他們就消失了。他們中有些人幾周之后出現在日內瓦的一些店里,這些店當時也在印《百科全書》。至少有一人去了巴泰勒米·德·菲利斯(Barthélemy de Félice)的店,當時他正在伊維爾東(Yverdon)出一版“新教”版的百科全書,與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版本是競爭關系。其他人也許是在伯爾尼和洛桑忙著印八開本的《百科全書》,因為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一個巡回銷售員報告,稱他在瑞士的其他幾家出版公司發現了之前離開納沙泰爾的“叛逃者”。而且至少有一名印刷工,名叫蓋亞特(Gaillard),一年以后又在巴黎出現,請求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再次雇用他。據巴黎的一位皮革商為他寫的求情信稱,蓋亞特為“自己犯下的過錯”懊悔不已,準備再次啟程前往瑞士——而這已經是他第三次去了。

德夫朗斯(Léonard Defrance,1735-1802)拜訪一家印刷工場(約1782年),藏于格勒諾布爾博物館
蓋亞特犯了什么“錯”?皮革商的這封信中并沒寫明,但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通信當中顯示,人們常常在遇到麻煩時“叛逃”。有時他們是因為債臺高筑,或是收到了下一周工資的一小筆預付款。他們很少積累資本,常常為了躲債想要離開某鎮,或是去另一個地方領取一筆旅費。基于這些情況,雇主在信中每每提及工人的時候,都透出一種根本不信任的口吻。工人不可靠。即便他們不是拿著旅費或預付款跑了,也會因為醉酒而缺席;而且最糟糕的是,他們還會為法國警方或其他出版競爭對手做探子。招工人員的推薦信中散發著一種性格學的東西,給人留下理想型工人的印象。他要有三個特質:按時上班,不醉酒,有一定的技術。根據日內瓦的一位招聘人員所寫,一位完美的排字工是這樣的:“他是位好工人,能做你交代他的任何工作,一點兒都不浪蕩,工作勤勤懇懇。”
類似的評論還透露了一些關于怎樣能吸引到工人的隱性條件。一條私下里給巴黎一位招聘人員的囑咐頗為典型,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如是說:“你現在可以繼續時不時地給我們派些人來,那些對我們這里的生活懷有好奇的人,但不要提前付任何錢。”不消說,“好奇心”會驅使人們走去異國工作,哪怕是在500千米之外。這些信偶爾還會提到其他一些動機,但對于現代讀者而言都匪夷所思。比如,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如此指導一位正要從里昂派工人過來的人:“我們答應,他們一到就支付12里弗赫的旅費,只要他們在我們這兒能待至少三個月……你可以讓他們放心,他們一定會對我們和這個國家滿意的,這里產的葡萄酒很好。”這里預設工作與美酒是分不開的——而且雇傭期不會長。
盡管這里提到了美酒和工人偏好徒步旅行的風尚,但這并不意味著18世紀不存在金錢關系。恰恰相反,招聘人員常常提到工人對工資的考慮,可以提供的工作量,還有一些特定的條件,比如排字版式的偏好,除了按件付費還要計時付費。一個招聘員解釋道:“他們就是在工資的問題上堅持,因為他們在一個地方過得還不錯就不會想離開,除非在其他地方能過得更好。”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甚至還派了密探,潛入日內瓦幾家也在印《百科全書》的店,通過許諾更高的工資把工人挖走。工人們應勢密謀抬高日內瓦的價格;日內瓦的老板們聽到了納沙泰爾印刷公司行動的風聲;最終老板們內部達成和解,聯合將工人的工資壓到同一個水準。
在聘用和解聘的過程中,雇主把工人當作物品來對待。他們都是一批批地雇工,就像訂購紙張和印墨一樣。正如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對里昂的一個招聘員交代的:“應該對招來的工人進行分類,即排字工是多少人,印刷工是多少人。”有時這些“分好類的工人”會遭拒,要是貨色品相不夠好的話,就和購買紙張一模一樣。該公司向一家出版同行這樣說,稱其被里昂的一個招聘員坑了:“他給我們派來的幾個人狀況太糟糕,我們不得不再把他們運走。”該公司責怪招聘員派人之前未能進行檢查:“你派來的人當中有兩個雖然安全抵達,但病得很重,會把其他人傳染了;因此我們沒法雇他們。鎮子里沒人愿意給他們提供住處。他們因此又動身去了貝桑松,想去那里的收容所報到。”而對于疾病纏身的窮人而言,進收容所就意味著死亡,因此納沙泰爾印刷公司一定清楚,自己正把這些人送上在法國的最后一程——而且從納沙泰爾到貝桑松要翻越汝拉山脈,路很不好走。
納沙泰爾印刷公司還是做了一些舊式的慈善。該公司工頭的工資簿上包含了一些這樣的條目:“給一個德國工人的救濟,7巴茨(相當于1里弗赫)。”來信中偶爾也有對工人的同情。例如,一個伯爾尼的印刷廠主這樣推薦一位老排字工:“他是個好工人,之前在納沙泰爾工作了挺長一段時間,但我得告訴您,他的視力和聽力都開始退化了,而且他年齡大了,已經不能像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那樣排字了。盡管如此,既然你可以只計件付給他薪酬,我還是懇求您能盡量雇用他;他因為貧窮落得十分可憐的境地。”但最后伯爾尼人還是開除了他,而納沙泰爾人也沒有雇他。事實上,《百科全書》一完成,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就解雇了2/3的工人,盡管一位主管的女兒對此表示抗議,她在父親出差期間負責打理印刷店,寫信給他:“不能一天天地把有妻兒的人趕到大街上。”這位主管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對女兒進行了一番有關贏利的說教就否決了她的反對。因此,把在法國的旅行生活想象成一種愉悅的、年輕人的漫游時光,或是認為工人與雇主之間相親相愛的想法都是錯誤的。
那么工人自己又是如何來表述他們的狀況的?這直到現在還無法明說,因為歷史學者沒能和18世紀的工匠進行直接的聯系,盡管像E. P.湯普森(E. P. Thompson)、莫里斯·加登(Maurice Garden)和魯道夫·布朗(Rudolf Braun)這樣的專家都進行了相關研究。但印刷工不同尋常,他們是識字群體。他們當中有些人相互通信,他們的書信有一些被廠主截下,被攔截的信件當中又有一些在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檔案中被保留下來。一個名叫奧弗雷(Offray)的阿維尼翁排字工寫給一個名叫杜克雷(Ducret)的薩瓦地區工人的便條,就是這種工人間通信的一個珍貴樣本,后者當時在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排字組(casse)工作。奧弗雷剛剛辭掉了納沙泰爾的工作,以加入伊維爾東巴泰勒米·德·菲利斯的店。在那兒,他向杜克雷保證條件要好得多。當然,為菲利斯工作也有不好的地方:“教授”——大家都這么稱呼他——從來不給雇員借一個子兒,德國工人和法國工人處不好。但那里生活成本低,店的經營也要比納沙泰爾的好。最重要的是,活比較多:“這里的活兒很充足……這點你根本不用發愁。”
工人會因沒活干而擔心,因為雇主都是有活才聘人。一本書印完后,他們往往會解雇之前印這本書的工人,等到準備印新的一本書時再去雇人。這樣一來,奧弗雷就是在推薦本地區其他印刷店的工作機會。洛桑的于巴克(Heubach)要招一位排字工,甚至還有可能招一位工頭;在伊維爾東至少缺兩位印刷工和三位排字工,因為奧弗雷的三位工友秘密計劃要在下周日就從菲利斯這兒辭職不干了。“不是因為沒有活干,而僅僅是因為工人們朝三暮四的——我本人首先就是這樣——一直換工作。”最后,奧弗雷還傳達了兩人在其他印刷店的共同好友的境況,還向他之前在納沙泰爾的工友問好:“我給戈蘭先生(M. Gorin)寫信了,若收到他的回信——我希望會——我就告訴你。請向克羅什先生(M.Cloches)、波萊勒先生(M. Borrel)、龐西翁先生(M. Poncillon)、帕當先生(M. Patin)、昂戈先生(M. Ango)問好,請別忘了我的老伙計蓋耶(Gaillé)……我妻子也向這些先生們問好。我漏了郎西先生(M.Lancy),我也要問候一下他,還有‘奶罐’夫人(Madame pot-au-lait)。”這些昵稱,信中提及的其他書信往來,還有這種形成了一種朋友圈的感覺,如此種種都表明,工人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信息溝通體系,相互之間通過書信交流來推薦自己的老板——或如他們所稱“資產家”,這和雇主與招聘人員之間通信交流工人的情況一樣。
工人之間的內部信息大多是通過口口相傳,每每都是印刷工在路上相遇,或是這一行業的人常去的小酒館里相互喝上一杯時傳播。消息的傳播和內容都難以追溯。但一些零散的信息表明,工人討論工作的時候都很懂行情,很現實。他們想知道哪兒的薪酬高,哪兒的工作多,哪兒的工友比較投契,哪兒的酒便宜,哪兒的工頭比較和善。而雇主之間的信息體系所流傳的情報體現了不同的考量。勞動力供應就像紙張和印墨一樣,要盡可能便宜、高效,要能聽從指揮,可以通過額外獎勵、懲罰和開除來規訓。一旦在生產過程中不再必要,就可以被丟棄。
工人和資產家并非像一些研究前工業化時代歐洲的歷史學者所想象的那樣,共存于一種家庭般的溫馨關系之中。他們彼此憎惡的程度很有可能與19、20世紀一樣。但兩方對彼此間關系有著共同的預設——也就是關于雇傭關系的根本認識:他們都預計雇傭關系會是不穩定、不規律的,還有可能風波四起,很可能不長久,但其中不會有和現代雇傭現象哪怕有一點點相似的情況,什么每周40小時,朝九晚五工作制,1.5倍加班工資,上下班打卡,投入和產出,生產時間表,合同,工會,自動化,通貨膨脹,實際工資,退休金,業余生活,工作內容枯燥乏味,異化等都不存在,也不會有那些想要理解這一切的社會學家。

堆放在比利時列日省的某家書店門外的成包圖書
印刷工的工作和氛圍
如此就是18世紀印刷工和他們的雇主對于工作的態度,但工作本身究竟是什么?其主觀現實也許讓歷史學者難以捉摸,但還是可以通過分析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工頭巴斯泰勒米·斯皮努(Barthélemy Spineux)所記的工資簿來衡量其生產力。每周日晚,斯皮努都會記錄過去一周每個工人的工作量,還有為此得到了多少報酬。斯皮努根據排版的書頁底部的簽名來計算排字工的工作量,根據數以千計的印次來計算印刷工的工作量。通過計算實際文本當中的半身數,我們可以利用斯皮努的記錄來計算每位排字工每周將鉛字字符從字盤里拿出、碼上排字手托所做的動作次數,還能計算每位印刷工拉動印刷機手柄的次數。可惜的是,這些計算涉及分析文獻學當中一些煩瑣費力的訓練,是一門頗為艱深的學科,似乎法國人認為很深奧,常常在前面加上“盎格魯-撒克遜”的定語。但這對歷史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值得一做,因為對斯皮努工資簿進行文獻學研究能得出對前工業化時代工人的工作量與收入的確切記錄。
我就不深入文獻學的復雜研究了,也不會呈上一整套圖表,我只想提一下我的數據統計得出的一些主要結論。第一,人事變動的速度顯然非常快。每六周差不多就有一半的雇工會換人,印刷店整體上每周都會有變化,因為工人們來去匆匆,亂糟糟,這背后既有工作機會不固定的因素,又有像奧弗雷說的那樣,工人們自己“朝三暮四”。從這樣一種極不穩定的模式當中總結出一般規律往往會有偏差,但工人似乎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短期臨時工,往往在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工作少于六個月;另一類是固定員工,會干滿一年或更長時間。固定員工一般年紀更大,已婚,不過也有一些年輕人。排字工的情況是,他們和某個工作機會同步。例如,一位老排字工貝爾托(Bertho)用88周時間處理了《百科全書》大部分的排字工作,最后一冊剛剛印好,他就離開了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因此,數據統計表明,工人對工作機會很看重——用印刷工的行話來說就是工作(ouvrage)或勞動(labeur),這在工人的書信當中非常突出。
第二,通過追蹤1778年五個月每位工人每印一頁所做的排字和印刷工作,我們可以了解到工頭是如何應對這種充滿變數的勞動力供應狀況的。在工作流程當中,印刷工處于排字工的下游,因此,要是幾個排字工辭去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工作,相應數量的印刷工就有可能被辭退。因此,在10月10日那一周,三個排字工離開了納沙泰爾印刷公司,讓排字隊伍從13人降到了10人,工頭就將印刷隊伍從20人砍到了12人,這樣一來總的產量就降了一半。一項新的工作任務加上新招募的排字工則有可能扭轉這一趨勢,正如9月5日-19日,排字工隊伍從9人增至12人,印刷工隊伍從13人增至18人,相應產量也翻番了。人力資源和生產力的圖標起伏很大,每周要么激增要么突降,跌宕起伏,這顯示勞動管理是一項需要去平衡的工作,不論是在經濟層面還是勞動力層面都會產生高昂的成本。
第三,我們可以考察每位工人的勞動產出和收入,而情況也多種多樣,不僅每個工人之間有差異,而且同一批工人每周的表現也不一樣。印刷工屬于通常所說的“勞動貴族”,他們是技術工人,收入是普通工人的兩倍。只要他們堅持工作,每周能給家里帶回100納沙泰爾巴茨或15里弗赫幣的收入,這足以支持一個家庭的生活,要比法國的紡織工人、石匠和木匠都賺得多。但他們實際賺到的錢往往比能賺到的要少,不是因為沒有工作可做,而是他們自動選擇少做。
例如在10月3日這一周,排字工戴夫(Tef)的工作收入下降了一半(從92巴茨降到了46巴茨),而另一位叫馬雷(Maley)的則增加了1/2(從70巴茨到105巴茨)。每個人都有很多冊的工作需要完成,但大家都喜歡按自己的節奏來,一陣一陣很不穩定。印刷工隊伍當中不規律的問題甚至更突出。尚布魯勒(Chambrault)和他的工友們在6月13日這一周賺了258巴茨,完成了18000印次;之后的兩周他們的產出降到了12000印次,之后又降到了7000印次,總共的收入降到了172巴茨,然后又是101巴茨。另一邊在三周時間里,尤尼科勒(Yonicle)和他的工友的產量從12525印次飆升至18000印次,之后又升至24000印次,他們的收入從182巴茨漲到258巴茨,又漲到344巴茨。在最高產的時期,他們賺的幾乎是效率較低星期的兩倍,是手腳慢的工人的三倍多。大多數工人在大多數時間里遠遠低于自己的工作全力。僅在少數情況下他們的產量下降可以歸因于節假日或是工作量減少。工人放慢速度或者干脆停工是去縱情聲色(débauche),這是印刷行業的一個老傳統了。1564年6月11日安特衛普普朗丁出版社(Plantinian Press)的記錄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提到的那個米歇爾(Michel)去了妓院,周日、周一、周二、周三都待在里面;然后周四早上回來,在他平時住的房間里的行李箱上睡了一覺。”
盡管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檔案并未提供有關工人如何度過閑暇時光的詳細細節,但顯示他們有錢有閑來享受。計時工又被稱為“良心工”(conscience worker),被認為是店里最可靠的工人,正如他們的這一稱呼所示。但即便如此,出勤記錄也顯示,他們常常沒有做滿一周六天的工作。例如巴度(Pataud)在1778年夏天做了五周的計時工(憑良心工作),第一周他工作了五天,第二周五天,第三周六天,第四周六天,第五周則是三天。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但無論如何來處理工資簿上的數據,我們都能發現勞動的不穩定狀態——時長、節奏、組織、生產力和薪酬支付亦是如此。
若將統計數據與書信中表達的態度進行比較,這一情況就顯得很重要了。這兩種證據互為補充,體現了工人自己對工作基本性質的體驗和理解。但在下結論之前,我想說一說第三種證據,在人類學意義上被稱作“文化”的證據。我是指關于傳統、民俗和印刷技藝的學問的信息。這類信息非常豐富,分布于像印刷工的手記和回憶錄這樣的資料當中,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尼古拉·雷茨夫·德·拉布雷頓(Nicolas Restif de la Bretonne)的記錄就是明顯的例子。最豐富的資料當屬尼古拉·孔塔(Nicolas Contat)的《印刷軼事》(Anecdotes typographiques)。此人是一位巴黎的排字工,記述了自己在18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一位學徒成長為圣-賽維朗街(rue Saint-Séverin)一家印刷店工頭的經歷。孔塔關于工人如何被雇傭、管理、付薪酬的記錄在很多細節上都符合納沙泰爾印刷公司檔案描述的情景。還為后者增加了新的維度,因為其中滿含印刷店文化的信息,特別是關于三個主題的:規矩、行話和笑話。
孔塔將自己的經歷安在一個名叫杰洛姆(Jerome)的虛構年輕人身上,描寫了很多慶典場景,主要是像圣馬丁和福音者圣約翰這樣的節日;但他著重強調了學徒在印刷店成長過程中的儀式。比如,當杰洛姆剛參加工作時,他經歷了一個被稱作戴圍裙(la prise de tablier)的儀式。他還得給印刷店組織——印刷職工會(chapelle)支付6里弗赫(這大概相當于一個優秀的計日工三天的工資)。計日工內部還會收一點兒費用[被稱作“認可費”(la reconnaissance)],然后全體工人就一同前往花籃酒館(Le Panier Fleury),這是于謝特街(rue de la Huchette)上一家印刷工常常光顧的酒館。酒館里計日工圍在杰洛姆周圍,工頭在中央,人人手里都端著斟滿了酒的杯子。副工頭走過來,手里拿著印刷工穿的圍裙,身后跟著兩位老資格,二人分別來自印刷店的兩個“集團”——排字工組和印刷工組。工頭做了一番簡短的講話,然后就給小伙子戴上了圍裙,在身后給他系好綁帶。隨后工人們紛紛鼓掌,為他的健康干杯,而他本人也接過一杯酒加入其中。
作為儀式的結尾,工人們走到房間盡頭準備好的豐盛大餐前大快朵頤。他們一邊往嘴里塞著肉和面包,一邊交談。《印刷軼事》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交談內容:“他們有人說,印刷工狂吃海塞難道不是最在行嗎?我敢說,要是有人給我們上一只和你一樣大塊頭的烤羊,我們也能吃個干凈,只剩下骨頭……他們根本不討論神學或哲學,更不會討論政治。人人都在講自己的工作:有人會跟你說排字的事兒,還有人說印刷的事兒,還有印刷機上的襯墊紙,或是墨球皮帶。他們都是同時開始講,也不管別人能不能聽清。”終于,在清晨時分他們相互分別——個個酩酊大醉,但堅持到最后一刻都還很有儀式感:“晚安,我們的工頭先生;晚安,排字工先生們;晚安,印刷工先生們;晚安,杰洛姆。”書中接著解釋說,杰洛姆在正式成為一名計日工之前,大家都稱呼他的名,而不是姓。
而這要再等四年才實現,這期間經歷了不少欺凌,中間還有兩次儀式,一是“入行”(admission à l'ouvrage),二是“入伙”(admission à la Banque)。儀式的形式都是一樣的——先收新人一筆費用,然后就去大吃大喝來慶祝——但這次《印刷軼事》提供了給杰洛姆致辭的具體內容:“新成員已經受到了教育,他已被告知永遠不得背叛他們的工友,不得壓低工資水平。一旦有工人不肯接受(某項工作)開出的工資而離職,店里其他工人不得以低于此水平的工資接受工作。這些是工人間的規矩。建議他堅持忠誠和正直的品格。印刷違禁品——被稱作‘栗子’(marron)——時,任何出賣工友的工人都會名譽掃地,被逐出印刷店。工人們會給全巴黎和外省的所有印刷店寫信,將他列入黑名單……除此之外,沒有什么禁止之事:愛喝大酒是好品質,風流放蕩只是年輕人犯渾而已,欠債是聰明的表現,不信上帝說明為人真誠。這是一個自由、共和的世界,凡事都可行。可隨心所欲地生活,但要做個誠實的人,不要玩虛偽。”簡言之,杰洛姆被一種清晰明了的文化特質所同化,這種文化看上去與馬克思·韋伯的節制苦行主義和現代工廠的勞動紀律簡直有天壤之別。這一刻他有了新的稱號:杰洛姆已經不再用了,換成了“先生”——也就是說,他現在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或者說社會地位。他經歷了嚴格人類學意義上的成人禮。
當然,在此期間他掌握了一門行當。《印刷軼事》的內容大多關于一位學徒是如何學會排字或如何裝印版的,甚至還有一份詞匯表幫助讀者理解技術用語。但仔細讀會發現,工藝用語其實與技術沒太大關系,更多是一種行話,因此不僅體現了工作是如何完成的,更體現了工作所處的氛圍。這些行話集中于六個主題。
①慶祝活動。除了已經提到的“歡迎會”(bienvenue)、“入伙會”(banque)和“認可活動”(reconnaissance),工人們還會慶祝“啟程送別會”(la conduite,為送別即將動身在法國巡回找工作的工友所舉辦的宴會),還有洞房會(le chevet,計日工倘若結婚,印刷職工會會付給一筆錢)。
②玩耍作樂。工人們常常會在下班后玩一場戲仿(copie,對印刷店生活中發生的事情進行滑稽的模仿),或逗笑(joberie,講笑話、嬉鬧),還有皮奧(pio,荒誕故事會),或者是鬧騰一場(une bonne buée,打趣胡鬧)。
③吃吃喝喝。像吃(fripper)、“抓胡子” (prendre la barbe,喝醉)、“一只袖子”(une manche,半醉半醒),還有“鬧個場子”(une faire la déroute,在卡巴萊表演酒館鬧一鬧)。這樣的詞都表明,工人們在印刷店與酒館之間往來頻繁。
④暴力。從行話像“抓山羊”(prendre la chèvre,情緒失控)、“頭羊” (chèvre capitale,大發雷霆)、“起摩擦”(se donner la gratte,爭吵斗毆)來看,印刷店經常會爆發斗毆事件。
⑤麻煩事。工人有可能會“掙脫枷鎖”(promener sa chape,停工),或是“拿走圣-讓”(emporter son Saint-Jean,辭職不干,拿著工具跑路,以印刷業保護神的名字來代指),或“做狼”(faire des loups,債臺高筑),或“拿符號”(prendre à symbole,賒賬消費);但他似乎總是惹麻煩。要是他去“小門”(la petite porte,老板的耳目),那他就是個馬屁精、叛徒,在工友這里會惹麻煩。
⑥工作性質。印刷工們自然會有很多關于疏忽、錯誤的表達,如“面團”(paté)、“貝殼”(coquille)、“僧人”(moine)、“大黃蜂”(bourdon)。他們遵循印刷店的主要分工,區別“猴子”(singes,排字工)和熊(ours,印刷工),出版學徒則是“海膽”(oursin)。說到排字組和印刷組時都將其看作兩個分立的階級。他們會使用“勞動”(labeur)或“工作”(ouvrage)來表達被某項工作雇傭的基本概念,這與現代概念中加入一個公司形成對照。
工人們還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舉止和幽默逗笑。這些逗笑最淋漓盡致的表達就是戲仿,或諷刺模仿劇,其形式和內容能博得滿堂大笑,還伴有嘈雜的音樂(嗡嗡聲)。杰洛姆在印刷店的日子里最精彩的戲仿是和他同做學徒的勒維耶(Léveillé)上演的,后者有非凡的模仿才能。這些小伙子們被迫早早起床,很晚收工,之后回到閣樓上糟糕的房間里,他們感覺自己得到的是動物的待遇——事實上還不如家里受寵的動物,一只名叫灰灰(la grise)的寵物貓。看起來當時在巴黎的印刷店店主中間開始流行養貓,有一個店主養了25只。他給每只貓畫了肖像,還喂它們烤熟的禽肉。杰洛姆和勒維耶只能吃上稀薄的粥食,而灰灰卻能從店主太太盤子里分得上乘的美食。一天清晨,勒維耶決定不再忍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他從房間里爬到房頂上靠近店主臥室窗戶的地方,開始很大聲兒地喵喵叫喚,把他的資產家夫婦給吵醒了。如此忍受了一周之后,店主認為自己被那些巷子里可惡的流浪貓下了蠱,命兩個年輕人去收拾它們。二人開開心心地照做,因為“店主們喜歡貓,那么[工人們]就討厭它們”。
兩個學徒歡天喜地地來了一場貓的大屠殺。他們手持店里的工具,找到一只貓就敲打一只,首當其沖的就是灰灰。他們把這些奄奄一息的小東西裝成一袋一袋,堆在院子里,然后演了一場行刑的戲。他們安排好衛兵,任命了一位告解神父,進行了宣判,然后向后一步,看著一位假裝是劊子手的人將貓掛在一個臨時搭起來的絞刑架上,人群爆發出大笑。店主的太太在人群興致正酣的時候趕到,看到灰灰在絞索上掛著,于是驚聲尖叫。店主連忙跑來,但除了責罵工人們消極怠工什么也做不了,因為是他給工人們提供了屠貓的機會在先,最后是以資產家在人群中爆發出新一陣的哄笑前離開收場。這件事后來成了這家印刷店里的一個傳說。之后的數月里,勒維耶一次次反復表演全過程,形成了一種逗笑的固定節目,一場對戲仿的戲仿。每當工作乏味難當之時,這個節目都給店里帶來了歡樂。當勒維耶完成一個節目之后,工人們都會在鉛字盒上敲打排字盤,用錘子敲打版框,像一群山羊一樣叫成一片,以此來表達歡樂之情。他們惹惱了店主,讓他發了火。工人們不僅喜歡吵鬧、逗笑,他們還痛恨雇主:“工人們聯合起來反對雇主,只要說他們的壞話就足以在整個印刷工當中贏得尊敬。”
當然,逗笑并不單純,而這場尤其富有深意。勒維耶的戲仿顯示出工人對資產家恨意之切,還有后者與之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這不僅是關乎財富和權力的事情,還關系到感受的不相容。對于工匠而言,逗弄寵物的樂趣非常不適,正如雇主無法接受虐待動物的樂趣一樣。虐貓行為當中的儀式元素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在舊制度時期的大眾文化當中有豐富的儀式,特別是在像狂歡節這樣的節日慶典當中,下層階級在慶典活動中顛倒社會秩序,常常最后以公開處刑來結束戲仿。通過給貓判刑,計日印刷工們以象征的形式審判他們的雇主,糅合了街頭表演、狂歡慶祝和混亂的獵巫行動等多種形式,以此來宣泄自己的憤懣與不滿。
從這份資料當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有主觀印象之嫌,但我意識到,首先一點,它很強調具體而實際的東西——工作的開展,對手頭工作的談論,對眼下情況以及日常世界里熟悉的事物之間直接聯系的一種普遍關切。工人用慶祝儀式來裝點這個世界,用嬉笑幽默為其注入活力,所以工作本身就含有儀式、成人禮和樂趣。工作與娛樂之間并無清晰的界限,勞動與我們今天意義上的“休閑”之間亦無分隔,而18世紀是不存在休閑這一現象的,那時候人們每天在12、14個小時,甚至16個小時的時間里將工作與娛樂混雜在一起。
與此同時,笑話和行話俚語突出了這種工作不穩定和不規律的性質——暴力、酗酒、致貧、逃工、被開除時有發生。工作就是辛苦的勞動,是因某項具體工作任務才有的,因此有一搭沒一搭,而不是像被一家公司雇用那樣穩定。行業的傳說印證了工資簿上人員更替頻繁的情況,也印證了雇主通信當中顯示的工人對旅費問題的看重。工人從一份工作換到另一份,到處奔走,他們不會認定自己屬于某個階級、某個團體或哪家公司,而是屬于這個行業本身。他們的自我定位就是計日聘用的印刷工,而不簡單是工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話語,拜自己的守護神(至少在天主教國家如此),還會光顧他們內部常去的酒館,會按照內部特定的路線在法國巡回找工作。他們甚至在周日出游的時候也會結伴而行,一起去逛鄉下的酒館。有時會根據不同工種團體分撥,排字工一群,印刷工另一群,還會和對立的鞋匠和石匠群體發生爭吵、沖突。印刷工將自己與其他工種進行明確的區分——同時也與他們的雇主區別開來。他們的行業有發展極為完善的知識傳統和文化特質,這讓其無法與更廣泛意義上的工人群體團結一致,但更表達出了對資產家的強烈痛恨。印刷店并未能起到類似于溫暖幸福大家庭的作用,而是一個關系緊張、危機一觸即發的小世界。
為了重建這個世界,我試著對工作進行數據統計測算,想以此來揭示工人和他們的老板對工作的態度,來考察其中體現的行業文化。這三個元素相一致,揭示出18世紀法國和瑞士的計日雇傭印刷工這一特定工人群體眼中何為工作的意義。其他行業的工人,還有廣大非技術工勞動群體,也許對自己的工作有不同的認識,因為他們的工作經歷肯定與印刷工有很大不同。但若說從這一特定的資料中可以總結出什么規律,那就是前工業化時代的工作一般是不規律、不穩定的,是基于具體行業和具體工作任務的,其組織形式是集體化的,但其工作效率因人而異——所有這些特點都讓作為一種普遍現象的工作在這一時期與工業化時代的工作截然不同。因此,通過觀察一家印刷店的運作,我們可以了解到人類生活的一項根本要素是如何發生轉變的,讓現在的我們與那些18世紀文學被遺忘的作者處于完全不同的狀況,而當時正是他們將這些書籍生產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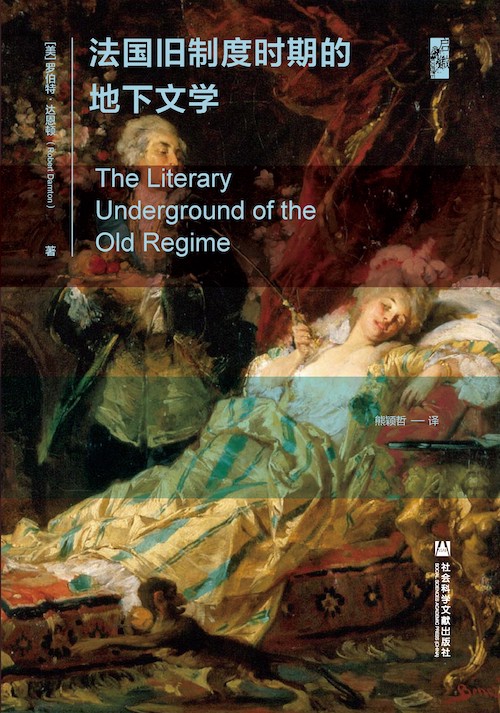
(本文摘自羅伯特·達恩頓著《法國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熊穎哲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7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