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阿里員工疑被領導性侵,受害者維權與舉證的困境
原創 詹青云 看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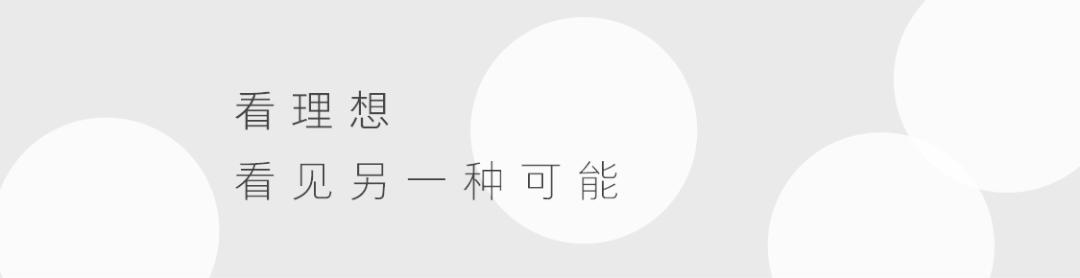
截止8月10日,#阿里巴巴女員工被侵害# 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達到9.1億。
根據受害者長文記錄,14天前(7月27日),阿里一位女性員工被領導強制要求前往濟南出差,而后被客戶與領導灌醉,并遭遇了猥褻與疑似性侵。7月28日,受害者第一時間選擇報警,并要求查看監控錄像,以及盡可能保存了物證。
在回到公司后,她按照流程在內網向上反映,并提出了自己的合理訴求,但經過多次溝通仍得不到回應后,她選擇在公司食堂發傳單抗議,卻遭到多名保安的勸阻,無奈于8月7日撰寫了一篇長文,才終于引爆熱搜。
8月9日,阿里內網終于正式公布了該事件階段性調查結果及處理決定,但聲明中將事件定義為“有過度親密行為”引發了大量輿論爭議。
同時,8月8日,一位網名為@投訴滴滴上級被開除的單親媽媽 發帖表示,去年她被客戶帶到私人飯局后遭強制猥褻,當時自己失去意識,等醒來發現臉上全是傷,報警后未立案。興化檢察院的回復函則顯示,現有證據無法證實有猥褻行為。
在現行的許多法律體系中,有關性侵犯罪的舉證與判決非常復雜,通常牽涉受害方的性同意問題,并往往會要求受害方承擔額外的論證責任;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與偏見之下,對性同意的表示也往往有著不同的界定標準。
但隨著觀念的進步,“no means no”(不即是不同意)以及“yes means yes”(需明確表示同意)的標準也逐步成為某些法律體系的共識。
今天,我們與你分享詹青云在看理想App節目《像律師一樣思考》中,對于強奸案判定和舉證的探討。她也指出,在現行的法律文化里,真正缺失的其實是從女性的視角去看待性關系,理解何謂“性同意”。
文 | 詹青云
來源 |(文字經刪節整理)
01.
一個人身體的完整性受到傷害,
這就足以構成暴力
許多刑事犯罪都帶有一些顯著的特征,比如殺人、放火,它的危害性是非常明顯的,它被人類社會所痛恨和鄙視,界定標準也是非常明確的。
但同為重罪,關于什么行為構成強奸、強奸應該被視作何等程度的罪行、強奸犯應該受到什么樣的懲罰,對于這些概念的理解,是深受罪行背后的社會文化,以及很多意識形態所影響的。
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里,我們開始重新看待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去看待所謂的性自由、性同意,去看待受害者,一個女人(或男人)對于自己身體的完整性的控制,對于自己身體不受侵犯的自由的堅持。
強奸有兩個核心的元素。第一個元素即為“強”字,意為使用了暴力,另一個元素則是違背了受害方的意志。
強奸案的法律標準在發展歷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關于暴力的界定。在漫長的歷史長河里,“強奸”中的“強”字指的是“性插入”這個行為以外的暴力。
比如把這個人壓制住,讓她/他無法反抗;比如用暴力傷害她/他,讓她/他不敢反抗;或者讓她/他陷入昏迷,失去反抗的能力等。
在裁定“一個性行為是否構成強奸”的時候,法官需要去尋找在性行為本身以外,被告方還使用了額外的暴力。

《日本之恥》
在過去二三十年之間,越來越多的法律和判例認定“性插入“這個動作本身就是一種暴力。
傳統的強奸案譴責的是“在發生性行為的過程當中,額外對受害的一方所造成的身體上的傷害”,現代的法律理念里,會認為它首要的傷害是“違背對方的意志,而強迫她/他進行性行為”這件事情本身。
這件事情的傷害不僅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人格尊嚴意義上的。
當一個人身體的完整性受到了傷害,這就足以構成暴力了。
這個界定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不止體現在“背后是一種全新的權利理念,而是一種我作為‘人’的完整性,我的尊嚴不受任何侵犯和踐踏的理念”,它也體現在法庭上要用什么樣的證據去證明有“暴力”。
02.
不能僅僅憑借“反抗”,
來衡量受害者是否同意
如果一個法律體系要求有性交行為以外的額外暴力,那么它通常是要求受害的這一方證明自己“有過反抗”,這就是一個額外的論證責任——她/他要證明“我反抗過”。
但一些典型的例子,比如一方是在熟睡過程中被性侵的,或者有受害者是因為大量飲酒陷入昏迷狀態,然后被性侵犯,這可以解讀為加害者“沒有使用額外的暴力”嗎?
更典型的情況,以及在之前的判例當中更難處理的情況是“被侵犯的一方因為害怕、恐懼,或者是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傷害的時候,失去反應的能力,而不知道該怎么反抗”。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刑法以“州”為主體,不同州之間,意識形態有很大區別,分布在光譜各個地方,有的州走向非常極端。在美國的南方,一些州甚至不允許女性墮胎。
由于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不同州對于強奸案的界定、法律的理解也大不相同。一個重要的差異是:不同州的法律要求女性遭遇強奸時反抗程度不同。
最嚴格的要求,是反抗時“要有口頭的明確表達,再加上有行為、有動作”;而有的地方法律可能允許“只要在口頭上表達我不愿意”即可;有的地方更進一步,把“沉默”當做一種抗議。
這就是我們說的那些情況,她/他在熟睡,她/他在酒后失去了知覺,她/他因為恐懼、僵硬而沒有辦法表達反抗,她/他這個時候的沉默是不是足以構成一種反抗?
對于這個問題,在最“激進”的那些法律體系里,它會認為“yes means yes”,就是你必須得說“我同意”。只要沒有得到一個自由意志下給出的明確同意,受害一方就算作在反抗,而對方就算是在違背她/他的意志。

《難以置信》
所以回頭再看這兩個問題:如何確定受害者有沒有同意呢?這是不是她/他的自愿行為呢?這兩個聯系非常緊密的問題,體現的是我們一再講到的刑法當中的兩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是行為,是加害者具體做了什么?有沒有使用暴力?暴力該如何界定?第二個元素,是加害者的意圖,是他的心理狀態。
當我們去衡量一個人是否犯下了強奸罪的時候,我們要求他的知識、他的意圖,他的mindset(心理狀態)是怎樣的?我們之前提到過不同的心理狀態,它會決定所作所為將構成一個什么樣的罪行。
03.
“yes means yes”
我們所聊的這些法律標準、規則的差異,是關于“強奸罪”定罪要素的具體差異、標準差異。原告要滿足什么樣的論證責任,才算把這個案子給“搭”起來了?被告想要推翻原告搭好的“房子”,他需要提供什么樣的證據?以怎樣的方式推翻?
在標準不同的情況之下,論證責任當然是不同的。以“行為”這一要素為例,有的地方要求除了有“性交”行為之外,還得有其它的暴力;有的地方不要求額外行使的暴力,這是非常明顯的論證責任的差異。
很現實地說,在目前的醫療手段之下,只要報案比較及時,要證明有性交發生,是相對容易做到的。可是要證明在性交的過程當中,伴隨著其它形式的暴力,卻并沒有那么簡單。
有的時候這種暴力可能表現得非常明顯的:在人的身體上留下了明顯的傷痕,或者有比較清晰的證據的記錄,有人證、有錄像帶或者有證詞。
但是經常會面對的情況則是,什么樣的力、什么程度的力,可被視作構成“暴力”?其實這個問題并不明確。
有很多一定程度的“暴力”,是足以使受害的這一方放棄或者沒有能力反抗的暴力,但它可能并不會留下清晰的證據;也有很多時候這種“暴力”是隱性的,它是威脅、它是精神上的恐嚇或者精神上的控制,它是在漫長的相處過程當中,所形成的一種威懾力。
這些東西更難以用證據證明,所以不同的論證責任,會提供不同的報案的門檻,或者論證為一個罪名的門檻。
如果一個法律體系之下,它要求有性交行為以外的額外暴力,那么它通常是要求受害的這一方證明自己“有過反抗”,這就是一個額外的論證責任。
反抗在有的地方是一個“一刀切”的標準——如果你沒有反抗,那么法律就默認你是同意的;有的地方則認同說,你有的時候不反抗,并不是因為不想反抗,而是因為沒有能力反抗。
但也有的法律體系會給予一個“機會”——這時的論證責任,并不是一種額外的義務,而是一個機會,如果可以證明恐懼是合理的,那么“沒有反抗”,就不再成為定罪的阻礙。
此前有過一個判例,一位女士被侵犯了,她并沒有嘗試逃跑,也沒有反抗。她當時感到非常恐懼,就問性侵者說“如果我按你說的去做,你能不殺我嗎?”
案件遞交到法庭上的時候,被告一方說“這不是強奸,因為沒有‘暴力’這個元素”。這個案件中的男方沒有使用身體暴力,因為女方根本沒有反抗,她只是因為恐懼,然后順從了。
這個案件的最終結果是,“當受害一方出于恐懼而沒有辦法反抗的時候,‘暴力’這個元素可以被證明”,也就是說,只需要證明這種恐懼是合理的(reasonable)。

《難以置信》
更明顯的論證責任的劃分不同,還體現在“什么情況下我們可以認為,性行為的發生是違背了一方的意志?”
有的法律體系要求要明確地說出“同意”,即“yes means yes”。假設在男女之間,當女方說出“yes”的時候,才叫做“她同意了”。這時的論證責任,在于案件中的被告一方(男方),他需要證明“她確實有同意”。
但如果法律體系要求的是,“如果你不同意,你得說no”,也就是“no means no”。這時的論證責任就落到原告一方(女方),因為如果女方沉默的話,那么這個法律體系就會默認她是同意的,她就得去證明“我確實表達過我的不同意”。
所以法律體系標準的設置不同,就將給雙方帶來巨大的難度差異。而這背后潛藏的,就是法律“默認”的狀況;而它所折射的,則是整個社會文化中的默認、偏見與常態。
尾聲.
在過往的法律歷程中,有大量類似的案子因為要求額外的“暴力”元素,而沒有辦法被定性為強奸。它隱含的意義是在絕大部分的強奸案當中,女性受害者需要反抗。
所以有很多人批評這種法律概念,這是在要求一個女人在被侵犯的時候還要像一個“男子漢”一樣反抗,才能自證清白。
從這一點出發,有很多法律理論家深刻地指出:這種兩性文化,或者是傳統的性別觀念傳統,它對法律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深埋在大家的潛意識之中的。
明面上,法律可以隨著時代相對容易地改變,但真正難以實現的改變是大家腦海深處的對性暴力事件的固有印象。

在現有的社會認知里,我們都認為在性關系當中男性有一定的攻擊性,男性占有主導地位,女性適當地反抗其實是一種順從。
這種意識形態才是最難糾正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法律文化,是從一個女性的視角出發,去理解一個女性在被侵犯的情況下,她所感受到的恐懼。
當她因為這種突如其來的傷害,陷入無法思考、無法反抗的狀態時,法律如何保護她們的權利?
法律認同“如果這個時候受害人因為感到恐懼而沒有辦法反抗,那只要證明這種恐懼是合理的”就可以了,這是法律當中通行的所謂“理性人”的標準。
問題就在于這里的“理性人”是理性的男人,還是理性的女人呢?
如果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法律都是理性男人的視角,大部分的法律工作者都是男性,大部分的警察和檢察官也都是男性,他們以男性的視角出發所衡量的“理性人”的標準,又是不是一個女人身處那樣的狀態之下的“理性人”的標準?
因而有很多人認為,現行的法律文化里,真正缺失的是從女性的視角去看待性關系。
所有的這些概念都深埋在我們的文化里,它也會在不經意之間影響法官的判斷、警方和檢方的判斷、律師的判斷,甚至影響受害人自己。
*本期內容摘選自看理想App節目,有大量刪減與調整,小標題由編輯添加。如想收聽完整觀點和講述,可移步至相關節目。
頭圖來源于《難以置信》
原標題:《阿里員工性侵下屬事件,受害者維權與舉證的困境》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