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7
- +1385
劉源上將已卸任總后勤部政委,曾誓言不要烏紗帽也要拿下貪官

任職總后勤部政委5年后,劉源卸任。
12月31日下午,國防部召開例行記者會,國防部新聞事務局局長、新聞發言人楊宇軍大校表示,經習主席和中央軍委批準,總后勤部政委劉源任正大軍區職滿10年,根據軍官法和任免條例有關規定免職,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
在“軍中打虎”行動中,劉源是得力干將,拿下軍中巨貪谷俊山,還連帶挖出了其背后的徐才厚、郭伯雄兩只大“老虎”。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少將在今年12月19日的一篇博文中轉載了劉源此前的“離職告別詞”——《心中永存——向總后勤部告別》。
在告別詞《心中永存》中,劉源提到,“(谷俊山)剛剛起事(我)就講:‘碰上這伙兒人,撞上這攤兒事,當政委的不擔當,誰來擔當?我不出頭,誰能出頭!’繼而(我)又說明:我確實有強烈的愿望——茍利全軍,舍我一人!但我又實在沒本事和力量撂倒誰、擺平誰,是主席、全軍、總后戰勝了邪惡勢力!”
十八大后,總后勤部成為軍隊反腐的“風暴眼”。在軍隊權威部門分14批對外公布的47名軍級老虎中,已有3名總后勤部軍級以上軍官被查,包括原副部長劉錚、司令部原副參謀長符林國及軍需物資油料部原副部長周國泰。
此外,在2012年年初從總后勤部領導名單中消失的總后勤部原副部長谷俊山,亦在2014年3月被提起公訴。
羅援在去年10月14日的博文《反腐旨在重拾民心,重振士氣,捍衛紅色政權》中指出,劉源在查谷俊山的貪腐問題時,幾經磨難。“后來劉源橫下一條心說,‘我雖然沒上過戰場,但我也死過幾回,活過幾回,我寧肯烏紗帽不要了,也要把貪官拿下來。’”
按照軍隊“首長分工負責”原則,政工首長負責組織實施屬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工作。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告訴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紀檢工作是政工首長的重點工作內容之一。
換言之,總后勤部的紀檢工作是總后勤部政委劉源的重點工作內容之一。
不過劉源本人反倒多次強調,在反谷(俊山)斗爭中,自己只是做了應當做的分內之事。

事實上,作為總后勤部政委,劉源對于軍隊反腐一直態度鮮明。
今年3月份全國“兩會”時,面對記者圍追堵截,全國人大代表劉源表示,中國軍隊反腐態度堅決主動,將會常態化反腐敗。
“腐敗問題,是古今中外、任何國家、任何政府、任何軍隊都有,我們軍隊的反腐可以說是很堅決的,人民群眾很關心。出了這些貪官,我們軍隊自己也是很痛恨的,非常痛心的,可以說是‘愛之深、痛之切’。正是因為我們對軍隊有感情,所以我們軍隊是主動反腐,自己率先抓出了‘大老虎’,像徐才厚、谷俊山,是我們軍隊自己抓出來的,而且頂著巨大的壓力。這可能在全世界各國軍隊中都是少見的。”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劉源如此回答鳳凰網提問。
2013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劉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評價“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的出臺“全軍擁護,效果顯著”。
劉源說,一段時間確實存在一些部隊官兵吃喝成風、鋪張浪費的現象,損害了軍人的形象,敗壞了部隊的作風,不少同志陷于其中,傷身誤事,自己也苦不堪言,早就希望改變。“恢復我軍優良作風,反對浪費,反對特權,反對腐敗,把精力和省下來的錢用于強軍建設,利已利軍,全軍拍手叫好。”
這種正直與他的經歷不無關系。
作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幼子,劉源這一路走得并不平坦。
他從小生活在中南海,16歲時被逐出,兩次主動到農村接受磨煉,37歲時便被推選為副省長,而后又轉戰軍界,成為一名將軍。用他自己的話說——從上跌到下,又從下翻到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曾在一篇自述中談到,“那時候(1982年)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
對自己的家庭背景,劉源并不回避:“盡管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物質上的東西,但是留下了最珍貴的精神財富。如果說有什么特殊的話,那就是一些‘特殊’的嚴格鍛煉的機會。”

中南海里的小列兵
1951年初春,劉源在北京出生,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中南海度過的。
他從小就對軍營生活很向往,于是“今天一個叔叔刻把槍,明天一個叔叔做柄刀”送給他,他就整天“沖呀殺呀”滿院子瘋。
1955年解放軍首次授銜后的一天,有人給4歲的劉源畫了副肩章,用針別在他肩上。這正好被路過的楊尚昆看到,就拉著他的手走到了正在說話的朱德、彭德懷、陳毅三位元帥和鄧小平中間。
楊尚昆說:“看看咱們未來的將軍。”劉源站在幾位久經戰火的長輩中間,得意洋洋。結果陳毅發現了肩章上的玄機:“嗯?還有字吶——‘芝麻醬’!”在場的人頓時笑成一片。
之后有很長一段時間,“芝麻醬”成了劉源的別稱“雅號”。
劉源雖然是這個大家庭里最小的男孩,卻從來沒有受到父母的特別優待。家里孩子多,生活開支緊張,劉少奇要求孩子們從小就要養成艱苦樸素的品德,他們的衣服總是從大到小輪著穿,破了由母親王光美打上補丁再穿。
劉源曾回憶,大概14歲以前,他都是撿哥哥姐姐的舊衣服穿,印象中自己小時候幾乎沒穿過不帶補丁的衣服,妹妹也跟他一樣。劉源用的舊鐵皮鉛筆盒是姐姐傳給他的,已經很舊了,以至于后來不得不用橡皮筋綁著用。
劉源7歲入學讀書,按照家里定下的規矩,他和哥哥姐姐一樣,都離開家住校學習,生活各人自理。上世紀50年代末起,“大躍進”造成了經濟困難,全國進入饑荒期。學校按定量給學生供伙食,劉源兄妹也經常餓肚子。
劉源曾回憶,“每逢星期天回到家里,開飯的時候都熱鬧非凡。餐桌上一般是家常菜,茄子、豆角、粉條……父親總是用一個空盤子,一樣夾一點,自己埋頭吃,吃完就走,不多說話。每次等他一夾完菜,我們這些孩子就上前搶呀,很熱鬧。”
1964年7月,劉源進入北京四中讀初中。
是年,他經過父親的同意,進入中南海警衛部隊“當兵”。以后連續3年的暑假,他都在部隊中度過。劉源在部隊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由列兵晉升為上等兵,還獲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戰士”的稱號。
“文革”磨難
1966年,劉源那一年15歲。“文革”的風暴,首先對劉源的家庭襲來。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院墻上張貼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標語。七八月間,中南海里分別召開批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大會。
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野蠻批斗中,劉源看著父親和母親受盡凌辱和摧殘,被打得鼻青臉腫,父親的鞋也被踩掉了一只,腳上只穿著襪子。
1967年9月13日凌晨3點多,一輛軍用吉普車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幾個不速之客闖進住處,宣布對她正式逮捕。
當天,劉源和姐姐劉平平、妹妹劉亭亭3人,連同他們簡單的行李,被拋上一輛卡車,強行逐出了中南海,回到各自的學校接受批斗。同天,劉源6歲的妹妹劉瀟瀟和從小照顧她的阿姨也一起被趕出了中南海。
1968年,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劉源毫不猶豫地向學校報名。1969年新年前,劉源離開了他熟悉的北京,來到風沙彌漫的雁北陰山深處——山西省山陰縣白坊村插隊落戶。
“當時,我腦中既無那種響應號召的狂熱,也無走向充滿艱辛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懼。可以說,當時我處于一種半麻痹狀態,周圍的一切對我都無所謂,說不定偏遠的鄉村倒能讓我躲開喧囂狂暴的環境與無法忍受的壓力。”劉源回憶。
在那里,劉源依然沒能避開審查和批斗。別的同學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他則是在貧下中農監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勞累了一整天,晚上還要沒完沒了地接受批斗。
終于,他那半麻木的神經也忍受不了了。
一天夜里的批斗會上,劉源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鉗,“騰”地跳到門口,發瘋般喊道:“你們還有完沒完?要不想讓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們拼了,出來一個我捅一個!”
不過,劉源并不怕苦。晚上只要不開批判會,他就學習到深夜,從馬恩列毛著作,到各種文化知識。他還自學了針灸,給農民看病,幫農民蓋房,上梁扣瓦。
1972年夏天,劉源決心回北京一趟,尋找父母的下落。
他在老鄉的幫助下,深夜悄悄離開村子,白天在野外躲避追趕,夜晚在崎嶇的山間趕路,餓了就嚼一把兜里揣的炒黃豆,走了三天三夜,終于趕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劉源和姐姐劉濤,妹妹劉亭亭、劉瀟瀟在北京永安里的一間小屋會合后,向毛澤東和中央辦公廳寫信,要求見爸爸媽媽。
8月16日、17日,中央專案組傳達了毛澤東的兩條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8月18日,幾個孩子第一次去秦城監獄看母親。王光美神情麻木,腰都直不起來,見到長大了的孩子們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沒想到你們能活下來。”
特殊的高考生
1975年秋,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全身黃疸的劉源“病退”離開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幾乎全村的人都出來為他送行,許多老人、大嫂和媳婦都哭成了淚人,劉源也泣不成聲。
劉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機廠當學徒工,不久后適逢“四五”天安門事件,他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對象。
工友們心照不宣地把他保護起來,他的師傅田文奎甚至為他擔保:“我白天黑夜和劉源在一起,他沒有問題!”
1977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長安街的高音喇叭里傳出頭條新聞:恢復高考。
北京起重機廠召開正式會議傳達相關文件,報考條件就張貼在車間的墻上。劉源經過仔細研讀,發現報名的政審條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說了本人不能有歷史問題、政治問題。
于是,劉源決定報考,但內心深處對會不會被允許參加考試非常懷疑。畢竟,他的父親劉少奇頭上,還壓著“全國最大走資派”的帽子。
劉源的不安很快被證實不是沒來由的。他的報名被廠里組織部門退回,理由是超齡。劉源那一年26歲,非正式的傳達里,恰好有“最好25歲以下”一說。
以劉源的年齡劃線,廠子里9個年齡大過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
30年以后,劉源分析當年攔他的原因時,已經釋然:“實際上就是出身問題,但人家不說。也不能說我本人有什么問題,就說我年齡不行。當時的環境中,不讓我考,不會犯錯誤,讓我考,就要冒風險。”
“我挺生氣,所以就給鄧小平寫了封信。”劉源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復述信的內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開頭就自報家門,說我是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我這幾年從農村又到工廠,聽說您恢復工作抓高考,很高興,大家都很振奮。我想考大學,現在廠子里不讓考,如果因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讓我考,我很不服氣,何況你這個招生簡章并沒有這么講。讓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誰也不怨。”
信不長,就一頁紙,鋼筆書寫工整。劉源在信封上寫就“中共中央鄧小平副主席”,貼上4分錢郵票,在自己的住處北京永安里附近隨便找了一個郵筒投了進去。
十余天后,來了回音。劉源和其余9個工友,全部被放行。
報考的時候,劉源填了政審表。父親一欄,填“劉少奇”,母親一欄,填“王光美”,本人成分一欄,填“戰士、學生、農民”,“現在是工人”。籍貫、政治面貌、社會關系等等,一概填了一個“眾所周知”。
劉源他們拿到的,是當年北京市高考考場里最后10個考號。離高考舉行,僅余一個星期。
鄧小平的批復,劉源至今沒見過,具體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鄧小平批給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吳德批轉給北京市負責高招的同志,最后是廠教育處通知劉源可以報考的消息。
1978年年初,劉源收到了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
劉源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學系,第二志愿是北師院歷史系。考試結果,雖然超過了第一志愿的錄取線,但北大卻不敢收,北師院則專門開會研究,才收下了這個身份特殊的學生。
到基層去
1979年1月,王光美出獄。1980年5月,劉少奇平反。
隨著父親的平反,劉源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從“黑幫子女”變成了“高干子弟”。
劉源曾在接受采訪時說,從上頭跌下來的時候,很痛苦,大家都理解都同情,但從下頭翻上去的時候,也很痛苦,那種痛苦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他說,“比如我剛上大學的時候,父親還沒平反,同學們對我都很好。在宿舍里,有的男生晚上打撲克,很吵,我就在床上喊,別吵了,我還要睡覺呢。有時候走路別人向我點頭,沒看見,也沒關系。但是父親平反后,情況就變了,人們對我的看法不一樣了。同樣你喊一聲,別吵了,人家會說‘你狂什么狂’。你見人不打招呼,人家就說‘你小子不認人’。這個時候,只好自己調整了:本來被吵得睡不著想喊一聲,但是算了吧,怪討厭的;走路時特別注意對面來個什么人,先向他點個頭。”
劉源在給中學老師的信中這樣表白心跡:“我曾努力去做,證明我同大家沒什么兩樣,是個極普通的人,但枉然……我明白了,我不能強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動來贏得人民的信任,以幾年、幾十年的不懈努力來拆除那道墻。”
大學畢業后,劉源決心重新回到農村去。
“我在農村待過7年,是樸實善良的農民在我最艱難最絕望的時候幫助了我,才讓我有一個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一種生存態度,所以我覺得我好像欠農民的,回農村是我的一個愿望。”劉源說。
王光美知道兒子的打算后,表示理解和支持,還為他下基層做了些安排準備,幫助兒子選擇了他父親曾經戰斗過、最后長眠的河南。
1982年春節前夕,劉源只身一人來到了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
那時,基層剛為老干部落實政策,許多同志才復職。在公社黨委、管委17個正副書記主任中,劉源當了個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個大隊分管一個區,后又分管公社的鄉鎮企業(當時叫社隊企業)。
夏收時,他在驕陽下赤裸著上身,和農民一樣干得灰頭土臉。領導修路時,他用在土坊插隊時取得的“經驗”,一趟又一趟地跑、磨,搞齊了材料,接著又和農民一起挖路基、鋪瀝青。
1983年4月,經新鄉縣人大常委會討論,全票選舉劉源擔任副縣長,主抓全縣的多種經營和工業。一年以后,由于成績顯著,他又被縣人代會全票選舉為縣長。
1986年,劉源調任鄭州市副市長,分管城建、計劃、工交等領域。
當時,市里正在爭取天然氣工程立項,工作難度很大。剛走馬上任,劉源就接下了這個棘手的差事。他一趟趟進京跑項目,用劉源自己的話說,像個“上訪戶”。奔波了一年多,天然氣管道鋪進了鄭州城,市民從此不再用蜂窩煤燒飯了。
37歲的副省長
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屆人代會爆出一條轟動全國的大新聞:37歲的劉源經人民代表直接提名為候選人,并當選為副省長。
100多名代表在推薦理由中說:“我們推薦劉源為候選人,并不是因為他是劉少奇同志的兒子,而是因為他謙虛謹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勞任怨,有突出的政績。”
那一天,劉源百感交集。
在河南人民大會堂里,從代表席到主席臺的6級臺階,他兩步跳了上去,向臺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謝。
上任后,劉源分管的是工業、交通和安全工作。第一項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門峽,處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車事故。
河南是個農業大省,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為了讓河南的工業交通有個較快的發展,劉源經常玩命地工作。為了跑項目跑資金,幾乎跑斷了腿,磨破了嘴,就連他年輕的秘書和司機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
劉源后來自己也調侃說:“有時碰到那些關鍵人物,我這個省長也像個孫子似的,不過好在咱們一來年輕,二來又不是給自己辦事,當當孫子也不覺得丟人。”
在擔任副省長的4年半中,劉源領導建設了多座大型電廠和全國最大的50萬伏直流超高壓變電站,使全省電力裝機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國投資最大的制藥廠中原藥廠等幾家藥企的興建,使全省醫藥產值躍居全國先進行列;利用外資引進電話設備,使全省程控電話增加了五六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三套設備之一的中原化肥廠的投產,為農民解決了急需的尿素供應問題;還有全國最大的周口味精廠、安陽玻殼廠以及黃河上的5座公路橋等。
1992年,劉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水電指揮部政委。
劉源在紀念楊尚昆的回憶文章中提到,“1991年,楊爸爸主動對我說,小平叔叔幾次講過軍隊與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什么。不久,中央調我到武警水電部隊。”
走之前,劉源完成了兩件心事:一是在他父親逝世的地方——開封市北土街10號的一所舊銀行宅院,立上一塊大理石紀念碑,由當時擔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親筆題寫了“劉少奇主席逝世處”的碑名;二是聯絡當年和他一起在山西山陰白坊村插隊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業家,捐資80萬,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學,王光美親筆題寫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學”的校名。
離開河南那天,劉源怕張揚,只去了七里營公社劉莊村告別,沒在鄭州市告別。“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許多人還是跑到火車站去了。”
“金獎鐵軍”
盡管武警水電部隊的條件非常艱苦,但對于從小就有“軍隊情結”的劉源來說,成為軍人等于圓了自己的一個夢想。
劉源帶領這支號稱“中國最苦的部隊”,建三峽、戰邊疆、上高原、下海島,參與了幾十項重點建設和搶險工程,被國家授予金獎,人稱“金獎鐵軍”。
1996年,這支鐵軍又榮獲“世界屋脊水電鐵軍”的稱號。“到了部隊之后,工、農、商、學、兵這幾個身份他全都體驗過了。如此全面的人才,在部隊里真不多見。”劉源在武警水電部隊的一位部下老郭曾這樣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于單位改制,武警水電部隊需要自己到市場上找項目、完成招投標,任務很艱巨。劉源利用自己在河南省主管經濟時積累的經驗和人脈,親自為部隊找工程、跑項目。
為了承包三峽的一個建設工程,劉源曾往返于宜昌和北京50余次。一次,他和老郭為了見到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的一位負責人,在對方家門口站著等了4個小時。
一次聊天時,劉源得知戰士們想看文藝表演,尤其喜歡看喜劇小品,便親自聯系總政話劇團來武警水電部隊慰問演出,還特意囑咐“安排喜劇節目”。
劉源去西藏考察時,無論工作地點多偏遠,哪怕只有一個戰士,劉源也要趕過去與他交流。很多人爭相與他合影,他總是耐心地滿足每一位戰士的要求。
在邊疆高原、大漠深山,哪里有犧牲官兵的墓地,劉源必定去憑吊。
“有一次,坐在車上的劉源看到前方有戰士的墓碑,就趕緊把車停下,走到路邊招呼大家采野花。一片肅穆中,只見他在墓碑前單膝跪地,手捧大把的野花,熱淚雙流。”老郭回憶。
1998年,劉源晉升為武警部隊副政委,負責水電、交通、森林、黃金等幾個警種部隊以及武警在西南、西北片區的工作。2000年,他被授予中將警銜。
2003年,劉源調到解放軍總后勤部任副政委。適逢中國軍隊第十次大裁軍,他參與了總后勤部系統4所院校人員向地方移交的工作。
劉源很看重這次移交對于軍隊的意義,將其形容為“剪掉尾巴,輕裝上陣”。他說,院校移交達到了精兵簡政的目的,軍費的使用將更有效率,“原來買CT機的錢,現在可以用來買飛機了”。對于院校來說,也可以實現從軍到民、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
在移交過程中,劉源親身感受到了工作的壓力,尤其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很難。因為軍隊的福利保障無所不包,但是地方已經鮮有鐵飯碗,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很多人不想離開部隊。
劉源挑起了這副擔子,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將心比心,盡量方方面面都照顧到。
2003年8月24日,在第一軍醫大學移交廣東省管理的交接儀式上,劉源鄭重地對時任廣東省長黃華華說:“我這個女兒多好!從現在起,就嫁給你家了。你可一定要好好待她啊!”
軍科院政委
2005年12月,劉源調任軍事科學院政委,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和期待。
就職見面會在軍科院的大禮堂里舉行,瘦瘦高高、皮膚黝黑的劉源一走上主席臺,臺下就掌聲四起。
“他說話語速很快,聲音洪亮,中氣十足。見面會結束,不少人在走出禮堂后還嘖嘖稱嘆,說他說話很大膽,很不吝,頗有將門之后的風范。”軍科院一位李姓軍官對環球人物記者如此介紹。
劉源剛到任時,軍科院的資金條件并不好,存在經費欠缺、研究資料少、干部住宿難解決等諸多困難,一些造詣很高的軍事專家也受到社會的冷落。
劉源一上任就想方設法,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拉來了經費,為干部、研究人員安排和改善住房,還新建了圖書館。
軍科院有很多資深的研究人員,業務水平很高,但他們之前和外界接觸較少,知名度也不高。劉源到任之后,一直在思考如何發揮這些專家的作用。
他把軍科院里的專家做了一個分類,把適合對外宣傳的人選出來,專門舉辦了一個由電視臺、廣播、報刊等媒體參加的見面會。在會上,劉源向媒體逐一介紹軍科院專家,幫助雙方建立起聯系。久而久之,軍科院的專家在媒體上露面的機會多了起來,全軍許多大單位也開始爭相邀請他們去講課、座談。
劉源眼界寬廣,對國際大事和戰略形勢了然于胸,經常與人討論中美關系、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等。因為站得高,看得遠,愛讀書,觀念新,劉源成了“學習標桿”,備受同事們的尊重。
劉源到軍科院不久,官兵們發現,院內的局域網上多了一個“堅定信仰信念,強化戰斗精神”的新欄目,刊登的都是“劉源政委推薦”的佳作。
欄目的文章不斷更新,連續貼出數百篇來源廣泛、風格不一的文章:從《百年潮》的《鄧小平談學習中國歷史和中共歷史》,到美國《洛杉磯時報》文章《美保守派鼓吹打“八十年戰爭”》;從加拿大《環球郵報》網站文章《諾貝爾獎金得主稱——請保持冷靜,地球會治好自己》,到著名歷史學家寧可的文章《中國古代吏治的得失與借鑒》,令人耳目一新。
劉源在推薦按語中說,他選這些文章是想作為正式學習文件的輔助,“有些言辭過于尖銳、刺激,但立意正確、倡導正氣;有些雖是漫談、雜議,卻予人啟迪、值得深思;有些觀點與經典理論相悖,但不失探討之新;有些更是極為反動,卻正好給我們以警示。”
劉源在軍科院做政委的5年里,每星期都通過這樣的方式和官兵們交流了思想,談了心,收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效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劉源政委推薦”的文章越積越多。軍科院政治部索性將文章匯編成冊,在院內印發,很快被聞訊前來的官兵索要一空。
2009年7月,當了8年少將、9年中將的劉源,晉升為上將,時任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親自為他頒發了命令狀。
2011年1月起,劉源開始以總后勤部政委的身份出席公開活動。
從軍方智囊機構調任解放軍后方勤務和保障的最高機關,劉源肩負起了更重要的職責。
值得注意的是,劉源在查處總后勤部原副部長谷俊山貪腐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劉源自己曾表示,“抓出(中央軍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總后勤部原副部長)谷俊山這樣的大貪巨奸,是習近平主席決定、督辦的……我個人即使起了點小作用,也是在履行職責,盡點本份,應該做的。”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稱,谷案是“中國解放以來軍隊出現的問題最大、性質最惡劣的案件”。而按照羅援的說法,劉源在查谷俊山的貪腐問題時,幾經磨難,“寧肯烏紗帽不要了,也要把貪官拿下來。”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福建古田召開。
劉源發言稱,受“四風”習氣影響、貪腐問題沖擊,特別是徐才厚、谷俊山對軍隊政治生態的破壞,高中級干部公信力缺失已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當前,反腐倡廉形勢不容樂觀,肅貪懲腐工作決不能松懈。必須深刻檢討反思徐才厚、谷俊山問題的教訓,堅持新老腐敗一起反、‘老虎’‘蒼蠅’一起打、存量增量一起除,從嚴糾治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切實扎緊管人管權管錢的制度籠子,把滋生在軍隊肌體上的毒瘤祛除掉,讓高中級干部成長進步的政治生態干凈起來。”劉源在這次“新古田會議”上說。
(本文參考了《劉源憶楊尚昆:做好人,才能做好官》《劉源:鄧小平批準我參加高考》《劉少奇之子劉源:在特殊環境下成長》《劉少奇之子劉源的將星之路:從人生谷底到上將》《換了人間今又是——劉源與毛澤東的后人們》《上將劉源》《上將劉源:中南海里長大的將軍》《劉源:磨難之后煉成上將》等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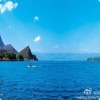


- 嬡巳荿傷:政协副主席或人大副委员长吧
- 2015-12-31 ∙ 广东8回复举报
- 阿德:无论去哪里,都是一条好汉!
- 2015-12-31 ∙ 未知58回复举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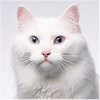
- 山王工业:已据兄意见修正,感谢感谢!
- 2017-06-01 ∙ 湖南1回复举报

- 山王工业:一时短路,感谢指正。
- 2017-06-01 ∙ 湖南1回复举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