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陳子善新書《不為人知的張愛玲》:解讀流言背后的傳奇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新書《不為人知的張愛玲》日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他探討張愛玲的最新文集。自2015年出版《張愛玲叢考》兩卷之后,陳子善在五年間陸續對張愛玲的文學史料作了新的發掘、考證、整理和闡釋,“自以為有了新的發現”。

《不為人知的張愛玲》分享會現場(從左至右分別為張偉、陳子善、周立民)。圖片來源:主辦方提供
7月31日,《不為人知的張愛玲》新書首發會“‘流言’背后的‘傳奇’”在上海朵云書院·旗艦店舉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張偉、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齊聚一堂,就陳子善“張學”研究脈絡、張愛玲作品風格等展開對談,分享了他們心中的張愛玲。
她還愛給小說設計封面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除了魯迅,為自己作品設計裝幀最多的是張愛玲。”發掘、考證了眾多張愛玲為自己作品設計封面背后的故事之后,陳子善總結道。
小說集《傳奇》在1940年代先后推出了三個版本,三版封面設計均有張愛玲的參與。這本書收錄了張愛玲早期的代表作,彼時不過二十出頭的她,借此書完成了“出名要趁早”的心愿,也奠定了自己在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三個版本中,以1946年推出的增訂本封面最負盛名。陳子善介紹,畫面的主體是一張晚晴仕女圖,借用了著名畫家吳友如的《以詠今夕》,而右上方那個不太協調的“怪形象”,便是張愛玲的手筆,她對這一形象的解釋是“像鬼魂似出現的現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窺視”,在偷看里面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這樣的一幅情景,或者說中國人千百年的平靜的日常生活,由于“現代人”的介入被打破了,所以這個封面的含義非常豐富、非常復雜。”陳子善評價。1977年臺灣皇冠初版本的《紅樓夢魘》則是張愛玲唯一一部學術著作,這本書的封面設計也由作家本人完成。《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京劇則是中國戲劇的精華,張愛玲在設計中采取了京劇臉譜的視覺化形象,把這兩個方面的經典巧妙結合在了一起。
在人們一般的印象里,張愛玲與五四文學的關系是疏離的。但陳子善特意提到,張愛玲的寫作與五四新文學傳統有很深的關系,《五四遺事》的寫作就是一個例證。據考證,張愛玲對魯迅的作品相當熟悉,對部分文章甚至有認真反復閱讀,熟知小說中并不引人矚目的細節。
但張愛玲對五四文學創作并非全盤接受,“她認為當時很多白話文文學作品的句法都是借鑒外來文,她對這樣的做法并不欣賞,所以她嘗試學習中國傳統,將《紅樓夢》的寫作方式運用到白話寫作上,事實證明她的嘗試相當成功。”在他看來,張愛玲的寫作非常“天才”,她將“五四”白話文的部分精神,和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寫法結合起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獨特的一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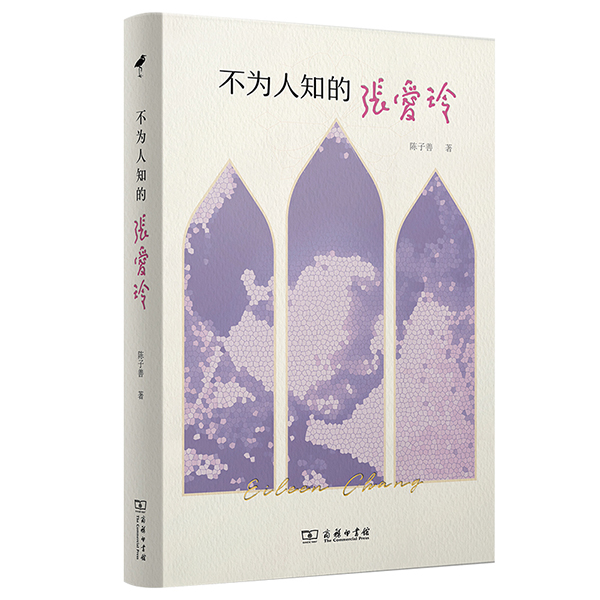
《不為人知的張愛玲》。圖片來源:主辦方提供
她更愛隱藏自己
12歲,張愛玲在當時就讀的圣瑪利亞女校校刊《鳳藻》發表“處女作”《不幸的她》,此后不斷有文字見諸報刊。曾于徐家匯藏書樓工作的張偉,借現存不多的刊登過張愛玲作品的校刊,追溯這位傳奇作家少年時期的創作往事。“現在大家看到的比較多的,是她登在《鳳藻》上的習作。但我當時在藏書樓里,注意到的是一本叫《國光》的薄薄的小冊子,她的《牛》和《霸王別姬》都登在上面。這本小型刊物由張愛玲的國文老師汪宏聲發起,他很鼓勵張的創作,盡管她只有十幾歲,足見當時女中的文學氛圍之濃厚。”
而早年的張愛玲真正引起大眾關注,還要從《天才夢》說起。這是時年19歲的她在上海《西風》月刊有獎征文活動中的一篇參賽文,最終拿了“名譽獎”,排在所有獲獎作品的末尾。陳子善提到,張愛玲并不滿意這個名次。“直至晚年的絕筆《憶<西風>》中,還在回憶此文得獎‘風波’。”
從19歲的“天才夢”,到24歲《傳奇》序言中的“出名要趁早”,張愛玲的寫作從不掩飾自己想被人看到、被人欣賞的欲望,早年的作品也絕少用筆名發表。但是隨著世事流變,張愛玲逐漸開始使用筆名隱藏自己。據陳子善的考證,“世民”、“梁京”、“范思平”、“愛珍”都是張愛玲可能使用過的筆名,且后兩個都與她的翻譯生涯有關。
張愛玲曾以“范思平”一名發表譯作《老人與海》,用“愛珍”署名在香港《中南日報》上的譯作《海底長征記》。陳子善如此解釋個中原因:“張愛玲甫到香港,對一九五零年代初的香港文壇幾乎一無所知,她不想過早亮出自己的曾毀譽參半的真名。”“毀譽參半”的原因來自張愛玲與胡蘭成的糾葛,已為當今世人熟知。
移居美國后,張愛玲自我隱藏的傾向更加顯露出來。1979年,她引好萊塢制片高爾溫的“把我包括在外”一語,婉拒臺北《聯合報》對其新近住址和工作性質的征求。陳子善則又發現了張愛玲對這句雋言的第二次引用:“當‘作家身影’攝制組擬采用更現代的技術手段以‘保存’她的影像和聲音而要求采訪她時,她再次援引‘把我包括在外’,選擇了婉拒。”張愛玲在寫信婉拒拍攝請求后的一年,就孤寂地離開了人世。

張愛玲(1920年—1995年)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善寫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
“張愛玲的作品為什么能夠得到這么多人的歡迎,也恰恰在于她沒有忘記我們人本身的存在,人的欲望,人的趣味,人和這個世界接觸后的感受。”周立民談到張愛玲作品中人本精神的重要性。“她的作品已經出版了幾十年,但卻仿佛是我們身邊的現代人,訴說著當下內心的感受。”
大家熟悉的張愛玲,多以大都市里的生活為寫作題材,在陳子善看來,這與她對待創作的謹慎不無關系,她對“真聽,真看,真感受”始終有追求。淪陷時期,她寫戰爭中備受摧殘與打擊的上海平民,而不僅僅是槍林彈雨、炮火連天;她特愛寫勞動人民,比如進城打工的女傭,描述當時年輕農村女子進城后,如何在上海這座洋氣十足的大城市里立足。
除此之外,她還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主義者。陳子善提到,早在張愛玲的時代,她就注意到了“廁所革命”,她曾在《異鄉記》中寫到農村中不堪忍受的廁所問題。“女性在農村解決排泄問題比男性難得多,張愛玲注意到了,并把它寫了出來。僅僅這一點她就比很多女作家要高明,因為這種細節往往特別感人。”
“品張的茉莉香片,看張的傳奇。”周立民如此形容這本《不為人知的張愛玲》。書的封面上,幾片深淺不一的紫色拼圖,湊成朦朧的側影。正如這位幾經浮沉、由絢爛歸于平淡、最終保留幾分神秘色彩的作家,在后世的研究中,逐漸浮現出真實鮮活的一面。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