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重走二戰滇緬公路的美國人:將壯麗故事重新注入血肉與靈魂
【編者按】
滇緬公路曾經書寫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緬、印、英、美等國人民共同付出鮮血與淚水的悲壯故事。2002年11月,受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的委托,資深撰稿人多諾萬·韋伯斯特從印度加爾各答啟程,穿越緬甸境內的熱帶叢林,再度踏上這條早已荒蕪的公路。通過沿途極為艱苦的實地考察,多方探訪當年的老兵以及修路者,韋伯斯特獲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完成了《滇緬公路:二戰“中緬印”戰場的壯麗史詩》(九州出版社,2015年9月版)。
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該書的“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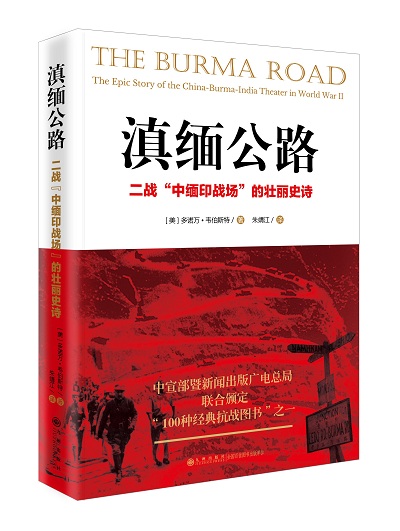
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堅信:那條在等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指引他們跋涉過陡絕的印度喜馬拉雅山埡口、深入悶熱蒸騰的緬甸叢林直至進入中國的道路,在時光的滌蕩下早已經湮滅無痕。他們毋寧說那條路本身僅僅以一場陳年的舊夢而存在著,并斷言道路如弦索般纖細的兩條軌跡——如今已有六十年的歷史——怕早就被山崩、雨浸以及沼澤般蔓延的熱帶叢林所吞噬了。
但現在,一步緊隨著一步——在一月中旬某個沁涼的早晨——我的雙腳正踏在老戰士們曾反復警告過我的同一條礫石路上。在道路兩旁叢林的墻隙之間,我仿佛穿行于上百英尺高的綠色帷幔,出發去找尋那些老戰士的戰友們陣亡的沙場,那些他們曾親身付出了血汗——或許最為重要的——那些如此深刻地烙印在生命里,以至于當他們被從午夜的噩夢中撼醒,仍可以品咂到酸澀的槍彈煙塵、仍可以感覺到叢林螞蟥在潮濕的棉布軍服下蠕動的地方。
在晨曦中,這條向前伸展的道路逶迤右轉,往復曲折地消失在另一座叢林覆蓋的山巔。而在我眼前,這一行程初始的開端——就在嘈雜的印度人聚居區利多鎮東北方幾英里開外,最早鋪成道路的礫石與柏油已然坑洼破爛。路肩風化散亂于森林的邊際,在一些路段,斑駁的孔穴橫亙于整塊路面,將一條條斷裂的傷痕留在它殘缺的身軀之上。
剛好與老戰士們所確信的相反——那條道路依然存在著。三十英尺的寬幅,它蜿蜒蛇行于藤蔓懸垂的古木林翳之下,復又仰身折向濃綠欲滴的莽莽群山。它悄然滑過印度邊防軍的哨所營房與土著部落的叢林茅舍;從它的轍印上經行的,不單有摩托以及滿載著煤炭工人的巴士,更有滿載盜伐得來的柚木的卡車——雖然這樣的砍伐在多年以前就被宣布為非法。這片文明世界的邊地是如此之遙遠,看起來沒有人會在乎這里究竟發生著什么。
周五的早晨,十點鐘光景。在我頭頂上方萬里無云的天空里,太陽正透過樹梢,將金晃晃的圓斑投映在路面上。空氣潮濕,氣溫約在65華氏度。幾縷晨霧從森林中飄溢而出,淡然的霧色將我周遭的日光柔和了下來。道路兩旁的叢樹梢頭,灰色的長尾小鸚鵡在騰挪跳躍。一輛吱嘎作響的牛車從我身邊經過,車身上緊捆著幾截柚木的樹干。一頭印度神牛就在前面不遠處的道路上游蕩:白色的毛皮,一支牛角被涂成光潔的綠色,另一支則是黃顏色的——它看上去根本無視那些拐來繞去想要躲開它的車子們。我抻了抻腰桿。喧鬧的利多鎮上,卵石鋪就的市集外邊,在“拉吉旅舍”一間帶馬桶與冷水淋浴噴頭的小房間里,我躺在膠合板床上渡過了上一個長夜。整個夜晚,當地人都出來站在旅館門外的空場上,瞪著二樓的陽臺,向我——這個陌生的到訪者——扯開嗓子問候。
“你好,美國人!”他們喊叫著。然后他們就站在碎石地面向上張望,期待我走上狹窄的陽臺,向他們揮手致意。而在小巷的另一頭,一家寒磣昏暗的餐館里,火苗在泥爐中跳躍閃爍,煨熱了咖喱,并且映照著餐館油黑煙墨的四壁。一群孩子在巷子里玩板球,也時不時地朝我喊上幾聲。在起先的半個小時里,我對樓下的歡迎人群所做出的唯一回應,僅僅是房間里那盤蚊香的一縷青煙,順著通風口散逸出去,隨它飄入茫茫的夜空。
最終,當意識到我不可能無視他們的存在,并奢望一份耳根清凈時,我走下樓梯,和一個名叫德杰拉的12歲小女孩打羽毛球。她身高大約四英尺,骨瘦如柴,烏黑發亮的頭發齊腮修剪,膚色黝黑并有一雙深深的黑眼睛,德杰拉滿面笑容地問我道:“你從哪里來?”德杰拉說,她和家里人也是才到這鎮子上不久。六個月前,他們全家剛從孟加拉搬到本地街邊的一間小房子里。她的父親之所以遷居到利多,是為了在當地煤礦找一份礦工的活計。然后,德杰拉遞給我一把弦索斷裂的球拍,我們就在小巷里一張假想的球網兩邊,上下翻飛地抽打起一枚小小的塑料羽毛球。
幾分鐘之后,我對和德杰拉一起打球表示了謝意,隨即穿過香料店的門面——也就是“拉吉旅舍”的一樓,像一只動物園里的野獸那樣被從頭到尾地打量著,返回了我那間位于二層樓上的客房。
“你好,美國人!”在我鎖緊門閂、鉆進蚊帳,并且吹滅了屋里唯一的光亮——一支蠟燭之后的好幾個小時里,那召喚我的聲音還在小巷深處回響不絕。
現在,又一個早晨,我注視著這條道路,拎起行囊繼續我的旅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架設的木頭電線與電話線桿勾勒出道路的輪廓——玻璃絕緣器依然還在原位,曾經密織的線網卻早已難覓蹤跡。回首1942年末,就在這條道路開始被美國工兵營破土修造時,沒有一位盟軍的指揮官或士兵會相信,未來的27個月里,當他們在崇山峻嶺中開巖鑿壁,抑或在沼澤濕地上夯土搭橋,以每天一英里的速度延伸這條路線的時候,日本人會寸步不舍地向他們發動致命的攻擊。還在道路完全竣工之前,日本的狙擊手與炮彈(再加上疾病和事故),就讓這條全長1100英里的道路途經的每一英里土地上,永遠倒下一名盟軍士兵。
在這條道路剛剛動工的1942–1943年,盟軍的官兵同樣也不會相信,在這場戰爭的中國–緬甸–印度戰場上,每每因戰斗而陣亡一人,就會另有十四人由于罹患(甚至死于)瘧疾、痢疾、霍亂等傳染時疫,叢林濕疹以及此前無人所知的一種名為“灌叢斑疹傷寒”的傳染病而減員。他們也決不會相信,就在這條道路完工之前,“中–緬–印戰區”最受人愛戴卻又暴躁易怒的指揮長官——美國將軍“醋喬”史迪威——將被迫離職;他們的性情乖僻卻讓部下誓死效忠的特種部隊領導人——英軍少將沃德?溫蓋特——將會在一場令人震驚的意外事件中陣亡;再有,或許也是最讓人無法接受的:他們曾浴血奮戰、拼死修筑的這條公路,甚至在它剛剛完工之際,就將被視為過時的廢物而遭到無情地丟棄。在精疲力竭地離去之前,史迪威除了靠一句蹩腳的拉丁語格言作為其最后的支撐之外,幾乎已無力回天。這句“Illegitimati non Carborundum”,被他譯作“別讓那幫混蛋把你壓垮”,成了史迪威最為著名的一句座右銘。
我跨過一條流水淙淙的陰溝,它用水泥砌成的槽床因為常年潮濕而呈棕紅的水銹色;溝底的水流絞纏如辮,淌過藤蔓懸垂的地下。這條道路曾被冠以諸多名稱——譬如利多公路、史迪威公路、匹克大道、“每英里亡一人”之路、山姆大叔高速路——但它最通行的名字卻是頗為簡單的幾個字:緬甸公路(中國一般稱之為“滇緬公路”——譯注)。盡管歷史學家們或許將其禮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為偉大的工程壯舉之一,但那些老兵們卻一次又一次地斷言:它只可躋身于現代歷史上最被人遺忘的道路之列。而最為重要的莫過于,他們寧愿相信:它仍應保持著那份孤絕的姿態。
就在前方,這條道路穿過印度阿薩姆邦,在一個名為齋蘭普爾的邊界小鎮進入阿倫納查爾?普拉代什地區。此后,它逶迤而上,盤旋在帕特凱山脈兩列海拔4000英尺的山麓之間,在班哨關翻越帕特凱山的第二高峰,最終深入緬甸境內。
我登上阿薩姆邦的最后一座山丘向下俯望,齋蘭普爾鎮低矮的棚屋散布在叢林蓊郁的山谷里。山羊與野貓四處亂竄,居民從一間茅舍游蕩到另一間茅舍——在這里大約有20來座建筑物。就在小鎮的中心,一座二戰時期留下的活動鋼便橋橫跨過泥濘的納姆齊克河,齋蘭普爾的檢查站就設置于此地。橋的跟前,道路右側,一座帶有環形走廊的黑柚木屋顯得飽經風霜,這便是哨所的安全檢查辦公室。身著咔嘰布制服、頭戴藍色貝雷帽的哨兵們坐在椅子上打盹,他們的機關槍斜倚在回廊的欄桿上。
看到我向他們走來,士兵中一個身高六英尺、鼻梁上架著一副航空太陽眼鏡的壯漢挺身站起。一群白色羽毛的小雞亂哄哄地穿過了街道。在路的左側稍稍靠后幾英尺,正對著檢查站的方向,是一座墻壁洞開的警備室,沙包堆成的防護墻后面,一挺架在底盤上的機關槍更具威嚴。一條子彈帶從擺在地上的鐵皮箱中伸出頭來,填進機槍的后膛里。隨著我步步逼近,一名原本趴在警備室陰影里的木桌上打瞌睡的機槍手,悄然轉移到他的武器身后。他伸手抓住機槍右側的槍栓,“咔咔”兩聲拉動手柄,將手指扣在了扳機上。
在這兩座房子的中間就是關卡的閘門:一根交替染成紅白兩色的長竹竿。它像一條杠桿那樣被壓低下來阻住通路;一塊大石頭被纏入繩網,綁在靠近警備室的竹竿一端,充作保持平衡的配重。
“你好!”我朝那個戴太陽鏡的哨兵打了個招呼,展顏一笑。他回報以一張冷臉。“你好。”他說,“請出示你的證件。”我將護照和簽證遞給了他。這下他笑了笑,然后就閃身消失在房間里。我可以聽到他正通過電臺向什么人呼叫。電波的頻率嘈雜混亂,在一片噪音之中,他的聲音依稀可辨:“是的,”他報告說,“沒錯,他是個美國人。”
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區迄今依然是外國人的禁足之地。其中一些地方甚至從19世紀早期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開始,就嚴禁外人到訪。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第56年,也是印度掙脫英國控制獨立以來的第54年,印度東北部終于在現代歷史上第一次緩緩地向外界開啟了門戶。與印度主體社會不同,部族體制仍然在東北部地區占有主要地位。在這一區域彼此隔絕的山谷中,至少并存著105種以上的地方語言,幾十年以來,一些勢力較大的部落為爭取他們自己的自由而與印度中央政府長期作戰。正因如此——并且以我個人的人身安全為根本理由——我未能獲得考察滇緬公路在印度境內最后十八英里所必需的“限制性區域許可證”。
我注視著在眼前奔走的雞群,用手掌摩挲著攔路門桿上的油彩。我指了指橋下二十英尺寬的混濁河流,向另一個哨兵詢問:“水里有魚嗎?”那是個小伙子,依然半躺在他的椅子里,把穿著黑皮靴的雙腳搭在門廊的欄桿上,斜挎的來復槍緊貼著他的小腹。他比那個戴墨鏡的士兵要瘦小一些,大約25歲年紀,咔嘰布軍服下面是條瘦骨嶙峋的身子。
“當然有!”他回答道,“有一次我們還見過一條大魚。”他舉起雙手,空出十八英寸左右的間隙,思忖兩手之間的距離是否恰當。
“太陽鏡”再度出現在我面前,面帶微笑:“生日快樂,韋伯斯特先生!”他說。我早就把今天是我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凈,太陽鏡一定是從我的護照上記下了這個日期。“韋伯斯特先生……”他停頓了很久,“您到這里干什么來了?”
在接下來的十分鐘里,我向“太陽鏡”解釋了我沿著全長1100英里的利多公路–緬甸公路旅行的計劃。在印度,我希望能再沿這條路上行18英里,至名為“班哨關”的山頂上抵達印度與緬甸的邊界。在那以后,我將飛去仰光,從緬甸境內再度啟程至班哨邊界。我很清楚,因為印–緬邊境恐怕是世界上把守得最為嚴密的邊界線之一,所以我不可能今天直接從印度入境緬甸。但我前往“班哨關”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知雙方的哨兵:我將會從邊境的另一側再度出現,這樣當他們在下個月又一次見到我時,就不會感到緊張慌亂。
一言以蔽之,我告訴“太陽鏡”說,我的滇緬公路之行將穿過印度的雨林與喜馬拉雅山麓的丘陵,下經緬甸低地蒸籠一樣悶熱的叢林地帶,最終攀上中國西南地區的西藏高原,在云南省昆明市結束我的旅行。我會在沿途必要的情況下徒步、搭車,或租用交通工具,但最重要地,我將尋找那些在戰爭中幸存的人們,讓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條最為漫長的戰線上所發生的壯麗故事——如今已為大多數人所淡忘——重新被注入血肉與靈魂。這段旅程將會持續三個月的時間。
“太陽鏡”又笑了笑,他以一種戲劇式的遲緩動作摘掉了臉上的墨鏡。盡管他的頭發烏黑,皮膚是印度人最為典型的深棕顏色,他的眼睛卻是令人吃驚的淺灰色——它們讓我有些心神不寧。
“我只想看一眼‘班哨關’,”我對他說,“這樣我就可以說我曾經到過那里。”我提起背包,將它靠著墻,放到門廊的條木地板上。門廊里有蔭涼,并且我意識到今天早晨的太陽已經開始火熱。“我會把我的東西放在這里,”我說,“這將是我肯定返回來的信物。”
我把手伸進褲兜里,年輕的哨兵立即警覺起來。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晃動著身體,雙腳牢牢地踩著木地板,用他的來復槍指著我。
“只是拿包香煙而已。”我說,“有誰吸煙嗎?”
我打開一包尚未開封的萬寶路香煙,將煙盒放在門廊的欄桿上。作為一種不那么昭彰的小小賄賂,這招在此前一直頗為奏效。
“太陽鏡”搖搖頭,再度一笑:“不,謝謝你。”“你是否清楚,”他接著說,“阿倫納查爾?普拉代什是旅游者行動受限制的區域?”我點點頭:“是的。”
“你是否清楚你的簽證上沒有附帶一份限制性區域許可證?”我又點了點頭。
“既然是這樣,”他說,“那么你就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了。想要進入阿倫納查爾?普拉代什地區旅行——想要經過利多公路到達‘班哨關’——你就需要辦理限制性區域許可證。如果你沒有獲得這份證件,那我也愛莫能助。我既不可能為你簽發一份,也不可能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必須把你遣送回去。”
我告訴這名士兵我曾如何與印度駐華盛頓的大使館聯絡,如何等待了足足六個月以接受取得限制性區域許可證的各項調查,以及在這半年的煎熬之后,印度使館官員卻通知我說,鑒于我以記者身份出訪印度,這份許可證恐怕還是難以到手。我對他談起使館的官員們甚至建議我來這個邊境哨卡,直接找戍守的衛兵們碰碰運氣。特別是因為我只打算在阿倫納查爾?普拉代什停留——多久?——才半天而已;不過是沿著公路走上十八英里——倘若能筆直地穿過叢林,只有區區六英里的距離。
“我很高興能在齋蘭普爾待上一段時間,為了表示我的誠意,”我指著我的背包,說道,“我已準備了一個星期的口糧:鮮咖啡、大米和豆子之類的,還有一瓶蘇格蘭威士忌。我很樂意把吊床懸掛在那邊……”我伸手指向公路另一側,警備室旁邊的兩棵樹。那廂的機槍手還在原地待命,虎視眈眈地把守在他的致命武器后面。
“太陽鏡”又在露齒微笑:“韋伯斯特先生,你盡可以待在邊界的這一側,歡迎備至。但法律是很清楚的,你不可以進入阿倫納查爾?普拉代什。沒有一份限制性區域許可證,你就不可以前往班哨。實際上,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射擊任何敢于違反該項法律的人。先將他們射倒在地,當其喪失行動能力之后,再調查他們為什么非法穿越邊界。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你明白嗎?”
我一面點著頭,一面將目光投向那條河流。我飛越了大半個世界來到這里,坐在擁擠不堪、令人筋疲力盡的汽車中在印度跋涉了六天,晚上睡在硬板床上,靠扁豆湯充饑,還要忍受本地人像看馬戲一樣注視著我的神情。而眼前——就在距“班哨關口”區區幾英里叢林旅程的地方——一排槍林彈雨豎起的圍墻卻即刻將我與我的目的地隔絕開來。
“當然,”“太陽鏡”接著說,“你也可以返回德里,再次申請一份限制性區域許可證。正如你所說的,前景并不樂觀,可能要花上幾周甚至幾個月等待被批準。但你也不妨一試。很遺憾我無法提供進一步的幫助。”
“你可以親自陪同我去班哨,”我拋出提議,在苦苦哀求的時候努力讓自己笑容燦爛,“在你今天換崗之后。我會很高興為占用你的時間而支付費用。我這么不遠萬里地跑過來,在離目的地這么近的地方被攔住,未免太令人沮喪。”“不行。”他說,“法律規定得很清楚。我再說一遍,我很遺憾。”
在檢查站的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木板棚子,看來是一家與哨所衛兵長期共存、相伴相生的飯館兼雜貨鋪。“太陽鏡”朝那房子的方向喊了一聲,他走到門廊邊上,伸長脖子四下張望,直到看見棚子里木頭板凳上坐著的一個小個子男人。“太陽鏡”用地方土話交代了幾句,那個男人站起身來,走到了店鋪柜臺的后面。一位當地納迦部落的老婦人向鋪子門外窺望了幾眼,在她的臉上,自發際線往下經過雙眼以及鼻翼兩側鑲嵌的黑色小紐扣之間,都刺有暗藍色的線紋。我向她揮了揮手,她卻慌忙躲進了屋里。
“太陽鏡”轉身面向我,“請你理解,韋伯斯特先生,這些法規不能違犯。本地走私猖獗,叛亂分子眾多。這些法律之所以存在確乎有著充分的理由。我并不樂意下命令向你射擊,但那就是法律。”他居然還在笑著。
“現在,”他繼續說,“我為咱們點了壺茶。你的茶里想加些牛奶,糖,還是二者都要?”“都要。”我說。“太陽鏡”朝雜貨鋪里的男人又喊了起來,而我將脖子伸出門廊另一側的圍欄,試圖讓目光穿過小鎮、掠過山谷,一直望到班哨關口。我目光所及只有連綿的叢林與山巒。甚至那條路在拐過第一道彎之后也消失匿跡了。這糟糕透頂的十八英里啊!
茶送來了。我們在門廊里找到兩把椅子坐下,然后又多聊了幾句,這只是更加深了我的挫折感。幾分鐘之前,這個家伙還以一種毫不含糊的口氣告訴我,如果我不照他說的去做,他就會一槍斃了我。現在他卻端給我茶水和淡黃色的糖果茶點,而我則把我妻子、孩子們的照片拿給他看。
或許那些老戰士們是對的。或許我的確不應該前來找尋這條道路。不管怎樣,我眼前的情形都越來越帶有一種超現實的色彩,它的彬彬有禮幾乎不能掩飾“太陽鏡”所暗示的生命威脅。小口地品著茶,我終于理會到:倘若我拔腿往“班哨關”的方向跑去,他們真的會在我生日的這一天,把我亂槍撂倒在這破爛的街頭。槍彈抑或是友誼?阻撓抑或是協助?前行的通路被堵死,但我又極不情愿轉身后退。而爭論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無論如何,進一步談判的可行性被這種邊疆風味的茶道表演徹底扼殺了。
終于,坐在塵灰滿布的門廊陰影里,當我的沮喪與絕望在晌午蒸騰的悶熱中幾乎達到極限時,我忽然破顏一笑。我意識到,較之這世界上其他任何人,唯有史迪威最能理解我此時的心境。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