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青椒”生存調查:85%不是上海人,自認社會地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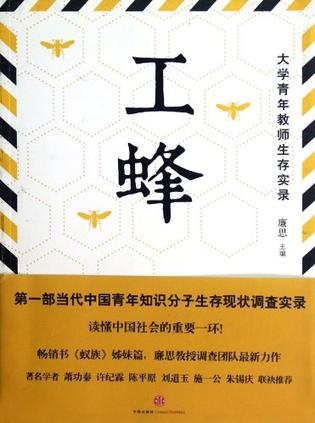
2012年一篇取名為《工蜂》的調查報告引起了全社會對于高校青年教師生存狀況的關注,一時間被稱之為“青椒”的高校青年教師成為“一高二低”(即高學歷、低收入、低生活質量)的代名詞。高校青年教師是一個什么樣的群體?他們的收入、工作以及生活真的像網上流傳的那樣嗎?
去年,受上海市社聯委托,由上海東方青年學社和華東師范大學共同組成課題組進行調查。課題組抽取了年齡在45歲以下,本科學歷以上,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從事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的人員,把這部分人員稱為“青年社科工作者”。調查范圍涉及上海的15個單位,其中包括4所“985”高校,5所“211”高校,4所普通高校,2所研究機構,共獲得有效問卷1528份。課題組試圖通過這次實證調查來真實地揭示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生存與發展狀況。
婚姻:超八成已婚,未婚率低于全國水平。本次調查對象年齡最小的為23歲,最大的為45歲,平均年齡為36.3歲;男性占50.8%,女性占49.2%。“已婚”的青年社科工作者占到了總人數的83.2%,其中男性的已婚率達到84.5%,女性的已婚率也達到82.1%。與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調查資料相比,同年齡段青年社科工作者14.8%的未婚率遠低于全國18.5%的整體水平。
學歷:八成青年社科工作者擁有博士學位。本次調查中擁有博士學位的被訪者占到了總人數的80.9%,教育程度為碩士的占總人數的18.2%,僅有0.8%的被訪者為大學本科。在所有擁有博士學位的青年社科工作者中,59.4%畢業于“985”高校,15.6%畢業于“211”高校,13.6%畢業于海外名校,3.3%畢業于海外一般學校。相比較外省市同類單位,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總體學歷水平較高。
職稱:從講師到教授呈現出了“541”的格局,晉職之路較為艱難。被訪者為講師(中級職稱)的占總人數的48.7%,副教授(副高)占39.0%,教授(正高)占8.5%,助教為1.9%。從職稱結構上來說,呈現出了“541”的格局。但這種格局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青年社科工作者的職稱晉升之路比較艱難,副高和中級職稱的人數比例積壓太多。
來源:85%為非上海“土著”,主要成長于中小城市、城鎮或農村。被訪者是上海“土著”的僅占總人數的15.1%。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出生地為外地中小城市的比例最大,占總人數的25.8%,其次為外地農村(19.8%)、外地縣城或城鎮(19.6%)、外地大城市與省會(16.2%)、其他直轄市(3.9%)。84.9%的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來源于上海以外的其他省市區,而超過6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青少年成長地為上海以外中小城市、城鎮以及農村。
信仰:七成以上為中共黨員,96%無宗教信仰。從政治信仰來說,黨員占總數的72.8%,比例遠高于上海市級機關61%的黨員比例。有16.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為無黨派,5.8%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為民主黨派。另外還有1.7%的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政治面貌為共青團員。從宗教信仰來說,無宗教信仰占到了總人數的95.9%。宗教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比例為2.0%,信仰基督教為1.6%。
國際化水平:四成以上有過留學經歷,但國際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隨著近些年國家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師生出國攻讀學位以及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有留學經歷人員在青年社科工作者中的比例較高,總共有43.3%的青年社科工作者有過各種形式的一年以上的國外學習或工作經歷。不過從國際化的比例來看,身份屬地為中國大陸的占總數的99.4%,中國港澳臺地區的人數占總數的0.4%,而其他國家的人數僅占總數的0.2%。可見,雖然近幾年從海外引進的學者以及留學歸國人員的比例在不斷增加,但是直接從境外到上海來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員比例較低,國際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
社會地位自我評價:呈現出低認同與內部分化的特征。從社會地位自我評價來看,1分最低10分最高。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總體平均得分為5.23,明顯低于2013年我們在上海市區對普通上海市民調查時7.56的平均得分。從高校類型來看,“985”高校內受訪者評價最高為5.43,而普通高校只有4.95;從職稱來看,教授(正高)的自我評價最高為5.75,而講師(中級職稱)只有4.99。在高校類型和職稱上呈現出明顯的分化。
職稱、單位和學科:內部分化和外部落差的收入格局
20世紀90年代之后,高校和科研機構經歷了市場化改革,工作人員的單位收入被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基本工資,主要由政府財政承擔;二是績效工資,主要由高校自行負擔。這樣就造成了不同的單位、院系內部以及不同職稱存在較大的差異和分化。
從不同單位的收入來看,“985”高校46.5%的受訪者年收入在8萬元以下,“211”高校的這一比例為43.3%,地方院校為24.2%,黨校和社科院分別為45.1%和73.0%。結果顯示,部屬高校青年社科工作者的收入普遍比上海地方高校低,而黨校和社科院的收入則更低。
從不同學科來看,受到學科與市場關系親疏程度的影響,不同學科之間有著明顯的收入差異。人文類學科有45.4%的受訪者年收入在8萬元以下,社科類的比例為42.3%,經濟管理類為22.0%。可見,學科的市場化、社會化越強,收入越高,反之則越低。比如,經濟管理類收入遠高于其他學科,基礎類學科如哲學、歷史等面向社會和市場的機會更少,收入則更低。
從不同職稱來看,教授(正高)中年收入低于8萬元的占9.1%,副教授(副高)的為28.6%,講師(中級職稱)的為53.9%。調查數據顯示,講師收入主要集中在年薪6-8萬區間,副教授則是在10-12萬之間,而教授則處在12-18萬之間,也就是說副教授的收入是講師的1.5倍,教授則是講師的2倍。
綜上所述,相比較上海公務員以及國有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的收入來說青年社科工作者總體收入不高,但是內部的差異較大。收入的高低除了要看職稱高低以外,還要看在哪一類高校以及什么學科工作。“窮教授,富講師”也是普遍存在的。
重科研、輕教學:科研成果往往決定了青年社科人才的生存與發展狀況
毋庸置疑,當前,科研實力是對高校和科研機構綜合實力評估的最為重要的指標。在各種評估體系和學科、機構排名的指標化壓力之下,高校和科研機構幾乎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科研,從而導致一定程度上對教學的忽視。這主要體現在:
職稱低完成的教學量更多。受訪者平均每周要完成9.36學時的教學工作量(每學時45分鐘),職稱越低,每周的教學工作量越大。相比較而言,教授平均授課時數為8.52,副教授為9.09,講師則為9.71,助教為12.03。不同類型的高校中,普通高校的課時數最高,為10.77,“211”高校為9.65,“985”高校相對較少,為8.57。工作年限與教學工作量沒有直接相關性,也就是說并不是入校時間越短教師承擔的教學工作量越多。
這主要的原因是教學在高校和科研單位中主要體現為工作量的完成。另外入校時間短并不意味著職稱低,一部分受訪者有可能是被當作教授或副教授直接引進的。數據顯示,促使被訪者對于教學投入的最主要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責任心(37.1%),第二位是工作量考核(22.2%),學生是否投入排第三(17.0%),個人興趣則居第四(14.4%)。這樣就可以解釋,盡管職稱越低完成課時越多,但是不同職稱課時差并不大,教授只要完成基本的工作量,其他工作量考核可以論文和課題來充抵,而職稱較低者則會更加傾向于通過多上課來充抵工作量。
收入與科研成果數量及質量成正比。科研成果是職稱評審的硬性條件,不僅如此,它也是拉開個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目前,各高校和科研機構普遍都設有對重要科研成果的獎勵政策,有些人的年度科研獎金甚至遠遠超過一年的單位總收入。而對于教學而言,僅有的獎勵一般只是蜻蜓點水式的。
調查顯示,如果將完成課時工作量及在國外核心期刊和國內核心期刊發表論文數量排名前10%的青年社科工作者進行比較,課時工作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萬以下占六成五,收入在12萬以上為一成五(其中18萬以上近1.9%);而國外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量排名前10%的收入在10萬以下不到四成,收入在12萬以上近四成(其中18萬以上20.5%);中文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數量前10%的收入在10萬以下占五成,收入在12萬以上近三成(其中18萬以上7.8%)。可見,科研成果越多,成果層次越高,收入就越多。
科研成果和科研項目:職稱晉升的兩座大山。在高校和科研機構中,職稱晉升是最重要的個人發展路徑。從調查數據來看,影響職稱晉升排在前五的因素分別是:論文、著作難發表是最主要原因,選擇此項的被訪者占到總人數的76.5%;科研項目申請次之,占總人數的52.1%;此外,把“科研時間不夠”“各種事務太多”“職稱評定標準太高”列為職務晉升的困難因素,分別占總人數的45.1%、40.1%和35.4%。
綜上所述,相比較科研,教學考核主要體現在工作量的完成,但是教學的質量以及學生的培養則顯得不太重要。科研,特別是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以及高級別的科研項目,成為高校教師們工作的核心,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未來發展。
未來的不確定與工作擠壓下的日常生活壓力大
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教學與科研人員盡管不需要像政府、企業部門朝九晚五上班,時間的支配大多較為自由,表面上令人羨慕,實際上他們受到來自科研、課題、晉升以及經濟收入上的多重壓力,自由支配時間主要用于科研和教學準備,這客觀上擠壓了他們正常的生活,作息時間不固定,心理壓力較大,日常生活質量反而較為低下。這表現在:
睡眠時間短,休閑時間少。總體上,受訪者日常的睡眠時間都少于6小時,職稱越高,工作日睡眠時間越少,日常休閑時間都少于2小時,職稱為副教授休閑時間最少僅為1.37小時。節假日睡眠時間雖然有一定程度提高,但仍然在6小時左右徘徊,教授(正高)睡眠時間為5.95小時,副教授(副高)為5.81小時,講師為6.20小時。節假日休閑時間提高的幅度較高,講師職稱受訪者達到2.73小時,副教授(副高)為2.40小時,教授(正高)為2.25小時。總體來說,無論是工作日還是節假日,職稱越高,休息時間越少。
職稱越低,情緒、心理方面的壓力越大。對于受訪者心理方面的指標測試(1為最低,5為最高),調查數據反映出了職稱越低,壓力反而越大,也就是說心理壓力更多的來自于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收入、考核、職稱這些都成為心理困擾的主要來源,而職稱越低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憂慮就越強,心理壓力自然越大。可見,雖然職稱越高,休息和休閑時間越少,但在情緒和心理壓力方面反而是職稱越低壓力越大。
目前中國以外的高校主要有英美體制以及歐洲體制兩種,前者實行“非升即走”,在聘期內給予較高的待遇,未獲終生教職者課時量較少,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另一種歐洲體制,主要采用學術共同體評價機制,不存在所謂的核心期刊,研究的質量由同行評判,雖然待遇不高,但是享有較好的國家福利,工作較為穩定。
對于中國的高校來說,目前正在逐步走向英美體制,也就是打破原來的“鐵飯碗”,許多高校已經不給予應屆畢業生固定崗位,而是采用師資博士后的方式,除了入校時進行面試以外,還要在聘期內接受科研完成情況的考核。另外,還有的高校也開始實行“非升即走”,這個“走”并不一定是離開學校,也可以轉做行政。
不過在高校教師基本工資還普遍低于政府機關的公務員和國有大中型企業專業技術人員工資水平的情況下,高校對于人才的吸引力在不斷下降,人員也在不斷流失。因此,如果不能夠保證較高收入,“非升即走”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英美體制并不是最好的辦法。相比之下,歐洲體制雖然在效率上比不上英美體制,但是對于人才穩定性以及考核和評價體系上更加人性化,從某種程度上說,可能更有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長。
(調查過程中,接受調查的15個單位的科研管理機構給予了大力支持。同時,華東師范大學的吳越菲、方筱、顧楚丹、吳曉凱等諸位社會學專業的研究生在數據處理方面也給予了大力支持。)
本文轉自《社會科學報》,原題: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基本狀況調查——在生存與發展之間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