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社論】紀念那些“能思想的葦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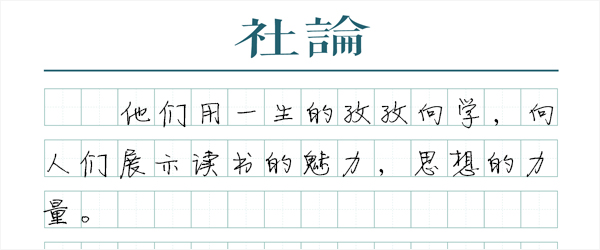
雙星隕落,5月28日,著名歷史學家何兆武、章開沅相繼離世。
相對于人們熟稔的、不久前逝世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中國肝膽外科學之父”吳孟超院士的成就,向普通讀者解釋兩位文科大師的功業(yè),著實有一些困難。甚至在這個功利時代里,當人文學科整體被邊緣化,了解文科大師就更為困難,因為困難,所以更有意義。
思想不能烤面包,文科有什么用?“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于思想……”何兆武在自己的隨筆集《葦草集》引用過這句話。
商務印書館那套《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何先生翻譯的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赫然在列,滋養(yǎng)了中國整整幾代學人。
何兆武的筆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引來天上的火種,成就文章不朽之盛業(yè),也將常識變成日常:理性、自由、獨立思考等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精神資源,卻是史上那些思想巨匠為我們爭取到的。
當下,學術考核KPI日益工業(yè)化,人文學科的內核被算績效、報項目的“學術勞工化”所擠占,甚至,當個別文科教授也公然宣稱“自己從不看書”,只“看文獻”時,回顧大師們的生平言行,更像是接受一場人文精神的洗禮。
何兆武先生畢業(yè)于西南聯合大學,讀了4個系,從建筑系讀到了歷史系。何先生把西南聯大“無問西東”的成就歸結為自由。他晚年在《上學記》里倡導著自由自在地閱讀,堅持讀那些“無用的書”:“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fā)展,就沒有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那種“不為什么”的讀書,才是讀書人該有的樣子。
另一位仙逝的大師章開沅先生,是著名中國近代史大家,他在辛亥革命研究、張謇研究、商會研究、貝德士與南京大屠殺研究等學術領域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他還曾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但先生的本色還是書生。章開沅先生身體力行地破除學術“終身制”,他數次請辭“資深教授”,把“位子”讓出來,給更多學者機會。
章先生作為史學大家,關注于新史料的挖掘,也有著強烈的社會關懷,提出“參與史學”“歷史社會土壤學”,他通過“重新發(fā)現”張謇,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轉型梳理發(fā)展脈絡,尋找本土資源。
文科大師不能提供糧食,不能解除病痛,但他們卻用一生的孜孜矻矻,向人們展示讀書的魅力,思想的力量。人文大師們的觀點、著作可能會過時,但是光啟后人、賡續(xù)人文的情懷,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寶庫中的重要資源。
這是我們紀念人文大師的理由,這是個不成為理由的“理由”,一如我們讀書本就不需要“理由”。
“能夠在思想里找到安慰,我以為,就足夠了。”何兆武先生如是說。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