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董少新談西文明清史文獻: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與中外關系史
本文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近期在南開大學所做的主題演講——“歷史文獻與研究視野:西文明清史文獻漫談”的內容,限于篇幅,分上下篇推出,本文為下篇,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西文文獻與中外關系史研究框架的突破
中外關系史在我國的學科體系當中,屬于中國史一級學科下的專門史二級學科中的中外關系史方向,就是這樣一個地位。而且傳統的中外關系史往往表現為雙邊關系,也就是中國與某一國家關系的歷史。比如說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英關系、中印關系等。開學術會議的時候,中日關系史的研討會我們看不到研究中英關系的學者;中美關系史研討會我們也看不到研究中印關系史的學者。這樣的雙邊關系史的研究框架,當然是很重要。開會相互之間都是涇渭分明的,這樣的現象也是很正常。但是歷史的真實情況往往比這種涇渭分明的劃分要復雜得多。例如當下的中美關系,不僅與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世界關系密切的,而且與韓國、日本、東南亞乃至印度、西亞、俄羅斯都有密切的關系。也就是說你研究現在的中美關系,你要考察很多復雜的關系,比如說伊朗問題、朝鮮問題,都是中美關系的重要內容。歷史上的情況大概也是這樣,只不過程度上未必是如此的緊密,但是大概性質上是一樣的。我接下來就舉幾個例子,目的是從中外關系視野的角度來談談引入西文文獻的必要性,并且進一步說明突破雙邊關系史的框架,在區域史的框架下研究中外關系史的意義。
第一個例子是16世紀中日關系中的葡萄牙。16世紀的中日關系,先后由于爭貢之役、倭寇問題,特別是壬辰倭亂而跌入谷底,乃至徹底中斷。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16世紀,中國實施稅制改革,大大增加了對白銀的需求,而日本則在16世紀發現了銀見山銀礦,并開始大量開采,這些日本白銀很大一部分流入了中國。那么這些日本的白銀是怎樣流入到中國的?這是因為中日之間出現了中間商,這個中間商便是從歐洲大西洋東岸來的葡萄牙人。有的日本學者認為葡萄牙人的東來時機不好,因為正趕上東亞區域時局動蕩。我在一篇小論文中反駁了這一觀點,認為葡萄牙人的出現正逢其時。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1571年他們又入居長崎,這正是得益于中日關系的緊張同時又相互需要。葡萄牙人經營的中日間貿易,從澳門到長崎,其利潤是當時葡萄牙人所經營的所有貿易線路中最高的,澳門和長崎在16世紀最后25年進入黃金時代,迅速發展成為頗具規模的港口城市。一些葡萄牙人已經“夢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鄉作故鄉”了,在澳門、長崎娶妻生子,建立房屋,不想返回葡萄牙了。而隨著葡萄牙人經營中日間貿易,倭寇問題也隨之基本消失了。所以研究16世紀至17世紀前期的中日關系,特別是中日貿易關系,需要使用大量葡萄牙文資料,這并不是一個奇怪的提法,而是歷史事實的要求。事實上有關16世紀中日關系的葡萄牙文文獻可能超出我們的想象。最近有學者在大英圖書館發現一份葡萄牙文報告,是關于壬辰戰爭的。我感覺這份報告很重要,但很遺憾由于疫情關系,我還沒有機會寓目。
第二個例子是17世紀中荷關系中的日本。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后,迅速走上海外擴張道路,其所宣揚的“自由海洋論”,主要針對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壟斷。在東亞海域,荷蘭人到來后對葡萄牙勢力發動一系列攻擊,而這些海上戰爭可以被視為荷蘭與西班牙戰爭在亞洲海域的延續。從1601年至1622年,荷蘭人多次襲擊澳門,均未成功,隨后他們占據了臺灣。1633-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發布了一系列所謂的“鎖國令”,針對的也是葡萄牙人,從而使荷蘭人取代葡萄牙人,占據長崎的出島,開展長崎-臺灣-福建之間的貿易,而這一貿易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李旦、鄭芝龍等海上勢力。1619年荷蘭人占據巴達維亞,1641年占據馬六甲,導致葡萄牙人在東亞海域的勢力進一步萎縮。

荷蘭東印度公司
而對葡萄牙人進一步的打擊是明清易代期間幾近斷絕的中外貿易。荷蘭雖然向順治朝廷派遣了使節,但也只得到了八年一貢的答復。在無法從中國購買瓷器、絲綢等商品的情況下,荷蘭人在日本尋找替代品,這直接推動了日本有田瓷器生產的迅速發展,伊萬里瓷器也在17世紀中后期一度取代中國瓷器,熱銷歐洲市場。直到清朝在1684年重新開海后,中國瓷器在國際市場上才逐漸重新占據優勢。有趣的是,為了適應歐洲市場的品味,中國在開海后曾有一段時間仿制伊萬里瓷器。更有趣的是,伊萬里瓷器是長慶之役日本抓獲的朝鮮陶工李參平在有田創燒的,而且采用了中國的赤繪技法。伊萬里瓷器從產生到暢銷歐洲再到中國仿制,這樣涉及整個東亞海域乃至跨越亞歐大陸貿易的歷史,在任何雙邊關系的框架下都難以展現,而記錄這一歷史的文獻,除了日文、韓文、中文之外,我推測最豐富的應該是荷蘭文。我為什么這里加一個“推測”,因為我很遺憾不會荷蘭文,為什么很遺憾呢?我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學習,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曾跟我說小董你過來,我提供獎學金給你來學習兩年荷蘭文。那個時候我剛剛從臺灣做博士后回到文史研究院,葛兆光院長還真幫我到學校去講了這個事情,但按照學校規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荷語夢斷,沒有學成。這是個題外話。
第三個例子我想講一下作為整體的東亞耶穌會史。日本天主教史和中國天主教史基本上是涇渭分明的兩群學者在研究。但歷史的事實是,在1618年之前,在耶穌會的傳教區劃分中,中國教區屬于耶穌會日本教省,直到1622年才正式從日本教省分離出來,成立了耶穌會中國副省。但是即使在此之后,兩廣、海南則一直屬于日本教省的范圍,即使到了日本徹底禁教后仍是如此。因此,如果完全用國別史的框架來研究天主教在中國或在日本的傳播史,就會造成一些割裂的現象。耶穌會和東印度公司是最早的全球化組織,一個全球傳教,一個全球貿易。研究這樣的全球性組織,即使不用更為宏觀的全球視野,區域性的視野也是有必要的。以下舉幾個小例子,來說明用東亞區域視角研究天主教傳播史的必要性。
一是從文獻的樣貌上來講,我剛才提到的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藏《耶穌會士在亞洲》系列文獻,共計61卷,大體上分為中國、日本和安南三個部分,但由于耶穌會在遠東傳教的組織架構,有關中國廣東、海南傳教的資料,需要在日本的部分中查找,而且很多文獻其實是混在一起的。例如我這半年上葡文手稿識讀課,主要研究一份明清易代的葡萄牙文報告,但這份幾十頁的報告的附錄部分,就是一份澳門葡萄牙人派遣赴日本使節的報告,一個中國文獻里面,附了一個重要的日本文獻。
二是日本教省和中國副省之間有著較為頻繁的人員往來,比如利瑪竇晚年陪伴于其身邊的游文輝修士,就是在日本耶穌會藝術學校接受繪畫培訓的;又如曾參與葡兵來華和登州保衛戰的葡萄牙耶穌會士陸若漢,在此前曾長期在日本活動。更重要的是,耶穌會專門設立了日本—中國巡按使一職,負責巡視日本和中國傳教區的教務、制定傳教策略,這個巡按使就像欽差大臣一樣,其位階高于日本教省會長和中國副省會長。擔任這一職位的最著名的耶穌會士就是對遠東傳教產生重大影響的意大利人范禮安。
三是在華耶穌會士有時候會參與到中日貿易當中去。那時候大帆船很多倉位,商人會給耶穌會士留幾個倉位,耶穌會士去投錢,買一些絲綢、茶葉、瓷器之類的貨物,塞滿這些倉位,然后賣到日本去,賺了錢用于發展教務。有的時候他們是跟中國教徒借貸。
四是利瑪竇最著名的一本書《天主實義》,這一本書出版后,傳播到朝鮮、日本和越南。所以這個文本本身就是一個東亞的區域文本。他的《坤輿萬國全圖》也傳到朝鮮和日本,也是一個東亞文本。因此我們最好還是用區域史視野來研究這樣的歷史。
以上例子說明,從16世紀開始,東亞海域由于西方人的到來而發生劇變,一方面局面變得更為復雜,另一方面東亞海域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了,而且這一區域已成為世界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我們用東亞海域這樣的區域史視野來研究明清時期的中國史,而在這樣的視野和框架之下,中國史研究的史料范圍中必須納入西文史料。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
近年來,隨著全球史的盛行,把中國歷史放在全球史脈絡中的呼聲也越來越高。但是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其實很不容易。大家也都是喊一喊口號,我們很少看到這樣一部比較成熟的作品出來。那么西文文獻是否有助于我們在全球史的視野中研究中國史呢?這是我今天想嘗試探討的第四個方面。
以全球史的視野研究中國史,不應是一個單純的口號,而是歷史事實的要求,因為從16世紀以后,中國與整個世界便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而且這種關系變得越來越密切。中國史不僅僅是中國疆域內的歷史,也不僅包括中國本土和邊疆,而應涵蓋一切與中國人或中國文化有關的內容,不論這些內容發生在中國境內,還是發生在中國境外。西方對中國商品的消費,對中國文化的關注與討論,這些較少見于中文資料記載的內容,不應被排除在中國史研究之外。
同時代的歐洲,也同樣開始了與世界聯成一體的過程。以往我們強調歐洲在世界走向一體化過程中的主動性,以及中國如何被動地進入世界,但我們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即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是被需求的對象,中國的物質與文化成為西方進入世界的動因之一,是我們吸引了他們進入世界。中國是世界網絡形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和評價16世紀以來中國在世界史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這就需要關注“他者”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西文文獻的目標讀者是歐洲人而非中國人,但完整地呈現了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和觀念,以及這些看法和觀念的演變,為我們研究他者眼中的中國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英國學者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已在這方面做了嘗試,可參見其《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常紹民、明毅譯,中華書局,2005年)。
16—18世紀間,有關中國的西文文獻數量,雖然與中文文獻的數量無法比,但若將這一時期有關歐洲的中文文獻與有關中國的西文文獻進行對比,便不難發現,在數量上后者遠超前者,在內容和類別上后者更為全面、豐富。這也表明,歐洲人認識中國的興趣比中國人認識歐洲的興趣更為濃厚,且更加全面和深入,傳入歐洲的中國信息要比傳入中國的歐洲信息多得多。
作為信息流動中心的歐洲,同時被世界各地文化、信息影響。美國學者拉赫的九卷本《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系統梳理了記載亞洲信息的歐語文獻,但還沒有全面分析這些文獻在歐洲到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這本來是他研究的重要目標,但他年齡太大了,前面鋪得太開,沒時間寫。這是學界應該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歐洲近代化進程有橫向因素,不能僅從歐洲自身的歷史淵源尋找歐洲崛起的原因。以往我們都縱向分析,將歐洲近代崛起的原因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這恐怕只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臆想。事實上,兩千年前的事情跟近代真的有這么大的關系么?殖民主義擴張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彭慕蘭《大分流》認為,歐洲通過殖民將美洲塑造成歐洲的新邊陲,這是歐洲崛起的重要原因。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講亞洲固有的且是世界中樞的體系,歐洲人東來是加入這個已存在的體系,并且將其以武力破壞,建立起受歐洲控制的體系。亞洲固有的體系本來是和平的,中國和印度人、穆斯林之間甚少發生戰爭,歐洲人來后一言不合就開炮。《白銀資本》《大分流》都突出了中國乃至亞洲在近代早期世界中的地位,但如果他們能夠使用更豐富的西文原始文獻(他們其實使用很少,更多的是使用中文文獻對中國經濟體進行量化),其論述將更為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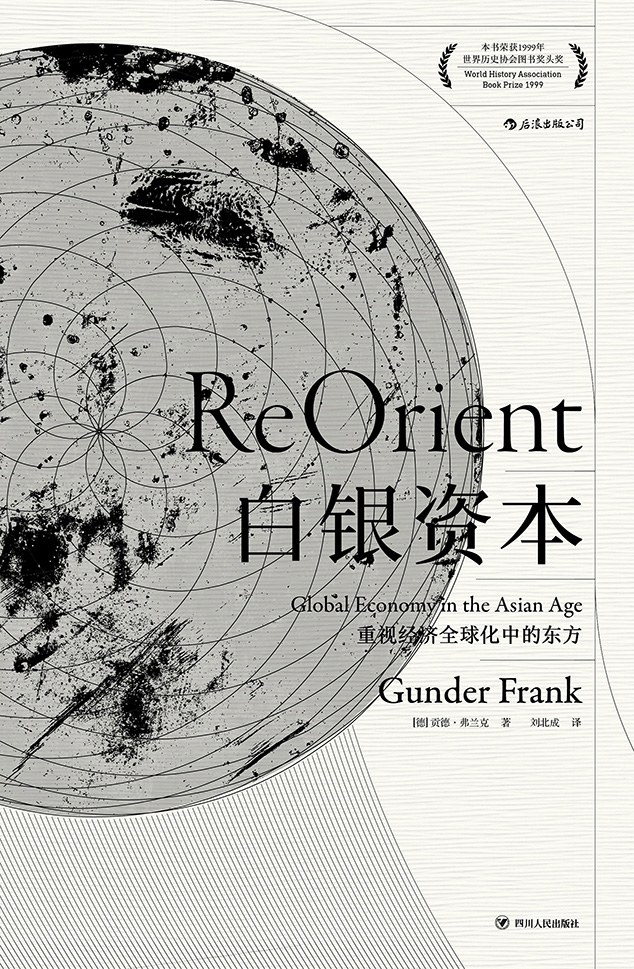
《白銀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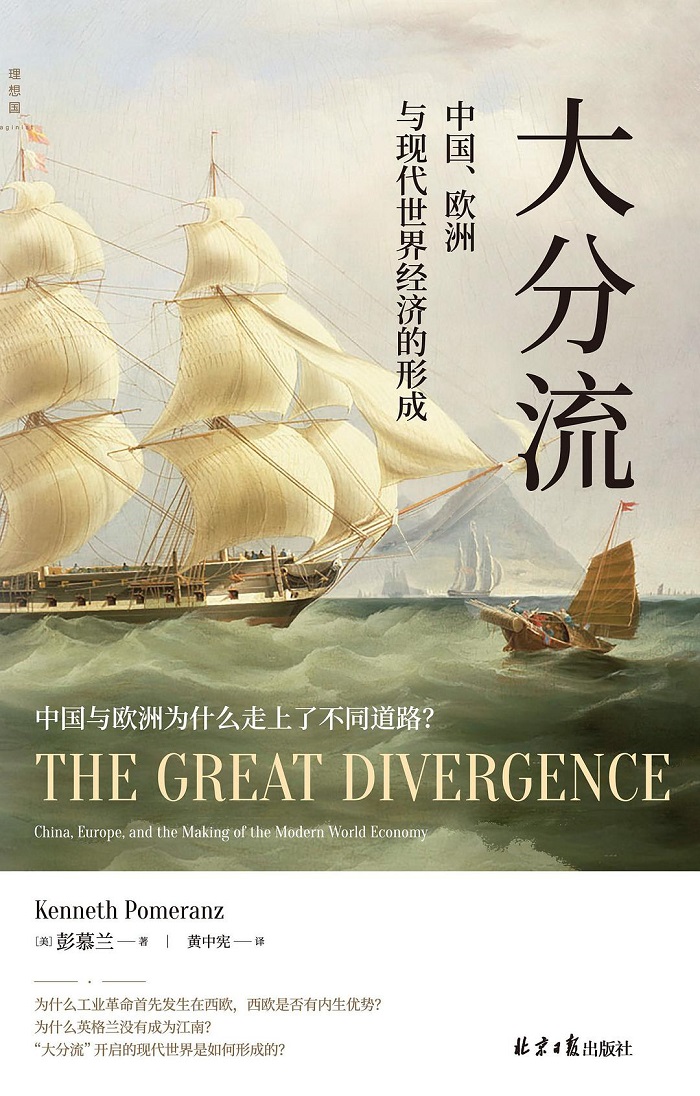
《大分流》
19世紀歐洲中心論盛行,影響深遠,認為中國是閉關鎖國的,是停滯的,是循環而沒有歷史的,生產方式是亞細亞式的。如果我們仔細看16—18世紀有關中國的西文文獻,會發現根本不存在這樣的論調。我舉一個例子,比如康熙說,我如果派100個喇嘛或道士到羅馬、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傳播佛教、道教,會怎么樣?我們想想,當時的歐洲情況,這些喇嘛、道士去了歐洲會是什么結局?基督教作為一神教,其排他性是非常強的。另一方面中國閉關鎖國嗎?歐洲開放嗎?奉行自由貿易嗎?當葡萄牙在澳門設立一個商業據點的時候,如果嘉靖皇帝隨后派一支艦隊到里斯本要求租一塊地貿易會怎么樣?他們的海洋自由是有前提的,就是我壟斷下的海洋自由,你壟斷就是不自由。
研究明清時期的中國歷史,一個重要的課題是研究中國在現代世界體系形成中的作用。這樣的課題,僅用中文史料或包括滿文資料在內的本土資料來研究是肯定不夠的,必須以全球史的視野,全面梳理中西文獻,作綜合研究。所以我們現在把西文史料全部引入進來,好好觀察這樣一段歷史。用西文文獻來批評歐洲中心論,這個才更加有效。
最后,談談我個人對學術界的期盼,也包括對同學們的期盼。
首先,要努力去構建西文中國史料學,納西文史料入中國史的史料體系當中,不能再忽視它。其實也可以納西文史料入日本史、印度史、朝鮮史,都是一樣的道理。盡可能掌握歐洲語言,還要能讀他們的手稿。同學們,現在大家是大學生,有時間趕緊去學英語之外的第二、第三門外語,然后他高高在上、趾高氣揚地歐洲中心論的時候,你就可以用西文史料來批他,跟他說你覺得事實上不是這樣。
其次,除了語言工具之外,還要掌握一批文獻,所謂的掌握就是你很熟,就像我有兩套安身立命的文獻,你要掌握這樣的一批文獻,使其成為你的根據地,你的堡壘,你的看家本領,你的學術根基,你的學術特色。我學葡萄牙語的那個時候,懂得葡萄牙語、能夠用葡萄牙文獻做歷史研究的中國學者很少,這也是我能夠順利在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找到工作的原因,我想主要是拜這個所賜。一些老先生或大教授說,小董我知道,他會點葡萄牙語,都是這樣的一個印象,我才有了進入了大學謀得一個差事的機會。所以你們也是,現在還有時間,趕緊去學,學一門獨門絕技,你會別人不會,或者很少人會,你就有特色,你被替代的可能性就比較小。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