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網紅電商時代的“如涵啟示錄”
如涵的故事沒能繼續打動資本市場。
近日,“中國網紅經濟第一股”如涵控股宣布完成私有化,從納斯達克退市,此時距離其2019年4月3日敲鐘上市,才不過兩年。
這樣的結局早有預兆。如涵的發行價為每股12.5美元,預計發行規模1.25億美元,但上市首日,如涵就遭遇破發,股價大跌37%,市值蒸發近四億美元。隨后如涵的股價一路走低,2020年10月30日,如涵股價來到了歷史最低水平,當天收盤價為2.34美元,較發行價跌幅逾80%。
如涵最后私有化價格為每股3.5美元,此時如涵的市值已經不足3億美元。根據公告,如涵創始人馮敏、孫雷和沈超組成的財團成立用于交易并購的母公司RUNION holding,其子公司RUNION Mergersub Limited如如涵合并,完成私有化。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持股15%的張大奕并沒有出現在收購的隊伍里。這位和如涵捆綁在一起的初代“淘寶第一網紅”,正在從如涵的核心體系中逐漸淡出。
如涵的成長史是一部“中國網紅經濟簡史”,它的每一次轉折,都踏著中國網紅經濟崛起的巨浪。結果表明,“如涵模式”并不是網紅經濟的“正確答案”,但它的發展對今天的MCN機構,依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1
“開拓者”和“逆行者”
2011年,在遍地紡織廠的杭州,陳思佳和丈夫馮敏開了一個名為莉貝琳的淘寶店,這是如涵的前身。2012年,正在苦于找不到模特的陳思佳被招商銀行廣告上笑容甜美的張大奕吸引,決定簽下張大奕做店鋪的專屬模特。
2014年,馮敏看準網紅經濟之后,便邀請當時已經依靠分享穿搭經驗成為時尚KOL的張大奕成為合伙人,那時她在新浪微博上擁有30萬粉絲。馮敏幫助其開設網店“吾歡喜的衣櫥”并設計營銷計劃——通過當時迅速崛起的微博為淘寶店引流。這種依附社交媒體“粉圈”實現流量變現的方式在當時可謂“先進”,張大奕淘寶店的銷量迅速攀升。而馮敏也開始幾年后才被人們熟悉的MCN業務。
2015年,如涵控股成立,開始“MCN+電商+供應鏈”的經營模式。這一年,如涵便拿到了1200萬人民幣的投資,開始擴大業務規模。
2016年,如涵在北京和杭州設立了紅人學院,孵化網紅。網紅的孵化過程從素人的挖掘、簽約,到為簽約紅人做人格梳理、內容創作、粉絲推廣,再到變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
此時如涵對KOL的培養模式的思路和早期培養張大奕的思路幾乎一致,即培訓網紅,再依托已有的供應鏈為其開淘寶店,實現“自給自足”。
馮敏認為,找到適合做意見領袖的人來做合作分工,重構價值鏈的比例分配,可以明顯發現,有人格背書的店鋪起得更快。
資料顯示,紅人學院從網紅培訓生到正式開店,至少要經歷兩三個月,但是最終能培養成,成功簽約的網紅比例不高。
張大奕的力量逐漸顯現。2016年“雙十一”,張大奕的微博粉絲超過400萬,“吾喜歡的衣櫥”店鋪成為淘寶第一家銷量破億的女裝類店鋪,全年營收超過2億元。
“雙十一”的余熱未散,如涵便獲得了阿里巴巴3的投資,估值暴漲15倍。
當年,張大奕的個人紀錄片《網紅》上線。紀錄片一開頭,戴著夸張的假發,揮著腔調紅人館扇子的張大奕笑著說:“2016年絕對是張大奕的時代。”
事實如此,那時在中國的社交網絡上找不到粉絲量級和影響力媲美張大奕的網紅。在如涵按照“張大奕模式”培養出的眾多青春靚麗、穿搭時髦的網紅里,再也沒有出現另一個張大奕。

下一個風口很快就來了。
《網紅》記錄下了張大奕第一次為“吾歡喜的衣櫥”直播帶貨的樣子,她在鏡頭前俏皮自然,向觀看直播的粉絲派發50元優惠券。
這場直播有個插曲,在新品上架時張大奕想要暫停直播讓粉絲下單被工作人員阻止。張大奕問工作人員:“人看直播怎么下單啊?”對“可以邊看邊買”的答復感到驚奇。
那天工作人員向她介紹柳巖不久前創下的14萬觀看記錄,她豪言破觀看粉絲破15萬就穿泳衣直播。這場直播最后觀看的粉絲數接近40萬,銷售額超過兩千萬元。一個晚上一家店鋪銷售額超過兩千萬,五年前,這是任誰看了都要驚呼的成績。
但這些數據沒有讓張大奕和背后的如涵看到一片新藍海。張大奕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說:“有點累,比拼時長的直播模式會讓大家產生審美疲勞,我覺得’雙十二’之后,這個模式會有改變,因為直播的轉化率在降低”。
2019年,短視頻已經成為了人們重要的消遣方式,后起之秀抖音和快手的月活超過微博,更多形態的網紅進入網民的視野,并成為人們追逐的對象,反觀如涵卻一直停留在微博圖文種草時期。登陸納斯達克時,馮敏表示如涵在微博上投入最大,因其和電商結合最大。
而面對直播,馮敏有言:“在網紅KOL這塊踩中了一個風口了,就像一條小船游在海里,沒必要再去北冰洋,也許會翻船。”
先是對局勢的誤判,再是偏安一隅的心態,讓如涵錯過了社交平臺的迭代和直播行業的流量爆發。
2019年3月,張大奕帶著自己的美妝品牌BIG EVE BEAUTY走進李佳琦直播間,一句話的時間,一萬支洗面奶售空。

張大奕終于見識到了直播帶貨的強大。
9月,張大奕率如涵旗下的多名網紅進駐淘寶直播,開啟了如涵的直播帶貨時代。如涵也為之專門成立了“主播新業務部”,給直播業務提供必要的輔助,此外,如涵的直播業務也拓展到了抖音、和快手。
然而,姍姍來遲的張大奕在直播領域的號召力遠不如前。根據胖球數據,張大奕近七場直播的場均觀看人數為50.27萬,總銷售額為1099.6萬,數據甚至不及五年前那一個晚上創造的銷量。對比李佳琦這樣的頭部主播,張大奕直播間的觀看人數和銷售額與前者已經不是一個量級。
而作為如涵的頭部網紅,張大奕的直播成績已經是如涵網紅隊伍中的最佳成績。

2
競爭與失衡
讓如涵的故事無法繼續的,是連年虧損的業績。
根據招股書,上市前的2017財年到2019財年,如涵的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分別為-0.55億元、-1.04億元、-0.81億元。
作為“網紅經濟第一股”,在資本市場中,如涵的營業模式缺少可以對標和參考的對象,營收和利潤直接決定了股民和投資者的選擇。
2017年,如涵開始布局平臺模式,做起了“代運營”生意,營業模式向專業的MCN機構靠攏——由旗下簽約KOL幫商家營銷和帶貨,從“自產自銷”的閉合模式到向外輸出,但著力孵化網紅必然伴隨高昂的營銷成本。
招股書顯示,網紅運營推廣、供應鏈管理、公司管理的支出,在總收入中的占比維持在40%左右,幾乎吃掉了所有毛利潤。其中營銷投入占了大頭。
據業內人士估計,行業內孵化一個可變現網紅的成本大約為300萬元,如果是李佳琦、薇婭這樣的的頂級KOL,則花費更高。2020財年財報顯示,如涵當年的營業成本為8.061億元,而營銷費用為3.052億元,占比超37%。
2019年到2020年初是直播電商的紅利井噴期。如涵也在不斷調整營業結構,加碼平臺模式,減少自營模式的比重。2019年3月到2020年3月,如涵自營模式下的網紅數量已經從14位減少至3位;店鋪數量由56個減少至19個;平臺模式下的網紅數量由122位增加到137位,同比增長12%;平臺服務的品牌數自2019財年的632個上升至2020財年的1035個。
這樣的模式消解了腰部和尾部網紅的“產能”,也帶來了良好的收益。2020財年,如涵代運營業務收入達到1.19億,在總營收中的占比提升至48%,去年同期僅占比24%。但就像天平的兩邊,如涵對代理業務的傾斜壓縮了本身的自營業務,虧損雖然收窄,但仍然沒能扭虧為盈。
此外,培訓和營銷的高昂成本沒有得到相當的回報率,如涵也沒能再培養影響力和變現能力如張大奕的頂級網紅。如涵2017財年到2019財年頭部KOL貢獻的GMV占比分別為60.7%、65.2%和55.2%,其中張大奕一人貢獻的GMV占比常年超過50%,如涵內部二八效應明顯。
收益的過度集中給如涵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低抗風險能力,如果頂級KOL受市場認可度降低,對如涵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2020年4月,張大奕和天貓總裁蔣凡的婚外戀被爆,如涵股價隨后下跌6.36%,市值蒸發約1.5億人民幣。許多人將如涵退市的原因歸結于這場輿論風波,但值得注意的是,事件之前的一個月,如涵的月股價跌幅超36%。張大奕和蔣凡的負面新聞確實是一記重錘,但就此說如涵退市是“敗也張大奕”顯然有些避重就輕。如涵退市的根本原因在于如涵的連年虧損和轉型成果不足預期。

綜合如涵業績和網紅經濟市場行情可以看見,如涵沒落的底層邏輯不是如涵無法培養出下一個張大奕了,而是“張大奕”不再是市場的稀缺品。
網絡已經越來越扁平化了,信息差的消失讓越來越多的網民能夠輕易接觸大量的時尚訊息。比如小紅書的出現,造就了大量風格各異的美妝時尚類網紅,網民的審美風格和范圍被大大拓寬,早期“網紅”的形象價值已經衰減。
張大奕在分析自己走紅的原因曾表示,自己是中國大多數女生的樣子。但在今天,單一的時尚品味和風格不再被多數人追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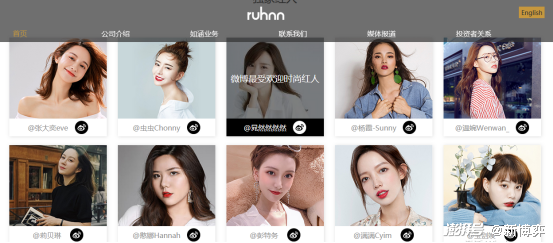
而錯過進入短視頻和直播電商的最佳時機,可以說是如涵最可惜的一步錯棋。MCN機構看看世界CEO李琪緣在回顧自身的發展時感慨新興平臺的“威力”,他認為,最先進入抖音的網紅,是被抖音的發展拽進去的,抖音巨大的平臺效應形成的流量黑洞將網紅和MCN機構吸進去,先入局者幾乎只需要“躺著順勢而為”,而不被淘汰的密碼,則是跟緊著時代在變遷。
3
如涵之后
2019年如涵登陸納斯達克時,一直活躍在吃瓜前線的王思聰在朋友圈提出三點質疑:一是如涵處于虧損中,每年1.5億的巨額營銷費用令人費解;二是如涵當時超過50%收入的張大奕,不具備可復制性;三是如涵的網紅孵化、網紅電商、網紅營銷模式都沒有被驗證成功,也沒有培養出新的網紅來。
這同時也是市場對如涵提出的質疑,但如涵并沒有用實際的回報消解市場的疑慮。對如涵而言,退市并不意味著“如涵模式”走到了盡頭。在網紅經濟這條賽道上,如涵想要跑得更遠,在現有的業務模式上,還有很大的優化空間。
一方面是發揮網紅的帶動效應,降低營銷成本。將網紅作為獨立個體運營,意味著包括如涵和許多MCN機構需要為每一個網紅付出幾乎等量的營銷成本。在結果難以預測的情況下,許多投入可能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MCN機構古麥嘉禾曾以“家族”模式組建紅人矩陣,通過一個網紅與一個網紅建立“關系”,以此為其引流的方式成功孵化出“子豪家族”,這種“種樹邏輯”能夠有效提升營銷投入的效益。古麥嘉禾副總裁高睿表示:“有這樣一個矩陣作為MCN主體,選擇會更豐富。首先,在一家機構有多個賬號可以選;另外,賬號之間可以形成很好的相互補充和聯動。因為這些賬號覆蓋的是同一波人群,而且這樣投放的效果會比單個投放要高得多,ROI(投資回報比)也比較高。”

另一方面是專注于產品,弱化“人設”,這是一種網紅培養思維的改變。過去如涵通過打造時尚KOL為其產品引流,但對當下的直播也業務而言,穿搭模板式的網紅并不是“帶貨密碼”。在直播間里,粉絲們的視線已經發生了轉移。
小葫蘆大數據CEO曹津認為,當下的直播電商核心是產品,“貨即內容”。人們觀看帶貨直播的動力已經從支持KOL轉化成為追求優質商品和最高折扣,帶貨主播的身份從KOL 轉換為引導消費的KOC。網紅的個人特質和“人設”不再是“圈粉”的要素。門牙視頻聯合創始人文宏晶認為,在直播電商時代,成為網紅的基本要素應該是很好的口播能力或豐富的測評經驗技巧,能夠讓粉絲產生真實的代入感。

近幾年國內MCN飛速發展,目前超過2萬多家,呈現爆發態勢,市場競爭激烈。在這片“紅到發黑”的海里,有人聲量漸稀,也有巨擘平穩航行。
資本市場中如涵的背影漸遠,它的沒落告訴市場,復制一個“爆款”對MCN 機構而言并不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另外,網紅經濟沒有“舒適圈”,及時把握風口并投入嘗試才能搶占先機。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