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疼痛的挽歌:顧桃的“鄂溫克三部曲”
顧桃的“鄂溫克三部曲”,《敖魯古雅·敖魯古雅》(2007)、《犴達罕》(2013)、《雨果的假期》(2010)為他在業內帶了眾多贊譽,比如,《犴達罕》斬獲釜山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獎,也曾入圍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不過,這些獎項的知名度是在小圈子內打轉,能夠造就的影響十分有限。我們知道,紀錄片的投資、運作和市場遠遠無法跟劇情片比擬,鮮有觀眾走進影院只是為一部紀錄片買單。“三部曲”充滿濃郁的民族影像氣質,吸引了許多專業研究者和對少數族群文化有特別興趣的人。因此,顧桃的作品常常以沙龍、學術放映或少數族群電影專題展的形式與觀眾見面。它們粗糲、坦率而充滿詩情,讓人過目難忘。

從“復原”到觀察
據顧桃自述,由于其父親與部落老人瑪利亞·索的舊交情,才讓他俘獲獵民的信任去拍攝。在拍攝期間,他們吃住同行,喝酒唱歌,或外出搜尋馴鹿。顧桃的工作頗帶人類學的意味:長時間深入到部落腹地,與本地人打成一片。也因此,紀錄片具有某種影像民族志的性質。攝像機秉持一種“不介入”姿態,要么佇立在人物面前,要么緊緊跟隨。從年邁的瑪利亞·索到青春洋溢的雨果,獵民對他們的生活有充沛的展現機會。影像引領我們對鄂溫克族群的認知,有種樺樹皮般粗糙的可感性。這些都是單純的文字記錄難以企及的。

顧桃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國家主導的民族識別、調查政策的加持下,八一制片廠和北京科學教育制片場聯合攝制了十六部影片,名為“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其中,就有一部《額爾古納河畔的鄂溫克人》(1959)(下稱《河畔》)。現在看來,這部黑白影像的片子年代感濃厚,使鹿鄂溫克(注:使鹿鄂溫克也稱為“雅庫特”,鄂溫克的另外兩支是通古斯和索倫)的狩獵、分配、交換、婚姻習俗以及薩滿信仰均一一呈現。拍攝是在“文化搶救”的理念下,民族學者力圖利用電影技術的“寫實性”去保留那些瀕臨消失的部落制度和文化。不過,在實際拍攝時,某些古老的儀式就已變得漫漶,族群風俗處于緩慢的衰變之中。為有所補救,拍攝工作者選擇提前撰寫好大綱和分鏡頭腳本,從而達到“復原”或“重建”的效果。模擬拍攝會請當地人穿上傳統的服裝,提前進行排演,以便讓逝去之物重現于銀幕。
“復原重建”的目的是搶救消失的文化,但其疑點重重,無法掩飾。擺拍或許是最大的問題,因為它跌破了紀錄片現實主義的邊界,所謂的“真實”只能殘留于視覺上的直接性。擺拍猶如隱蔽的操縱,讓影片深陷于拍攝的倫理困境。攝制內容上的組織,在性質上,使紀錄片開始向劇情片靠近。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在此變得模糊難辨。在后期制作中,解說和字幕發揮著類似的牽制作用。在《河畔》中,與一場婚禮畫面伴隨的是相應的解說:新娘帶來了幾頭鹿的嫁妝,詳細地講解整個婚禮的流程。在此意義上,影像只是為研究提供比文字更直觀的素材,從而闡釋特定意識形態下對少數族群的認知。這批影片拍攝的初衷,是將少數民族“在社會發展史上的早期形態”用影像留存下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復原重建”的缺陷之一,就是在拍攝者的價值體系當中,已經存在落后/先進,原始/現代等不平等的預設標準。
與《河畔》相比,顧桃的“三部曲”恢復了以被拍攝對象為主位的倫理。除了必要的背景交代,影片中沒有任何冗余的解說詞,將主動權交給拍攝對象。紀錄即觀察,避免越俎代庖。顧桃讓鄂溫克人自己去闡述對狩獵文明的認識,表達他們的心聲。影像的不加修飾,讓“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結實地落地。通過自我表述,我們知道鄂溫克人是如何遵循季節規律而狩獵,比如:馴鹿交配的時節他們收起槍支,鹿群中的母鹿也非狩獵的對象。用片中維佳的話說,打獵是幫鹿群精減老弱病殘。在薩滿信仰的訓喻下,他們會尊重任何生命,即便微小如一窩螞蟻。不論從生態意識還是人文精神上看,馴鹿文化都令人肅然起敬。片中,有幾處新聞節目對鄂溫克人“新生活”字正腔圓的解說播報,它們構成了影片中維佳、柳霞等人嬉笑怒罵、掙扎徘徊的時代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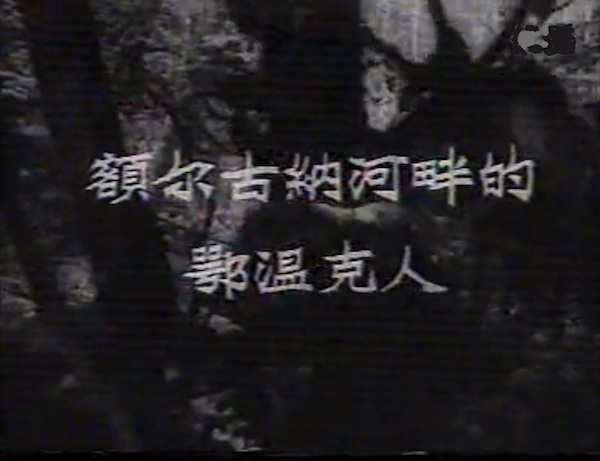
人的挽歌
在該片的豆瓣條目下,維佳的孤注一擲的詩句被頻繁引用。比如:“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代表消亡。”毫無疑問,“三部曲”整體上被理解為一首鄂溫克狩獵文明的挽歌。
影片主要聚焦于鄂溫克使鹿部落。他們最早自西伯利亞遷徙而來,在大興安嶺生活,以狩獵和馴鹿為主要的生產方式。早在1960年代,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他們建立了敖魯古雅獵民鄉,部分人實現了定居,開始了山上獵民點-山下定居房的“二元結構”生活。從2003年開始,隨著“生態移民”工程的推進,政府想讓鄂溫克獵民徹底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定居”。搬遷之后,獵民住宿條件有所改善。但因為山下生活資料無法自給自足,大量的花銷支出卻缺乏經濟來源,生活水平反而降低了。居民點附近的苔蘚稀薄,加上偷獵“套獵”猖獗,搬到山下后獵民的馴鹿損失嚴重。(《犴達罕》中有一段,就是把馴鹿從山下拉回山上。)當地政府似乎并未做好充分的民意調研和搬遷預算,以致于,此項工程很難說是成功的。不少獵民無法適應徹底的定居生活,后又返回森林。影片中的三家便屬其中,他們組成了一個獵民點。從2007年開始,顧桃用將近四年的時間跟蹤拍攝素材,紀錄一個小型部落最后的變動和衰敗。
顧桃無官方背景,也沒有抱研究性的目的。他拍攝的重點不再是體系性的文化角色,主角一轉:那些個性突出的人物走到了鏡頭前面。他們的氣質撲面,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折射出族群的命運。在顧桃眼中,“鄂溫克”不再是詞條、界定和對民族源頭的追溯,而就是維佳、柳霞這些充滿冒犯與哀傷的人。
維佳曾在中央民族大學學習畫畫,后來還是返回了山里,這個人身上有種藝術與野性的綜合。他畫中的森林和鹿充滿靈動,用色細膩而飽滿,常常出口成詩。在嘈雜擁擠的綠皮火車上,他蓬頭垢面,裹著棉襖大談德國表現主義和莫迪里安尼的裸女畫作。維佳長不修邊幅,是大興安嶺的波西米亞人。除了森林,他似乎不適合待在其他任何地方。《犴達罕》即以維佳為主角,前半部分是他在林中的生活,包括他講述獵民如何從“黃金時代”衰敗至此。后半部分,則逐漸染上了某種象征意味。當我們看到獵民大漢蜷縮在海南三亞市的一間出租屋、乃至后來被送進精神病院時,就像一頭桀驁不馴的犴終于被死死地套住。在導演顧桃眼里,維佳就是森林里最后的犴達罕——大興安嶺體態最大的動物,敏感而富有尊嚴。

《犴達罕》劇照
相較之下,柳霞是在林中生活的內部囈語。她是老人巴拉杰依的女兒,維佳的姐姐,愛唱歌,愛曬太陽。柳霞的牙齒脫落,突出的顴骨因常年醺酒而日益膨脹,以至于眼睛幾乎擠成一條縫隙。《雨果的假期》便是以小雨果的視角,講述他的回鄉之旅。小雨果常年在外地上學,日漸與母親生疏,而尤其讓他難以忍受的是母親屢勸不改的酗酒惡習。為讓兒子開心,柳霞常常做一些笨拙的事情,比如讓這個大小伙去騎一頭體格比羊大不小多少的馴鹿,那場面既尷尬又讓人心酸。在《雨果的假期》中,柳霞是一位深情但不可救藥的母親,她的愛笨拙,魯莽,不得要領。
影片對人物的跟蹤觀察上一絲不茍,但并不意味在其他方面就毫無技術可言。比如,《敖魯古雅》一開始,柳霞就跟一位東北口音的漢族婦女就敖鄉新修的房子是否適宜獵民居住,表達不同的看法。顯而易見,柳霞認為跟山上相比,定居點遠不盡如人意。由此觀眾就獲得了一個山上/山下的比較性視野,期待后續的走向。再比如,《敖魯古拉》和《犴達罕》的結尾都是以維佳的詩句作結:“在咱們這個時代,狩獵文化消失了,慚愧萬分!”尤其是《敖魯古雅》中,隨著部落老人馬里亞·索牽著一頭馴鹿,緩緩走向景深處,維佳的詩句再次作為畫外音出現。維佳的詩不僅加強了影片整體的挽歌性,也構成了對林中生活的釋意。加之畫外音和民族歌謠的援引,顧桃不僅以觀察為己任,更是通過剪輯提出了觀點和批評。
酗酒和暴力
這些人物不拘格套,充滿冒犯,對習慣于“文明禮節”的觀眾來說難以體認。不過,他們迸發出蓬勃的藝術感和生命力,沖擊著我們疲軟的認知神經。“三部曲”中出現了不少酗酒和暴力的鏡頭,令人側目。柳霞和維佳姐弟二人嗜酒如命,母親巴拉杰依對此恨得咬牙切齒。姐弟倆常常交換眼色,把酒藏在母親看不見的地方。維佳因為無法戒酒,最終跟他的南方女朋友分手。柳霞則因為酗酒,失去了撫養兒子的權利。
除了醉酒,此外就是驚人的大打出手。《敖魯古雅》中有一幕:柳霞返回鄉下,看到屋里臟亂不堪而心生不滿,在嘟囔中,她毫無預兆地就掄起板凳連續砸在維佳的腦袋上。頓時,后者鮮血直冒。柳霞因為跟人打架,頭部屢次受傷,意識變得混沌不清,這從她說話總是顛倒重復就能看出。閱讀顧桃的拍攝日志《憂傷的馴鹿國》,酗酒和干架似乎是家常便飯。據說有一次,有個年輕人把酒藏在了高高的樹杈上,沒想到柳霞為了喝酒直接把樹給放倒了。又比如何協,部落酋長的兒子,獵民點最有權威的男人,因為爭執被表弟連捅了四刀,刀刀致命,在重癥監護室里躺了很久。
對于獵人為什么愛喝酒,我們當然可以給出許多解釋,比如在森林御寒,或出于同漢族類似的“無酒不成席”的飲食風俗。但維佳、柳霞等人醺酒,超越日常調節而變成了一種病態的癮癥。酗酒和暴力的場面生猛無比,我們感到,激烈的身體行為,難以僅僅從個人脾性的層面去理解。尤其是一旦因喝酒而亡的人形成一份數據統計(維佳說他知道“喝死的就有八個”),這些言行就不可避免地就表征了鄂溫克人精神狀況的重要面向。維佳是這樣解釋的:“鄂溫克人沒有搬遷之前,他們不敢喝酒。搬遷以后無所事事,把槍也沒收了,無所事實,就整天喝酒,喝得非常累……”“咔,喝死,喝死拉倒!”獵槍沒收之后,年輕的獵民們喪失了繼續在森林中馳騁的權利,身體的能量難以施展,積郁憤懣又不知如何疏導。于是,他們選擇用酒精自我麻痹。
醺酒和干架,像是為鄂溫克下了定義。頹廢、殘忍和傷感的自我放縱,表征一個族群的無計可施。它們超越了個人癖好,變成一個民族面對文化失落時的無奈反應,某種意義上抗議。然而,一旦酗酒者的形象被認領,就會造成危險的效果。任何少數族群在主流媒介中的再現中,唱歌跳舞可能是最好的標配,而零星的負面形象都會病毒般地增值。對外,考慮到普遍存在于歷史教材中“社會進化的早期階段”的錯誤想象,它會加劇主流世界對少數族群“野蠻”、“文明低下”等偏見。對內,在日復一日對酒精的沉溺中,昔日的獵手會把自我體認為苦難和怨恨的化身,而對外部報以敵意。當悲哀的情緒在族群內部渲染,也會造成自我的定位悲情化,籠罩于消極之中。

鄂倫春獵人在狗的陪伴下騎馬狩獵。
尾聲
烏熱爾圖也許是1980年代以來鄂溫克族最重要的小說家,他的短篇曾在1981-1983年連續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獲獎小說《琥珀色的篝火》(1983),講述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鄂溫克獵人尼庫在送病重的妻子去醫院的途中,發現幾個迷路人的蹤跡。在妻子的鼓勵下,他選擇先去解救那幾個奄奄一息的城市漢人。找到他們后,尼庫生火、收拾木柈、砍樺樹皮燒水。他不遺余力地展現精湛的生存技藝,因為他深諳自己正在被外人所注視。
獵手與外來探訪者之間的這種目光關系,實際上,構成了一種文化間性的隱喻。在這樣流動與遷徙加劇的時代,沒有文化會封閉地孤存。相反,總是有人出走,有人闖入——它們恰是在邊地與外省、多數與少數之間的交涉中再度生成。少數民族文化與內地的遭際,讓他們開始走出自為的狀態,參與到交互之中。這決定了,他們無法再孤懸地自成一體,而是在交往中言說,并渴望被承認。烏熱爾圖作為意欲為本民族代言的作家,正是在這樣不可避免的間性關系中寫作。因此在小說中,我們讀到了面對造訪者的鄂溫克獵手是如何地竭盡全力。
然而在現實中,面對少數族裔,我們內地的漢族讀者,多少都是所謂的“大寫的異己讀者”(the Other reader):下意識地懼怕和抵制那些同我們迥異的感覺,而希望能篩選、尋找、定位足夠的相同之處。這是一種普遍的怠惰心理,因難以直面陌生的存在和環境,情愿留守于舒適區。我們習慣于把異質性過濾,只留下安心的部分。這其中存在知識上的疏忽,當然也不乏心態上的傲慢。然而,顧桃的影片恰好形成了一股沖擊,讓我們始料不及。在嚴酷的森林地帶,喝酒、唱歌、哭泣。這些激烈的身體以及充沛的力比多,讓我們感到疼痛。
注釋:
[1][4]顧桃:《憂傷的馴鹿國》,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
[2]朱靖江:《復原重建與影像真實》,《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2期
[3]謝元媛:《生態移民政策與地方政府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5]烏熱爾圖:《琥珀色的篝火》,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