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趙德明:從1975到2003年,波拉尼奧在文學上追求什么
編者按:智利作家波拉尼奧近四十歲才開始寫小說,作品數量卻十分驚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說、四部短篇小說集以及三部詩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偵探》在拉美文壇引起的轟動,而其遺著《2666》更是引發歐美輿論壓倒性好評。短篇小說集《重返暗夜》由十三個故事組成,是波拉尼奧寫作風格的典型樣本,他所關切的主題、偏愛的人物盡在其中。
此文為《重返暗夜》譯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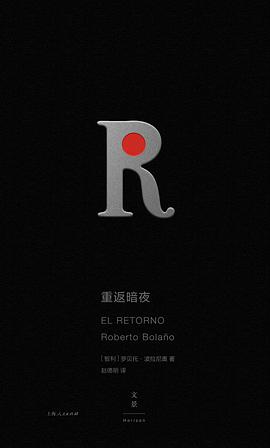
作者: [智利] 羅貝托·波拉尼奧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譯者: 趙德明
到今天為止,波拉尼奧的作品本人已經翻譯了五部:《2666》《地球上最后的夜晚》《護身符》《美洲納粹文學》,以及這部短篇小說集《重返暗夜》。對這位智利作家的文學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有了一個粗淺的了解。寫下來供讀者參考。
影響波拉尼奧文學創作的外部條件是他生活的時代和社會。1953年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2003年病死在西班牙巴塞羅那,終年五十歲。父親是卡車司機,母親是中學教員。家境平常。在母親的慫恿下,父親于1968年帶著全家到了墨西哥。這時羅貝托?波拉尼奧十五歲,沒有上完中學,正好趕上了這樣一堂“課”:1968年10月3日在墨西哥城爆發了學生運動,呼吁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實行獨裁統治的執政黨派遣軍警去三文化廣場鎮壓學生,開槍殺害數百人,打傷幾千人,捕人無數;同時對國立自治大學校園進行搜捕,制造了震撼世界的“特拉特洛爾科大慘案”。同年10月12日至27日墨西哥奧林匹克運動會如期在墨西哥城舉行。這兩件大事都給少年波拉尼奧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七年后,他在一系列作品中都有詳細描寫。1999年問世的中篇小說《護身符》的主要情節就是以軍警搜查大學校園為背景的。1973年,波拉尼奧二十歲,欣聞祖國巨變,由智利人民陣線推選的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急需國內外的聲援和具體幫助,以便進一步推動政治、經濟改革,他用搭車的方式輾轉回到了智利,時間是8月。9月11日陸軍司令皮諾切發動軍事政變,派遣飛機、裝甲車、正規軍攻打總統府,阿連德頭戴鋼盔、手持沖鋒槍英勇反擊,不幸陣亡。11月波拉尼奧在前往首都的途中被捕,在監獄里蹲了八天,被兩位中學老同學營救出獄,這兩人是警探,在監牢里登記囚犯時發現了波拉尼奧。出獄后,他重返墨西哥。1974年1月回到墨西哥家中。1975年天天讀書,天天寫作。智利這段經歷多次出現在他筆下。《重返暗夜》這個短篇小說集中的《警探們》就提到了他在獄中的表現。1975年他與十九位墨西哥青年詩人組織了“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口號是:“放下一切,重新上路!”對墨西哥和拉美一些文學巨匠,例如,大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小說家加西亞?馬爾克斯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提出:“炸飛官方文化的腦殼”。該組織多次去官方舉辦的文化活動場所破壞搗亂,例如沖擊圖書首發式、官方文學授獎儀式、詩歌朗誦會等。他們自辦詩會,出版《下現實主義通訊》《散文》《狐貍回雞窩》等刊物。第一批成員共二十人,年齡最大的28歲,最小的15歲,大部分人的年齡22歲,跟波拉尼奧一樣,都是大學生和輟學青年,但喜歡文學。他們認為自己代表“大眾文化”,有革命思想,贊成文學藝術家“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風骨,主張與官方文化唱對臺戲。波拉尼奧是他們的領袖,起草了《下現實主義宣言》,組織出版《下現實主義通訊》,編輯《下現實主義青年詩人選集》。他在長篇小說《荒野偵探》中對“下現實主義”青年的活動有詳細描寫,例如,咖啡館聚會、酗酒、吸毒、斗毆,揭示出這一代文學青年的絕望和憤怒的情緒。美國文學評論界普遍認為,下現實主義的主張是“發生自內心沖動的現實主義”,是受美國“垮掉一代”的影響。但墨西哥文學評論家蒙塞拉特?瑪塔里阿卡(Montserrat Madariaga)則認為,下現實主義的主張在于“寫詩的態度。詩中做愛是真愛,不是編造;不用意象,是把生活經驗化為詩歌。在政治思想上,他們渴望擺脫社會以有序的名義而強加于人的常規和限制。他們贊成革命,不主張建立黨派。”“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成果之一是出版了一系列刊物和詩選,例如,《下現實主義通訊》《散文》《狐貍回雞窩》《空港區》等,到2011年還有這樣的文章問世:《應該消滅奧克塔維奧?帕斯》,2012年《炸飛官方文化的腦殼的確是健康措施》。
1977年波拉尼奧本想去瑞典謀生,但是此前已經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定居的母親希望他去她身邊生活。于是,他告別了“下現實主義”的弟兄們,來到了巴塞羅那。起初沒有固定工作,只好干臨時工,他洗過盤子,當過飯店門童,在餐廳里當跑堂,收過垃圾,為夏令營營地守夜,在碼頭上卸貨,去葡萄園里摘葡萄,在雜貨店當售貨員。但是,只要有空閑,就讀書,就寫作,跑圖書館,甚至偷書。天才加勤奮,陸續開花結果了:從1980年開始到1999年的時間里,出版了詩集和小說多部,獲得多項文學獎,重要的有:《莫里森的門徒和喬伊斯的粉絲的忠告》(1981年),這是波拉尼奧出版的第一部小說,與A.G.Porta合寫;第二部小說《大象之路》(1984)獲得Felix Urabayen 文學獎;第三部小說《溜冰場》(1987)獲得伊倫市文學獎;1996年有兩部小說問世:《美洲納粹文學》和《遙遠的星辰》;1998年長篇小說《荒野偵探》出版,先后獲得西班牙Herralde小說獎和拉美羅慕洛?加列戈斯文學獎,從此名聲大振。
西班牙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恩里克?維拉-瑪塔斯(從1973到2012年創作小說25部,獲得各種獎項21種,在歐洲和美洲享有盛譽)給《荒野偵探》的評價是:
“《荒野偵探》可能是一個突破,為新千年的文學流派打開了一個突破口。另外,對我本人來說也是一個突破口,迫使我重新設計自己敘事藝術的方方面面;它給了我勇氣,鼓勵我繼續寫作,挖掘出我寫作的潛力。”
2003年6月拉美作家在西班牙塞維利亞聚會。阿根廷作家、新聞工作者羅德里格?弗萊撒【Rodrigo Fresán,1963— ,成名作《阿根廷故事》(1998)】認為:“毫無疑問,波拉尼奧作為拉美文壇領袖是當之無愧的。”
2003年7月15日波拉尼奧去世。他在6月30日曾經與好友西班牙作家、出版家霍爾赫?愛拉爾德(Jorge Herralde)有過一次長談,談及《2666》等文稿的處理問題。霍爾赫根據這次談話,寫出了《為了羅貝托?波拉尼奧》(2005年出版)。書中在談及《2666》的價值時,他寫道:“這是一部沉甸甸的偉大作品,潷出了波拉尼奧敘事藝術的全部精華;這是一次偉大的文學歷險,他把文學語言發揮得淋漓盡致。”霍爾赫是西班牙Anagrama出版社的創始人和社長(1969年至今),他慧眼識人,近三十年來幫助一批西班牙和拉美作家走上成功之路,例如,西班牙的阿爾瓦羅?彭坡(Alvaro Pombo)、恩里克?維拉-瑪塔斯(Enrique Vila-Matas)、哈維爾?馬利亞斯(Javier Marias)、拉美作家塞爾西奧?皮托爾(Sergio Pitol,墨西哥作家,2005年塞萬提斯文學獎獲得者)、羅貝托?波拉尼奧、阿朗?鮑爾斯(Alan Pauls,阿根廷作家、文學評論家、教授、電影編劇,成名作《往事》。2007至2013年創作了阿根廷20世紀70年代生活三部曲《眼淚史》《頭發史》和《金錢史》)等人,他領導的出版社先后在1994、1998、2002、2003、2005、2006年被歐洲出版界評為最佳文學出版社之一。
在波拉尼奧與友人的談話以及《2666》的藝術追求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在乎作品的結構,可以說,結構先于情節。從他的短篇小說中,我們知道,故事里的人物,作者早就熟爛于胸了,問題是如何巧妙地把他們安排到《2666》里的各個崗位上去,要求他們各司其職,因此全書的結構成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2666》的結構像一棵參天大樹,但它是倒置的,即故事從葉子開始講起,先說說法國文學教授讓-克勞德?貝耶迪是如何接觸到一位德國作家、本諾?馮?阿琴波爾迪著作的,再說說一位智利教授在墨西哥的遭遇,然后再說說一個美國記者法特采訪經歷。此后,別開生面,講起了墨西哥黑幫的罪行。最后才是阿琴波爾迪。表面上沒有情節聯系的五個部分最后都指向墨西哥的特萊沙市——全書的“根”。真像條條小路歸“羅馬”的敘述方式。這樣的結構顯然是作者運籌了多年的結果,《重返暗夜》中的短篇故事,就是未來長篇小說的一個個板塊。
更為引起我們思考的是,從1975到2003年的文學創作歷程中,波拉尼奧在一步步追求什么?是什么呢?他想告訴讀者什么?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波拉尼奧們這一代從來到地球上之后,他們的親身體驗是什么?他們耳聞目睹的是什么?簡言之,就是人類的罪惡,就是邪惡、貪婪、殺戮、欺詐,就是人性中惡的一面,這在戰爭販子、政客、為富不仁者身上表現得尤甚,他們當然是全人類中的少數,但是他們吹起來的邪惡之風、貪污腐敗之風、享樂奢靡之風為什么能風靡全球?為什么恰恰是這群邪惡之徒掌握著政權和財權,操縱著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呢?人類中的多數是善良、真誠、勤勞、勇敢的,但是,為什么這些人理性和健康的思維會為病態、瘋狂的說法所左右呢?當今的“文明”越來越下流無恥、越來越野蠻了,越來越赤裸裸地、無所忌憚地殘害自己的同類了,多數人為什么寧可沉默,寧可自保,而不愿意挺身相助別人呢?為什么科技進步了,而人們變得自私自利了呢?而稍有些良知的文學家、藝術家們呢,面對這樣丑惡的現實,又表現如何呢?他們早就分化了!宮廷御用文人早已有之,他們的使命就是為權貴服務和欺騙老百姓。有膽識、講道義、講擔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作家,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始終橫眉冷對,始終以文學為生命,始終相信即使地球爆炸了,空氣里仍然會殘留著詩歌的符號和韻律。在貪官眼里,這樣的文學家是傻子,但恰恰就是在這群“傻子”的精神世界里還飄揚著人道、人文、人性真善美的光輝旗幟。盡管這樣的精神越來越被邊緣化,越來越顯得絕望和無助。
波拉尼奧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絕望情緒是顯而易見的。面對著如此惡劣的社會環境,弱勢群體的壓迫感是很強烈的,孤零零的個人就更加看不到出路了。但是,波拉尼奧的性格中有叛逆的元素,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在拉美文化發展的道路上,以1810年為論,玻利瓦爾就高舉獨立的大旗,發動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戰爭。獨立、自由的口號成為一種傳統。這種傳統教育可以從拉美中學教材里得到證明。波拉尼奧喜歡讀歷史、哲學、文學,因此他說自己的詩歌和散文是“堂姐妹:詩歌是柏拉圖;散文是亞里士多德。她倆都討厭沉湎酒色。”他喜歡看德國歷史,尤其是第三帝國的興亡過程中,優秀的日耳曼民族在十九世紀創造了那樣燦爛的文化之后,為什么會在二十世紀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為什么會衍生出法西斯主義并且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他還喜歡看蘇聯史,他想知道為什么開創了人類新紀元的十月革命,隨后的政權殺害了那么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這樣的問題在《2666》,在《雪》《又一個俄羅斯故事》里都有明確的表述。他的觀點是:要革命,不要政黨。因為黨派里有過多“保持一致。我特別討厭這個一致性。”拉美的知識分子特別喜歡自由散漫,放蕩不羈,幾乎很少有例外。知道他們身上這個性格特征,才會比較容易理解他們的為人、為文。因為從十九世紀拉美各個共和國成立起,他們反對的就是“依附性”,主張“獨立、自由”。這種思想早就深入骨髓了。面對二十一世紀種種危機,拉美的有識之士都在考慮如何擺脫金融危機、體制危機、文化危機。波拉尼奧通過文學創作表現出來的“末日感”就是這樣一種憂患意識罷了。
翻譯完了波拉尼奧的五部作品之后,腦海里時時想起安徒生童話里的《皇帝的新衣》:當眾位大臣紛紛為皇帝的新衣喝彩時,那個黃口小兒的一聲斷喝音猶在耳。
趙德明
2013年7月31日下午五點八分北大燕北園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