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催生無聊雜志的正是“編輯會議”
【編者按】
都筑響一是日本一位天才的“野生”編輯、攝影師,40多年來,他一直保持體制外的獨立自由身份,參與過POPEYE、BRUTUS等日本知名潮流生活文化雜志的工作,也曾編輯當代藝術全集ArT RANDOM系列(共102 本),出版探訪世界各地的“ROADSIDE”系列等。近日,他的工作手記《圈外編輯》中文版推出。這本書記錄了他這個“圈外編輯”這些年來的工作經驗和思考的總結,雖是談編輯工作,卻有很多共性之處。本文經授權摘自其中一章,標題為編者所擬。

都筑響一
我編輯之路的起點,是平凡出版(Magazine House前身)發行的雜志POPEYE的兼職打雜人員。
當時(說是當時,那也是將近40年前的事情了)正逢第一波或第二波滑板風潮,我和大學朋友也在玩滑板。我為了滑板的事寄明信片給編輯部,結果那成為我日后進去打工的契機,就這么單純。我完全不曾把“成為編輯”當作目標。
因此我一開始只是一個跑腿小弟。在那個年代,稿子完全手寫,連傳真都還沒普及,更別說網絡了,我負責的工作便是去作者那里取稿,幫忙倒茶,或寄送印好的雜志之類。當時POPEYE有許多資訊是從美國雜志獲得的。工作一陣子后,上頭得知我是英語系的,開始托我翻譯雜志上的文章。翻譯完交給別人寫稿等于花了兩遍功夫,于是他們又進一步問:“你要不要自己寫稿?”我一寫就寫到了今天。也就是說,我有一段時期是領時薪,后來就改成了稿費制,一張稿紙領一定金額。
POPEYE于1976年創刊,跟我上大學是同一年。不久后,大學生和20歲出頭的讀者群體與我一樣踏入社會,公司希望做一本讀者年齡層再略高一些的雜志,BRUTUS便在POPEYE第五個年頭時問世了。我受邀過去工作,最后在這兩本雜志里共待了十年。我認為這段時間打下了我身為編輯的所有基礎。入行時真的沒多想什么,卻碰巧找到了與自己如此契合的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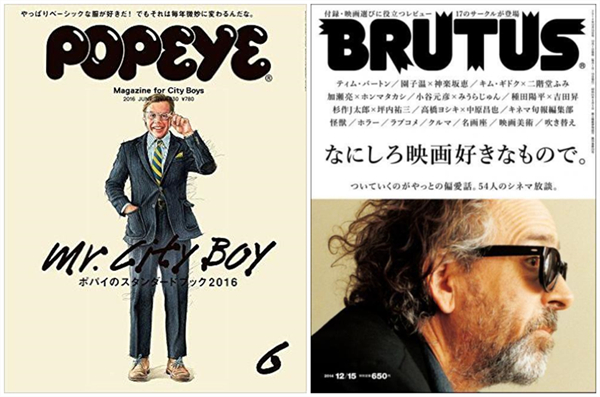
POPEYE和 BRUTUS是日本兩本知名的流行生活文化雜志
POPEYE和BRUTUS的編輯部都是不開編輯會議的,現在回頭想想才知道那并非常態。尤其是在BRUTUS的那五年,我記憶中根本沒開過半次會。POPEYE應該也沒開過,不過也可能是我不在的時候開的。
不開會要如何編出雜志呢?首先,腦海中如果有了策劃思路,就先去查找各種資料。查歸查,但那畢竟是沒有網絡的時代,所以也做不了太詳細的事前調查,要是覺得大概搞得定就到總編辦公桌前報告:“這個似乎很有趣,請讓我寫報道。”
接著總編就會說:“那某月號給你幾十頁篇幅,去采訪吧。”編輯就出去采訪了。我還在POPEYE時,組成大陣仗的采訪團隊是理所當然的安排,不過到BRUTUS后我已經做慣了,來自各種背景的國外友人也變多了,所以最常采取的做法是:只跟攝影師兩個人行動,或一個人前往采訪地再雇用當地攝影師幫忙,只帶底片回國。接著再去編輯部,或更多時候是直接帶著排版表單和底片回家,一個人寫稿、做版。
由于做事方法如此,所以大家都要等到雜志出版后才會知道隔壁編輯采訪的主題。只有負責定版(決定把收集來的報道在雜志上排序)的編審和總編才會知道所有雜志內容。那是獨立思考策劃、自己負責完成版面的工作制度,成功的甜頭和失敗的苦頭全部只有一個人嘗。
我發自內心認為,催生無聊雜志的正是“編輯會議”。不管在哪家出版社,開會(有時也會讓銷售部門參加,視情況而定)決定策劃都是常態。比方說,每個星期一在中午前開會,每人提出五個方案,所有人一起討論。
接著大家開始一個一個抹殺彼此的方案,這不有趣,那也不有趣。有方案幸存下來獲得采用,再分配給某人:“這個你來負責。”從那時候開始,負責人的采訪動機就已經是零了,因為那不一定是他想做的內容。
“能過的策劃”是什么?就是內容大家都懂的策劃。要讓大家懂,就得進行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介紹。介紹當中如果沒有案例就會缺乏說服力,而案例不外乎是這樣那樣的雜志、網絡或電視上都有過的報道。“看,這么多人做過。”簡單來說,就是用別人已經用過的題材,而這除了炒冷飯外,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成果。
采訪要訪的不是“你知道很有趣的東西”,而是“好像很有趣的東西”。別人報道過的題材,你可以直接掌握內容,但沒人報道過的題材就不能“喏”一聲展示給別人看了。不知道能不能順利寫成文章,但感覺似乎很有趣,所以就過去看看。采訪就是這么一回事,這種工作基本上跟會議格格不入。
說到底,會議也算是一種避險行為。大家一起做決定,就算失敗了也可以把“是大家一起決定的嘛”掛在嘴邊。某種意義上會議只是一種集體回避責任的制度。就在會議一個接一個開的過程中,題材的新鮮度也在不斷下降。
我一路走來都靠自由接案,我認為,專業工作者不該采取“大家一起來”的做法,分攤責任是不行的。銷售的意見和市場調查都無關緊要,編輯就該全力寫出最好的報道、做出最棒的書付印,銷售就該全力推廣、營銷。做不出好書,編輯要負責;任誰來看都覺得好的書如果賣不出去,銷售要負責。我認為這就是專業人該有的覺悟,但我的看法也有過于天真的部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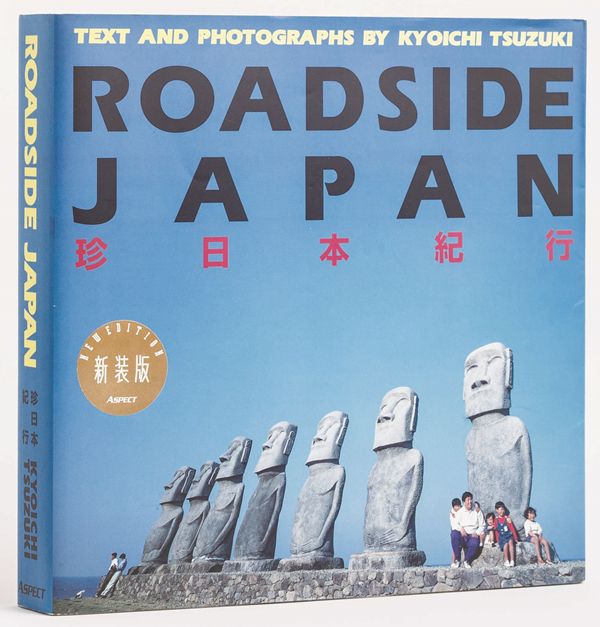
都筑響一的《ROADSIDE JAPAN——珍奇日本紀行》封面
不過,應該也有很多人會擔心自己的策劃無法擊中讀者喜好。我一開始也會這樣。
比方說,在BRUTUS創刊的20世紀80年代前期,紐約比現在野得多,但非常有趣。藝術圈原本流行難解的概念藝術,但當時新繪畫運動從截然不同的源頭冒了出來,蔚為風行。像基思·哈林、讓-米歇爾·巴斯奎特等,全都是在同一個時期浮上臺面的。
我一直都很喜歡當代藝術,但并沒有受過專業的學院訓練,專業知識完全為零。不過跑紐約久了,和那些藝術家也成了朋友,越來越覺得當時的場景很有趣。那剛好是眼光銳利的藝廊開始推基思和巴斯奎特的時期,他們的作品先前只被當作“涂鴉=亂畫=違法行為”。
于是我采訪了他們。回到東京后,為了寫報道,我開始找各種參考資料,閱讀《美術手帖》和《藝術新潮》,結果到處都沒有刊載相關信息。
于是,我一開始當然會認為自己押錯了,因為專家完全沒提到過他們。不過這種狀況實在太常發生,久而久之我突然間就想通了:專家只是沒實際去過那里,所以不知道罷了。他們有知識但沒有行動力,所以無法知曉該領域正在形成的新潮流。另一方面,我雖然沒有知識,但有行動力……或者說有經費。(笑)而且主管也從來不曾對我說:“去向專家確認文章內容有沒有錯。”現在回想起來,他認同我的地方并不是我對采訪對象的客觀評價,而是我身為采訪者非常享受采訪對象帶給我的樂趣。就這樣,漸漸地,我不再信任專家說法,轉而相信自己的眼光和感覺。對我來說,這是做雜志的十年里最好的訓練。
只能像那樣自以為是地獨立作業,所以失敗的話會慘到極點,有時手忙腳亂地向旁人求援也來不及了。完全不想回顧的失敗多得很,不過呢,唉,兩個星期后下一期就要出了(當年POPEYE和BRUTUS都是雙周刊),只能告訴自己:失敗就靠下一期扳回一城吧,沒別的辦法了。然后硬撐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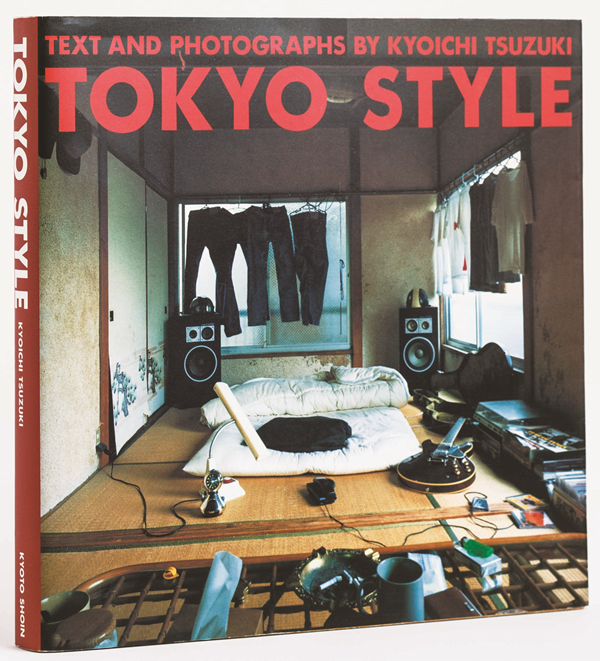
都筑響一的《東京風格》封面
前面提到,我沒想太多,順勢就成了編輯。不過在POPEYE打工期間,我其實考慮過考研究生,繼續研究美國文學。因此,當我赴美采訪,在當地發現同代年輕人喜歡的年輕作家時,都會興奮地把他們寫進報告中。可是教授們卻毫無反應。
也許現在也沒什么差別吧?當年大學的美國當代文學課堂上,“當代”指的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他們。兩人都老早就過世了啊……那種狀況看久了,就會對學院的封閉性,或者說遲鈍性、慢半拍感到極度厭煩。
于是我漸漸地不在乎學校,越來越覺得跑現場有趣。
四年級交畢業論文的時候照樣為了POPEYE跑到美國去采訪,交不出東西結果留級一年。第二年校方大概想給我留情面,決定讓我畢業,但對我說:“我們是特別網開一面,所以你別參加畢業典禮。”我到現在都還沒去拿畢業證書。唉,不過我也不想要啦。
遇到真正新穎的事物時,并不是每次心里都能迸出一句“太棒了”!既然新,你當然沒聽過名字,也沒見過,無法判斷好壞。不過碰到的瞬間內心會騷動。
要斬釘截鐵地說它“好”,當然會很不安。也許只有自己不知道它,也有可能完全押錯寶。
即使到了現在,我大部分的報道都還是懷著這種不安做出來的。(真的!)克服這種不安的方法之一,就是把花錢作為考慮基準。
比方說,當我考慮做冷門畫家的特輯時,只要問自己會不會想掏錢買對方的作品就行了,這樣立刻就能判斷自己是“喜歡到愿意花錢”還是“覺得好像還不錯所以想采訪看看”。養成不要立刻上網搜尋的習慣,靠自己的頭腦與內心感受進行判斷。這也許是培養自己的嗅覺最不費功夫的方法吧。
假設我和責編兩個人去某個陌生城鎮采訪,當午餐時間來臨時,如果那個編輯一下子就拿出手機查“Tabelog”(日本類似大眾點評的網站),我絕對無法信任他。我們不該遵從他人意見,應該先靠自己挑選,先吃吃看再說。也許會吃到萬分糟糕的餐點,也可能會挑到從沒吃過的美味食物。所謂磨煉嗅覺、強化味蕾,指的就是這么一回事。
事前查“Tabelog”決定好要去哪家店,或者先自己挑、先吃吃看——總覺得人的工作方式也會隨著這個指標產生分歧。因為每個領域都有類似“Tabelog”的系統。
美術也好,文學也好,音樂也好,在這些領域如果不試著自己開啟新的一扇門,把他人的評價放一旁,就無法累積經驗。反復經歷成功與失敗,久而久之,當你看到覺得好的東西,不管其他人看法如何,就能斷言它是好東西了。“逐漸增加段數,開始我行我素”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說到底,比起押錯寶被恥笑,想做的東西先被別人做了更令人不甘心、更討厭吧。沒有這種想法的編輯還是轉行比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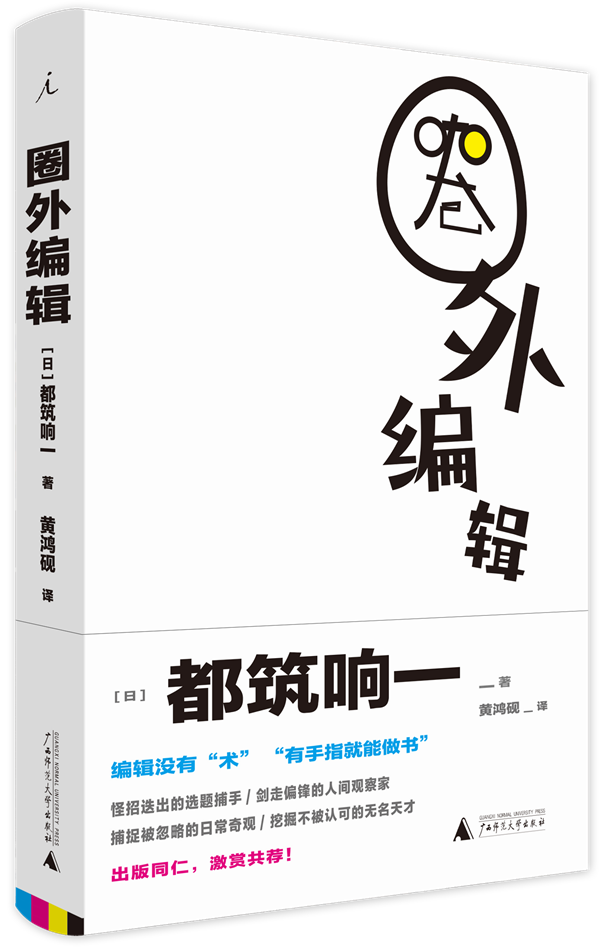
《圈外編輯》,【日】都筑響一/著 黃鴻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21年1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