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等收入國家應如何設計增長政策,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國家應該如何促進生產率增長,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呢?本文將圍繞決定企業生產率和生產率增長的潛在因素展開討論,分析企業擴大規模的潛在障礙,重新審視縱向目標政策(或部門政策)的作用,并在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中等收入國家新增長戰略的必備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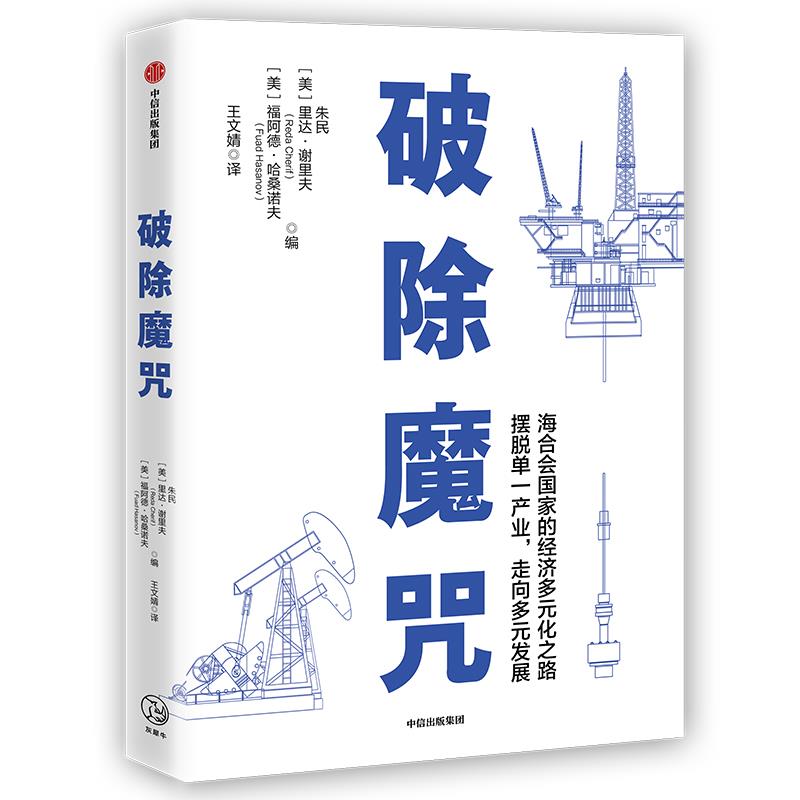
《破除魔咒》,朱民、里達·謝里夫、福阿德·哈桑諾夫 編,王文婧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月出版。
促進生產率增長
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是如何促進生產率增長的?觀察各國的技術浪潮及其擴散模式,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么?本文基于以上問題對生產率增長的決定因素展開研究。首先提出一個簡單的框架,分析生產率的增長來源,接著看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何實現增長,最后分析、比較各國的技術浪潮及擴散模式差異,并從中吸取可用的經驗教訓。
思考生產率增長來源的框架
索洛在1956年開發出的模型表明,在沒有進行技術升級的情況下,人均GDP無法實現長期增長。此外,也有其他證據表明,生產率增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Helpman,2004)。但哪些因素能夠促進生產率增長呢?熊彼特范式為這類問題提供了一個可用的思考框架,圍繞以下四個主要思想展開。
第一,生產率增長離不開以效益為導向的創新。這里所說的創新,可以是流程創新,進一步提高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也可以是產品創新,推出新產品等;或者是組織創新,使生產要素更加有效地組合起來。政策規劃和機構建設能夠增加預期效益,不僅如此,還能促進知識產權保護、研發稅收抵免,加強競爭和優質的教育體系建設。因此應該積極發揮作用,進一步激勵創新,加快生產率增長。
第二,創造性破壞。有了新的創新成果就要淘汰已經過時的舊技術和舊技能。同時,這也反過來表明了在增長過程中進行再分配的重要性。
第三,創新既可以是推動特定領域前沿技術繼續向前發展的“前沿”創新,也可以是“模仿”或“適應性”創新,使企業或經濟部門趕上目前的先進技術水平。這兩種類型的創新,需要不同的政策和制度予以支持。
第四,熊彼特波動。這就是大技術浪潮塑造技術發展史的地方。大技術浪潮指的是新通用技術(如蒸汽機、電力、信息通信技術等)傳播到不同的經濟部門的過程。
促進發達國家的生產率增長
前沿創新是發達國家促進生產率增長的著力點。加大對大學教育的資金投入,最大限度地提高產品和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并發展依賴股權融資的金融體系,這些做法都能促進發達國家的生產率增長。
阿格因和布倫德爾等人(Aghion,Blundell and others,2009)向大家展示了,競爭水平(以滯后的外國進入率來衡量)對國內現有企業的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大致來說,在各行業中,那些技術水平越接近全球領先水平的企業(與中位數相比),越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實現生產率的快速增長。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競爭回避效應”,這類企業提早進行創新,幫助它們避免了更激烈的競爭。相比之下,世界范圍內的那些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的企業,在面臨激烈競爭時,其生產率卻表現出增長乏力的狀態。這也反映出一種“抑制效應”。總之,一個國家的生產率越是接近世界領先水平,其中等水平以上的企業就越多,產品市場競爭就越能促進其生產率的提高。同樣,人們也能看到,越是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就越能加快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促進發達經濟體生產率的加速增長。
碩士教育是促進發達經濟體生產率增長的另一個杠桿。前沿創新離不開優秀的研發人員。阿格因和布斯坦等人(Aghion,Boustan and others,2009)的研究表明,美國發展水平越高的州,也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越高的州,其研究教育對于提高生產率方面的作用就越大,加利福尼亞州和馬薩諸塞州就屬于這類情況。與此同時,對于亞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發展水平欠佳的州,兩年制學院教育也能有效提高生產率。以上結論對于其他國家同樣適用: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高等教育尤其是碩士教育對于提高生產率的幫助更大。
金融部門對于提高生產率也很重要。正如科赫(Koch,2014)所表明的那樣,選擇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能夠更有效地幫助欠發達國家提高生產率,而對于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來說,基于市場的金融體系更有助于提高生產率。
阿格因和阿斯肯納齊等人(Aghion,Askenazy,and others 2009)針對信息通信技術在總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額,進行了一組生產率增長的跨國面板數據回歸分析,發現信息通信技術對生產率增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但有趣的是,研究人員發現一旦對產品市場監管因素進行控制,信息通信技術的影響作用就不那么明顯了。這就反過來表明了產品市場自由化對發達國家生產率增長的重要作用,可以說是關鍵作用,這也是信息通信技術浪潮能夠在各經濟部門間加速傳播的原因。塞特和洛佩茲(Cette and Lopez,2012)證實了這一點,還表明與美國相比,歐元區和日本在信息通信技術的傳播普及方面做得還不夠,并因此受到了負面影響。學者們通過計量經濟學進行分析,發現歐元區和日本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但國家對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的監管卻比較多,故而認為制度因素是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這就意味著這些國家只有通過結構改革,才能進一步趕上美國信息通信技術的普及程度,嘗到生產率加速增長的甜頭。
塞特、洛佩茲和梅雷塞(Cette,Lopez,and Mairesse,2013)利用上游部門的投入數據,分析了上游服務業部門的反競爭法規對下游產業生產率增長的影響。通過分析經合組織15個成員國在1987-2007年的一組不平衡的國家-產業面板數據,發現上游反競爭法規會對下游產業的生產率增長造成顯著的不利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會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下游產業的研發和信息通信技術的投資發揮作用。
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
適應性創新和要素積累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實現增長的主要方式,謝和克勒諾(Hsieh and Klenow,2009)對此進行了研究,并強調了投入再分配效應的重要性,這一點尤其在比較印度和美國的企業生產率分配時就能發現。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在美國的發展空間也很有限,而生產率較高的企業發展勢頭更足。或者說,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很難在印度發展壯大,但生產率較低的企業反而更容易在印度存活下來,這與美國的情況恰恰相反。因此,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只有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中才能更有效地運作起來。這種差距可以歸因于各種潛在因素,和美國相比,印度的資本、勞動力和產品市場僵化,技能發展水平低,基礎設施質量較差,產權保護和合同執行的質量也不高,這些都是阻礙印度企業生產率增長的潛在因素。但這些因素也反過來提供了一些實現生產率增長的途徑。其中,管理實踐這一增長途徑特別有意思。最近的研究成果(Bloom and Van Reenen,2010)表明,印度的管理實踐水平跟美國相去甚遠,而且各國在管理上的平均得分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水平密切相關。
企業實現增長的阻礙
有關企業動力及其對總體生產率增長的影響,有大量的研究文獻。其中關于增長、再分配和企業動力之間相互作用的著作中,比較突出的有克萊特和科頓(Klette and Kortum,2004)、阿西莫格魯等人(Acemoglu and others,2013),以及阿克希吉特、阿爾普和彼得斯(Akcigit,Alp and Peters,2014)的論文。這些論文以熊彼特增長范式(Aghion and Howitt,1992;Aghion、Akcigit and Howitt,2013)為基礎,將企業建模為多線生產者和創新者。創新能夠提高企業在生產特定中間產品時的生產率,擴大現有企業規模,即企業經營的產品線數量。外部因素對現有企業產品線的成功創新消除了該企業產品范圍內的這條產品線,減少了企業覆蓋的產品線數量。這種框架產生了一種均衡穩態的企業規模分布,這不僅依賴于創新技術、政府對現有企業和潛在新進企業的政策以及監管或信貸市場特征,也會影響企業進入市場的能力以及進入市場后的發展能力。
特別的是,有關企業動力和企業規模分布的各種典型事實可以用熊彼特框架來解釋,這些事實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企業規模分布存在嚴重偏差。
第二,企業規模與企業壽命高度相關。在熊彼特框架中,新企業都是單線企業,要想發展壯大并擁有更多的生產線,就需要對現有的所有生產線進行創新,而且企業以往經營的大量生產線還要在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中幸存下來。
第三,小企業會更加頻繁地退出市場,但那些幸存下來的企業往往會在后面的發展中超過平均水平,實現更快增長。一次外部創新就能淘汰一部分單線企業,而幾次成功的外部創新就能把最初的多線企業淘汰出局,因此小企業的退出會更加頻繁,但幸存下來的企業更有可能成為有效的創新者,并且能在多條產品線中進一步挖掘研發的協同效應。
第四,美國整體研發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在職者完成的。
第五,新加入的企業和市場內現有企業之間的投入再分配是生產率增長的重要來源。
熊彼特框架還能解釋,為什么那些抑制發展中經濟體企業規模增長的因素也會抑制總體生產率增長。阿克希吉特、阿爾普和彼得斯(Akcigit,Alp and Peters,2014)認為,在發展中經濟體中,在企業發展壯大的同時,合同糾紛也會更加激烈。隨著公司掌握的產品線數量逐漸增加,企業管理者很難回避那些阻礙企業發展的因素。但這反而抑制了那些最高效的企業,也就是具有較高創新能力的企業的增長。這些企業的增長動力不足,在于企業所有者希望同管理者一道解決阻礙企業發展的問題。但創新能力較低的企業為了避免被創新能力更強的企業所取代,反而會在更長的時間里保持積極態度。
雖然契約的不完全性和信任不足是阻礙企業增長的明顯障礙,但之前的研究也強調了現有企業因研發、廣告、創建新企業以及勞動力市場法規變化等原因引起的成本調整給企業發展帶來的影響。
阿格因、法利和斯卡佩塔(Aghion,Fally and Scarpetta,2007)以實證研究為依據,證明了金融發展對于不同規模的新企業以及對于企業成功進入市場后的增長的影響。巴特爾曼、霍爾蒂萬格、斯卡佩塔(Bartelsman,Haltiwanger and Scarpetta,2004)等學者通過產業和規模等級等統一的企業數據,并以處在工業化過渡過程中的拉美國家為樣本進行研究。他們考慮了金融發展的兩個主要指標——私人信貸比率與股票市值,并使用了一套詳細的監測指標,將銀行和證券市場當作控制這些金融發展變量的工具。繼拉詹和津伽勒斯(Rajan and Zingales,1998)之后,他們為了盡量減少變量偏差和其他錯誤,讓不同的金融發展指標與美國相對依賴外部融資的對應部門進行相互作用。
阿格因、法利和斯卡佩塔(Aghion,Fally and Scarpetta,2007)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首先,較高的金融發展水平能夠幫助企業進入那些更加依賴外部融資的部門;
其次,更高的金融發展水平更能夠幫助小企業進入市場,然而對較大的企業來說,金融發展既不會有正面影響,也沒有負面影響;
最后,當企業進入更加依賴外部融資的部門后,金融發展也會增強企業進入該部門后的增長,這種情況即使在控制勞動力市場法規時也成立。
直到目前,關于規章制度對企業發展動力和企業規模的影響這一話題還沒有太多研究,但這一課題本身就很有意思。2013年,加里卡諾、勒拉爾熱和范·雷南共同撰寫了一篇論文,分析了法國50個員工監管閾值的靜態福利效應,并指出了分配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企業規模的低效集中度恰好低于閾值(Garicano,Lelarge and Van Reenen,2013)。
我們還需要制定縱向目標政策嗎?
爭論
不論是從產業層面到企業層面競爭重點的變化,還是有關企業層面的競爭力與生產率之間關系的證據,或者是有關促進生產率增長的決定因素和政策的相關討論都指明應該優先進行橫向發展,也就是優先制定能夠促進所有部門生產率增長的政策,作為縱向目標政策的替代政策。這種優先橫向發展的政策可以涉及競爭、勞動力市場自由化以及專利和研發等方面。但縱向目標政策是為了增強特定產業與其他國家類似產業在全球中的競爭力而采取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普遍采取了這種縱向目標的發展方式。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也贊同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政策,用國內需求拉動產業發展。這些機構也同樣支持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通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及保持低估本幣匯率等方法促進出口發展的方式。在“二戰”后的二三十年,這兩類國家都實現了迅速增長,而且關于它們所采取的這些產業政策也沒有太多爭議。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縱向目標政策就受到了越來越多來自國際金融機構的學者和政策顧問的批評,尤其是這種政策允許政府以自由裁量的方式選出“優勝者”和“失敗者”,并因此增加了當地既得利益集團利用政府獲利的范圍。弗蘭克爾和羅默(Frankel and Romer,1999)還有瓦茨阿格(Wacziarg,2001)的實證研究不僅指出了貿易自由化對增長的積極影響,還特別強調了反對縱向目標政策的案例,后來有關競爭和增長的研究(Aghion and others,2005;Aghion and Howitt,2006)也是如此。
但是21世紀以來出現的三種現象,又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首先,因為氣候條件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如果政府不進行干預,鼓勵清潔生產和創新的話,全球變暖將進一步加劇,并在全世界引發多種不利的外部環境因素,比如干旱、森林砍伐、移民和沖突等。
其次,全球金融危機也揭示出自由放任政策導致一些國家,特別是南歐國家,以犧牲有助于長期融合和創新的貿易部門為代價,放任非貿易部門,尤其是房地產業的肆意發展。
最后,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突出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對產業政策的不斷追求。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開始譴責自由放任政策帶來的危險,這些政策導致發達經濟體將注意力集中在上游研發和服務業,卻將制造業任務外包給那些勞動力技能水平不高但成本很低的發展中經濟體。但也有些學者指出,德國和日本通過尋求更加積極的產業政策,有效地維持了價值鏈的中間制造環節,這一點又反過來幫助它們從其他外包部門獲得更多效益。
如上所述,學者對于工業干預主義的辯駁主要圍繞在它對“優勝者”的選擇上。誠然,產業政策總會側重發展某些領域,有計劃地選出優先發展的部門,但正如英國商業、創新和技能部前大臣文森特·凱布爾(Vincent Cable)所指出的,這種意義上的“優先發展的部門”是政府經過判斷認為將來所需要的技能(Cable,2010)。然而本文卻認為挑選“優勝者”的論點站不住腳,尤其在政府選擇特定部門而非特定企業時,以及政府通過部門干預措施保持甚至增強相應部門內的競爭和熊彼特范式選擇時。
對傳統產業政策的另一個批評在于其捕捉和尋租行為的風險。但是在對產業進行選擇和治理(競爭力和退出機制等)時,制定明確的規則應該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
從根本上看,知識溢出是支持增長型部門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舉個例子,選擇在非清潔技術方面進行創新的企業并沒有內化一個事實,就是這些技術當前的發展也能使未來的創新更加有利可圖。一般來說,當企業選擇進行生產和創新時,并不會將那些可能對其他企業和部門有利或者不利的外部因素內部化。信貸約束也能起到強化的作用,進一步限制或者減緩企業向新的、更有利于推動增長的部門進行再分配。人們可以爭辯說,市場失靈的存在不足以證明部門干預的合理性。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活動,尤其是高科技部門中的活動,會對其他資產高度無形的經濟部門產生知識溢出效應,從而增加了企業從私人資本市場中融資以促進增長的難度。因此,政府確實有理由對這些部門的進入和創新進行補貼,確保這些部門內部的公平競爭。這時候,我們通常能夠想到能源、生物技術、信息通信技術及運輸這幾個部門。
關于產業政策設計與治理的再思考
納恩和特拉夫勒(Nunn and Trefler,2010)進行了一項有說服力的實證研究,支持推行經過適當設計的產業政策。學者注意到關稅保護措施更加側重于技能密集型,也就是說更偏向于那些使用熟練勞動力的活動和部門。因此,他們通過一組國家的微觀數據來分析一個國家的生產率增長是否如幼稚產業保護理論的觀點那樣,受到側重于技能密集型關稅保護措施的積極影響。他們發現,生產率增長的確與關稅保護所導致的“技能偏差”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當然,這種相關性并不意味著絕對的因果關系,這兩個變量可能都是國家機構質量等其他因素造成的結果。然而納恩和特拉夫勒(Nunn and Trefler,2010)表明,這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至少有25%的因果關系。分析表明:對于產業政策進行適當的定向設計(這里指的是技能密集型活動和部門),不僅可以促進被補貼部門的增長,還能帶動整個國家的增長。
阿格因等人(Aghion and others,2012)認為部門政策不應與促進競爭的政策相悖。他們開發了一個簡單的模型,表明可以通過定向補貼的方式促使多家企業在同一部門中運營,而且該部門的競爭越激烈,企業就越需要進行創新來避免競爭。這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產業政策的設計,而且產業政策應該側重于特定的經濟部門,而不是特定的企業(或者說國家冠軍企業)。這又反過來提出了新的實證分析,即某些部門的干預措施可能會導致某些有關生產率增長、專利申請,以及其他促進創新、創業的措施發生倒退。這些措施將與各部門的競爭程度相互作用,并且對每個部門的干預并不僅僅集中在某一個企業,而是涉及一部分企業。
為了研究國家對經濟部門的補貼與該部門產品市場競爭程度之間的相互作用,阿格因等人(Aghion and others,2012)使用了《中國商業調查》(針對中國所有銷售額超過500萬元的企業進行的年度調查)中各個產業的企業面板數據。ak樣本選取的時間范圍從1988年到2007年,調查包括投入和產出、國家對企業的補貼等信息。產品市場競爭程度用1減去勒納指數來計算,而勒納指數則是經營利潤減去資本成本再與銷售額的比率來計算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產品創新(新產品產值與總產值之比)均與國家對某一部門的補貼以及該部門市場競爭之間的相互作用呈正相關關系。因此受補貼部門的競爭越激烈,國家定向補貼對該部門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和產品創新的積極作用就越大。事實上,如果該部門的競爭程度較低,那么這種影響就是負面的,而在競爭程度足夠高的部門就會產生更加積極的影響。此外,當國家發放的補助相對分散時,某一部門的國家補助與其產品市場競爭之間也會產生更加積極的相互作用。事實上,如果將注意力限制在國家補貼集中程度的第二個四分位數(指國家援助不是非常集中的部門)上,就能發現國家補貼會對所有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和產品創新產生積極影響,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超過中等水平。
清潔創新
在自由放任的經濟環境中,企業可能會朝錯誤的方向創新,比如進行污染型能源方面的活動等。這些企業雖然獲得了進行這類活動的專業知識,但并沒有考慮到這一選擇所帶來的環境和知識外部效應。阿格因等人(Aghion and others,2013)對一組汽車產業專利的跨國面板數據進行了研究。他們先是對作用于內燃機的非清潔創新和電動汽車等清潔創新進行了區分,發現企業在過去進行的非清潔創新比例越大,該企業在目前所進行的創新的污染性就越重。這種路徑依賴現象以及到目前為止進行的大多數非清潔創新都說明,如果沒有政府干預,經濟活動中往往會產生更多的非清潔創新。因此,政府干預能夠使技術朝著清潔創新的方向轉變。
正如阿西莫格魯等人(Acemoglu and others,2012)所說的,不盡早進行直接干預不僅會導致環境的進一步惡化,還會阻礙清潔創新活動的盡早開展。這樣下去,非清潔創新會繼續加強其領先優勢,提升非清潔技術的生產率,并進一步拉大與清潔技術之間的生產率差距。因此,清潔技術想要趕上這種逐漸擴大的差距并取而代之就需要更長的時間。緩慢增長是這一追趕期的主要特征,越是往后拖延,進行干預的成本就越高,這其中的代價是昂貴的。
其實不難理解,越早進行干預,貼現率就越高,現值越低,成本也就越低。這是因為暫緩干預后所獲得的收益在一開始就是以更高的消費形式來實現的,但長遠的損失則會表現為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和消費水平的降低,因為這里有兩個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即環境問題和創新問題。雙管齊下比僅在單個方面施力更容易解決問題。因此最佳的政策方案是一方面通過碳價來解決環境的外部效應問題,另一方面對清潔性研發活動進行直接補貼(或對非清潔技術征收利潤稅),以此來處理知識外部效應問題。這種政策方案再次表明了縱向目標政策的必要性。
可能會有爭論說,碳價本身就同時涉及環境和知識外部效應的問題(不鼓勵使用非清潔技術以及對這類技術的創新)。但是單單依靠碳價來解決外部性問題可能會導致短期內的消費驟減。但從兩方面同時發力可以降低之前短期消費的成本,這也強化了立即推行這一政策的必要性。即便從貼現率的價值來看,標準模型也建議推遲,但實際上也應該盡早采取行動。
這一部分的總體討論表明,對特定部門進行適當的干預,比如對技能密集型或者更有競爭力的部門進行干預,可以促進該部門的增長。此外,我們不贊同集中對企業進行補貼的做法。但以上討論只是相關課題的研究起點,如何設計、管理產業政策以促進更有效的良性競爭和創新等,都還有更廣泛的課題需要研究思考。特別是如何設計產業政策才能確保不良項目無法進行再融資?政府如何才能更新其競爭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并將這些新思路有效地納入產業政策設計和實踐的最新思考中?有關氣候變化、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新近占據世界市場主導地位的討論也在不斷地強化我們的觀念,雖然市場競爭是促進增長的主要動力,但不能把專業化完全留給自由放任主義而不加干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即便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也會將精力集中在上游研發和服務上,并將其他一切資源外包給新興市場經濟體,但從長遠來看,這種專門化的模式可能不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方式。
對中等收入國家制定新增長方案的啟示
雖然改善對現有企業的管理方式可以縮小生產率差距,或者實現基于再分配的增長,但從長期來看,并不能實現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自由流動、金融部門發展以及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可持續發展。其中一些特別的原因是:再分配一旦完成,就會耗盡從農業到工業的資源再分配而來的,以及從吸收進口技術而獲得的效率收益;此外,工資上漲還會削弱新興市場經濟體目前向世界其他地區出口的相對優勢。
因此,以下兩個問題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
第一,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何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實現從追趕式增長到創新主導型增長的成功轉型?
第二,這類國家如何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實現更高質量的增長?
企業生產率增長是企業競爭力的最終來源,關于這一點和生產率增長的驅動因素,我們已經進行了很多討論,并由此提出了創新型經濟的四大支柱。
·競爭和創造性破壞。競爭和自由進入更容易促進前沿創新,因為目前處在技術前沿的公司可以通過創新來避免競爭和進入市場所帶來的威脅,而且大多數突破性創新都是由新的進入者完成的。因此,為了保證自由進入和充分競爭,就有必要進行制衡,以盡量減少地方政治家和大型企業之間的勾結。
·頂級研究型學府。近期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表明,各大學想要獲得更高的排名,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對大學系統的投資,而且大學自身還要在預算管理、工資政策、雇傭解聘決策以及學術課程設計等方面掌握自主權。而且這種自主權必須與大學之間和研究人員之間更有效的競爭相互配合。而其他經濟部門則需要通過向下問責制和競爭壓力來取代向上問責的方式(Aghion and others,2010)。
·充滿活力的勞動力市場體系。這一點需要和以下幾方面結合起來:第一,企業招聘和解雇的靈活性;第二,良好的培訓系統,幫助員工應對不同崗位的工作;第三,社會安全保障體系,包括完善的社會保障和養老福利制度以及慷慨的失業救助政策(反過來以進行失業員工培訓并接受新工作為條件)。以上這種兼具靈活性和安全性的體系能夠推動創造性破壞,即創新型增長的全速運轉。
·更加依賴風險資本、私人股本和股票市場的金融體系。創新投資的風險更高,因此投資者既需要獲得上行回報份額,也需要獲得控制權。
因此,新興市場經濟體需要在組織和制度上進行哪些變革,才能實現以創新為主導的全速增長?我們對于當前制度體系的組織方式及其在實踐中的運作方式還沒有足夠的了解,所以目前還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此外,還有一些實證研究和其他偶然發現的證據表明,國家為了刺激以創新為主導的機制建設,可以采取后面這種非常“聰明”的做法,建立能夠實現以下三重目標的財政體系:
第一,增加收入,并對教育發展、大學建設和基礎設施等方面進行投資,促進創新;
第二,進行再分配,避免過度的不平等和貧困陷阱;
第三,以不損害創新者利益的方式鼓勵創新。
此外,“聰明”的國家還會建立適當的體制機制,加強各級政府的相互制衡,以確保充分的競爭,有針對性地使用國家為促進創新而進行的投資,并進行適當的監督。
為了促進新興市場經濟體從模仿型增長向創新型增長的轉變,如果建議其模仿現有的創新導向型經濟體的制度安排,這從某種程度上看有點自相矛盾。
每個國家都必須找到適合本國的發展方式,通過國家機構改革,讓四大支柱充分發揮作用,為以下問題找到自己的答案:如何從現有的制度背景出發,形成有效的競爭政策手段和機制?為了能讓國家在推進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創新型經濟增長時獲得充分的動力,應該引入哪些契約、組織或體制改革,尤其是區域和地方一級的改革?在對區域或地方領導人進行評估并在他們之間組織標尺競爭時,除GDP增長外,如何將環境和社會(即包容性)維度考慮進去。如何改進稅收和福利制度,以便在創新型國家之間達到最佳的標準和實踐,尤其是通過創新激勵措施,協調好重新分配,以及為良好的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進行融資的需要。
結論
在本文,我們使用了現代貿易經濟學的觀點,特別是一國的競爭力取決于該國各個企業的競爭力這一觀點。我們在最近的實證研究報告中表明,企業競爭力與其生產率和發展能力有關。此外,我們還研究了企業生產率的決定因素以及阻礙企業規模增長的潛在障礙。我們認為,提高企業生產率首先需要橫向政策的支持,比如產品和勞動力市場自由化、貿易自由化、高等教育投資等,但也需要設計合理、管理得當的縱向政策助力企業發展。
最后,我們討論了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一些微妙的問題。近期針對跨國和跨產業層面的研究(Aghion,Hemous and Kharroubi,2009; Aghion,Farhi and Kharroubi,2012)表明,推行更多反周期財政和貨幣政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財政政策的反周期性是指國家在經濟衰退期間增加公共赤字和債務,在經濟好轉時減少公共赤字和債務。貨幣政策的反周期性則是指中央銀行在經濟下滑期間下調實際短期利率,并在經濟回升時提高利率。盡管這些政策在經濟不景氣時會造成信貸緊縮,卻可以幫助那些信貸受限或流動性受限的企業在整個經濟衰退周期內進行研發、技能發展和培訓等創新投資,而且如前所述,這些政策還有助于維持總體消費水平,從而保持企業在整個周期中的市場規模。這反過來又表明了創新型經濟能從更多的反周期宏觀經濟政策中受益,通過在經濟衰退期間提高赤字、降低利率,而在經濟回升時降低赤字、提高利率的方式,幫助信貸受限的創新型公司在整個商業周期中維持它們的研發和其他類型的投資增長。
(作者菲利普·阿格因為哈佛大學Robert C.Waggoner經濟學講座教授,本文原題為《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政策設計》,摘自中信出版集團《破除魔咒》一書,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