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追念我們共同尊敬的長輩、熟悉的朋友沈昌文先生
【編者按】
2021年1月10日,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去世。1月18日,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和草鷺文化公司主辦的沈昌文先生追思會,在上海的朵云書院·戲劇店舉辦。追思會由陸灝主持,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戴燕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汪涌豪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江曉原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陳子善,上海巴金故居副館長周立民,著名作家、上海市作協副主席孫甘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總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王為松,真格基金創辦人、草鷺文化董事長王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前董事長陳昕等學者、作家、出版人、媒體人,以及沈昌文先生的侄外孫女沈鍇等出席。以下為部分嘉賓的發言整理。

追思會現場
陸灝:我們今天在這里追念一位剛剛去世的共同尊敬的長輩、熟悉的朋友沈昌文先生。
前年(2019年)夏天,沈公最后一次來上海,在上海書展參加了《八八沈公》的新書發布活動。那天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不忘初心,上海就是我的初心。”我們知道,沈公是1951年3月份從上海去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他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他早年艱辛而豐富多彩的生活,我們平時聽他講和看他的書都了解得非常多。1949年6月,上海剛剛解放,沈公考入了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采訪系,后來他在回憶文章里說,正是因為他進了民治專科學校采訪系,“這以后也就跟文科、跟文化、跟新聞出版業務搭界了”。當年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就在我們今天這家書店所在的長樂路上,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家書店緬懷沈公,不僅是他的初心所在,也是他輝煌的出版生涯的初始點,所以特別有意義。
首先,我大概匯報一下沈公最后的情況。因為在沈公去世以后,媒體的報道說他是在睡眠中安詳去世,這個沒錯,但是并不是無疾而終。我們記得前年夏天沈公來上海的時候,這里大多數的朋友都跟沈公見了面,那時候他雖然耳朵不好,但是身體還是很硬朗,思路也很清晰。那年秋天我又去北京參加了《八八沈公》的宣傳活動,在前門Page One書店,我當時看到他拿出了講稿,寫得很多,但他從頭到尾沒有看講稿,一直拿在手里,沒看,而講得很風趣,很得體。那天晚上我們一些朋友在北京的徽商故里——沈公比較喜歡去的一個飯店,里面有臭鱖魚——給他和白大夫祝壽。那天晚上歡聲笑語,但是沒有想到這是我跟沈公的最后一次見面。
去年一年的疫情,對喜歡社交、喜歡熱鬧的沈公來說肯定影響很大。經常請沈公出去吃飯的俞曉群也沒辦法找沈公了。我過一段時間跟他的女兒沈懿聯系一下,了解沈公的情況。她說他還可以,每天在家就是上網弄電腦,已經搞壞了三臺電腦。去年書展,他沒有能來。三聯書店的副總編鄭勇來,跟我說9月26日是沈公的生日,三聯書店想給他搞一個祝壽活動,讓我到時候過去。但后來9月份沒有舉辦,一直到10月16日三聯書店給他搞了一個祝壽宴,范圍很小,就是三聯書店的領導加上趙珩、揚之水等幾個熟人參加。他們傳了照片給我,那個時候照片上老沈就瘦得非常厲害,我說怎么瘦成這個樣子,他們說不只是瘦,腳還腫,有腹水,可能是有病。聽鄭勇說他們去接他的時候是一輛商務車,他的腳就抬不起來,后來送他回去的時候,換了一輛低一點的車他才能上車。
那天飯后過了一兩天他們就把他送到醫院里去了,檢查出來說是肝癌晚期。沈懿說他住院三天吵了三天要出來,后來很快就出院了,出來的時候看到他照片又很神氣了,俞曉群他們還請他出來吃過飯。沈懿告訴我,確診是肝癌晚期,但并不是最末期,生活完全自理,他們每個星期帶他到外面去吃頓飯,還可以,還每天上網,晚上還做點簡報掃描之類的事情……
元旦過后,更虛弱一點。一直到1月9日,那天是星期六,沈懿說他有點糊涂,像微醺狀態,沈懿用按摩器給他敲背,他搖頭晃腦好像很舒服的樣子。那晚沈懿就留在了沈公那里住,半夜看看他情況還蠻好,呼吸平穩,但到早晨6點鐘去看,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體溫還在,所以她趕快打120。120過來說已經去世了,可能是6點多剛剛去世。我們大家熟悉的、喜歡熱鬧、喜歡胡說八道、風趣幽默的沈公就此永遠離開了我們。
離開了。沈公的家人本來也不準備任何的儀式,但是三聯書店討論下來,沈公在出版界的影響那么大,而且那么多人也想去送送沈公,所以他們還是覺得應在八寶山舉辦一個告別儀式。因為疫情的關系,他們發的訃告里面就說,限制五十個人,但是14日上午的告別儀式,據說還是去了兩百多人。
沈公去世了以后,紙媒和網絡對沈公的報道紀念非常隆重,澎湃新聞不僅做了系列報道,還全程直播了告別儀式。尊重家屬的要求,直播沒有進入告別廳,在院子里采訪了一些參加告別儀式的沈公的朋友。沈公一生喜歡熱鬧,最后走得那么風光,他自己應該是蠻開心的。
在沈公去世之后,鄭勇委托我和揚之水、王為松擬了一副挽聯,就是大家看到的三聯印的沈公簡歷后面的那副:“讀書無禁區,寬容有情有愛,終圓書商舊夢;知道有師承,溯往無雨無晴,俱是閣樓人語。”用沈公出版的書和他自己著述的書名串起,上聯寫他在出版事業上的成就,是作為一個書商的成就,下聯是他作為一個作者后來寫了那么多書,給我們留下的東西。上聯的最后一句,原來是“難圓書商舊夢”,后來給吳彬看,她說改成“終圓書商舊夢”,這樣比較正面一點。我們覺得非常好。老沈一生轟轟烈烈,創造了那么多輝煌,又高壽,瀟灑離去幾乎沒有痛苦,應該是功德圓滿了。
沈公給我們讀者留下最大的影響是他主編的《讀書》雜志,前兩天有人問我,當年《讀書》對我的影響,現在回顧,我所知道的老一輩作者、年輕的學者,幾乎有百分之八十是通過讀了他們在《讀書》上的文章才知道的,包括金克木、張中行、黃裳、谷林、呂叔湘、陳原等等;稍微年輕一輩的學人,也幾乎是從《讀書》上最早了解的,包括今天在座的葛兆光先生,我也是讀了他在《讀書》上的文章才認識他,1990年代以后去北京,跟葛先生的見面,幾乎都是在老沈組織的飯局或者座談上。作為一名《讀書》的骨干作者,跟沈公有那么多年的交往,我們就請葛先生先說兩句吧。
葛兆光:今天來談老沈——我們平常都叫他老沈——其實也有點懷舊的感覺。因為我大概是1986年認識老沈的,也就從1986年開始成為《讀書》的作者。大概估計一下,可能在《讀書》上寫了有40多篇文章,不算太少。但是我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老沈是屬于有故事的人,所以我在這兒只能講一講老沈在當《讀書》主編的那個時代,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說的1980年代——我說的這個1980年代其實一直到1995年。我一直在想,我們今天來談老沈,懷念老沈,實際上某種意義來說是懷念一個時代。
我記得以前李澤厚曾經講過一段話,很多人引用,說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區別是思想家和學問家的不同時代,1990年代就成了學問家上天、思想家落地的時代。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說法。1995年以前,還是老沈在主持《讀書》工作,那時候發表了很多關于陳寅恪、王國維、胡適等的文章,實際上還是在通過學術在講思想,并不是什么學問家上天、思想家落地。我記得那時候我跟老沈在這方面沒有什么太多討論,因為我更熟悉的是吳彬,吳彬的先生曾經是我的一個同事,是編《中國文化》的兩個編輯之一,所以我的很多稿子基本上都是通過吳彬拿到《讀書》上的。
雖然每次見到老沈,都有一點跟他沒大沒小地開玩笑,但是我跟老沈其實沒有那么熟。我這個性格跟老沈好像有一點不大能擦出火花來,因為老沈是一個嘻笑怒罵的人,我是一個可能過于學院式的人。但是我跟《讀書》確實有非常多的交集和往來,所以我想老沈當初開創了中國編輯界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個沒有自己專業、沒有自己特定立場、沒有特別固執角度的人,也許在那個時代當一個雜志的主編恰恰能夠開出一個百花齊放、自由爭鳴的雜志。我想老沈最大的作用就是他沒有自己的偏見,這是他最大的好處。
陸灝:葛先生說跟老沈沒有什么故事,我記得九十年代初有一次他們在華僑飯店討論一個什么評獎活動,正好我在北京,老沈讓我一起過去,有葛兆光,好像還有趙一凡等。討論請誰當評委主席,老沈突發奇想,說我們這次能不能請金先生出來當。我記得很清楚,葛先生一邊搖頭一邊說:“鎮不住鎮不住。”最后還是決定請季羨林先生。這個評獎活動后來好像沒搞成,但葛先生的這個“鎮不住”我印象很深。
陳昕:沈公的成就這兩天已經有很多的人從不同的角度談了,我自己也在兩年前沈公米壽之時,寫過《智者沈公》一文,談了與沈公接觸的往事。今天在這里追思沈公,我想談談沈公最令我欽佩的一點,那就是在錯綜復雜的環境里,沖破重重阻力,想方設法出版好書、辦好雜志,為社會進步作奉獻的本事和智慧。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滄海橫流”的時代,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新的學派,新的學科,恰如千重細浪,滾滾而來。然而,要把這些新思想、新潮流介紹給讀者又談何容易,我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策劃編輯出版黃皮書——“當代學術思潮”時深有感觸。沈公與眾不同,他主要采取的是“向后看”的策略,跳過某些當代敏感的領域,翻譯出版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重要著作。據他自己說,這是從李慎之先生處受到的啟發。于是就有了《寬容》《異端的權利》《情愛論》等風靡一時的著作的出版,影響了整整一代人,讓大家補足了人類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其實不了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思想,是很難真正理解當代學術思潮的。
《讀書》雜志在八九十年代的十年間,之所以能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呼應時代的改革開放主題,團結老中青,包容左中右,推出那么多有思想有創見的文章,也與主編沈公尊重表達的自由,文前文中文后的編輯處理相關,他總是把那么敏感的話題消弭在硝煙之間,讓讀者得到啟蒙。他還常給我們講怎樣做檢討寫檢查的故事,為的是讓更多的好書和文章與讀者見面。他就是有這樣的本事,把一本有著爭議的雜志,辦成讓知識界喜歡、領導也覺得有必要存在的充滿濃郁人文氣息的刊物,以至在《讀書》最困難的時候,連喬木同志都出來,通過投稿的方式以解其困境。
沈公的這個本事不是簡單地通過學習便可獲得的,他更多的是一種政治體驗、人生體驗。不過沈公另一點本事是可以學到的,那就是廣交學界朋友,借用外腦。八十年代初期,新三聯的人文風格在我看來,是沈公從陳原先生一輩那里繼承下來的,而夏衍、呂叔湘、錢鍾書、金克木、黎澍、李慎之等那么多文化名人支撐著《讀書》和三聯,他們筆端下流淌的人文氣息成就了三聯。八十年中期以后,甘陽、梁治平、周國平、蘇國勛、汪暉、黃平等一大批青年學人聚集三聯的大旗之下,提升了《讀書》和三聯出版物的現代學術思想水準。沈公在其中是一個重要的支點,他的組織才能、包容態度和不恥下問,以及各種各樣服務作者的辦法,使三聯獲得了不竭的文化資源。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不恥下問的出版人,八九十年代每次到京看見沈公,他總要放下身段,向我這個毛頭小伙編輯了解經濟學界的方方面面,更不要說他面對名家大腕時的姿態了。有了這樣虛心求教的態度,還會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嗎?
沈公作為一個別具一格的出版人,永遠留在了我們的記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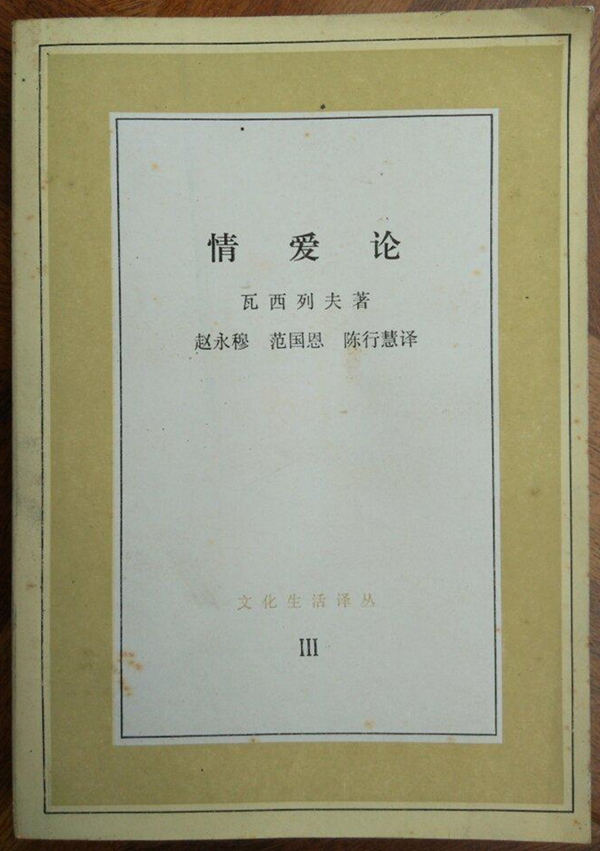
《情愛論》,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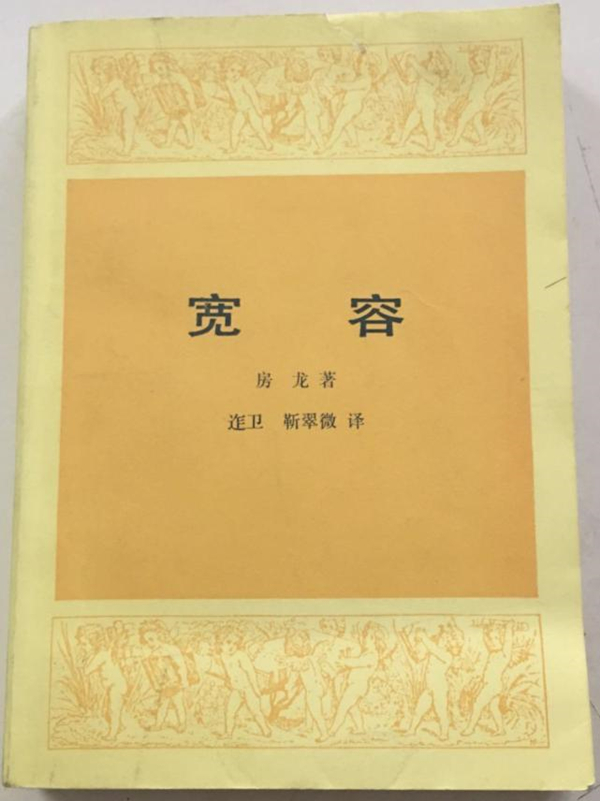
《寬容》,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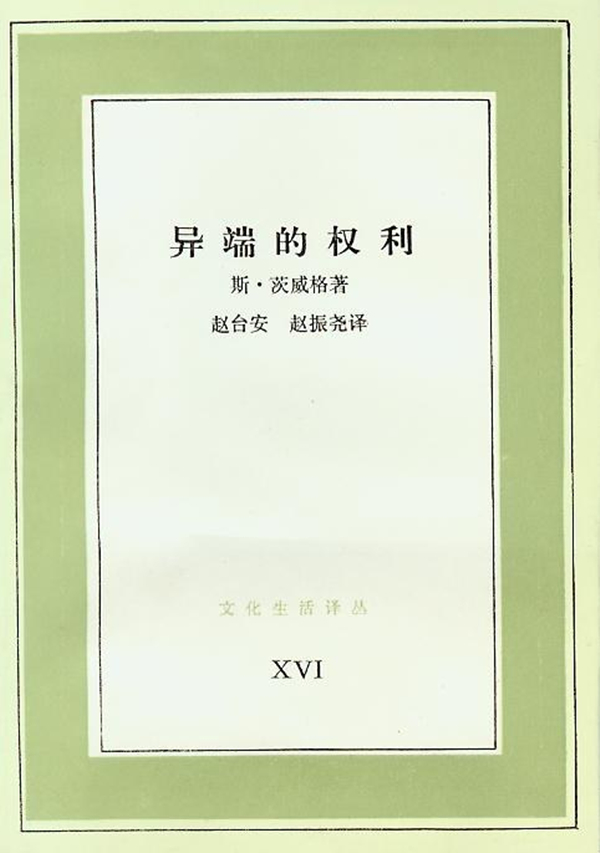
《異端的權利》,1986年
陳子善:剛才大家都講到沈公對《讀書》的杰出貢獻,我就想到1990年代俞曉群跟沈公第一次成功合作“新世紀萬有文庫”也有很多讀者,這個書印得很普及了,價錢很便宜,很多人都從這個書進一步來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這個也值得特別提出來。我也參加一部分工作,接下來的海豚書館我也參加了一部分工作,老沈都是靈魂人物,具體執行的是俞曉群跟陸灝。老沈的眼光很遠大,在他退休以后他的天地更廣闊。還應該要提到,他聯系中國的香港、臺灣,還有美國的很多出版家、作者,金庸是他引進的,蔡志忠也是,都是很了不起的。
在網上看到胡洪俠擬的一副對聯,我說我不會擬聯,我就八個字:何止知道,真正寬容。他是真的寬容。他接觸的人各種各樣,有的都不能發表文章的,但是老沈還是欣賞,真正寬容。
王為松:我跟沈公真正有接觸很晚,但我進出版界就早聞大名。沈公跟我們上海人民社還真有關系,他自己講過好多次,1951年3月份上海人民出版社招聘,他來應聘被錄取。但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時間并不長,就調到北京去了。后來我看他的簡歷里面說是人民出版社委托上海代為招聘,這樣算的話,他說他也應該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員工。2007年,在上海書店的海上文庫里面,我們出了他兩本書,就是《書商的舊夢》和《最后的晚餐》,2011年,我們又把兩本合起來出了一本《任時光匆匆流去》,作為給他八十歲生日的賀禮,沈公講非常喜歡聽鄧麗君的這首歌。
我雖然很晚才見到沈公,但是對我來說,我們并不陌生,或者說,他是我的一位陌生的熟人。因為關于他的傳奇和流言,我早有所耳聞。況且,他主持出版的那些書,我讀大學的時候就見一本買一本,至今仍擺在我的書架顯眼處。我入行后也一直把能夠做幾本像這樣的書作為自己的目標,希望自己像沈公等前輩一樣,做一些能流傳下來、影響一代又一代人的書。但是我很快發現,老一輩做人做事的風范,我們這一代是學不到的。上次范用先生的展覽在上海舉行,我有幸聽董秀玉、汪家明兩位前輩講了不少故事,還是有一點吃驚。當年的編輯為了出書,甚至還要動用各種社會關系,先去幫助解決作者的歷史遺留問題,然后才有可能來為他出書。我就想,那時候的出版社真是管得寬啊。
出版因為它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它連接著社會的方方面面。我記得剛到人民社的時候也聽陳總跟我們說,人民社的編輯,在經濟學會、歷史學會、美學學會等社團組織里往往多是會長或者副會長,起著重要的作用。那時候出版的社會地位相對比較高。后來,我記得我在上海書店的時候,也是和陸灝一起搞過一次“理想的學術出版和學術出版的理想”座談,當時江曉原先生因為出版過多地關注“項目書”而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我想,這也是出版人的擔憂,當一個職業有可能成為市場奴隸的時候,其行業地位就只會往下走。
文化強國必定是出版強國。今天,我們如果要反思的話,那么從沈公等前輩出版人身上,應該看到他們是以一種怎樣的態度來做出版的。以前說對一個作家最好的紀念就是讀他的書,我覺得對沈公最好的懷念,就是如何把一個好的出版理念,把出版對社會的正向推動作用,發揚光大。

江曉原:大家都把沈公和《讀書》聯系起來,現在如果要講沈公的勛業的話,他對《讀書》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內容。剛好在這個事情上,我這兩年老是研究西方的刊物,所以有那么一點點一得之見。我覺得沈公在《讀書》這個事情上所做的探索和貢獻,在我們國內是非常罕見的,我相信很多人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在西方像Nature這樣的雜志,它的第一任主編干了50多年,一直干到死掉,第二任主編干了30多年,也一直干到死掉。這種長期的主編,給雜志造成了強烈的個人風格。我們的《讀書》也是有強烈的風格,這個風格老沈肯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雖然剛才大家都說老沈寬容,其實寬容并不意味著沒有他的個人風格,《讀書》肯定是有強烈的個人風格的。這種強烈的個人風格跟我們國內現在的大部分辦刊理念是不一致的。我們國內的大部分刊物特別是學術界的刊物,他們總說自己是要做學術公器。什么叫學術公器?就是說這份刊物是為這個學術界服務的。學術公器的標準配置是一個編委會囊括了一些名流,特別強調的是匿名審稿制度,稿件都送到外面請專家審閱。絕大多數學術刊物都是這樣辦的,國外也是一樣。這種刊物是辦不成神刊的,因為這樣的刊物一定會變成一個平均化的東西。你要想做學術公器,就不要指望這個刊物有強烈的獨特風格,更不要指望有主編的個人色彩在里面得到反映。因為學術公器是天然排斥這兩個東西的。在西方現在大家所熟悉的Nature這樣的雜志,恰恰是反著來的,Nature的主編多次向媒體強調,我們是沒有編委會,我的稿件是由我決定用不用的,跟外面的人沒關系。我即使讓人審稿,他也沒有權力決定這個稿件用不用,哪怕他們審完,一致槍斃了,我也還可以用,他們一致推薦了,我也可以不用。這種完全由編輯部來決定的刊物國內當然也有,很多科普刊物就是這樣。但是《讀書》從創辦之初起就沒打算當一個科普刊物,用沈公自己的書里面說的,他是要辦成一個思想文化評論。《讀書》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著跟Nature類似的辦刊方式,這就是為什么我在《讀書》40年的那本書里說,我認為《讀書》就是中國文科界的Nature,因為從辦刊的理念上來說它就是這樣辦的。沈公自己在那個書里特別說了,他說有一些文章寫得很好的人,文章本身的內容很好,但是文本差勁,他就不登他們的文章。他對文本有美學追求,這種對文本的美學追求,完全就是沈公的個人風格。
再后來《讀書》經歷了一個嚴重“掉粉”的時期,那個時候已經不是沈公主政了,它讓沈公很失望,所以沈公后來對別人說他現在不看《讀書》了,只看《萬象》,因為對文本的美學追求,那時候又寄托到《萬象》上去了,就是在《萬象》上仍然有對文本的美學追求。當然《讀書》現在又回過去了,又重新開始有文本美學追求了。我那會兒說過開玩笑的話,我跟媒體說,我知道為什么《讀書》現在變得不好看了,那是因為李零不在上面寫文章了,這個話被沈公在他的書里引用,他說這個話流傳很廣。當然《讀書》后來又恢復了對文本的美學追求之后,李零也又重新在上面寫文章了,大家又覺得它好看。這個在《讀書》辦刊的理念中,沈公非常強烈的個人風格,我認為是非常值得學習的,盡管國內的大部分上檔次的學術或者文化刊物,目前看來可能還很缺乏學習的條件,但是至少《讀書》堅持了這條,其他的那些刊物也是可以跟上來的。
陸灝:江曉原先生剛剛說到我學沈公,當然確實從我認識沈公開始,就有追隨沈公、做沈公的徒弟的想法,但是機會不多,因為他后來退休了。本來《萬象》完全是為沈公做的,因為覺得他有那么多資源,那么多精力,退休了,很可惜,再搞一本雜志讓他編。結果這個雜志刊號過了兩年才下來,那時老沈說這兩年我人已經散掉了,你再讓我每個月編一本雜志,我沒那個耐心了,你拿到上海去編吧。我編雜志確實學了沈公,但是沈公在《知道》那書里接受采訪時說了,他編雜志喜歡要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但是《萬象》不強調這個,說我最不喜歡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說我比較喜歡純凈的文化。其實老沈的弦外之音正是我最為欣賞的手段,但是在《萬象》那個時候沒有機會嘗試。后來我協助創辦《上海書評》,《上海書評》的領導們比較開明,所以在這份報紙上多少體現了一部分老沈編《讀書》時候的那些弦外之音。所以,老沈對《上海書評》評價很好,比較合他的胃口,有點弦外之音。
沈鍇:首先還是很感謝今天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大家能夠在上海給公公舉辦這樣一個追思會,非常感謝大家。其實之前每次公公到上海來,我也都會像小跟班一樣地跟在后面去蹭一些飯局,吃一些飯。
公公喜歡吃這件事是從小到大都這樣的,但是我小時候對他的印象就是一個字“臭”。我6歲的時候開始住在西總布,那時候打開冰箱,里面放的全部是王致和臭豆腐,還有他特別喜歡做臭咸魚那種炒飯。他經常會在廚房里面炒一盤炒飯什么的,又臭又香的那種,他自己特別喜歡吃。后來我媽跟我說,其實他那時候已經炒得很少了,我媽小時候應該是吃他做的各種各樣的飯長大的。據說他年輕的時候特別喜歡做飯,應該是屬于酷愛吃的這么一個人。
去年因為疫情嘛,家里面聚餐比較少,10月份查出來他肝癌晚期的時候,按照他的性格,我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住院的,他一定要吃吃喝喝非常開心地過完他最后這一段時間。所以那個時候我爸我媽就給我發消息說,今天我們又去哪兒吃了。當時他們有一個約定,就是每周公公會找我爸去南小街上一個新開的阿文湯包,公公特別喜歡吃這種南方菜,特別是上海菜、寧波菜,那個阿文湯包每周都要去吃。我爸作為一個回請,就會請他每兩周去吃一次俄式大餐,或者江浙菜。
他在家里面還有幾個比較好玩的事情,他在家里面和白大夫、懿阿姨還有我們之間是一種斗智斗勇又聯盟的關系,怎么說呢?他后來耳朵不太好,聽不清了,要戴助聽器,我發現他戴助聽器其實有些間歇性耳背,有的話他就特別清楚地一下子就能聽到,有些話就聽不到。比如說我們去吃飯,要喝啤酒這件事你只要一說啤酒,他就立馬能聽見,立馬就說好的,來一杯,還可以再來半杯;但是如果說要吃藥了,你就怎么說他都聽不見了。所以家里的醫生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們家里面做什么的都有,做醫生的,學化工的,他就會給我們一個一個都起外號,比如說我姐姐學化工出身的,他就說化學家,你什么時候可以研究出一種新藥來,是紅燒肉口味的藥,這樣的話我就能頓頓都吃進去了,我就可以就著酒吃了。
戴燕:我要說的是,老沈對于很多人來講,是在那個特定時代、那個環境一個特別的出版人。其實在同時代跟他一起的,有各種各樣的出版家,各種風格的出版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但是沈公是一個可能再也不會有的一位出版人。他所在的那個時代恰逢其時在變動,他真的是用夠了空間在做事情。就好像說無知為大,他自己沒有一個特別的立場,沒有特別放強的一面,反而使得他有一個很大的空間自由活動,借用各種力量,借用各種資源。而且他真的很有本事,你看他在吃飯時胡說八道,其實他在說那些亂七八糟話的時候,心里早想好了他要干什么。這個真的是讓人佩服的。我想老沈是特別有定力的一個人,這才讓他在飯桌之上,在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時候做成了他想做的事情。
孫甘露: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讀《讀書》對那個時代的精神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包括后來的《萬象》。一個是他編雜志的風格,確實就像剛才幾位老師講的,編法是越出了一個完全學院或研究性雜志刊物的方法。還有剛才江曉原講了,他不僅是編寫得有學術價值的文章,而且是漂亮的文章,通俗講是一種美文。為什么說對我有影響呢?我后來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做讀書會也好,編《思南文學選刊》也好,不是說一個單一的文學雜志、藝術雜志,或者說是一個研究性、思想性的雜志,而是希望通過跨領域的,有小說、有詩歌、有隨筆,包括藝術史的,也包括研究文字的,中外的,把它們放在一起。這實際上跟當初《讀書》雜志,包括后來《萬象》、《上海書評》的風格,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后來陸灝、俞曉群做海豚書館,我也受邀編了一部分,有一個系列是小說。也是受沈公的影響吧,編書的方式以及進入的角度選擇,實際上是拓展了,不管從臺本上,人的選擇上,各個角度,都是在當時的主流出版之外另辟蹊徑。一個時代的出版可能確實也是需要這樣一種看上去像花花草草,實際上都是在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豐富,來印證我們關于時代的記憶或完整性。因為這些花花草草真不是簡單的事情。像《讀書》也好,《萬象》也好,后來的《上海書評》也好,實際上是非常豐富的,在文化的主線上,把那些邊邊角角,人們的想象,人們的日常生活,關于日常生活的記憶,都匯總起來。剛才為松也在講,再過50年,當我們這一代人都過去的時候后人怎么來看待沈公?換了一代人,隔了一代人的時候,可能就是通過沈公所做的工作,編的這些雜志,出版的這些書。當時三聯出了大量的作品,塑造了一個時代的風尚,他的工作或者在飯桌上談笑風生,這些看似是閑話的東西,其實都是有深意的。
最后我打個比方,當然也是借用別人的說法,《藝術的故事》說的,一個時代的藝術的精神風尚就像旗幟一樣,你看見旗幟在飄,但實際上是風在吹,但你直接是看不到風的。一個時代的精神風尚、藝術風尚,是背后有這個東西在驅動,沈公就是做的這個工作。
王強:我當年在《八八沈公》里寫了一篇文章,叫《思想的郵差》。其實沈先生作為一個出版家,最大的貢獻就是思想的郵差,這個郵差非常敏銳準確地遞送思想的包裹,這是我寫那篇文章起這個題目一個非常清晰的印象。因為大家知道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郵差是所有人翹首以盼,最重要的一個人了。后來我一想沈先生無論是編《讀書》的時候,還是《萬象》的時候,或者陸灝他們后來做的《上海書評》,我為什么愿意投稿,就覺得他們實際上是把思想做成了集市、廟會。這個集市充分體現了一種自由的東西,體現了自由、美、高尚道德。
汪涌豪:沈昌文先生與整個1980年代文化的新生是密切相關的。一個人的工作和整個時代變化發展,文脈、氣脈相關聯,這是何其了不起,而且他死后這個時代的標志性人物紛紛懷念他,他的身前是非常精彩的,他的身后也有足夠的哀榮,這是很了不起的。
從他的身上我感到,出版絕對不是和書打交道的問題,出版從本質上說是和人打交道的問題。在這點上沈昌文先生堪稱模范,以前孔子說是有教無類,我認為沈昌文是有交無類,而且交的過程中顯出了難得的識力、判斷力、親和力。為了做成書,他可以屈就、寬容、順從,可以屈己從人,這里面有很大的學問。專業之外要能夠分別事項,體會人情,要能夠應付領導,激勵員工,這些東西都是干出版的人所必備的,但是今天似乎這些都在慢慢消失。
周立民:剛才大家聽到范用跟沈公的事情,恩怨我們不評論,最近我是越來越體會得到,確實他們兩個人是兩個傳統。沈公在他的回憶錄里說,有革命家,有學者,他是學徒。我們可以不這么看,如果從兩個傳統來講,沈公的傳統應該是出版里面比較務實的傳統,范用先生大概是一種精英或者更文人化的傳統。范用的傳統跟巴金、魯迅更接近,他們是不管書賣不賣錢的——當然也不是完全不管。但是他們這些朋友辦出版社,自己不拿工資的,魯迅也是,書不賣錢我自己掏錢印。沈公的傳統可能更接近于鄒韜奮的傳統,老的生活書店是很注重成本,包括跟大眾之間、市場的需求,所以說魯迅跟生活書店鬧掰了很正常,他們的理念就是不一樣的。在這兩種傳統里面,我們這些所謂的文人,肯定更喜歡范用的傳統,因為想怎么樣就怎么樣,但是說實話,這些年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認為這兩個傳統是不可以偏廢的,也是不可以分割的,甚至某種程度上來講,沈公的很多傳統更值得我們重視。
今天再談三聯也好,談沈公也好,談《讀書》也好,我們不應該把他們從那個時代剝離出來,不然的話,可能年輕人或者后輩僅僅把他們當做一個個人的傳奇故事來講。他們是這個時代里面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在這個時代里面,能夠抓住時代提供他們的條件大有作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也不必抱怨今天怎么樣,過去怎么樣,未來怎么樣,時代提供給我們的條件,我們是否充分地利用,或者盡我們知識分子可以發揮的東西,或者堅持的底線,這是在前輩面前需要我們來叩問自己的良心的。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