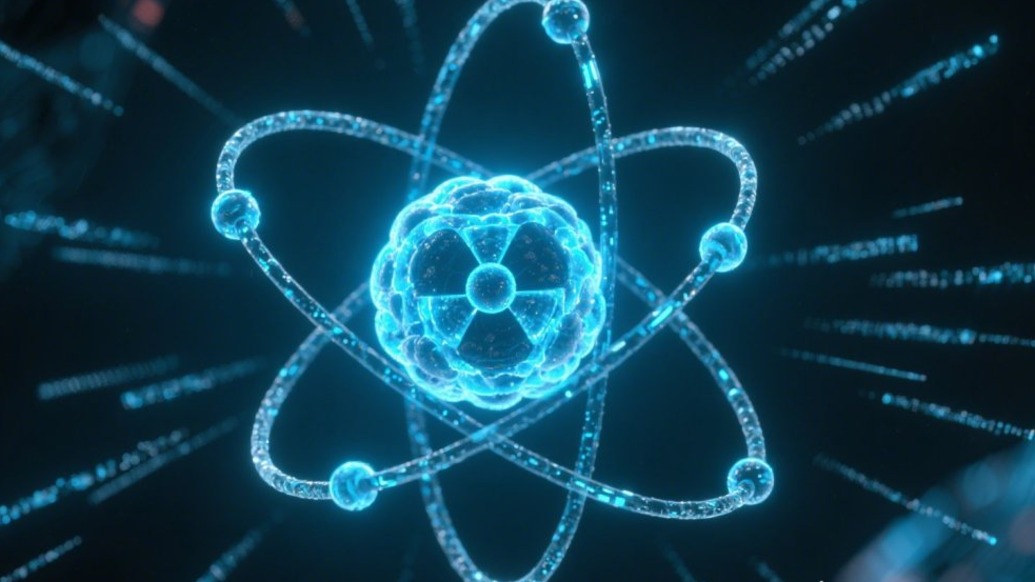- 3
- +167
趙英男評《成人以德》|法律會讓我們更道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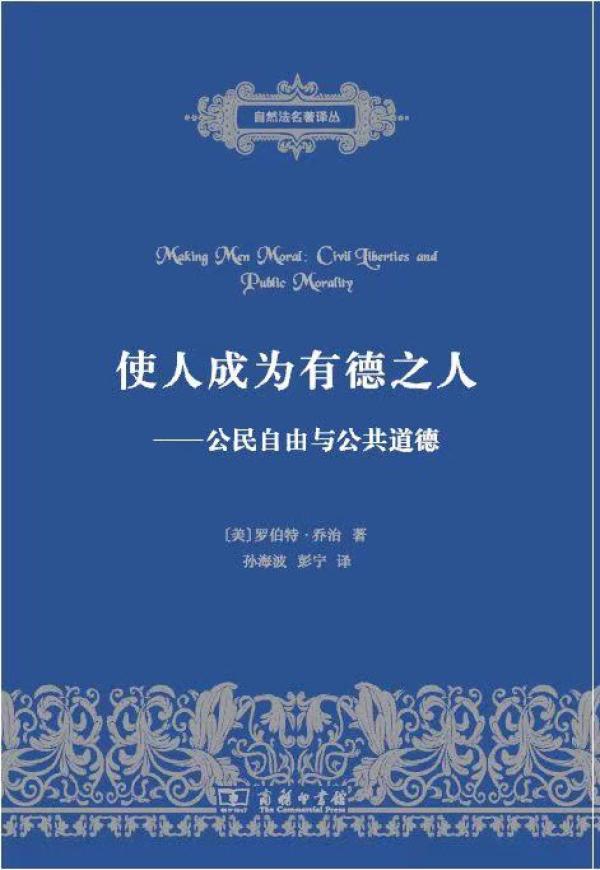
《使人成為有德之人——公民自由與公共道德》,[美] 羅伯特·喬治著,孫海波、彭寧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11月出版,407頁,68.00元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成為一個有德之人,不僅是我們每個人的自我期許,更是這個我們賴以生活的世界中根深蒂固的價值。可惜生活中我們往往不能如愿。當老人抱著孩子走進通勤高峰時的地鐵,疲憊癱坐在座位上的我們總是在掙扎要不要立刻讓座;看到四下無人的十字路口,即便是紅燈我們多半也會覺得直行不停沒有任何問題;明明知道家里的父母期盼著假期與自己團聚,可還是忍不住和朋友訂好了飛往新馬泰的旅游機票;心里清楚世界的某處正有人由于饑餓而掙扎在生命線邊緣,但我們還是喜歡在周五的晚上約好朋友大快朵頤,饕餮之后殘羹冷炙剩滿一桌;口中承認捐資助學是項善舉,可我們還是更愿意用一個月的工資購買最新的蘋果手機,甚至不惜分期付款……
不得不承認,我們在日常生活里有無數時刻稍稍偏離了道德的正確軌跡。可我們是否有權主張這種輕微的偏離是我們的一項權利,他人特別是國家不得干涉?社會中最重要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否可以禁止我們的任意,通過刑罰的威脅或懲罰,讓我們重回道德的正軌,一板一眼地走下去?
當代自然法學派代表人物、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喬治(Robert George)初版于1993年的《成人以德:公民自由和公共道德》(Making Men Moral: Civil Liberties and Public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譯本題為“使人成為有德之人——公民自由與公共道德”)一書,即是對上述問題的系統探討。他希望通過復興亞里士多德-阿奎那所代表的“至善主義”(perfectionism)傳統,保護個人自由的同時,又維護當代社會中由于自由主義泛濫而飽受侵害的公共道德。在此意義上,他的學說既是美國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理念在當代法律與道德領域的映現,又是這種思潮與自由主義多元價值的一次調和。于是,關心喬治教授的論斷,不僅是掛懷抽象的法律理論如何能夠有助于我們理解和改進這個世界,更是操心在共識日漸稀薄的當下社會氛圍中,不同立場之間如何能夠有效溝通與對話;而分析他的論述,則不僅有助于我們剖析他在視個人權利為生命的自由主義,與重視社群價值的至善主義保守傳統之間的調和是否成功,也有助于我們在紛繁復雜的現代社會中厘定道德與法律的重重糾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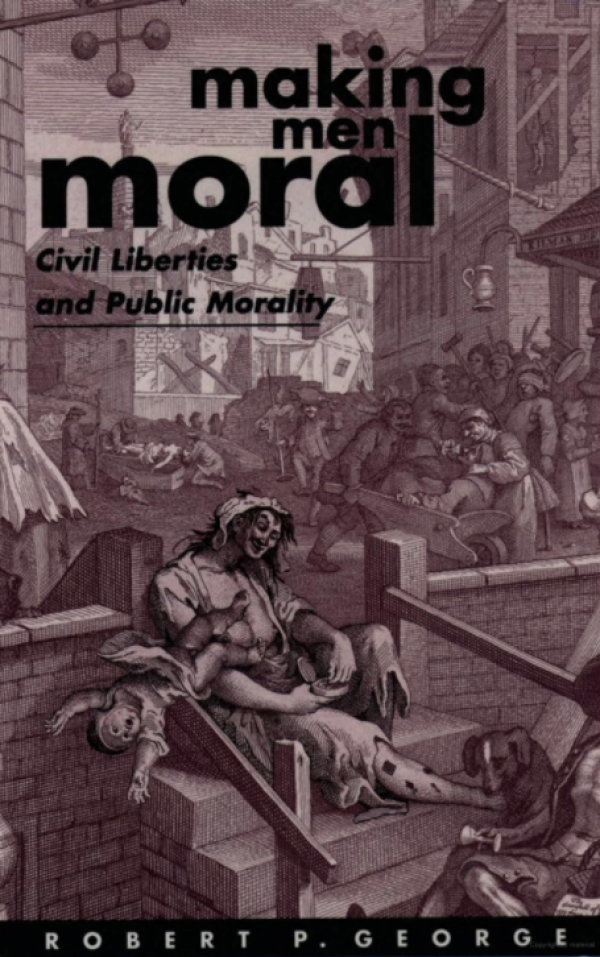
《成人以德:公民自由和公共道德》英文版封面
至善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憂慮
在喬治看來,至善主義指的是這樣一種思想傳統:它往往認為我們的共同體不僅如自由主義傳統所認為的那樣,要滿足其成員在溫飽與安全方面的基本所需,還要使之具備德性。簡言之,共同體不僅關注其成員的基本利益,還關切其道德福祉。具體來說,發揮維系共同體功能的法律,不僅有定紛止爭的作用,還可以“輔助”人們變得更加道德。之所以說法律只有輔助作用,是因為人類意志之外的任何事物都不會增進人們的道德——一個人具備道德,就是說他會自由地選擇去做道德上正確的事物,而非受到強迫或引誘如此。從這個角度出發,法律可以在如下四個方面增進個人與共同體道德:(1)阻止人們選擇沉溺于不道德行為的自我墮落;(2)阻止會誘使其他人模仿同樣行為的壞榜樣;(3)有助于保護道德環境,進而(4)教導人們在道德上的是非觀念。總體來看,在最低限度上至善主義想要表明,我們的共同體與法律并不是中立的,它總會贊成會反對某種價值或立場,這令它會對人們在道德上的某些選擇持支持或允許態度,但又對某些選擇加以否定或禁止。這種態度進一步使得法律在間接意義上影響了人們對于共同體,及其所尊崇價值的態度與行為。
不消說,這種立場會遭到源自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嚴重懷疑。在自由主義看來,共同體的目標是為其成員提供基本安定與和平的秩序,保證其生存基本所需。在成員福祉與道德上的沉默,并不是自由主義共同體的弱點,反而是其美德:唯有如此,共同體才是足夠多元的,才可以容納每位成員的自主選擇和目標。這既保證了他們的平等,又維護了他們的自由。這兩者正是自由主義視域下認為人之為人,或人之尊嚴中最重要的要素。這一立場源自笛卡爾與霍布斯對亞里士多德傳統的翻轉顛覆:笛卡爾以徹底且激進的懷疑打消了一切既定的宇宙論和目的論,它們再也無法為人類提供為之奮斗的先在目標;霍布斯則將恐懼深深植入現代人的底色——無論是對同儕相爭的恐懼,還是對狀似利維坦的主權者的恐懼,都使得人們明白,社會與國家是人為建構的,而非源于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自然或第二自然。因此,出于至善主義可能帶來的后果,自由主義主要有如下三重憂慮。
其一,如果說共同體及其法律不是中立的,而是特定道德立場的體現,這是否會導致多元性的喪失,進而使得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只有一種聲音?在這種情形演化為極致的時候,是否意味著現代各國憲法中確立的、來之不易的各項自由權利喪失殆盡?
其二,如果說共同體及其法律支持特定道德立場,進而鼓勵或允許持有相似立場的公民,反對甚至懲罰與之立場不同的公民,這是否意味著共同體違背了平等關切每位公民的承諾,使公民得到平等對待的道德權利受到侵害?
最后,如果說共同體及其法律具有特定道德偏好,這難道不是意味著它們已經為公民選定了應當追尋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這是不是說每個公民無法自主選擇或決定自己的人生,他們的個人自主權(autonomy)受到了侵害?
可以說,任何基于至善主義的學說都要回應這三重憂慮,因為現代性是我們這個世界必須面對的現實,它既是歷史的(由一系列物質變革產生),又是哲學的(由一系列思想更迭出現),我們并不能單純地以 “回到古典”來應對,否則便是一種逃避。在這一點上,喬治顯然保持了法學家頭腦的敏銳與清明,他意識到闡發自己學說的關鍵便是應對這三重憂慮,因而本書更多是駁論性的,通過批駁對立學說展開自己的觀點。正是因為如此,把握喬治的思想也殊為不易——他往往長于在不同學說間調和穿梭,而對自己立場的勾勒則稍顯簡略。我們先來看他構建自己學說的第一步:對至善主義批判性的繼承。
至善主義中的活東西與死東西
在回顧傳統時,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需要秉持克羅齊對待黑格爾的態度,那就是從當下出發考察其中活的與死的東西。喬治顯然也要對至善主義傳統做此剖析。但這并不簡單。按照以賽亞·伯林的說法,至善主義其實是“西方思想的核心傳統”(19頁,本文所標頁碼系英文版頁碼)。這一傳統內部無疑存在各種各樣的紛爭,但卻秉持著一種一致性,即“優良的政治與善法不僅渴望確保人們的安全、舒適與繁榮,而且也想要人們變得有德性”。從這個角度來說,剖析這一傳統的代表性學說則能起到化繁為簡的效果。于是,亞里士多德和他最著名的評注者阿奎那進入了喬治的視野。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出,“任何一個不是徒有虛名而真正無愧于城邦之名者,必須以致力于實現善德為目的”,“否則的話,政治的聯合只會淪為一種同盟而已……政治聯盟存在的目的并不在于社會生活,而是維護一種良善的行動”(21頁)。為什么會這樣?這是因為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美德與一個人的自然本性(nature)或品格(character)有關,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他指出有些人生來具有美德,但有些人卻生來依靠激情生活,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貴與快樂,只是追逐著自以為的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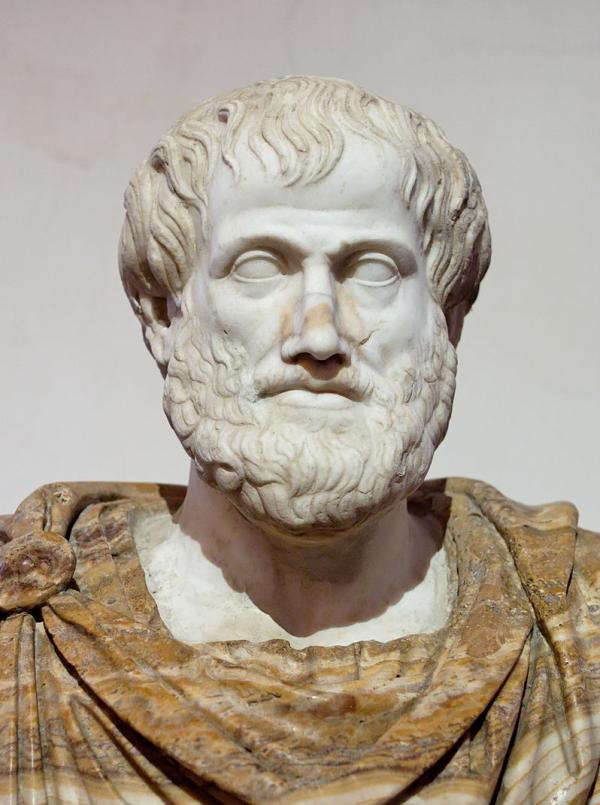
亞里士多德
要想使這些天生并不具備美德的人能夠過上具有德性的生活,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并不能夠依靠單純的道德教化,因為當激情主宰理性的時候,理性論辯總是徒勞無益的。這就使得一種具備德性的共同體生活變得必不可少。法律因之能夠對缺乏德性之人施以強制,通過外在強力約束,使得他們具備德性。這呼應著柏拉圖筆下人與城邦之間的同構:具有怎樣靈魂構成的公民,自然就有怎樣的政制與城邦特征;反過來,政制與城邦特征又深深影響著它的公民。
我們可以將亞里士多德上述講法視為對于刑罰正當性的闡釋,但喬治認為更好的方式,是我們將之理解為亞里士多德在強調社會環境對于個人德性培育的重要性。借助法律的強制力,城邦將其珍視的道德價值貫徹于公民之中,讓每個人的行為都向此價值收斂,特別是使激情主宰理性之人的理性逐漸奪回“靈魂的高地”。在此意義上,法律不僅有助于社會道德生態的確立,同時也是一種公民教化方式,許多人由于法律強制而逐漸意識到或發現自己的自然本性(理性),進而產生對道德價值的尊崇敬畏,這便構成了亞里士多德意義上人之為人的第二自然。
但從當下的角度反思,亞里士多德這套學說不無問題。如喬治所言,我們可能并不具備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共同自然本性,我們的人生也并不都是朝著同樣的目的進發。這種以自然哲學宇宙論為前提的目的論圖景,早已不適合理解現代人。更何況,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許多人生來便不具備德性,這也有違現代社會人人平等這一價值理念。但更重要是,喬治認為,道德是一種反思性的善,這意味著我們要完全基于自己的意志選擇去做符合德性的事情。亞里士多德希望通過法律強制而使人們具有德行的想法難免落空,因為外在強制往往只能帶來人們行為符合道德要求,卻未必能夠使人們內心真正接受和尊崇德性。最后,亞里士多德并沒有言及他筆下的城邦是否會尊崇多元價值。這是喬治認為古典至善主義傳統中一直回蕩的一個頑疾,即便在阿奎那這里也沒有得到解決。
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持有同亞里士多德類似的看法,“……保障他人能夠生活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我們就有必要通過使用強制力和恐懼加以威脅來限制其惡行”(29頁)。但不同于亞氏,他認為每個人的最終目標或終極善不是實現自己的自然本性,而是獲得上帝的神圣福祉,這是教堂得以存在的理由,也是政府得以存在的依據。國王應當通過自己頒行的法律來促進人們的善行,使得人們能夠獲得這一福祉。同時,阿奎那注意到,人類律法與神圣律法不同,因為大多數人在道德上并非盡善盡美,所以人類律法并不是禁止一切惡行,而只是禁止一些為大多數人所盡力避免的較為嚴重的惡行。他進一步指出,法律若想服務于共同善,就一定要“契合一國的風俗”(32頁)。簡言之,法律并不要求人類完美,而是強調與人的實際境況相契合,并不會強人所難。

阿奎那
喬治認為,亞里士多德與阿奎那所代表的至善主義傳統雖然在維護共同善方面有諸多可資借鑒之處,但卻一直未能對善的多元性加以系統論述。這里的“多元性”喬治采取了相對溫和的立場,也即沒有像當代自由主義者那樣將多元主義同相對主義劃等號,而是如以賽亞·伯林一般,強調多元性不過表明了每個人并非任由自己自然本性的擺布,而是能夠以或好或壞的方式調整自己。“人們以不同方式將他們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在不同價值的基礎上作出不同的選擇和承諾,并且這些價值為選擇和行動提供了不同的理由。”(39頁)從這個角度出發,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論點都包含有某種粗糙的精英主義傾向,他們似乎都認為:人類并非生而平等,德性往往源自天生且與其身份地位密切相關;這些社會中的精英群體所推崇的價值或生活,才是每個社會成員都應效仿和追求的。這不僅忽視了多元價值的存在,也忽視了針對同一價值人們可選擇的多種不同實現方式。
但即便如此,至善主義在當代仍有許多價值。首先,它雖然主張國家與法律不是中立的而是某種道德立場的體現,但卻并不主張國家和法律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對不道德行為加以禁止。因為一些行為雖然從道德角度來看是不被允許的,但基于審慎理由(比如,禁止這類行為的成本比較高昂,禁止該行為對人們自由的損害較大等)我們可能并不一定有必要禁止它們。因此,法律依舊是法律,道德也仍是道德,兩者并不能夠彼此混同。
其次,至善主義強調國家與法律在維護公共道德方面的積極作用,但也承認就維護公共道德而言,家庭、教育以及其它社會制度同樣必不可少。國家與法律不是維護道德的唯一工具,甚至也并非第一工具。它在促成人們具備德性的過程中只是起到輔助作用,因為它之所長在于營造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與氛圍,為人們的成長與人生選擇提供有助于德性養成的總體框架。
最后,至善主義傳統承認法律并不會讓我們更加道德,因為法律及其所代表的國家強制力都是推動我們行為的外在因素,而道德則是一種反思性的善,也即我們要從自己意志出發選擇道德上正當的行為。簡言之,是我們自己而非法律與國家,才能讓我們更加道德。
多元至善論的總體框架
在對至善主義傳統加以批判性繼承后,喬治將圍繞自由主義提出的挑戰在法哲學論域中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如前所述,自由主義傳統首先擔心至善主義傳統壓制多元道德立場,這在法理論中體現為哈特-德弗林有關法律能否強制執行道德(法律道德主義)的爭論;其次,它擔憂至善主義傳統會損害人們的道德權利,這在法理論中體現為德沃金對個人權利和集體利益的剖析,以及沃爾德倫對我們錯做事權利的辯護。最后,它憂慮至善主義傳統會阻礙個人自主權的實現,這在法理論中體現為羅爾斯與拉茲有關個人自主權的論證。《成人以德》這部作品的主體便是對以上三重憂慮的剖析。我們現在來依次簡單看看喬治在這些議題中持有的理論立場。
1. 至善論與道德多元
1957年9月,約翰·沃爾芬登(John Wolfenden)爵士向英國議會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他在其中指出,成年人之間彼此同意的同性性行為不應再被視為犯罪,因為這屬于私人道德領域的事物,法律不應干涉。這份著名的《沃爾芬登報告》引發了當時英國高級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德弗林(Patrick Devlin)的強烈不滿:他認為個人道德與公共道德之間并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我們的任何行為都具有公共意味。一種行為如果嚴重導致社會主流意見不滿,那么它就具有可責性,法律也應加以禁止。在此意義上,在道德中放任同性性行為,就如同在政治秩序中放任叛國罪一樣,最終會引發社會崩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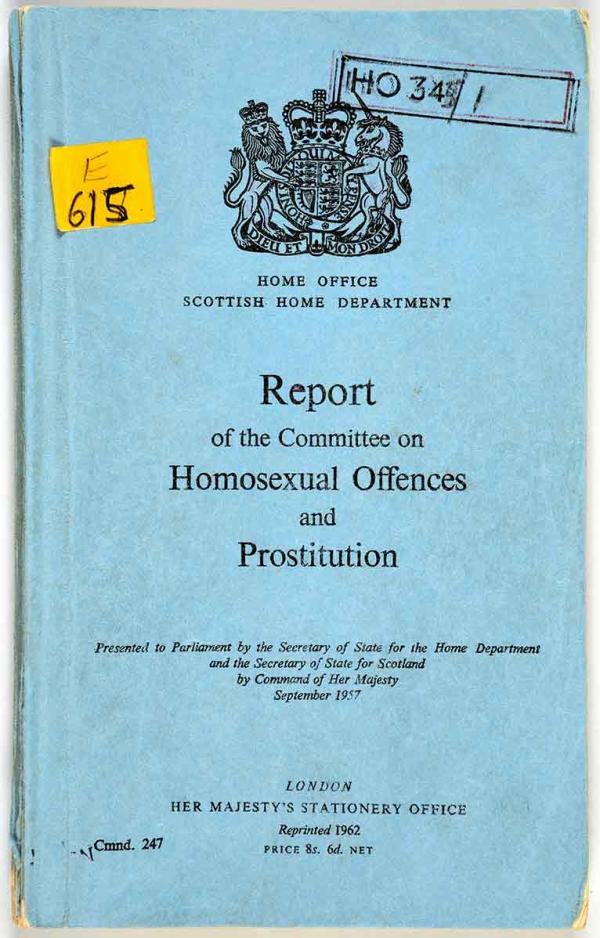
《沃爾芬登報告》
德弗林激烈的措辭使得時任牛津大學法哲學教席的哈特(H. L. A. Hart)非常不滿。他立刻撰文同樣嚴厲地駁斥了德弗林的觀點。在他看來,德弗林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首先,道德崩潰是否會導致社會崩潰,我們應當從經驗層面加以驗證,而非簡單加以斷言。其次,我們的社會中不僅存在實證道德(既定的傳統風俗與習慣),還存在批判道德(我們運用理性對實證道德加以評判和分析)。德弗林沒有理由認為一種行為只要不為主流意見接納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更沒有必要危言聳聽地說一種非主流行為會導致社會的崩潰。不過哈特也指出,德弗林的整體立場雖然不可靠,但如果我們把他的看法理解為一種保守立場,也即社會中一部分群體對既有的道德價值與行為模式具有期待利益,貿然改動會使之無所適從,那么德弗林的學說也不算太過荒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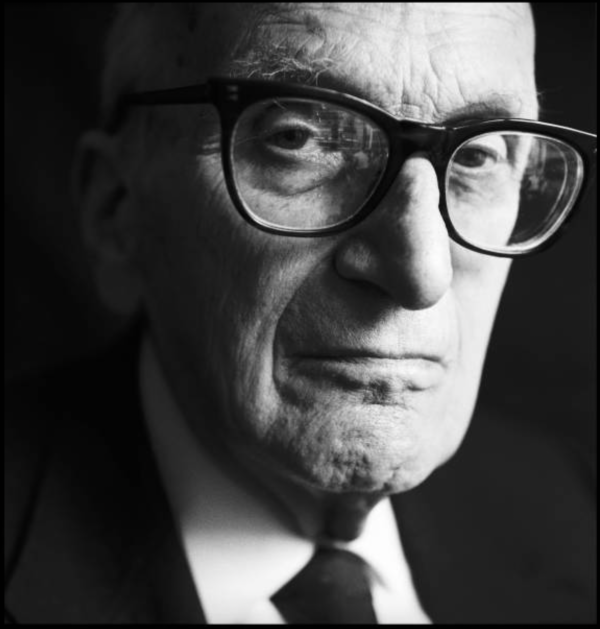
哈特
喬治認為哈特的立場并不正確,因為他依舊堅持存在著國家法律不可介入的私人道德領域。但無論哪種道德都不可能完全與他人無關。在此意義上,德弗林的學說顯然更符合直覺。但他從兩個方面修正了德弗林的學說。其一,法律并不是可強制任何與主流道德相悖的行為。具體哪種有違道德的行為需要受到法律規制,要滿足兩個要求。一個是理性的要求,即該行為違背的道德必然為真,而非我們不經反思的觀點態度;另一個是有充分的審慎性理由支持我們通過法律強制實施該道德,比如,對色情文學的嚴厲管控并不應阻礙藝術創作或娛樂產業的蓬勃發展。其二,德弗林有關道德崩潰導致社會崩潰的看法并不是一種對歷史事實的描述,而是一種譬喻修辭,它指的是當一個社會的主流道德瓦解后該社會中成員間的凝聚力會下降。此時人們雖然彼此生活在一起相安無事,但人與人之間的伙伴感或親密感不再,頗有同床異夢的味道。喬治因此認為一種源自至善主義的法律道德主義并不必然排除道德多元主義,我們不必因為法律實施道德而擔心它會成為壓制我們的手段。
2. 至善論與道德權利
有關至善主義與道德權利,喬治通過剖析德沃金論述平等權、沃爾德倫論述做錯事的權利加以闡釋。德沃金是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典型代表,他堅信國家與法律應當在道德立場上保持中立,因為每個社會成員都擁有得到國家平等對待和關切的道德權利。如果法律秉持特定道德立場,就會有違公民的平等權。概略來看,他提出兩種論證來支持這一點。
在早年著作中,德沃金認為一個國家的立法是以政策為導向的,在功利主義指導下選擇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但是一個國家的司法卻是以原則為導向的,以保護個人權利為鵠的,裁判時并不能出于功利主義原則而傷害個人權利。在這個意義上講,從結果出發的功利主義論證并不能證立國家有理由通過法律干涉個人選擇。這一論斷雖然富有魅力,但喬治認為德沃金夸大了立法具有的功利主義色彩。立法者需要針對多種目標和價值加以權衡,但這些不同的目標與價值往往是不可通約和測度的,因此并不存在德沃金意義上功利主義式的單一的立法目標,而更多的是各種社會成員利益的綜合。此時,我們通過執行法律來實現法律目標,也即保護社會成員的利益,其實無可厚非。

德沃金
在稍后的作品中,德沃金又提出新的論證。他認為每個人的人生都具有同樣的價值,國家與法律應當尊重這種平等。喬治則認為,法律對個人價值的尊重,是尊重人之為人的價值,是尊重他們作為理性個體能夠擁有做出自由選擇的能力,以及具有獨特的人類善好。這并不意味著法律應當尊重人的一切行為與選擇。當人們由于情感偏好、意志薄弱等因素影響了理性能力與實現善好的能力,法律無疑應當出手干預。因此,至善主義并不會同公民的平等權利相矛盾,反而是實現該權利的一種途徑。
有關至善主義和道德權利的另一重關系,就是我們是否擁有做錯事的權利,它意味著一件事雖然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但是法律干涉我們不去做這件事,同樣也是不對的。如前所述,喬治認為在道德層面我們并沒有這種權利——一件事在道德上受到負面評價,就意味著我們不應當去做;但是否阻止別人去做,則不僅涉及道德因素,還與一系列其它理由相關。比如,干涉這種行為會導致其它更為重要的義務無法履行,或者它會對第三方帶來嚴重損害,抑或會導致執法機構陷入腐敗等。當這些道德外理由的力度強過道德因素時,我們便沒必要干涉有違道德的行為。因而至善主義并不承認我們具有做錯事的道德權利,但并不是要牢織一張鐵網將我們束縛在道德教條之下;相反,它具有高度靈活性,使我們的日常生活不必事事上綱上線。
既然至善主義不會影響道德多元立場,也不會有違我們的道德權利,那它是否必然侵害我們的自主權,使得我們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3. 至善論與自主權
并不會。喬治發現,以羅爾斯為代表的當代自由主義者在論證個人自主權時,背離了這一詞匯在康德學說中具有的道德客觀性意涵,而將之理解為個人主觀偏好的產物。在康德眼中,個人自主意味著在先驗領域個人為自己立法,該法則不僅是個人行為的準則,也是依據理性得出的普遍原則,能夠為所有人接受,每個人既是立法者又是該律法的遵從者,理性、權威與自由因此得到調和。如果說自由是康德學說的拱頂石,那么自主便是康德以降自由主義傳統的至高價值。但問題在于,康德學說與羅爾斯頗具代表性的契約論自由主義存在根本差異。康德論述的是先驗自由,是實踐理性視角下基于自由的懸設,來考察我們的行動如何展開、社會何以可能等問題。羅爾斯雖然提出了無知之幕與原初狀態的理論裝置,模擬了類似于康德意義上的先驗世界,但究其本質,其學說內含著某種博弈論要素,旨在通過程序性控制,使原初狀態下基于自利的各方能夠達成一致,選擇出彼此認同的道德。這就在相當程度上主觀化了個人自主權這一價值,個人自主不再是康德筆下理性律令的要求,而是基于個人偏好的選擇;基于個人自主權獲得的結果也不是理性的必然,而是基于個人偏好的偶然。此外,羅爾斯雖然主張原初狀態的參與者,除了基本理性外不再有其他預設,但卻悄悄偷運進自由主義傳統下的個人主義價值。簡言之,他的學說距離理性和客觀性太遠,但卻距離感性很近。這讓他及基于他的當代學說,誤解了個人自主權的意義,也誤以為自主權與至善論存在矛盾。
犯有類似錯誤的還有約瑟夫·拉茲。作為自由主義陣營內的至善主義代表人物,他與喬治持有類似觀點,都認為該傳統若想在今時今日依舊發揮作用,就需要承認善的多元性。他指出,“存在著諸多彼此并不相容但都具有道德價值的生活形式”(164頁),這意味著,有價值的選擇或個人自主權依賴于我們所說的“社會形式”,它包含著各種選擇與允諾,我們“必須要根據這些選擇與允諾的道德合理性來對之加以判斷”(165頁)。因此,拉茲也將個人自主權等同于個人選擇權,認為這是人之為人的一種構成性特征。但在喬治看來,個人自主權或許難當此重任:個人選擇雖然重要,卻未必構成我們行動的終極理由。只有符合實踐合理性(practical reasonableness)的選擇,才是終極行動理由。簡言之,自主權應當從屬于實踐合理性,以此保證我們的選擇符合客觀與理性的道德價值。因此,至善主義并不必然與個人自主權沖突,毋寧說它希望的是將個人自主權所具有的偶然與任意規訓于實踐合理性的客觀與理性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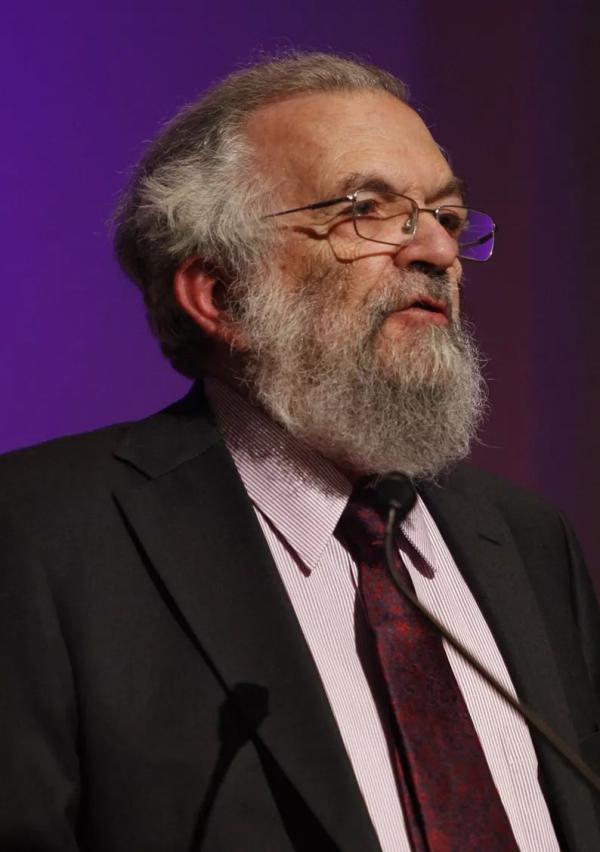
拉茲
以上是喬治對多元至善論總體框架的闡發。從實質觀點來說,喬治的思考當然不無可商榷之處。除卻有關具體人物學說的評判外,可能比較重要的問題包括如下方面:它強調的既尊崇共同體價值,又尊重個人權利的立場,或許更加接近現代社群主義學說,而與古典至善主義稍遠;他所倚重的實踐合理性概念,在具體意涵上與康德意義上的自主是否有所不同,也有待進一步澄清;他強調我們秉持的道德價值不僅多元,且具有自明性與客觀性,或許多元與自明性容易理解,但如何證明我們秉持的價值是客觀的呢?這種有關客觀性的確信,是否能夠逃過笛卡爾筆下的那個喜好變換模樣的魔鬼?這些問題其實都有待進一步思索。但無論怎樣,我們都要承認,喬治成功地讓我們以更深邃的目光凝視美國政治文化傳統中的保守主義思潮,這對今天來說尤為重要。接下來我們將目光轉向這部著作的形式方面,看看喬治在本書中呈現出的學術風格。
告別干癟的法哲學
《成人以德》無疑是一部關注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著作。法哲學中往往在如下三個層面展開有關兩者關系的討論。首先是經驗層面:各國法律的發展是否受到道德的影響,法律內容實際上是否包含道德要素?其次是概念層面:當我們判定一條社會規范是否屬于法律時,是否必要要援引道德要素作為判準?最后是義務層面:我們是否應當遵守法律這個問題,是否與道德義務相關?
可以說自哈特以降的法哲學主要圍繞這三個問題展開論辯,且尤以后兩個問題為甚。有關它們的學術分析,無疑也曾產出了巨大成果。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法哲學發展至今天,這三個問題似乎排他性地成為這門學科的關注對象。法哲學家窮盡畢生精力,似乎就在討論法律的概念、法律與道德關系,用盡各種哲學技巧,試圖表明法律與道德必然無關抑或有關。這些精細但又繁復、深邃卻也晦澀的哲學思辨和技術詞匯,不僅讓初學者感到困惑,就連常年浸淫其間的學者也覺得難以把握。這些堆疊的術語和一遍又一遍被法哲學家引述闡發的文本,好像形成了一個高高的門檻,它告訴世人:這個門檻里面是一個不容玷污的純粹圣殿,門檻之外一些自稱法哲學甚至法理學的研究都是不純粹的。而運用這些術語和操持這些文本的學者,仿佛是這個圣殿的衛道士,他們驕傲而自得地宣稱:你們看,只有我的研究才配叫“法哲學”。
可是圣靈仿佛已經離開了這座輝煌的圣殿。無法掩飾的事實是,法哲學距離法學越來越遠,但又沒有跟上當代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在形而上學、真理論,以及語言哲學等領域的發展步伐。越來越抽象的法哲學在失去對現實問題解釋力的同時,仿佛也未呈現出足夠的理論廣度與前瞻性。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喬治的著作凸顯出超越理論論辯的意義。他將法律與道德關系的抽象思辨,具體化為國家及其立法是否,以及如何強制實施道德的問題。這不僅為法哲學中有關法律與道德關系的討論補足了重要的一環,也將法律理論同更為廣闊的政治哲學背景關聯在一起。無論本文歸納的喬治的核心立場是否成立,他的寫作無疑都表明,法哲學不僅是哈特、拉茲、德沃金,不僅是《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權威》《法律帝國》,還包括整個思想史中一切可為今時今日所用的有關法律的論斷與學說。這些理論資源并沒有讓圣殿變得虛無,只是實在地指出衛道士所拜的不過是偶像而非真神。
此外,本書將分析哲學進路與對思想史資源的創造轉化融為一體。通過在不同理論資源和學說立場之間的牽引關聯,喬治筆下的法哲學不僅如一些法哲學者所認為的,是對法律現象的直白描述,還是一種敘事和述說。它告訴我們,那些在今天教科書中被歸納為一個個命題的論點,具有怎樣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關切,又對今天具有何種啟發。在此意義上,他也讓我們發現,法哲學也可以是一種嘗試性的溝通與理解,我們面對文本努力地重構作者試圖表達的觀點,不(僅)是為了批判,而是想聽一聽與我關心同一問題的人們在想些什么,對于發現事理中本身包含的是非曲直又有何價值。在此意義上,重視本書的風格與關注法律是否能使我們更加道德同樣重要,甚至在當下來說更加緊迫。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